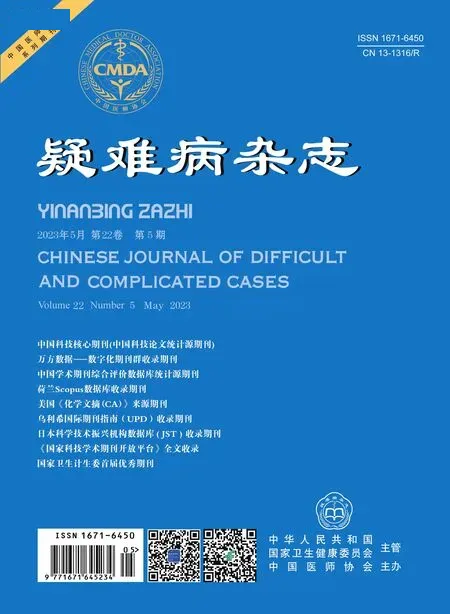脓毒症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王静 乔佑杰
根据脓毒症3.0的定义,脓毒症是因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目前可用于脓毒症早期诊断的资源有限。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评分虽然可以帮助诊断脓毒症,识别高死亡风险的患者,但它不是针对脓毒症的特定工具[1]。人们一直在研究针对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希望通过它们能对脓毒症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带来益处。目前已有100多种关于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被提出[2],确定哪种标志物可能有助于优化诊断和治疗策略仍然是一个挑战。本文将目前有助于脓毒症早期诊断或对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有潜在价值的标志物做一综述。
1 传统的与感染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1.1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 PCT是过去10年间研究最多的与感染相关的炎性标志物,它是一种细菌感染后刺激细胞释放出的由116 个氨基酸组成的糖蛋白。1993年Assicot等[3]发现血清中 PCT含量与感染性疾病密切相关,并提出PCT可作为人体细菌性感染的血清标志物。之后有很多对于PCT的研究,认为它是脓毒症早期诊断的可靠生物标志物。近期一项多中心的研究,纳入了266例符合脓毒症3.0标准的患者,其中一部分患者以PCT指导抗生素治疗,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PCT组可以减少感染的远期后遗症,并可显著降低病死率[4]。
1.2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是临床最常用的脓毒症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之一,也是临床广泛使用的炎性指标。其敏感度高、但缺乏特异性。2019年发表的一篇meta 分析纳入了9 项临床研究,其中脓毒症组 495 例患者,非脓毒症组 873 例患者,通过评价PCT和CRP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结果显示:PCT 和 CRP 在成人脓毒症诊断中具有中等程度的价值,PCT的诊断准确性和特异性高于CRP[5]。所以临床上CRP应注意与其他标志物联合使用和动态监测,以提高其诊断准确性。
1.3 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作为参与免疫调节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所有有核细胞中。机体失控性炎性反应学说被认为是脓毒症发病机制的重要基础。炎性细胞过度激活并释放大量炎性细胞因子是脓毒症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细胞因子也被认为是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目前作为标志物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6和IL-10等在文献中反复被提及并相互比较,证明其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优越性。有研究者比较了脓毒症患者以及非感染性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10水平。结果表明,脓毒症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10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非感染性SIRS患者,且病情严重程度与TNF-α和IL-10表达水平正相关[6]。最近在一项以脓毒症3.0为诊断标准的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研究中,血清IL-6区分脓毒症与非脓毒症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3-0.94(P<0.001),敏感度0.804,特异度0.889[7]。
2 与炎性反应激活和免疫失衡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2.1 钙卫蛋白(calprotectin) 钙卫蛋白是中性粒细胞胞浆中含量最丰富的蛋白质之一。这种钙结合蛋白由2个亚基S100A8和S100A9组成,广泛分布于人体细胞、组织及体液中,是一种重要的炎性反应蛋白。当细菌感染后由中性粒细胞释放入血,通常在数小时内随着细菌或内毒素的反应而增加[8]。近年研究发现,在脓毒症时,钙卫蛋白表达水平可明显升高(正常人的血清钙卫蛋白浓度通常低于1 mg/L,发生脓毒症时可升高100倍[9-10]。
在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中,脓毒症患者的血清钙卫蛋白浓度显著升高,较PCT浓度更敏感地区分脓毒症患者和非脓毒症患者。同时发现,在评估脓毒症严重程度及预后方面,钙卫蛋白水平与30天病死率直接相关[11]。Dubois等[12]研究发现,当脓毒性休克患者SOFA评分相似时,较高的血清钙卫蛋白水平可提示更高的死亡风险。
2.2 血清穿透素3 (pentraxin3, PTX3) PTX3是属于长链五聚蛋白亚家族的急性期蛋白,在炎性细胞因子刺激下,各类免疫细胞、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均分泌PTX3。它通过激活经典补体途径以及促进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识别病原体,在炎性反应早期发挥作用。在脓毒症后6~8h可见PTX3水平显著升高(>100 μg/L),而健康者体内PTX3水平几乎检测不到(<2 μg/L)[13]。
一项针对101例脓毒症患者的研究,检测脓毒症患者发病第1天的血浆PTX3水平,并与健康组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脓毒症组的PTX3显著增加,它预测脓毒症休克的最高AUC为0.798(95%CI,0.666-0.921,P<0.001)[7]。另一项前瞻性单中心研究也显示出血清PTX3水平可以确定脓毒症的诊断,而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这项研究认为PTX3是评估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严重程度的早期生物标志物[14]。
2.3 可溶性CD14亚型(soluble CD14 subtype,sCD14-ST或Presepsin) CD14是一种跨膜糖蛋白,是存在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表面的受体。它是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的成员,能够识别革兰阳性和革兰阴性病原体的配体组。CD14以2种形式存在,即膜结合形式(mCD14)和可溶形式(sCD14)。sCD14具有不同的亚型,sCD14-ST亚型的N端片段称为Presepsin[15]。健康人血液中sCD14水平低,浓度仅为微克级。当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感染时Presepsin血清水平急剧升高,是诊断和检测脓毒症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之一[16]。同时在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预测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17]。
2019年的一项系统回顾和meta分析,纳入了19项观察研究,共有3 012例患者,结果显示,Presepsin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4(95%CI,0.80-0.88)和0.73(95%CI,0.61-0.82),PCT诊断败血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0(95%CI,0.75-0.84)和0.75(95%CI,0.67-0.81)。结果显示,Presepsin和PCT的AUC分别为0.87和0.84,在脓毒症早期诊断方面两者表现相当[18]。另一项纳入了40例ICU患者的小型研究结果显示,与SIRS评分或序贯器官衰竭评估快速(qSOFA)评分相比,ICU 患者的早期 Presepsin 测量在诊断脓毒症和预测病死率方面更准确[19]。
2.4 中性粒细胞CD64(nCD64) nCD64又称免疫球蛋白Fcγ受体1(FcR1),在单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上表达,在感染发生的4~6 h内,在促炎细胞因子的作用下nCD64表达明显上调,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脓毒症诊断生物标志物。有研究提出nCD64 是脓毒症早期诊断的敏感而特异的检测方法,在健康志愿者中,nCD64 在中性粒细胞上的表达水平极低,但在炎性反应或感染后显着升高。nCD64值≥2 398分子/细胞能区分脓毒症和非脓毒症[20]。
在2019年对14项研究、2471例患者进行的一项meta分析中,nCD64优于CRP和PCT诊断脓毒症的效果[21]。最近几项关于儿科重症前瞻性双盲研究结果显示:儿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入院时nCD64与PCT和CRP呈正相关,而且nCD64可能成为区分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新型标志物[22]。据报道,中性粒细胞上的 nCD64表达与 SIRS 和脓毒症的严重程度有关。nCD64的缺失通过下调TLR4 信号通路提高脓毒症小鼠的存活率[23]。但是,由于nCD64需要使用流式细胞术来测量,因此在临床中快速检测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2.5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MCP-1) MCP-1是 MCP家族中研究占比较多的成员,通常由氧化应激、细胞因子或生长因子诱导,由内皮细胞和单核细胞等细胞分泌,与趋化蛋白受体2结合后发挥不同的生理作用,如诱导淋巴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归巢、迁移、激活、分化发育及炎性反应发生等。
一项研究纳入了143例脓毒症患者,结果发现,血清MCP-1水平与脓毒症严重程度直接相关。MCP-1预测28天病死率(AUC 0.766)高于PCT(AUC 0.621)及SOFA评分(AUC 0.640)[24]。此外,脓毒症患者血浆MCP-1水平与其他细胞因子(TNF-α、IL-6、IL-8和IL-10)水平直接相关,是预测脓毒症发展的潜在生物标志物[25-26]。许志平等[27]的研究表明,MCP-1对于脓毒症死亡风险评估具有很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能够为脓毒症临床评估提供更好的检测指标。
2.6 肾上腺髓质素(adrenomedullin,ADM)和肾上腺髓质素前体(Pro-adrenomedullin ,ProADM) ADM是一种由52个氨基酸组成的肽,主要在内皮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中产生,由多种组织分泌。ADM通过介导血管舒张,参与调节体循环。由于循环中的ADM会迅速降解并从血液中清除,因此使用标准免疫分析法不易检测其水平。近年来研究发现,由45~92个氨基酸组成的肾上腺髓质素前体中区片段(MR-proADM)有更长的半衰期,可间接反映 ADM水平,且检测方便,已被作为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生物标志物[28]。
王来等[29]对比脓毒症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血清中的MR-proADM,结果显示严重脓毒症患者检测MR-proADM水平非常有必要,且联合检测PCT水平能够更为及时地诊断脓毒症。另一项纳入了215例患者(109例脓毒症患者,106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研究中,ADM四分位数与器官衰竭的数量以及 SOFA评分、心血管、肾脏、凝血和肝脏功能损伤相关。ADM水平也预测了30天病死率,与SOFA评分相似(AUC 0.827对0.830)。可见,ADM可以作为脓毒症诊断及预测脓毒症患者的严重程度、器官衰竭和30天病死率的一种标志物[30]。
2.7 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1,sTREM-1) sTREM-1是一个表达于中性粒细胞、成熟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表面的跨膜糖蛋白。细菌感染可增加细胞表面的sTREM-1 表达。它参与触发IL-8、MCP-1和TNF-α的分泌,并诱导中性粒细胞脱颗粒。在Wu等[31]的meta分析中,纳入了包括11项研究、1 795例患者。他们发现在脓毒症诊断方面,sTREM-1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79(95%CI,0.65-0.89)和0.80(95%CI,0.69-0.88)。结果表明,血浆sTREM-1在区分脓毒症和SIRS方面具有中等的诊断性能[31]。另一项纳入19 项研究、2 418例患者的meta分析中,探讨了sTREM-1在疑似脓毒症中的诊断价值。发现sTREM-1对高危患者脓毒症的诊断具有中等准确性,其综合敏感性为0.82(95%CI,0.73-0.89),特异性为0.81(95%CI,0.74-0.86)。可见,还需要更多的大规模研究来进一步评估 sTREM-1 的诊断准确性[32]。
2.8 可溶性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受体(soluble 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suPAR) suPAR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血液和体液中的膜结合受体,与某些疾病如关节炎、肝纤维化、疟疾和细菌感染等的严重程度有关,所以suPAR可能作为一种感染性疾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其浓度与免疫系统的活性直接相关,包括细胞黏附、迁移、趋化性、蛋白质水解、免疫激活、组织重塑、侵袭和信号转导等。
一项纳入17项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suPAR对细菌感染或全身炎性反应具有中度诊断价值,AUC为0.83[33]。另一项对涉及30项研究,6 906例患者系统回顾和Meta分析中,suPAR和PCT对脓毒症的诊断准确性相似。suPAR诊断脓毒症的总敏感性为0.76(95%CI,0.63-0.86),特异性为0.78。此外,区分脓毒症和SIRS的AUC为0.81(95%CI,0.77-0.84),敏感性为0.67(95%CI,0.58-0.76)和特异性为0.82(95%CI,0.73-0.88)[34]。可见suPAR敏感性不强,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评估suPAR与其他生物标志物结合使用是否能提高诊断效果。
2.9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4) TLR4可以识别细胞表面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及其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引发下游信号级联反应,诱导产生TNF-α、 IL-6、IL-12等炎症因子进行防御。
研究发现当脓毒症患者体内TLR2、TLR4等TLRs表达急剧增加,并激活NK-κB,使炎性因子大量释放时,可诱发重症脓毒症[35]。尽管缺乏大规模的研究证明TLR4与PCT和CRP等生物标志物在脓毒症诊断中的相关性,但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总结了通过TLR4表达作为评估脓毒症严重程度的生物标志物的可能性(P<0.05)[36]。
2.10 程序性死亡-1(programmed death-1 ,PD-1)受体 PD-1最初是从凋亡的小鼠T细胞杂交瘤中克隆而来,属于CD28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主要表达于活化的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表面。可诱导共抑制细胞表面蛋白,对建立免疫耐受非常重要。PD-1存在2种已知配体,即PD-L1和PD-L2,二者均通过竞争与PD-1结合。PD-L1是PD-1主要的结合配体。
之前的研究表明,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患者表现出PD-1更高的表达[37]。在最近的一项前瞻性观察中,纳入114例患者进行分析,四种信号分子(PD-1、CD28、PD-L1和CD86)的NK细胞表达程度与SOFA评分直接相关[38]。在脓毒症等高抗原负荷的环境下,PD-1/PD-L1的异常上调会引起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紊乱,造成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PD-1作为一种新的预后生物标志物的能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脓毒症患者SOFA评分的预测能力。
2.11 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1型受体(soluble tumor necrosis factor-1 receptor,sTNFR1) 脓毒症时, TNF释放增多,2种TNF膜结合受体TNFR1和TNFR2被释放到循环中以调节炎症反应。这些受体进一步裂解,产生可溶性片段,分别为sTNFR1和sTNFR2,这些片段与TNF结合并抑制其活性。
一项关于脓毒症免疫反应的临床研究纳入了163例重症患者,评估了与TLR4信号通路相关的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的变化。发现sTNFR1浓度可有效区分感染及其他导致 ICU 住院的原因。与在 ICU 接受治疗的其他患者相比,sTNFR1在脓毒症患者组中观察到更高的浓度。除了脓毒症的诊断价值外,这种蛋白质似乎还具有评估预后的价值。在死亡的患者组中也显示出更高的浓度[39]。
3 与器官功能障碍相关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3.1 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Ang-1)和血管生成素-2(Angiopoietin 2,Ang-2) Ang 存在2种常见的亚型Ang1及Ang2,二者均以酪氨酸激酶受体Tie 作为受体。二者可竞争性的与Tie-2受体结合。Ang1和Tie2的结合主要起到稳定血管屏障的作用,而Ang2和Tie2的结合则介导了血管内皮屏障的破坏,参与脓毒症毛细血管渗漏的发生,这是器官功能障碍的主要机制之一[40]。Ang-2 主要由激活的内皮细胞分泌。在静止的内皮细胞中Ang-2 几乎不表达。脓毒症时在各种毒素和炎症介质的刺激下, Ang-2从内皮细胞中迅速释放出来。导致血管渗漏,刺激细胞迁移到周围组织,触发炎性反应和凝血途径的激活,最终导致器官功能障碍[41]。
在多项脓毒症的临床研究中,高水平的Ang2和低水平的Ang-1或高Ang-2/Ang-1和低Ang-1/Ang-2比率与脓毒症的器官功能障碍和不良临床结局相关,包括预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严重程度等[25,40,42]。
3.2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s) 基质金属蛋白酶是一个大家族,因其需要Ca2+、Zn2+等金属离子作为辅助因子而得名。MMPs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metalloproteinases,TIMPs)是调节损伤后伤口愈合的关键介质[43]。
Hoffmann等[44]为了研究严重脓毒症患者的MMP-2、MMP-9、TIMP-1、TIMP-2和IL-6血浆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纳入了37例严重脓毒症患者和37例健康志愿者,并通过ELISA方法测定了MMPs水平。结果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脓毒症患者的MMP-9、TIMP-1、TIMP-2和IL-6水平显著升高(P<0.001)。在另一项单中心纳入48例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入院时的MMP-3和住院前72 h内IL-6的变化可以为脓毒症患者提供预后的评估[45]。当然,这还需要的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些细胞因子作为衡量脓毒症严重程度和预测死亡率的效用。
3.3 MicroRNA (miRNA) miRNAs是一组由20~24个核苷酸组成的RNA分子,通过裂解或是抑制mRNA的翻译,起到调控蛋白表达的作用。miRNA是宿主对感染反应的关键介质,可在转录后调节多达60% 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表达。它主要通过调节参与免疫途径的蛋白质表达来发挥作用。
蔡华忠等[46]检测88例脓毒症患者血清,发现血清miR-155-5p 和miR-133a-3p 在脓毒症心肌损伤中的表达增高,且其特异性与敏感性均高于血清脑钠肽和肌钙蛋白。一项关于脓毒症大鼠模型的研究显示,当脓毒症肾损伤时,血清中miR-21-3p的表达显着增加[47]。目前已经描述了50多种不同细菌和病毒感染的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miRNA特征。通过多项研究筛选出的对脓毒症具有诊断价值的miRNAs包括miR-25、miR-122、miR-133a、miR-146和miR-4772等多个相关标志物,但是目前尚无针对脓毒症诊断的特异性miRNAs标志物[48]。建议多种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的模式可能更值得研究和推荐[49]。
3.4 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s) lncRNA是长度大于200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能与DNA、RNA 和蛋白结合,参与调控基因的表达,在机体的生长发育和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多种生物学过程中发挥作用[50-51]。尽管许多与炎性疾病(包括脓毒症)相关的非编码RNA已被确认,但它们的功能和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且存在争议。
转移相关肺腺癌转录本1 (metastasis-associated lung adenocarcinoma transcript 1,MALAT1)是具有保守特点的非编码RNA,早期可作为肺癌转移的预后标志物。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ALAT1 是炎性细胞产生的重要调节因子,可作用于不同的miRNA,调节不同靶基因,进而调控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在炎症性疾病中受到广泛关注[52]。一项对120例脓毒症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MALAT1(AUC 0.910)比APACHE II评分(AUC 0.868)和乳酸水平(AUC 0.868)更准确地诊断脓毒症,预测28天生存率[53]。由于lncRNA 临床应用的研究较少,若lncRNA和miRNA 成为脓毒症诊断的新型标志物还需进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深入探讨。
4 小 结
虽然目前已经确定了许多与脓毒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然而,很多标志物在脓毒症中的确切作用尚未十分明确。为了提高脓毒症诊断治疗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仍需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这些生物标志物在体内的作用机制,从而明确生物标志物对脓毒症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的价值。将患者临床特征与生物标志物相结合进行早期诊断和风险评估将是脓毒症诊断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