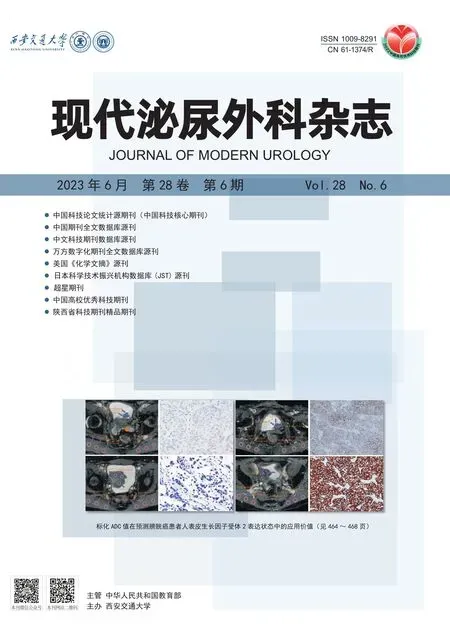抗体药物偶联物的作用机制及在膀胱癌中的研究现状
詹 辉,谭智勇,付 什,李 宁,王剑松,王海峰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云南昆明 650101)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是泌尿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年约有43万例患者被诊断为BC,并且每年导致约165 000例患者死亡[1]。BC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尿路上皮癌,约占90%以上,鳞状细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肉瘤相对少见[2]。根据肿瘤的浸润程度,BC可分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NMIBC的发生率和复发率较高,约75%的患者初诊为NMIBC,虽然其预后好、肿瘤特异性死亡率低,但仍有10%~20%的患者会进展为MIBC[3]。手术联合放化疗是BC的主要治疗手段,NMIBC通常采用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联合膀胱灌注化疗,而MIBC多采用根治性膀胱全切加辅助放化疗,部分患者术后易复发和远处转移。免疫疗法与化学疗法这两大治疗策略虽然能够改善疾病预后,但疗效局限或毒副反应严重,且部分患者出现耐药,因此,寻找新型、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由靶向肿瘤特异性抗原或肿瘤相关抗原的单克隆抗体与不同数目的小分子毒素通过连接子偶联组成[4],兼具单抗药物的高靶向性及细胞毒素在肿瘤组织中高活性,能在发挥抗癌作用的同时避免损伤正常细胞,有效提高了患者的获益风险比[5]。目前全球已有十余种ADC获批用于治疗实体瘤,此外还有80多种ADC单药或联合治疗各种肿瘤的临床研究已经或正在展开[6],例如:使用恩美曲妥珠单抗通过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治疗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7];对于复发难治性CD30阳性淋巴瘤患者,维布妥昔单抗不仅可以直接与CD30阳性淋巴细胞结合,还能够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以及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作用增强对肿瘤的杀伤作用[8];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戈沙妥珠单抗通过与人滋养细胞表面糖蛋白抗原2(trophoblast cell-surface antigen 2,TROP2)相结合,将化疗药物伊利替康的活性代谢物递送到细胞内,导致细胞周期终止和细胞凋亡[9]。继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之后,ADC近年来已在BC治疗中崭露头角,膀胱癌领域针对不同靶点的ADC临床研究已初显成效,ADC单药或联合传统化疗为患者带来了新希望[10]。本文就ADC的结构、作用机制及其在BC治疗中的现状进行简要介绍。
1 ADC的结构与作用机制
ADC由高特异性和亲和力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高效的小分子细胞毒性荷载以及高稳定性的连接子3部分组成,抗体与细胞毒性药物通过连接子偶联,共同赋予ADC细胞靶向性和杀死细胞的能力。根据靶点的不同,ADC在体内发挥靶受体中和与下调、信号传导阻断、免疫检查点抑制以及抗体介导的细胞毒性等不同的作用。以下逐一阐述ADC的3部分结构。
1.1 ADC核心组件之一: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作为ADC的核心组件之一,抗体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①靶抗原识别特异性高;②靶抗原结合能力强;③低免疫原性、低交叉反应以及易连接小分子[11]。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IgG)是ADC常用的抗体,通过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实现ADC特异性杀伤肿瘤的作用,IgG主要包含4个亚类:IgG1、IgG2、IgG3和IgG4,它们的恒定结构域和铰链区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会影响单克隆抗体的溶解度和半衰期以及IgG对效应细胞上表达的不同Fcγ受体(Fcγ receptor,FcγR)的亲和力[12]。目前,大部分ADC使用IgG1为抗体骨架,少数使用IgG2或IgG4。与IgG2和IgG4相比,IgG1具有相似的血浆半衰期,但有更高的补体结合率以及FcγR结合率。除了肿瘤特异性以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ADC的疗效,例如研究者发现对于肿瘤内或肿瘤间HER2异质性表达的乳腺癌患者,ADC的应答水平较差[13]。此外,靶点周转率、内化率和溶酶体降解率等均会影响药物的活性。
1.2 ADC核心组件之二:细胞毒性荷载细胞毒性荷载是ADC中的另一个重要组件,需要具备以下特征:①高细胞毒性;②可修饰性;③高稳定性;④疏水性、透膜性强[14]。目前常用的细胞毒性荷载主要有3大类:DNA损伤诱导物、DNA转录抑制剂和微管蛋白抑制剂。除了细胞毒性外,作为有效载荷的药物,在选择时还需考虑其共轭性、溶解性和稳定性,此外,药物的可溶性和血液中的稳定性也至关重要[15]。
值得一提的是,药物-抗体比例(drug-to-antibody ratio,DAR)决定了ADC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力和毒性,DAR的异质性会导致药物结构不稳定、脱靶毒性增加以及药物聚集[16]。为了使ADC纯度更高,需采用位点特异性偶联,即工程化半胱氨酸残基的插入、抗体序列中非天然氨基酸的插入、通过糖转移酶和转谷氨酰胺酶的酶促结合等。
1.3 ADC连接组件:连接子连接子是将细胞毒性荷载与单克隆抗体相连接的化学结构,它既要保证细胞毒分子在循环系统中不释放且处于非活性、无毒性的状态,还要能在靶细胞内部有效地释放细胞毒分子[17]。连接子分为可切割型和不可切割型。可切割型连接子通过细胞中的生理条件释放细胞毒性物质,而不可切割型连接子只有借助细胞的溶酶体才能被降解。相比于可切割型连接子,不可切割型连接子ADC在血液中具有更长的半衰期和更低的脱靶毒性。
1.4 ADC组件联合作用产生抗肿瘤效用清楚了ADC组件结构,那么它的作用机理就显得非常直观了:首先由抗体引导特异性靶向肿瘤细胞,当ADC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之后,通过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进入细胞,在内体中(可切割连接子)或与溶酶体融合后(不可切割连接子)通过酸性条件或水解酶等释放细胞毒性物质[11-12],这些细胞毒性负荷(DNA转录抑制剂、微管蛋白抑制剂和DNA损伤诱导物)进入细胞质或细胞核中与靶分子结合,进一步诱导细胞凋亡,从而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效应。
2 与膀胱癌相关的几种ADC
目前已经有数种ADC被批准用于膀胱癌治疗或处在研究阶段,下面逐一介绍其组成、作用机制及相关研究。
2.1 Enfortumab Vedotin(EV)靶向连接蛋白4(nectin cell adhesion molecule 4,Nectin-4)是一种在尿路上皮癌中高表达的细胞黏附分子,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的发展[18]。EV由Nectin-4的人源IgG1单克隆抗体Enfortumab与细胞毒制剂单甲基奥瑞他汀E偶联而成,其靶向肿瘤细胞表面的Nectin-4抗原,导致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19]。
基于铂类化疗和PD-1/PD-L1抑制剂治疗后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预后较差,然而既往的Ⅱ期和Ⅲ期临床研究(NCT02091999、NCT03219333和NCT03474107)都已证实EV治疗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0-22]。在其中的一项大型开放性临床研究(NCT03474107)中,608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并分别接受EV(1.25 mg/kg,28 d为1周期)或其他化疗方案(多西他赛、紫杉醇、长春氟宁)治疗。结果发现,与化疗组相比,EV组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降低了30%的死亡风险,两组的中位OS分别为12.88个月和8.97个月;同时,EV组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两组中位PFS分别为5.55个月和3.71个月;EV组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疾病控制率均显著高于化疗组;而两组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和≥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22]。此外,EV与帕博利珠单抗的新组合疗法也有优越表现,一项多队列、多中心的Ⅰb/Ⅱ临床试验(NCT03288545)的最新数据显示,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4.9个月,ORR为73.3%,PFS为12.3个月,OS为26.1个月[23]。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EV用于既往接受过含铂化疗和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后线治疗[24]。
2.2 Sacituzumab govitecan(SG)TROP2是一种跨膜糖蛋白,其参与了细胞内钙转导、MAPK以及NF-κB等多种信号通路,与肿瘤增殖、侵袭和迁移密切相关[25]。SG由TROP2的人源化IgG1抗体、伊立替康的代谢产物SN-38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通过可水解连接子偶联而成,这种偶联方式能够实现药物的“旁观者效应”,发挥更强大的抗肿瘤作用[26]。
目前,免疫治疗是含铂化疗失败的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的标准治疗,然而其疗效有限,ORR仅为20%左右[27]。一项Ⅱ期临床试验(TROPHY-U-01)数据表明,SG对于接受铂类化疗和免疫治疗后进展的尿路上皮癌患者依然安全有效,接受SG治疗的患者ORR为27%,77%的患者测量可见病灶缩小,PFS为5.4个月,而接受化疗的患者ORR为10%,PFS为2~3个月[28]。在TROPHY-U-01的基础上,Ⅲ期临床研究(TROPiCS-04)对比了SG单药与其他化疗方案治疗进展期或局部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29]。在联合用药方面,I期单臂DAD研究(NCT04724018)从不同靶点与载药出发,将两个不同的ADC药物SG与EV联合,探索适宜的剂量与疗效[30]。此外,对于不耐受铂类治疗的人群,Ⅱ期SURE研究探索了SG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SURE-01研究(NCT05226117)对患者予以4个周期SG单药新辅助治疗,SURE-02对患者予以4个周期SG+帕博利珠单抗新辅助治疗并在术后予以13个周期的帕博利珠单抗单药辅助治疗。相信随着更多新的研究的开展与新组合方式的开发,SG在局部晚期BC治疗中的地位将日趋稳固。
2.3 Disitamab vedotin(DV)HER2是一种跨膜受体酪氨酸激酶,其通过RAS/RAF/MAPK、PI3K/Akt等信号通路介导肿瘤增殖、侵袭和转移,其不仅是乳腺癌的重要靶点,在BC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31]。HER2的表达丰度不仅与肿瘤负荷有关,HER2的过表达也意味着患者的预后不良。DV是由人源化HER2抗体和毒素载荷——甲基奥瑞他汀E通过可被组织蛋白酶剪切的连接子偶连而成。
一项开放性、多中心、非随机性Ⅱ期研究(RC48-C005)共纳入了43例一线全身化疗失败的HER2阳性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其结果显示,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0.3个月,ORR为51.2%,中位PFS为6.9个月,中位OS为13.9个月,疾病控制率为90.7%[32]。在另一项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RC48-C009)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接受DV治疗后,患者的ORR为50%,PFS为5.1个月,OS为14.2个月[10]。以上两项研究中,DV都能够使HER2阳性(IHC2+/3+)的患者生存获益。然而,DV对于HER2阴性或IHC为0/1的患者是否适用呢?RC48-C011的研究结果显示,患者ORR为26.3%,中位PFS为5.5个月,中位OS为16.4个月,亚组分析显示13例HER2(IHC1+)患者的ORR为38%,而HER2表达为0的患者最佳疗效仅为稳定,DV对HER2低表达人群表现出获益,这可能是其通过“旁观者效应”发挥抗肿瘤的效果[10]。事实证明DV的疗效确实优于化疗或PD-1等单药治疗,这增加了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生存获益,打破了既往治疗选择有限的局面。
2.4 Oportuzumab monatox(OM)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ar,EpCAM))是一种Ⅰ类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能够促进细胞增殖、分化、迁移及免疫逃逸[33]。OM由靶向EpCAM的人源化单链抗体片段与铜绿假单胞菌外毒素A偶联而成,药物一旦结合癌细胞表面的EpCAM就会被转运至细胞内,诱导细胞凋亡,常用于治疗高风险的、对卡介苗无应答的NMIBC。
在一项开放性、多中心的Ⅱ期临床研究(NCT00462488)中,46例既往接受卡介苗治疗失败的膀胱原位癌患者被分为两个队列,分别接受6周期(队列1)或12周期(队列2)的30 mg OM的治疗。结果表明队列1中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为41%,中位复发时间为274 d,而队列2中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为39%,中位复发时间为408 d,虽然两组完全缓解率相似,但队列2的中位复发时间较长,表明强化治疗可能更有优势[34]。VB4-845-02-ⅢA是一项开放性、多中心的Ⅲ期临床试验,用于评估OM治疗既往接受过卡介苗治疗的NMIBC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一项单臂的Ⅰ期临床试验(NCT03258593)用来评估度伐利尤单抗联合OM治疗既往接受过卡介苗治疗的NMIBC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35]。虽然研究结果尚未公布,但OM对既往接受过卡介苗治疗的NMIBC患者已经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耐受性。
3 小结与展望
随着个体化诊疗技术和精准医疗理念的提出,ADC在BC治疗中崭露头角,它为患者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治疗策略,特别是在既往免疫治疗失败患者的治疗中展现出了良好的效果和安全性。然而,ADC的复杂性也使得其推广应用面临着许多挑战,例如抗体对抗原识别的调节可能产生新的机制,导致部分患者出现耐药。此外,ADC各组成部分的优化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包括如何使用完全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以降低免疫原性,利用不同作用机制的细胞毒药物,优化连接子设计和连接方法以减少其脱靶毒性等。相信随着国内外更多的ADC进入临床试验,以及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问题将来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