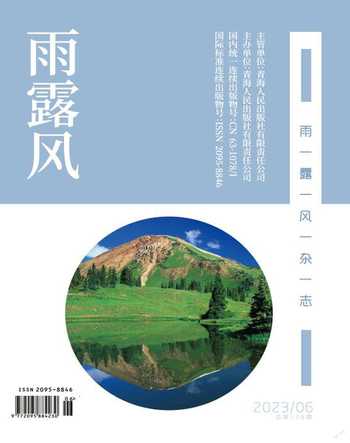论吉本文学作品中新型家庭的“新”
自1987年以处女作《厨房》斩获海燕新人文学奖后,作家吉本芭娜娜笔耕不辍,持续发表了四十余部作品。从创作特点上看,其作品一反传统日本文学的整饬与规范,语言表达上摆脱了传统书面语的生硬和疏远,采用了简洁平实的口语体,题材上多为讲述日本现代社会中某个平凡、孤独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平凡事。评论家中村真一郎称她的创作“具有旧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感觉和思考,完全无视传统的文学教育,是一种描绘手法奔放的文学作品”。笔者注意到吉本作品所塑造的许多现代新型家庭,正如其文风格、文学思考与传统迥异一样,也在各方面展现出了与旧时代的传统家庭迥异的新内容。这些“新”既是吉本在观察现代社会日本人家庭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同时也是其对现代家庭的反思,对传统家庭的超越。
一、新功能:情感功能变为中心
从社会学来说,家庭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对生养子女的责任、为家庭成员提供经济保障以及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保障三个方面,简称为生育功能、经济功能和情感功能。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下的大家庭最被看中的功能是前两者,而情感功能是被忽略的。在农业时代,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个单位的延续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其延续依赖子嗣的繁衍,其繁荣则有赖于经济条件。但是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核心小家庭逐渐取代了传统大家庭,家庭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家庭生活重心也发生了巨变。首先,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人们较容易获得生活物资,社会物质的丰富极大地解决了生存的经济问题,从而弱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其次,核心小家庭的结构使得成员之间更专注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幸福,而不再关注如何实现家庭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延续,因此生养子女的繁衍任务变得不那么紧迫,生育功能也不再位居中心。与此二者逐渐式微相比,情感功能则日益被期待,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成员中个体的成长和幸福感也逐渐变成人们追求的目标。吉本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新型家庭所体现的家庭功能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其笔下的人物对家庭的最大诉求是情感需求,经济支持和繁衍后代两个功能则基本不被提及,甚至完全被忽略。
吉本文学作品只是展现了新型家庭的各种可能性,并没有反对家庭,其对家庭的功能是认可并且高度重视的。在众多故事中,尽管家庭会遭遇各种变故以致崩塌毁灭,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作品人物都憧憬和向往一个理想的家庭。它的构成条件不必是血缘,更不必是金钱,但一定要具有成员之间情感上的融通。登场人物都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的环境里,他们从不被生存和经济困扰,他们对情感的需求远远大于物质的需求,心灵上的愉悦给他们带来的慰藉远远超过物质上得到的满足。由此可见,“家”作为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或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场所,提供情感保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提供经济保障,人们更需要情感上的满足以滋养个体生命和生活。在作品中,如果家庭成员间情感交流顺畅,这个家则显得流光溢彩,它能给人带来生机与幸福,反之则是枯萎衰败的,给人带来不安和不幸。例如,《彩虹》中的老板事业有成,物质生活优渥,但其与太太之间并没有感情,双方都表现冷淡,相互不沟通,无法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尽管他们的家豪华无比,看似万般俱备,有花园,有宠物,但因为情感上得不到满足,生命失去了滋养之源,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呈一副衰败之貌,连家里的动植物也完全失去生机。花园“表面看起来很整齐,其实已经有树枝枯萎,土壤开始干涸,散发出悲凉的气息”,家里的猫狗也“总是很惊恐的样子,毛的光泽感很差”。尽管请了人每日来打扫,收拾花园呵护猫狗,可是“无论家里多么干净漂亮,动物跑来跑去追打嬉闹,因为家的支柱并不在那里”,这里“家的支柱”指的就是情感的融通,所以这个家即使“表面看起来干净整洁”,实际犹如一个“宽敞的、没有人居住的废墟”。同样的情形在其他作品也有体现。《蜜月旅行》中宏志的家因为缺少情感沟通和爱,犹如一个祭坛、一个黑房子,长年显露出一副要吞噬人之一切活动的死气沉沉状;《白河夜船》中“我”小时候的家;《鸫》中“我”的父亲与前妻的家等等,皆是没有情感的交流和滋润的。这些“家”里,因为无法提供情感的保障,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家”不再是家。与此相对,《厨房》中的雄一母子家,尽管缺失父亲,但因为有母亲理惠子对雄一浓厚的爱以及母子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使得整个家充满了明朗、乐观向上的生命力量。它不但给予生活其中的母子俩温暖,还治愈了坠入人生至暗时刻的美影,给予她重生的力量。美影与祖母的家也因为有爱和相互的关心,因能给予家庭成员所需求的感情,即使在祖母去世许久后,这个家的各种生活场面,仍然在美影的记忆里熠熠发光,并使她生出尽管只剩自己一个人也要顽强活下去的勇气。
二、新观念:追求个体的幸福
日本传统家庭理念的根本是将维持整个家庭的延续视为高于一切,极其重视家庭整体的荣誉,个人的尊严和幸福则被忽略甚至被牺牲。家庭成员从祖先那里继承家业,终身目标则是努力将其经营得更加繁荣昌盛,使家产更加丰裕,使家庭的名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哪怕牺牲了个人的追求和愿望也是理所应当的。在此理念中,家庭是永久不灭的,而构成家庭的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不断更替的,故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占绝对地位,它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是“个人为家庭而存在”,只有家庭,不见个体。
吉本作品中的现代家庭脱离了这种旧有家庭制度的禁锢,家庭不再优先于个人,也不再是稳固不变的,它脆弱易碎。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把家庭的延续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个体幸福。如果一个家不能带给个体幸福,人们便会想方设法逃离它,家是可以被放弃、抛弃甚至打碎的。在小说《鸫》中,女主人公玛丽亚是一个私生子,是其父亲在婚外与其母亲所生,直到她十五岁时,她父亲和原配离了婚,与她母亲再婚,重新组合家庭。这里可以想象这位父亲在追求个人幸福的漫长道路上所经历的苦闷、纠结、矛盾和最后的决绝。在谈及原来的家庭时,他说“世界上也有那種喜欢独自享受生活的人,但是爸爸生来就是个喜欢守着小家庭过日子的人。这也是我和前妻过不到一起的原因……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期待的确实是一个可以每天在一起看电视,星期天即使再麻烦也愿意一起出游的和睦的家庭,所以和她相识相爱本身可能就是个错误”。从中可见他和前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解的冲突,只是因为他在婚姻的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个体的幸福,为了追求理想的幸福生活,他放弃了那个家庭。而谈及现在的家庭时,他说“也许有一天会惹你和妈妈生气……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大家的心已经不再融洽了”,那就“不得不分开了”。父亲平静地将这些话说给女儿玛利亚听,传递出来的观念是个人的幸福最为重要,如果一个家没有让人感到幸福,那么它就不值得留恋,抛弃它打破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是这么做的,也这么教给女儿。吉本并没有从道德的角度鞭笞这位父亲对婚姻的背叛,也并不认为其是自私的,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展现了人物的观点,并通过人物的口说出了其文学设想:个体幸福大于家庭。在《厨房》中也一样,雄一的父亲原是他妻子父母的养子,两人的结合遭到上一辈的强烈反对,为了追求幸福他们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离家出走私奔结婚了。通过这些故事的情节,作品展现了一个与过去传统的以家为重、忽略个体幸福完全不同的新观念,即个体幸福远比家庭这个形式重要得多。
三、新属性:家的时间属性
在一般观念里,“家庭”指共同生活的一家人,但因“庭”有家的内部构造之意,又指和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所。即家是一个场所,正如诗人常常把家比喻为精神港湾一样,家具有空间属性。然而吉本作品中所描绘的家除了空间属性之外,还被赋予了时间属性,家不但是成员们的立身之地,同时也是人生活其中的时间,这是对传统家庭属性的增补和扩容。
在《厨房》中,祖母去世后,经受不住悲痛的美影被雄一家收留,有一天她回到曾经的家去整理行李,尽管原本所熟悉的一切东西都还在,但她感到所有东西都变得无比陌生,都对她不理不睬,这时她突然冒出的想法是“奶奶离去了,这个家的时间也随之消亡了”。也就是说她的切身感受不是失去了曾经生活于此场所的家,而是失去曾经生活于彼时间的家,房子如故,它没有变,但时间已荡然消逝无可追回,她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无家可归。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表达家具有时间属性观念的故事情节反复出现。例如在《鸫》中,当玛利亚要随父母远赴东京开启新生活时,她觉得离开海边小镇的家,就是要告别自己的青春岁月。那里的家既是承载她十几年的现实生活的场所,更是承载她十几年的青春时光的时间。在《哀愁的预感》中,父母车祸双亡后姐姐独自留在原家庭生活,妹妹被领养去了新的家庭。离开家的妹妹失去了记忆,暗示她忘记了属于过去那个家的时间;留在原地的姐姐一直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像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其实则暗示她将自我封存在了原来家庭的那段时间里。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此类细节赋予了家时间属性,家就是时间,一个家就是一段时间。然而时间是流动的,人生变化无常,家也是变换迭出、易破易碎的,這是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他们的出路。
如前面所言,吉本作品中呈现了各种破碎崩塌的家庭,传达出一种家庭是不稳固的、脆弱不堪的观念。直观原因多表现为死亡和外力的冲击,这是现代核心家庭的结构使然,由一对夫妇及其子女构成的家庭结构过于单一,少许外来的冲击也轻易使其崩塌,如《哀愁的预感》中的车祸、《厨房》中的疾病等。另外家庭功能的转变也使其脆弱易碎,感情发之于心,人心有坚强的一面,但更有其脆弱的一面,吉本作品中所描绘的人心尤其如此,他们对未来不确定,认为没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即使没有外力的冲击,家庭也未必就能牢固不破,因为他们对他人的“心”,甚至对自己的“心”也无法作出不变的保证,感情亦如是。人心易变,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易变的,由人组成的家庭自然也是易变的。此时聚在一起,彼此温暖,也许不久就会分离。如作品《鸫》中的父亲,尽管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离开原来的家庭组合了现在的这个新家庭,但他对现在的家庭能持续多久也并没有多少信心,甚至认为也有可能会和现在的家人分开。除去以上两者,最重要的原因是家特有的时间属性,时间是不停流逝的,因此家也是有时效的、易变的。所谓“静之物其姿不变,动之物常变其姿”,如果把家当作场所和港湾这种静物,自然就会企求它的稳固和永恒;如果打破这个常规,把其视为不断流逝、奔涌向前、瞬息万变的时间,则知企求它的稳定不变是无妄之念,能认识到家暂时的安定是多么难得,懂得珍惜身在其中的可贵与幸福,也能在失去时坦然接受,如同接受季节的流逝。当美影发现“这个家的时间也随之消亡了”时,她悟到了这一点,才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家已经消逝的事实,并重新生出向前出发的力量和勇气,铆足劲头奔赴下一个家,走进下一段时间。
四、结语
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进程中,日本人的家庭生活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旧时代的大家庭制度分崩离析,旧有的家庭观念也土崩瓦解,新的生活方式和新观念不断涌现。吉本以细致的观察和大胆的思考,在文学创作中以新颖的手法展现了现代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挑战下的生活风貌和情感追求,对新型家庭生活的“新”展开了多维度的想象和探讨,为人与人、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更多可能性。
作者简介:何木凤(1980—),女,汉族,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