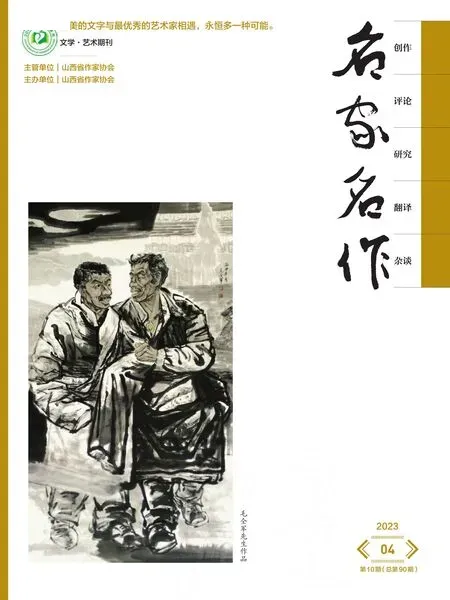日本天明、宽政年间碑文中人物记载的史料价值
曹 磊 沙丽娟
所辑录的碑文主要记载了日本德川幕府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到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近200年间儒者的生平。碑文以“年庚前后”为依据排列碑主次序,分列碑主共计171位,总字数长达18万字,不仅保存了江户中后期儒者的家世、婚姻、交游等珍贵的原始史料,更为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儒者情况提供了最可靠、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些史料对于考补史籍的某些内容颇为有益。
一、 保存大量的人物史料
碑文作为历史的载体之一,是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就此而言,碑文所辑人物之多,保存的资料之丰富,为这一时段的儒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下仅就碑主家世源流及家族通婚、交游之资料整理介绍如下。
(一) 追溯家世发展变迁
这些家世源流的记载保存了碑主家世谱系发展及身份变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谱系发展中存在的出嗣冐姓或受命承袭他人的情况,那么家世源流的记载能够厘清其流转变迁或不知所出的问题。如《先哲林子平碑》记录了林子平先祖所出之地、后世子孙由四门氏复改林氏的过程,以及到子平一代家庭的成员。碑文如下:
其先出于伊豫探题河野伊豫介通清。十二世孙。曰林七郎左卫门通兼。通兼次子。曰新左卫门通安孙。曰四郎兵卫某。以其邸有四门。自称四门氏。晚又改冈村。子助之进至政。始仕幕府为铳队。传四世。至半次郎讳良通。有故削籍。养于叔父林从吾。因复林氏。改称摩诘。晚号笠翁。读书通大义。着有数种。即子平考也。娶青木氏。生二男三女。仲女清有姿色。善和歌。聘为吾忠山公侧室。生公子。因召嘉善。禄赐百五十石。
另一方面,辑录的碑主都是江户中后期从事儒学研究的儒者,而要想探究其是否为家学传承,就要借助碑文对其先世身份的记录,它能够帮助我们追溯其先世家族身份的发展变化。对此,通过追溯其家世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碑主都是出身于拥有特权的底层武士阶级。而其先世的身份在世代变迁中或为底层的医者、没有职位和俸禄的一般武士,或为从事农业的乡士。其中,仅有间重富、帆足文简、藤森弘庵、高岛秋帆四人的先世是有世袭的高级武士。
一般来说,无关的外人在其他史料中是很难得到关于先祖家世的谱系及出身情况的信息的,但碑文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追溯碑主的家世发展变迁这一点上,碑文可以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
(二) 资考家族婚姻状况
碑文所保存的家族婚姻资料,不仅有碑主的配偶,还涉及其子女的适配情况。特别是世家姻亲关系方面,从碑文可见碑主自身或其子女与世家豪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可以说这方面的文献在史料价值中是十分珍贵的。
辑录碑文中关于家族婚姻的记载大抵如下:
先生娶福本氏。先殁。再娶伊藤氏。无子。乃以弟维显为嗣。(《蓝田先生墓铭》)
配革岛氏。先卒。有一男一女。亦早世。再娶中村氏。生男环。承厥后。(《履轩先生墓志》)
后配来岛氏。生三女。长夭。次为惟完妻。次为江户昌平教官尾藤孝肇妻。(《处士饭冈澹宁先生墓铭》)
长女亦先卒。三女皆适麾下士族。(《冈本丰洲墓碑铭》)
娶葛冈氏。生三女一男。长女适于府内侯臣岩下政德。次于鸟取支封清水长年。次于同族光准。(《太室涩井先生墓碑》)
从上述史料能够看出其婚配带有阶级色彩。众所周知,到了江户时代,幕府统治的封建社会开始衰败,为此而采取了身份制度来巩固统治的稳定性,尤其是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使各阶级之间很难移动。反映在碑文中,一方面是碑主配偶的选择,反映了门第相当的阶级家族的联姻。“如崇信暗斋学的大阪儒者饭冈义斋,其长女就嫁给了赖春水,次女则嫁给在中央推动‘异学之禁’的另一代表人物尾藤二洲,所以赖春水与尾藤二洲其实是姻亲兄弟。”①金培懿:《江户宽政年间以降学术态势与安井息轩之学风》,《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7-71页。另一方面是碑主子女的婚配,因为江户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所以基本上都实行封建家长制。他们在精神伦理层面上以“三从四德”等儒教的道德要求为标准,甚至在普通的寻常百姓阶层也是这样。因此,子女的婚姻多由家长择配,子女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因此,很多人为了维护自身阶级的稳定,在嫁女上多选择士族或身份相当的侍臣,基本上没有出现两种阶级之间的婚姻流动。
实际上,按照当时《武家诸法度》的有关规定,身份阶级不同的人之间的通婚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武士与商人、农户等之间的婚姻更是受到各种令文的禁止,故由此看来,门第相当是当时通婚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这种通婚条件明显带有阶级特色。
(三) 反映儒者交游特点
从宏观上看,江户中后期碑主的交游情况主要反映了三个特点:一是儒者在交友上大多趋向儒雅名士;二是从学师承的都是当时较有名气和学识的名师;三是交游地主要集中于江户、大阪和京都三地,尤以江户最为热衷。
首先,关于碑主所交名士,碑文中的记述非常详细,可以发现其中不乏有许多碑主与碑主之间的交往,如尾藤二洲、古贺精里、柴野栗山、赖山阳、片山北海、立原翠轩、芳野世育、木下子勤、藤森弘庵、市河宽斋等一大批名士。他们皆为当时名儒,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故而彼此之间常常进行切磋交流。如《伯兄谷堂先生墓碣铭》描述了碑主在当时所推崇的耆硕之间交往周旋:
年二十余。学于江户。使才栖先子家塾。尔时柴野栗山尾藤二洲二博士。及阪中井竹山艺赖春水诸先辈。世推耆硕。先生周旋其间。深见称许。栗山最号知己。赞先生不容口。
其次,在师从的选择上,碑主都以在社会或文坛上有一定影响力、知识渊博的儒者为师,如安积艮斋、片山琴浦、大洼天民、淡窗广濑、古贺精里、那波鲁堂、林述斋、竹村悔斋等人。他们或在文学的某一方面有一定的特点和影响力,或为当时官方所认可的庠校博士。如《竹堂斋藤先生墓碣》讲述其所从师者兰园增岛,为当时的昌平黉教授,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时下的名师。最后,无论是交友还是游学,他们在游地的选择上都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性。多数碑主在成年后皆游于江户、大阪、京师三地,特别是江户地区的频次极高。这表明江户是当时儒者交游的首选地,也从侧面说明江户地区当时的文化之兴盛与繁荣吸引着众多儒者向往。
因此,通过对儒者交游的考查可以发现,在江户中后期,随着幕府政权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江户城逐渐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促使更多的名士、名师来到文化环境和氛围浓厚的中心城市活跃。
二、 证史籍之正误
从内容上看,碑文是对江户中后期情况的真实反映,是彼时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真实记录。所以,基于真实性的特点,碑文生动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及儒者群体的生活状态等细节。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记录对于考证史籍之内容正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说史籍中的人物记载极富史料价值,但其中亦存在讹误。如关于江村北海少时游学的部分,具体来看,在《先哲百家传》中的记录在卷六第二、三条:“北海九岁至十八岁。在于其叔父河村某许。成长于赤石。未甞知学。好为习俗所谓俳谐者。颇究其奥。时人目以为锦心绣膓。……北海感激之言。始志于学云。”②干河岸贯一:《先哲百家传》,青木嵩山堂,1910,第233页。“北海自志于学。昼夜孳。手不释之。诵读既遍。从事之仅三年。……诱掖虔诚。殆若老成之人。”③干河岸贯一:《先哲百家传》,青木嵩山堂,1910,第233页。《先哲丛谈后编》之相关记载亦同。然而通过与碑文中的内容对比发现,虽然所记江村北海少游的经历较为详细,与碑文内容也无太大差异,但其游于播州的时间段和还京后的就学发愤时间存在误差。
碑文《北海先生墓碣》用简洁凝练的文字记载其少时游于播州及返京就学的整个过程:
龙洲先生娶明石侯臣河村氏女生先生。是以先生少时。数游播州依舅氏。专学骑射。旁嗜和歌及谐歌。深奇其才曰。伊藤氏世以文鸣。以子之锦心绣膓。移之艺文。广誉覆宇宙。岂不惜哉。先生感其言。乃还京。励志就学。时年十六矣。自此昼夜愤励。四岁学成。
但《先哲百家传》和《先哲丛谈后编》内容所述皆为江村北海九岁至十八岁游于播州,依叔父河村某许。虽与碑文中所依舅氏表述不同,但其母氏即为臣河村氏女。据此推断,河村某许应为其舅,表述的不同可能为称呼之差异,应不为错误所至。但碑文中明确表述北海还京就学时十六岁,然而前述其九至十八岁仍游播州,可见其在少时的交游时间上是存在误差的。再者,碑文所述北海还京后励志就学四载学成,但传中所记其学成仅用三年,也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此事时间当以碑文为准。因此,按碑文所记,《先哲丛谈后编》中这两处所记均为误记。
可以说,碑文所录人物在江户后期日本私修史籍中大量可见,其中记录了大量的人物历史事实,是作为史料来源最好的途径。而通过将碑文内容进行与史籍的相互比照,也可以更加明确碑文在考证史籍方面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三、 补史籍之阙失
对于地方来说,碑文中的诸多人物事迹有着引导和教化地方风气的作用,所以碑文对人物史料的保留,于地方人物志的记载是大有裨益的。从数量上看,碑文辑录了171位江户天明、宽政年间到维新前期的儒者。故碑文中的人物事迹,尤其在碑主生平经历、才能学识等方面的资料,可以补阙地方志史籍的漏缺。
《佐贺先哲丛话》①中岛吉郎:《佐贺先哲丛话》,木下泰山堂,1902。载录了肥前佐贺地区的85位德才兼备者,也是该地最具代表性和突出成就的人物。将碑文中所记171人放入其列传中逐一比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古贺家族,其中仅见古贺精里和古贺榖堂的记载,而未见古贺侗庵和古贺茶溪父子的记载。关于古贺侗庵,据碑文所载“文化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擢列儒员,父子相并,同董学政,世以为荣。”可见,其与父古贺精里同样才学渊博,为世所称荣。茶溪亦承籍家学亦班进两番上,碑文记录:“其学亦汉亦洋。亦古亦今。无所不通。其董学政也。屡为浪人狙。而名望益隆。负笈踵门者不绝。佐贺侯米泽侯及数侯。以先生为师焉。晚年门庭萧寂。惟日左右图书。披阅校雠。倦则间行。恝如无意于斯世。”由此可见,碑文所载二人皆应为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同董学政皆曾仕于藩侯,也参与了当时的许多学政制度、人际交往及人物事件等,作为史料的珍稀程度自不言而喻。如此重要之士,《佐贺先哲丛话》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许多人物事件无法明朗、确定。在此之前的《先哲百家传》亦未载录二人之传。后来刊发的《先哲百家传续》则依据此碑所载的传文记事,撰写了古贺侗庵和古贺茶溪的传记,以弥补《佐贺先哲丛话》与《先哲百家传》之不足,这也为后人了解他们的事迹提供了史料参考的来源。
关于林子平之生平,《仙台藩人物丛志》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其与藩医工藤球卿、真葛女史的交游史,但关于林子平被禁锢的始末则较为简单。细见传文内容:
于时子平名一时噪,议者之见,虚说主张,搅乱人心,命禁其书,毁其版。其兄嘉善家幽,遂幽囚中。殁时宽政五年癸丑六月廿一日。②宫城县编:《仙台藩人物丛志》,宫城县,1908,第26页。
至于被禁锢原因及过程,史载或阙略或未详。而碑文所记载则详述其略记,是这一事件的第一手史料。因此,如按碑文所载,乃是由于林子平关注海内外形势,着书以论其边防之重要。然而有司认为事关幕朝,疑其夸大其词,不尊朝政。故而命禁毁其书,并将其禁锢于仟台。子平作以《六无歌》自嘲,端坐一室而殁。
可见,对于史籍记录不清之事,碑文能够顺其事、尽其详。因此,碑文对人物事迹的保存能填补方志史籍之缺,从更深层次的来说,亦可为学界研究地方名人史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史料。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上只是择其要对日本天明、宽政年间儒者碑文之史料价值作了总体性的概述。“事实上,碑文既是时代的产物,就能反映时代之特征。其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丰富多彩,远不止上述史料。”通过对辑录碑文的详细考析,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了不少家世、婚姻、交游诸方面的珍贵史料,可成为后世大量官私史籍之史源;二是碑文作为编撰史籍的史料来源,能够佐证史籍中关于人物记载的相关部分,它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之高更能证明其史料价值。进一步来说,碑文对近世日本儒者的生平做了全面、生动、详细的记载,从中我们既看到日本儒者的个人、家族生存状况,也从侧面展现出中国儒学对日本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包容力、影响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