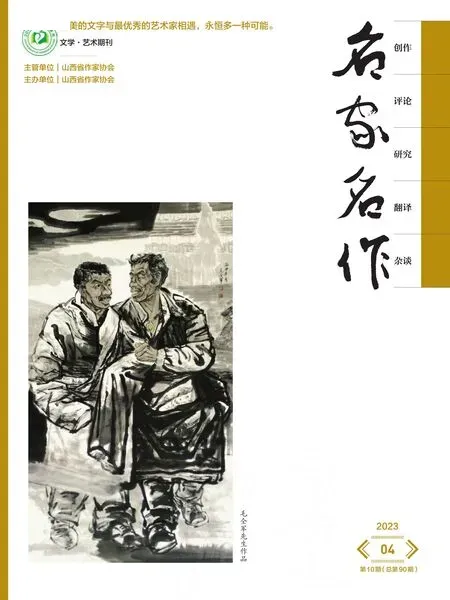装在囚笼中的悲剧
——由《呼啸山庄》谈开去
谢路遥
《呼啸山庄》自成书以来在文学评论界几经沉浮,在最初一面倒的批评声中,独具慧眼的马修·阿诺德在凭吊勃朗特三姐妹的诗作《海沃斯墓园》里,对艾米莉·勃朗特不吝盛赞:“她灵魂间体会的激情、酷烈、悲哀与勇猛/自拜伦死后/无人企及。”而应他所言,《呼啸山庄》果然在世界文学史留下了夺目的光彩,也留下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经济研究、勃朗特家族史研究等一系列课题。而本文尝试着直接从文本出发,挖掘其中悲剧的多重内涵与深意。
一、尽意或失意:交互中的言语、人物和场景
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言不能尽意”“得鱼忘筌”等命题,到西方索绪尔“能指—所指”对应关系的提出,再到拉康对于“能指—所指”的重写,语言及其表意的争辩在哲学界从来不曾停息过。而在《呼啸山庄》中,这样抽象的哲学命题被具象化了,并使读者切身体会到在不同交互场景之中语言对人物命运走向的影响。
其中最频繁出现的是语言场景与时机变化造成的误解。而最致命、最记忆犹新的误解便是,凯瑟琳向奈丽坦白心迹,而隐匿在屋角的希斯克利夫只听到她说“如果嫁给他(希斯克利夫)等于自轻自贱”①勃朗特:《呼啸山庄》,张玲、张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顿时伤心至极,在狂风暴雨里连夜逃走,却无暇听到她后面的那番热烈表白,表意的断裂和缺失带来创伤,这就导致传意的错误和空白造成了创伤。并且这些“创伤”是听者在神智健全的“尽意”基础上,或是因为话语遗漏、或是因为背景情境缺失而导致的完全“失意”,不管从客观时空上还是从主观意志上都回避了被治愈的可能性。于是,读者在故事内部产生完型体验的可能被打破。
而将焦点转移到故事叙述上,站在故事外部再次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读者与山庄中真正发生的故事之间隔了两层。山庄中爱恨情仇的故事首先是由奈丽进行讲述,但一系列语言表意的失败和奈丽对人物前后不一的多变态度使她的讲述显得不够可靠。并且读者也并非是故事的直接倾听者,而是借由“外来者”洛克伍德的耳朵去听奈丽的讲述。行文之中也透露出洛克伍德视点的不可靠性。而随着真相缓缓被揭开,温情的外壳以一种骇人的方式褪去。所以《呼啸山庄》是否本身就是一个悬浮于真相之外的故事呢?看似“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在作者巧妙的叙述安排下也被“击溃”,读者在故事外部产生完型体验的可能也被打破。
通过对交互中的言语、人物和场景的呈现,艾米莉·勃朗特让我们充分领略到:种种看似普通,乃至于无意识使用的语言,往往最能揭示我们的根本认知谬误。而这种“失意”所造成的悲剧在文本内部被冲突性的情节所印证,在文本外部的接受层面被读者“犹疑”“惶惑”的阅读体现所实践。书中的人物和读者一并被艾米莉·勃朗特装进了语言认知的囚笼。
二、复仇或自戕:受困的希斯克利夫
《呼啸山庄》在悲剧性的故事叙述中塑造了希斯克利夫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他所遭遇的爱情悲剧是易于看穿的文本表层,而在深层隐含着更为结构性的悲剧根源。
回顾古今中外的爱情悲剧,其中的一种模式是产生爱情的双方爱而不得酿成的悲剧;另一种模式是爱情本体的悲剧,即爱情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如同钻石般坚固,而是如泡沫般破碎消失了。《呼啸山庄》所呈现的爱情悲剧是这两种悲剧模式的统一。可以从凯瑟琳的那番表白中找到她对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根源:我爱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俩的灵魂是用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也可以将这样的爱情观归咎于没有情感体验的作者对于爱情的一种纳西索斯式的想象。假使真正的爱情的确要求相爱的两个主体拥有极高的相似性,那么,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在漫长的分离之中难道没有产生任何的差异?或者以另一种模型来进行比喻,将凯瑟琳视为“原乡”,那希斯克利夫便是“离散者”。在经历了漫长时间和巨大空间的阻隔后,离散者即便归乡,但是身上已经不可避免带有间居性(inbetweenness),而原乡自身也在不断更迭。那么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爱情就丧失了合法性,他们再度相遇后爱情所指向的对象是对于过去彼此的想象。
希斯克利夫的归来也是他实施复仇行动的开始,而向谁复仇首先就是一个难题。在凯瑟琳濒死时,痛苦万分的希斯克利夫对她说:“我原谅你对我做过的事。我热爱这个害死我的凶手——可是害死你的呢!我怎么能原谅她?”实则害死凯瑟琳的凶手和“害死”希斯克利夫的凶手并无不同,并且这其中也包括了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本人。这句话内在的悖论直接揭示出希斯克利夫冰火两重的内心煎熬,暗示爱情悲剧背后的虚幻难以攻击坚固的社会结构。因而小说也超越了传统的婚姻、爱情和家庭小说的模式。
在凯瑟琳死后,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行径也愈发变本加厉,但是他的复仇最终没有得到他心目中的理想结果。美国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希斯克利夫的本质是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男性独裁家长身份颠覆父权制度的人。①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这既是人物希斯克利夫反抗的不彻底性所在,也是其深层悲剧性所在。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斯克利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斯克利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正因为他采用了上层阶级的标准,在他早期反抗中和在他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如果说在最初希斯克利夫尚未出走之时,他的反抗尚且有受压迫底层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的努力,那么他蜕变复仇的过程并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改革者,而是让他把这套精英规则体系内化,并将这套社会建制在他由金钱和权力所创造的场域进行再生产的过程。
希斯克利夫在道德行为上当然不能被称为一位“完美受害者”,然而“非暴力不合作”这类将自身摆在道德制高点以取得同情的抗争模式。当时的英国社会不但缺乏效率,而且还可能会失败得悄无声息。希斯克利夫所采取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的复仇方式,将他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所遭遇的虐待报复回辛德雷身上的同时也报复回辛德雷的儿子哈顿身上,在爱情上所遭遇的失意报复回林顿和凯瑟林的身上的同时也报复回林顿的妹妹、自己的儿子小林顿、凯瑟琳的女儿小凯瑟琳的身上。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话语来形容,希斯克利夫的步步复仇都是他“死本能”的外化和展现。而当他发现他的复仇对象,小凯瑟琳的神貌和凯瑟琳如此相似,而哈顿的秉性又非常像过去的自己时,他感到无尽的痛苦,最后在接连数天的癔症的影响下走向死亡。这是希斯克利夫超我对本我的惩戒。希斯克利夫的确是一位充满执行力的复仇者,但这种复仇在实质上就是一种受困后无路可寻的自戕。
三、重建或失落:哥特式的艾米莉
将《呼啸山庄》视为一部哥特风格(Gothic)的小说是学界的共识。哥特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最早是文艺复兴时期用来区分标记中世纪的艺术风格而创造的词汇,其来源于公元3—5世纪时侵略意大利并瓦解了罗马帝国的德国哥特族人。15世纪时意大利人为了振兴古罗马文化而掀起了灿烂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对于被哥特族摧毁罗马帝国的历史释怀,便将中世纪时期的艺术风格称为哥特风格,意为野蛮。而哥特文学的显著特质是黑色浪漫主义,在人物、环境、情节的设置上具有阴郁、恐怖、怪诞、离奇、神经质的特点。
首先,在最为核心的小说背景上,呼啸山庄的存在本身就是哥特风格的体现。“呼啸”是指山庄所处地的风吼雨啸的暴烈自然环境。同时,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间形成了鲜明对比。画眉山庄中的生活是真正古典的雍容华贵的美好梦境中的上流生活,而呼啸山庄中的生活则是最为原始、狂野又热烈地展现了美好幻想遮蔽下的现实世界。而对于梦碎后现实的呈现是对形而上幸福的讽刺,同时也是对于追寻世俗幸福的号召。
而在描写的细节上,小说一开场,读者便能感受到一种阴郁的气氛。而这种恐怖随着外来者洛克伍德在呼啸山庄度过第一个夜晚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就在它说着的时候,我影影绰绰看出有一张孩子的脸从窗外向里探望——恐惧让我变得残忍了,我发觉无法将这个东西抖落开,就把那只手腕拉到碎玻璃渣上来回划,直到流出血来,染透了铺盖;但它还是哀泣:‘让我进去吧!’而且一直死死抓住不放,几乎都要把我吓疯了。”洛克伍德出于自卫将“陌生女人”的手腕拉到碎玻璃渣上来回滑动,是一个典型的“身体恐怖”场景。而身体恐怖场面的展现不止这一处,对于病态躯体的描写和对于身体残酷伤害的呈现贯穿全文。同时身体恐怖在《呼啸山庄》中还体现在“生育的恐怖”上。尽管故事中对生育的直接场景是讳莫如深,生育时刻的痛苦也被拒绝展现。但其中分娩为小说中的所有女性人物带来悲剧,生育给凯瑟琳和弗兰西斯带来了死亡的悲剧。而这种身体恐怖的呈现,越过了一道界限,当几个世纪之前的文艺复兴将身体从禁欲之中拖拽而出,在给身体解绑的同时仍然在对身体进行“美”“健康”的规训。而《呼啸山庄》正是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在言说这些孱弱的、病态的身体,将并不完美的身体重新纳入审美的范畴,并试图重建新秩序。
除“身体恐怖”外,《呼啸山庄》中的异教色彩也加剧了小说的哥特特质。例如,彭尼斯东崖底的“仙人洞”和正统中的“神迹”相对,既是凯瑟琳癔症发作的幻觉场景,也是后来吸引小凯瑟琳偷偷离家误入呼啸山庄的原因。而对于人物的指称也带有异教色彩:奈丽看到希斯克利夫去世前的怪异表现,心里怀疑“我只不过掠了他一眼,就把我吓得简直没法形容啦!那对深深抠进去的黑眼睛!那种微笑和那死人似的惨白!我看着眼前的他,仿佛不是希斯克利夫先生,而是什么鬼怪”,立刻对这个自幼熟悉的人产生莫名的恐惧感;约瑟夫经常责骂称奈丽是巫婆,而凯瑟琳生病出现幻觉时,也把奈丽看成了“捡拾精灵弩箭,要拿来伤害我们的小母牛”的巫婆,后来又把镜子当成“黑橱柜”,将自己的影像当成了鬼魂。等到她发觉奈丽故意向埃德加隐瞒她的病情,导致埃德加对她不管不问,愤而指责:“奈丽是我暗地里的仇人。你这巫婆!这么说你真要找精灵弩箭来伤害我们了”。这里面既有精神紊乱导致认知混淆的因素,也从侧面揭示了奈丽暗中施加消极影响,导致事态恶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各种巫术以及精灵的出现是传统信仰体系的反叛,甚至在主人公对天堂与地狱的态度也是颠倒、消极、怀疑的,这是对于信仰体系的质问。这种信仰失落的离心结构是否在呼唤着一种向心?或者去中心化就是目的本身?作者应当更加倾向于后者。
正如学者蒲若茜所言:虽然哥特体裁在艾米莉·勃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显得陈旧,但它打破了“古典的”和“理性的”生活秩序,敢于反映被列入禁忌的事物,在社会规范、理性裁决和习俗制度所认可的情感之外展开了新的视野,扩大了现实感的范围及其对人的影响,成为情感的解放者,承认人性深处的非理性层面。①蒲若茜:《〈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第47-54页。艾米莉·勃朗特在继承哥特风格对于社会旧有秩序进行批判、试图冲破旧有信仰体系的同时对哥特式的风格进行了拓宽,并且从对于阶层囚笼的揭露方面更进一步走向了对于观念囚笼的冲击。
四、结语
虽然《呼啸山庄》以悲剧为基调和底色,但是在小说结尾仍然留下了一线希望,在一切的阻挠因素都相继死亡或在悲剧中醒悟后,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化身,小凯瑟琳与哈顿最终成婚。失落之后才能有重建,这或许也就是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所期望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呼啸山庄》囚笼般悲剧的背后反映的是18世纪末期英国囚笼般的现实氛围。作者艾米莉·勃朗特以奇崛的笔法刻画出囚笼的模样,以悲悯的笔调平视囚笼之中挣扎的人,以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呼唤着人性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