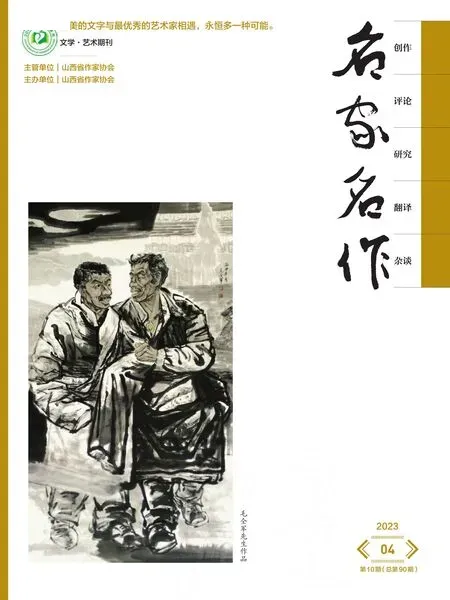论西海固乡土小说的日常叙事
周昕洁
乡土文学扎根于深厚的农耕文明土壤之中,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学创作中,“故乡” “乡土” “乡愁”不断被重写、被建构。故乡之于个体而言,有着特定的情感与记忆。乡土小说是西海固小说创作的重点。相比于其他地区,西海固发展较为缓慢,呈现出一种和当下生活稍微拉开距离的滞后感,这种环境条件孕育出西海固独特的乡土小说景观。本文试图以西海固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聚焦乡村日常生活和乡民精神状态,对其日常叙事展开研究。
一、日常生活的叙事风貌
谈及乡土文学,我们无法回避两种基本叙事模式,其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具有启蒙意味的乡土小说范式。基于“改造国民性”的宏大主题,聚焦于乡土生活中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给予揭示并借以实现“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其二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范式中,浪漫、人性、自然是关键词。不同于鲁迅侧重批判国民劣根性,沈从文选择从“人生的形式”角度立意,正面勾勒出乡土之于城市不同的宁静、和谐和质朴的一面,赞美和歌颂乡土生活中的善与美。到了新时期以后,对乡土书写的作家们转向新课题,关注乡土与城市之间微妙的界限,关注离乡与归乡的些许愁绪,或追忆或惋惜,各自写来,各呈其志。值得注意的是,在偏远的西部大地,西海固作家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中偏于一隅,从普通乡民视角出发,消解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讲述西海固独有的乡土生活和生活态度,具有特别的意义。
西海固作家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将故乡土地上的人、事、物置于小说创作文本之中,透过某一生活片段,书写个体生命经验与体悟。譬如石舒清在《清水里的刀子》中聚焦于普通老人马子善的心理变化,围绕死亡仪式中的片段展开,从而引发对生死的感悟。了一容的《样板》通过“我”这一年轻人民教师的视角,描绘出生活在西海固的乡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刻画了这片土地真实而又贫瘠的面貌。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通过浆水和酸菜两种家常食物的制作和分享这一日常细节,讲述一个家庭清贫却又充满温情的凡常生活,表现出来自西北大地乡土最底层普通人群的生存百态。在这些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他们并不热衷于社会浪潮的变迁,也不执着于宏大叙事,反而将创作视角转向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着眼于可以触摸到的当下,将日常生活的琐屑与个体的精神世界作为乡土小说叙事的底色,呈现出西海固乡土小说独特的日常叙事特色。
除了个体生活图景的呈现,西海固作家还经常将地域特色、地方民俗和节日文化置于小说创作中,呈现出西海固民俗景观书写,使其作品带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郭文斌的小说中对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的刻画就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长篇小说《农历》按照时间顺序,刻画了元宵、龙抬头、端午、清明、中秋等十五个节日以及与节日有关的习俗,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了有趣而又详尽的叙述。千百年来的节日习俗得以延续至今离不开每一个国人的传承,在这一传承过程中,乡土的农村家庭恰是最小而又最为重要的单位。除民俗节日的刻画之外,西海固作家对农民的日常耕作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譬如石舒清在《农事诗》中对劳动场景的描摹,刻画出社员们挥着锄头劳动的场面,充满浓厚的农耕气息。
在西海固作家的创作中,西海固的乡土生活总是处于一种慢节奏之中,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人们在缓慢而又悠然地前进着。事实上,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学景观和西海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西海固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发展较为缓慢。正如马金莲所说:“时至今日,西海固山区还是比外界慢了一个节拍,无论是生存环境还是生活水平。”①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第200页。山区生活使生活在西海固的人们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作家们受此影响,用他们缓慢而又细腻的笔触,刻画着普通农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些作品中,村庄得以被重新“复魅”,乡土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劳作之中,呈现出之于乡土的真实性。
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西海固乡土小说消除了革命和政治化的宏大叙事,不再刻意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的“形式”,而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关注家乡的民俗风情、农耕生活和日常琐事,刻画出平凡而又真实的乡土生活图景,在作家个体经验和公共认同中实现一种平衡,书写当下正在逝去的乡土记忆,呈现出一种“向内转”的形式。
二、日常叙事的诗意呈现
20世纪80年代,新写实小说开辟了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脱离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宏大叙事,将关注点置于普通的“人”和“日常生活”中,实现了日常叙事的新发展。日常叙事之于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的书写,在乡土小说领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新时期以来,西海固作家群以特有的文学风貌为大家所关注,其笔下的西北乡村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日常叙事在西海固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在西海固乡土小说中,不同作家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但是却始终贯穿日常生活美学,他们追求对西海固原生态生活的还原,同时赋予日常生活以审美内涵,呈现出一种自然、质朴而又诗意化的日常叙事风格。
西海固作家偏爱用儿童视角进行叙事,他们透过儿童的眼光观察生活中发生的人或事,呈现出诗意化的凡常生活。相比成年人来说,儿童看待世界的过程是简单、朦胧而富有童趣的,进而表现出的世界更加纯真、诗意和美好。郭文斌在《吉祥如意》中以五月和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角,写出了对乡村过端午的回忆。在孩童们的眼中,“这端午有神秘的味道”②郭文斌:《吉祥如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第16页。,“在地上磕头的感觉特别美好”③郭文斌:《吉祥如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第20页。,“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④郭文斌:《吉祥如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第26页。。从父母的立场来看,按部就班、顺顺利利地完成这些活动,才能采个好兆头。但是,与成人世界不同,儿童有着自己特有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节日中禁忌的打破并不意味着责罚和灾难,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升温。正是孩童们出的差错以及彼此之间的打趣、玩耍,构成了小说富有趣味的来源。当郭文斌透过孩童们的眼光来书写具有浓郁民俗民间色彩的节日时,文本世界弥漫着童真而又美好的气息。
马金莲善用儿童的经验书写底层生活的琐碎以及在琐碎中生长出来的坚韧力量,其作品有着超越苦难的温情意味。《蝴蝶瓦片》以六岁半的“我”偷溜进老刀的家中找蝴蝶瓦片为引,借以讲述了老刀的儿子小刀的故事,体现出平凡个体生命之存在的意义。小刀遭遇意外瘫痪,终日在家中,快要被全村人所遗忘。这种平静在“我”意外闯入小刀的屋子时被打破,“我”发现了小刀的炕上放满了各种样式精致的鞋子,其中,有一双绣着蝴蝶的鞋子竟然是为“我”专门做的。于是,当“我”穿上这双鞋子时,小刀又被大家记起来了。“一夜之间,我们庄里娃娃大人的脚上全穿上了小刀做的鞋子。”⑤马金莲:《蝴蝶瓦片》,《作品》2010年第5期,第48-56页。小刀非常态的生活无疑是痛苦的,大家无不关注其残缺的双腿及邋遢的形象,试图给予其帮助。但于“我”而言,小刀却仅仅意味着神秘:能认出“我”是马老旦的二女儿,在出生之前就为“我”做了合脚的鞋子,知晓外面发生的一切,拥有做精致鞋子的本领……同时,在小刀的帮助下,“我”还成功地得到了蝴蝶瓦片,实现了祈雨的愿望。小刀生命的尊严和力量在“我”的眼中得以诠释出来,在儿童的世界中小刀展现出坚韧的力量,远远要超出生命给予的苦难色彩,一双双鞋子承载的是小刀从未停止的希望。这份希望被六岁半的“我”偶然触碰,并实现了救赎般的延续,蝴蝶瓦片终于飞进了山谷。在马金莲的小说中,苦难绝不是单一的审美体验,其小说中表现出生活给予的残酷与苦难中更多地孕育着一份温情与暖意,这些温暖的“美色”在灰色的底板上熠熠生辉,呈现出马金莲式的“日常生活美学”。
撕开西海固那片土地的固有面纱,其乡土小说呈现出一种诗意叙事的倾向。这种叙事倾向和儿童视角的选取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海固作家立足于家乡记忆,相对于成年世界中残酷而现实的法则,他们选择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于儿童来说,对西海固的感受往往不是贫瘠、干旱和苦难,而是那无忧无虑,充斥着美好和快乐的童年时代。在这种视野下的西海固乡土小说无疑呈现出一种温暖而又充满诗意的色彩。同时,西海固作家群这样的审美追求侧面反映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实问题无可消解时,孩童的世界成了一处暂且避世的桃花源。
三、日常叙事的精神向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乡村社会的空间逐渐变小,其文化形态也发生了改变。相较于对浓郁地域色彩的刻画、以纯粹的农村生活为叙述内容的传统乡土文学,作家们更多地选择叙述商品经济下日益凸显的城乡问题,将创作重心进行转移。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北边陲地区,西海固的作家们并没有着眼于城乡二元对立热点话题的呈现,反而坚守缓慢而又宁静的乡村生活,基于自身的乡土记忆来描摹乡民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呈现温情而又真实的乡村风俗人情,书写乡土记忆。他们从个体经验入手,不单单是抒发对故乡的追忆与留恋,也在寻找重建精神原乡的途径。未来的乡土生活如何演变和发展,西海固作家进行了各种尝试和探索,这种探索与突围对乡土文学创作和乡村文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地理意义上的乡村可能会消失,但文化意义上的乡土精神永远不会泯灭。西海固作家满含眷恋地回忆故土,书写那片土地留给他们的美好记忆。郭文斌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坚守,其小说一方面展现出西海固庆祝节日的日常形态,营造了祥和而又温馨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展现出节日民俗背后的民众审美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乡民们对于善和美的渴望,表达了民间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尤为可贵,民俗文化中那种感恩、孝敬、和谐等精神不仅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坚守和传承的精神,恰恰也是郭文斌的小说所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同样,西海固的乡土精神还表现在苦难背后孕育出的顽强精神。作家们在刻画西海固的乡村生活时,逃不开苦难书写,西海固环境恶劣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并不单单在表现苦难,而是着重凸显苦难背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坚韧力量。马金莲长期生活在扇子湾,观察着身边的人和事物,以真实的笔触记录西海固底层人们的落后、贫穷的原生态面貌,对生命和人性进行叩问,彰显西北底层劳苦大众为求生存而不畏艰苦的坚毅品质。难能可贵的是,西海固作家从日常生活入手进行小说创作,却并没有陷入日常经验琐事所面临的空洞、碎片和无意义困境中,而是试图用文学审美的方式寻找文学本身的精神向度。
西海固作家固守于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以独特的感知力来观察乡村现状,透过文本表征,更多地呈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识到了乡土社会中内在的精神文明,使西海固乡土小说呈现出新的精神向度。在西海固作家的小说中,乡村记忆仍保持着传统伦理的状态,根植于乡土文化的文学表达仍是对精神原乡的追寻。
综上,西海固作家扎根于乡土土壤之中,着眼于日常生活琐碎和民俗生活,以儿童叙事消解苦难色彩,试图以自身的审美追求唤起社会对乡土伦理和民间文化的关注。在个体乡土生活经验的书写背后,呈现的是西海固作家对乡土精神的固守、对乡村文明的依恋,在乡土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乡土生活难以为继,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西海固作家的乡土小说日常叙事中的乡土生活呈现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
——评钟正平《知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