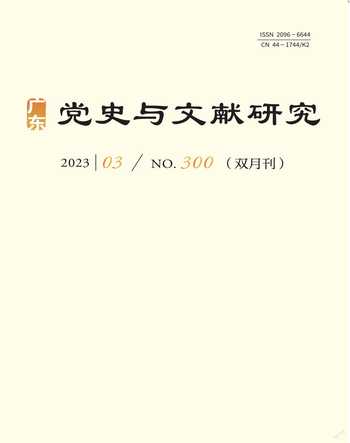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新探
【摘 要】一般认为张太雷曾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但此说法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张太雷主要是因俄共(布)党员、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成员等特殊身份而被共产国际选为代表的。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张太雷报告亦不是中共早期组织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共最终被共产国际正式认可,主要是由中共的性质、坚定的信念、强大的凝聚力等自身因素所决定的。
【关键词】张太雷;俄共;共产国际三大;中共早期组织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3-0017-11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一般认为张太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共尚未正式成立,代表从何而来?已有成果大多将张太雷所代表的中共等同于中共早期组织,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将就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史实探析,以期深化对张太雷以及中共早期历史的研究。
一、张太雷特殊的身份
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张太雷的中共代表身份应源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简称远东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材料一,1921年5月16日,远东书记处签发了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的委任状。这应是张太雷的中共代表身份的最早出处。材料二,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该报告关于张太雷是中共代表的记载,成为学术界认定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最重要的证据。但该报告关于张太雷是中共代表的记载不能确信。其一,该报告存在明显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一是关于张太雷、杨和德(即杨明斋)二人与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结果决定建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记载。而实际上,杨明斋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间是1921年7月,中国支部建立的时间不会迟于1921年3月。二是关于张太雷和杨明斋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记载。而实际情况是,杨明斋因错过了开会时间,并没有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其二,该报告标注的时间是1921年6月,但并不是当时形成的文献,而是出自1928年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回忆文章。该报告和舒文均刊于苏联刊物《革命的东方》第4—5期合刊,前者页码是216,后者页码是194—230。材料三,1928年舒米亚茨基撰写的《中国共青团史和共产党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该文说:“张太雷同志到伊尔库茨克以后,接到中国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在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了发言。参加远东书记处工作、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亦是学术界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的两条重要依据。简而言之,关于张太雷中共早期组织代表身份的记载,主要出自舒米亚茨基1928年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既然是几年后撰写的悼念文章,可信度就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该文翻译成中文后,译者在文后以附言的方式特作说明:“舒米亚茨基在这篇文章里有记载失实之处……望读者注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通过对该文的考证认为:“舒米亚茨基所作的回忆录有恣意窜改之处”,“把多少带有革命性内容的事迹都归在了张太雷的名下”。总之,舒米亚茨基悼念文章涉及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方面的内容不可尽信。
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认定张太雷中共党员身份的信息来源,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来自中共早期组织。因为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前,中共早期组织根本就不知道远东书记处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向远东书记处派出代表的问题。此外,也基本可以排除张太雷随身带去有关材料的可能。因为张太雷随身带去了不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的材料,似乎没有涉及中共早期组织方面的材料。
当然,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对张太雷中共党员身份的认定,并非杜撰或空穴来风,而应与张太雷的两个特殊身份有关。
特殊身份一:张太雷是俄共(布)党员。据瞿秋白牺牲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一文后所附的《记忆中的日期》记载:1921年5月他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是年9月“始正式入党”。而瞿秋白当年参加共產国际三大所填履历表“何党派代表或成员”栏目中,填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有论者据此认为,张太雷赴俄前当然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的是俄共(布),而非中共。首先,中共草创阶段,入党手续相对简单,既无入党介绍人,亦无预备期。李达回忆:1920年夏,“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周佛海回忆:1920年9月,陈独秀就建党之事约其谈话两次,第二次谈话“请我加入,我便答应了”。林伯渠回忆:“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有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的规定,但明确规定“考察期限最多为两个月”。这显然与瞿秋白经过近四个月的预备期不同。其次,195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这是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的最权威说法。在此后历次纪念瞿秋白活动的讲话中,中央领导同志均坚持此说法。既然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他此前加入的就只能是俄共(布)。再次,涉及瞿秋白入党问题的研究成果均认为,瞿秋白1921年5月加入俄共(布),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笔者认为,只要瞿秋白加入俄共(布)是确定的,作为瞿秋白入党介绍人的张太雷,其俄共(布)党员身份就同样是确定的。
既然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的是俄共(布),何以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三大的履历表中填写的却是“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笔者推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在张太雷、瞿秋白等人的观念中,俄共(布)是比中共更高层级的组织形态,加入俄共(布)不仅等于加入中共,甚至比加入中共更荣光。其二,张太雷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自认为就是中共党员,瞿秋白亦自认为加入的就是中共。其三,共产国际有关机构人员要求瞿秋白填写中共预备党员。
特殊身份二:张太雷是俄共(布)在华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亦译作革命局)的成员。有必要先对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作一简述: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开启了俄共(布)在远东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维经斯基来华后取得的最主要工作成果,就是先后成立了由他领导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和由鲍立威、斯托杨诺维奇领导的北京革命委员会。将威廉斯基1920年9月1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列举的奠定了共产主义组织基础的六地,与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信中提到的已经成立或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地相比照,革命委员会即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也应是准共产党组织。因为威廉斯基的报告明确提出:“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此处的“代表大会”应该是指各地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学术界关于革命委员会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笔者认为,革命委员会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具有共产党或准共产党性质。因为革命委员会由俄共(布)在华党员组织和领导,吸收中国革命者参加,然后通过召开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方式实现在中国建党。由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委员会持排斥态度,各地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并不顺利。如被维经斯基派到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米诺尔,到广州后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包围,导致最后参加广州革命委员会的几乎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正因为各地革命委员会组建的不顺利,威廉斯基报告中提到的召开各地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以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一再延期,直到维经斯基离开中国时也未能召开,最后实际是不了了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也随之停止。
张太雷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具有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其一,早在1918年下半年,鲍立威就从《华北明星报》找到张太雷任其英文翻译,开始了二人之间密切的互动。1920年夏,鲍立威酝酿组织北京革命委员会之际,适逢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故鲍立威邀请张太雷参加北京革命委员会是完全可能的。其二,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拒绝参加广州革命委员会,除了与无政府主義者“观点不一致”外,还可能与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也“观点不一致”。笔者推测受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中国革命者,除须是社会主义者外,还应接受俄共(布)领导。上述张太雷的俄共(布)党员身份,意味着其接受俄共(布)领导不成问题。其三,根据张太雷女儿张西蕾和他的中学同学李子宽的回忆,1920年6月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没有去谋取社会职业,而是投身京津一带的革命活动中。张太雷虽然参加了北洋大学毕业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但是没有回学校领取毕业文凭。这应该与张太雷观念转变及觉悟有关。1921年1月他在赴俄前夕给妻子的家书表示:“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因此,张西蕾、李子宽二人的回忆应符合历史实际。也就是说,张太雷从北洋大学毕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按照一般认知,当时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就意味着参加到建党建团活动中。由于京津建党建团活动发生在1920年10月、11月间,而张太雷1920年6月毕业,其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不太可能是参与京津建党建团活动,只能与鲍立威在京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相关。其四,根据俄共(布)有关文献记载,作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的张太雷,也应该是北京或天津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最后,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张太雷于1920年8月参与北京革命委员会工作。
在远东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看来,张太雷无论是俄共(布)党员身份还是革命委员会成员身份,无疑是地道的、十足的共产党员或中共党员。
二、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正式代表
张太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但他却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派出的正式代表,因为他的委任状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签发的。有论者认为,远东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开展工作的最高机构,自居是中、日、朝等国已有的共产党组织的上级。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惯例,上级机构和领导对某一同志的身份认可及任用,通常比下级机构的正常组织程序更有效。对此论点,笔者不能认同。因为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尚未确立,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决定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远东书记处的委任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委任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不少学者认为,张太雷的中共代表资格,得到了中共早期组织的批准和委任,是中共的合法代表。此说的依据是中共早期组织代表杨明斋在远东书记处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笔者认为,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应该是张太雷任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状。其一,远东书记处对张太雷中国支部书记的任命有“暂任”二字,即具有临时性。张太雷任中国支部书记一职,需要得到中国国内组织的同意。其二,1928年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中共早期组织所批准的是张太雷“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而未提及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代表的委任状。舒米亚茨基的悼念文章,极有可能是在参阅了上述联席会议记录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不太可能是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第一,如果远东书记处所发电报中有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的内容,这与报告建议中共早期组织派遣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内容相矛盾。按照后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团由张太雷、俞秀松二人组成的情况来推断,中国代表团的限定人数当为二人。如果张太雷已占用了一代表名额,就应建议中共早期组织再派另一代表与张太雷组成代表团。而实际情况是,中共早期组织收到电报后“决定派遣两同志前去代表大会”,这“两同志”显然不包括张太雷。第二,如果远东书记处所发电报中有批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的内容,即意味着远东书记处给张太雷的委任状在前,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在其后,这显然有悖正常的办事程序或规则。正常的办事程序或规则,应是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电报在前,在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迟迟未到的情况下,远东书记处相机行事,任命张太雷为参会代表在后。第三,如果张太雷的委任状在前,随后又要求中共早期组织批准对张太雷的委任状,这不仅存在越俎代庖的问题,更意味着远东书记处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中共早期组织。这种凌驾于中共早期组织之上的做法,不太可能被具有强烈独立自主意识的中共创建者们所接受。第四,即使杨明斋所说的“批准了他的委任状”,是批准了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的委任状,那也属于事后追认。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期间的身份,仍不能算是中共的正式代表。第五,中共早期组织选派了自己的正式代表杨明斋,只因错过了开会时间未能参会。中共既然有自己选派的正式代表,其他人应不能称为正式代表。
在远东书记处签发张太雷委任状的时候,是否在伊尔库茨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答案是否定的。当时,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始人之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俞秀松,因受上海党团组织委派,作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正式代表已抵达伊尔库茨克。当张太雷尚忙于北洋大学毕业考试的时候,俞秀松已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建党活动;当张太雷大学毕业后但尚未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之前,在中共上海发起组“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俞秀松“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包括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参加成立工会组织、编辑《劳动界》等刊物、组织外国语学社等。显然,俞秀松比张太雷更具代表资格。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远东书记处签发张太雷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委任状的同时,也签发了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委任状。其中缘由,自然与二人是否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及在中共早期组织中的地位无关。张太雷比俞秀松更具优势的地方在于他自身所具有的俄共(党员)、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成员等身份。
三、张太雷报告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提交的报告
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张太雷向大会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1921年6月10日)》(简称张太雷报告),该报告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所作的介绍中国国内全面情况的报告,是中共早期组织写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报告。但实际上,张太雷报告并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提交的报告。
第一,张太雷报告是由张太雷和舒米亚茨基起草的。二人能否代表中共早期组织?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尚未确立,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正式代表,无论是舒米亚茨基还是张太雷,都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組织的资格和权利。
第二,中共早期组织在选派代表的同时,也准备了一个报告,该报告才是中共早期组织提交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报告。由于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未能参会,从而导致该报告未能在会议召开期间向大会提交。1921年7月20日在远东书记处举行的联席会议之前,远东书记处仍没有收到该报告。如果该报告不曾遗失,那么很可能是涉及该报告的档案尚未公布。
第三,张太雷报告与中共早期组织提交的报告相比较,在内容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篇幅结构存在差异,前者共由九部分构成,后者的内容只有五部分;而且涉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内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苏联学者M.A.佩尔西茨通过比较刊登在《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的张太雷报告和原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的张太雷报告发现,前者删节了有关地方党组织的部分,此外还有近30处作了省略或改动。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删改,很可能是在《远东人民》准备刊载张太雷报告时,手头已有了中共早期组织或杨明斋提交的报告,因二者在有关党组织的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才对这部分的内容作了删节处理。
第四,张太雷报告的署名中,除张太雷外,还有杨明斋。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张太雷报告中有杨明斋补充的内容。杨明斋随维经斯基来华,除担任其助手和翻译,还负责外国语学社和华俄通讯社的工作,对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早期组织的情况应比较熟悉。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记载与中共早期组织存在的差异表明:杨明斋为张太雷报告提供材料的可能性极小。笔者认为,张太雷报告加上杨明斋的署名,是为了使该报告带上中共早期组织的色彩,毕竟杨明斋是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正式代表。
第五,张太雷报告中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存在明显不同。前者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5月,地点是上海和北京,后者是1920年年中,地点是上海;前者领导人是维经斯基,后者领导人是陈独秀;前者称为省级地方组织,后者无此称呼;前者分布于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等地,后者分布于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东京、巴黎等地;前者吸收了不少工人党员,后者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既然张太雷报告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不同于中共早期组织,张太雷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太可能是中共早期组织,张太雷报告就不太可能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报告。
张太雷报告中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与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二者最先成立的地区,均为上海和北京;二者工作机构相同或相似:前者有情报、组织、出版三部,后者有出版、情报、组织三处;二者工作内容不仅相同,甚至语言也近似;二者地域分布十分接近: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七地,涵盖了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信中提到的已经成立或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地,也涵盖了威廉斯基1920年9月1日报告中提到的奠定共产主义组织基础的六地。加之张太雷的俄共(布)党员、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背景,张太雷报告中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极有可能就是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张太雷报告也极有可能就是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四、远东书记处助力亮相国际舞台之辨
张太雷以中共代表身份成功亮相共产国际三大政治舞台,并在与江亢虎、姚作宾等伪“共产党”代表资格之争中胜出。论者多认为是远东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助力的结果。考之史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远东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专门负责远东各国工作的机构,在中国选派什么类型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三大问题上,应该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但在中共早期组织代表权问题上,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似乎并没有多做什么。突出体现在:
第一,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公布的受邀请中国代表团的名单中,不仅赫然写着“社会主义党左派”的名字,而且与中共早期组织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对中共早期组织则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贬损的名称。完全看不出共产国际有关机构对中共早期组织的重视。不仅不重视,而且带有明显的轻视。无论是“只有发言权”的限定,还是“共产主义小组”的贬称,实际都是不承认中共早期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地位。舒米亚茨基还否认中共早期组织是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称“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共早期组织不是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现在已有六个小组,计五十三个成员”从何而来?
第二,迟迟不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与会通知,使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未能及时参会,也失去了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的机会。资料显示,共产国际确定召开三大的时间是1921年4月间,而远东书记处签发的张太雷代表委任状的时间是1921年5月16日,中间有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在任命张太雷为代表之前,远东书记处完全有时间提早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邀请电报,但它并没有这样做。有论者认为,因为共产国际三大临近,中共早期组织选派的代表迟迟未到,于是远东书记处相机行事任命张太雷为中共代表。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并不成立。更加可能的原因是,远东书记处对中共早期组织缺乏信任或心存疑虑,对于是否邀请中共早期组织派出代表一事存在犹豫,从而延误了时间。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远东书记处根本不希望中共早期组织代表出现在共产国际三大政治舞台,从而有意延误了时间。远东书记处之所以在最后还是给中共早期组织发出了与会通知,只不过是为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早期组织提供一个合理的交代。
第三,中国代表团由张太雷、俞秀松二人组成,但这个代表团是一个混合组织的代表团。因为张太雷和俞秀松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代表统计表中的中国代表人数为两人,其中一人是共产党代表,另一人是青年团代表。即使张太雷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指中共早期组织,这个代表团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团。张太雷、俞秀松登上共产国际政治舞台,很难说是中共第一次正式亮相国际政治舞台。
第四,当张太雷得知江亢虎已经抵莫斯科后,即向舒米亚茨基提出不要发给他代表资格证书。舒米亚茨基表示同意。但在大会开幕时,江亢虎却取得代表证并与会。作为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同时又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为何没有信守承诺阻止江亢虎与会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江亢虎在《新俄游记》中写道:当时五个“共产党”云集莫斯科,“此五党者,各不相能,而皆自以为是,互为正统之争”。这种乱象的出现可能是共产国际有关机构对中国实际情况不了解或者工作失误所致。如果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有心助力中共早期组织亮相共产国际三大舞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共产国际组织系统将姚作宾、江亢虎二人排除出局。鉴于舒米亚茨基的身份,他应该完全具备这种能力,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学术界对张太雷、俞秀松二人在共产国际三大与江亢虎、姚作宾等进行的代表资格之争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此举奠定了中共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正统地位。对此,笔者提几点不同看法:其一,中共是否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并不具有决定性。其二,只有那些伪“共产党”组织,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才需要竭力争取正统地位。“伪”,才需要争取“正”或证明“正”;本身“正”,又何须争取“正”或证明“正”。其三,争与不争,应符合创建时期的中共对待共产国际的原则立场。这个原则立场虽未见诸文字,但应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能损害中共的独立自主。所以对于加入共产国际,中共领导层一开始是持慎重态度的。其四,打铁还要自身硬。在中共诞生前,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即以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先后派刘绍周和张永奎、刘绍周和安龙鹤为代表,分别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并以唯一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身份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正统身份当无疑义,但在共产国际三大政治舞台,却没有了该党的身影。张太雷、俞秀松二人在与江亢虎、姚作宾等进行的代表资格之争中胜出,与其说是远东书记处及舒米亚茨基助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江亢虎、姚作宾等“都不成样子”的无奈选择。1929年《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记载:“1920〈年〉5月,苏联代表到沪,独秀与其接洽(当时有许多中国人朝鲜人从俄国派到东方活动),因为张东荪、陈哲时、姜博若……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1960年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后,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戴季陶、吴佩孚、孙中山等人,并帮助和推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总之,中共在共产国际唯一、正统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共的性质、坚定的信仰、强大的凝聚力等自身因素所决定的。
五、结语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有关早期张太雷研究的成果,许多建立在并不十分可靠的回忆史料基础上,或多或少均带有演绎、推理的成分,至今仍有不少事实真相模糊不清,本文所讨论的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有关的四个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及公布,为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共产国际有关档案资料中提及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如其中提到的革命委员会、张太雷报告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等。因此,对于共产国际有关档案资料,如同对于回忆史料一样,不可简单直接加以引用,有必要先作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本文正是通过对有关资料的鉴别、考证,对过去曾广为流传的某些说法进行辨析,认为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派遣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张太雷报告也不是中共早期组织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而张太雷之所以被选为代表更多的是因為他是俄共(布)党员和北京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共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共产国际的认可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其指导思想、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内在因素。
[黄爱军,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何飞彪)
—— 张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