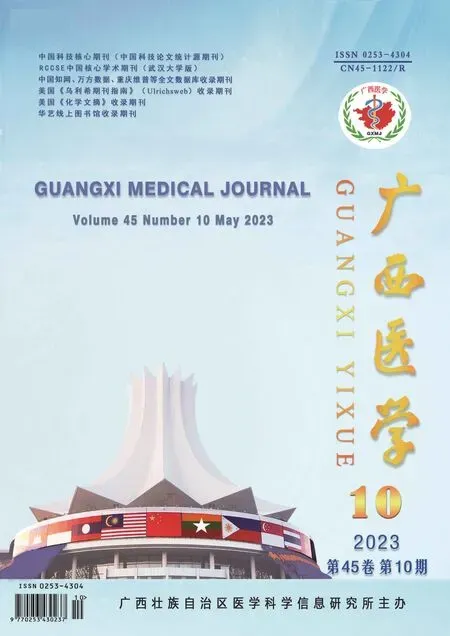未明确诊断患者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决策风格的相关性▲
赵 霞 朱 政 王田田 白 霞 李小容 王东旭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北京市 100730;2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上海市 200032;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河南省郑州市 45005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是一种器质性个人心理动力特征,它源于个体对于不确定感和未知的负性信念,并可在不确定情境下产生一系列情绪、认知和行为水平上的负性反应[1]。IU广泛存在于各类患者,当患者处于因未明确疾病诊断导致治疗方式未知和治疗结局未知的情况时,IU尤为突出[2-3]。目前在国内各地综合性医院中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患者未能明确诊断,部分患者由于无法忍受因疾病诊断及治疗方式不明确导致的不确定感,会产生一系列负性情绪,并做出不合理或不适合自身的决策和判断,给患者和医护工作者的共同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4-5]。既往研究显示,影响患者决策风格的主要因素为决策情景的不确定性[6]。不确定情景下的行为决策理论提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常常凭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和抉择,最终出现认知偏差和行为陷阱[7-8]。未明确诊断的患者在就医时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但不同个体对于不确定性的忍受程度有差异。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个体间IU程度差异与决策风格相关性的研究报告。基于本课题团队前期关于未明确诊断患者IU的现象学研究结果[9],本研究探讨未明确诊断患者的IU与决策风格的相关性,以期为提高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决策科学性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在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全科医学科病房住院及门诊就诊的215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住院或等待入院的未明确诊断的患者;(3)神志清楚,能正确阅读文字和回答问题;(4)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因病情恶化或其他心理因素不适合调查的患者。本研究已通过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编号:JS2148)。
1.2 调查工具
1.2.1 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采用自制的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患者的一般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民族、家庭状态、是否独居)、社会经济变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居住地、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健康相关变量(在本医疗机构入院次数、在本医疗机构门诊就诊次数、本次入院等候时间、是否服用药物治疗)。
1.2.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采用戴必兵等[10]翻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评估患者的IU程度。该量表共27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法计分,其中1分表示极为符合,5分表示极不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患者IU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6。
1.2.3 7条目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采用Spitzer团队[11]编制的7条目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Item Scale,GAD-7)评估患者的焦虑程度。该量表共7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4级评分法计分,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会,4分表示几乎每天都会,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焦虑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2.4 9条目患者健康问卷:采用卞崔冬等[12]翻译的9条目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该量表共9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4级评分法计分,其中1分表示完全不会,4分表示几乎每天都会,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1.2.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肖水源[13]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估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5。
1.2.6 决策风格量表:采用Hamilton等[14]设计的决策风格量表(Decision Styles Scale,DSS)调查患者的决策风格。该量表包括理性决策维度(5个条目)和直觉决策维度(5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法计分,其中1分表示强烈同意,5分表示强烈不同意,得分越高代表患者越倾向于用直觉进行决策。本研究团队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检译及专家咨询,10名专家的平均量表水平内容效度指数为0.9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采用不记名填写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正式调查前统一培训5名调查员,培训内容包括本次调查目的、内容、研究意义及统一使用的调查用语等。调查员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现场提供二维码,调查对象扫描二维码并现场将电子问卷填写完毕。对于无法使用电子问卷的12名调查对象,采用纸质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员在回收纸质问卷时,查看问卷完成情况。项目负责人每月抽查当月获得的50%调查问卷。采用在线系统导出电子问卷的数据库;通过双人录入纸质问卷的数据,并由第三人核查以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TETRAD 6.7.1软件构建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识别不同路径下的最小充分调整集(即混杂因素)。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x±s)或[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构建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回归模型1为非调整模型,模型2为部分调整模型(调整变量仅为最小充分调整集变量),模型3为完全调整模型。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未明确诊断患者的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15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0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21%。209例患者中女性95例(占45.45%)、男性114名(占54.55%),年龄(41.69±15.53)岁,汉族192例(占91.87%),有子女149例(占71.29%),独居60例(占28.71%);大专及以上学历80例(占38.28%),已婚159例(占76.08%),居住地为本市44例(占21.05%),就业状态为在职93例(占44.50%),家庭人均年收入为[7 500(3 000,30 000)]元;在本医疗机构入院平均次数为1.56次,在本医疗机构门诊就诊平均次数为2.32次,本次入院等待时间为1.34周,正在服用药物治疗140例(占66.99%)。
2.2 未明确诊断患者的IU程度、焦虑程度、抑郁程度、社会支持水平及决策风格 209例未明确诊断患者的IUS得分为(81.10±18.87)分,GAD-7得分为(13.86±4.94)分,PHQ-9得分为(17.15±6.12)分;SSRS得分为(39.42±7.76)分,其中客观支持维度、主观支持维度、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维度的得分分别为(7.76±2.88)分、(24.51±5.00)分、(7.15±2.20)分;DSS得分为(24.54±5.48)分,其中直觉决策维度、理性决策维度的得分分别为(11.34±3.33)分、(13.20±3.33)分。
2.3 DAG识别的最小充分调整集 DAG显示,以IU程度(IUS得分)为暴露因素、决策风格(DSS得分)为结局的路径中,无混杂因素;以社会支持水平(SSRS得分)为暴露因素、以IU程度(IUS得分)为结局的路径中,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最小充分调整集;以IU程度(IUS得分)为暴露因素、以焦虑程度(GAD-7得分)和抑郁程度(PHQ-9得分)为结局的两条路径中,社会支持水平(SSRS得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最小充分调整集。见图1。

图1 DAG
2.4 不同路径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以决策风格为因变量(以DSS得分纳入),以IU程度(以IUS得分纳入)、就业状态(在职=0,非在职=1)、本次入院等候时间(以原值纳入)为自变量,构建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IU程度越严重、非在职、本次入院等候时间越长的患者越可能采取理性决策。见表1。

表1 不同路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以IU程度(以IUS得分纳入)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水平(以SSRS得分纳入)、就业状态(在职=0,非在职=1)、本次入院等候时间(以原值纳入)、决策风格(以DSS得分纳入)为自变量,构建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非在职、本次入院等候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采用直觉进行决策的患者IU程度越轻(均P<0.05)。见表1。
以焦虑程度(以GAD-7得分纳入)为因变量,以IU程度(以IUS得分纳入)、社会支持水平(以SSRS得分纳入)、抑郁程度(以PHQ-9得分纳入)为自变量,构建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抑郁越严重的患者焦虑越严重(均P<0.05)。见表1。
以抑郁程度(以PHQ-9得分纳入)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水平(以SSRS得分纳入)、焦虑程度(以GAD-7得分纳入)为自变量,构建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焦虑越严重的患者抑郁越严重(均P<0.05)。见表1。
3 讨 论
3.1 IU在社会支持水平与决策风格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与未明确诊断患者的IU程度有关(P<0.05),而DAG显示,在以IU程度为暴露因素、决策风格为结局的路径中无混杂因素,说明在未明确诊断患者中,IU是社会支持水平与决策风格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还显示,IU程度越严重的患者越可能采取理性决策,而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患者IU程度越轻。因此,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未明确诊断患者越倾向于根据直觉进行决策,这与Reb等[15]和Remmers等[16]的研究结果相似。一般而言,患者IU程度越严重,越可能主动寻求各类信息,有利于增强患者在主观上对未知的把握,从而做出最佳决策。然而在临床实际中,患者和医务工作者获得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患者无法通过理性决策获得最优结局。Lamb等[17]也认为患者过于偏向理性决策更容易导致“医患双输”的局面。因此,针对这类倾向于理性决策的未明确诊断患者,可通过相关措施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首先与其明确问题所在,给予多种策略供其选择并进行重要性排序,其次为其提供正确的医疗信息,从而防止其基于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同时也可以降低其主观不确定感。
另外,既往研究显示,与倾向于理性决策的患者相比,倾向于直觉决策的患者寻求的是令自己满意的方案而不是最优方案,更倾向于对问题总体而非细枝末节的把握[18]。决策目标和个体知识经验储备是进行决策的依据,因此建议对于这类倾向于直觉决策的患者,医护工作者有必要告知其客观上决策应该达到的标准和主观上可能的预期目标,并且向患者提供疾病诊断方向、生活干预方式和生命质量预期等信息,避免患者在关键医疗问题上盲目决策。
3.2 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IU-决策风格路径的关系 DAG显示,焦虑和抑郁均未出现在所有路径的最小充分调整集中,并且在以决策风格为因变量和以IU程度为因变量的完全调整模型中,焦虑和抑郁均不是影响因素,说明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IU-决策风格路径无关,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论[9]和既往研究结果[19]均不一致,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未明确诊断的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P<0.05),与既往研究结果[20]不一致,这可能与患者在未获得明确诊断前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潜在负担来源有关。当个体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时,会将通过家庭成员、亲友、相关团体或组织获得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视为一种负担。亲属和朋友反复询问患者的疾病诊断,势必会进一步加剧患者的焦虑感。因此,医护工作者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交流时应弱化“疾病”和“诊断”的概念,宣导例如“症状管理”和“整体护理”等理念,让患者和家属聚焦于患者自身体验,从而避免他们对于疾病诊断的执着。
3.3 对临床实践和管理的启示 在“知情决策”和“医护患共同决策”的背景下,医护工作者应了解患者个体的决策风格,基于证据做出最优的决策,提高患者就医体验。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临床实践和管理工作:(1)提供清晰且明确的疾病诊断方向等信息,减少患者的不确定感,避免患者盲目决策或基于错误信息做出错误决策。(2)除了评价患者的决策能力,还需要了解患者的决策风格,倾向于理性决策和直觉决策的患者的决策目标和所需要信息量存在差异。最佳的决策风格应处于理性决策和感性决策之间,因此可通过调节患者就医期间的社会支持水平和IU程度,从而调整患者的决策风格。对于过于理性决策的患者,可以邀请其与家属共同参与决策期间的谈话,并向其提供丰富的专业资料,减少患者的IU;对于过于依靠直觉进行决策的患者,应单独与患者对话,促使患者独立冷静思考后进行决策。(3)对于未明确诊断患者,宣教时应淡化疾病诊断的概念,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沟通时也需要把握分寸,缩小患者个人期待与现实的落差。
3.4 小结 在未明确诊断患者中,IU在社会支持水平与决策风格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患者越倾向于根据直觉进行决策。医护工作者应为未明确诊断患者提供清晰且确切的疾病诊断方向、生活干预方式和生命质量预期等,减少患者的IU,避免患者盲目决策或基于错误信息做出错误决策。短期内可以通过调整患者就医期间的社会支持水平,长期可以通过调节患者IU来调整患者的决策风格。此外,医患沟通时应淡化疾病诊断的概念,以免引起患者不必要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