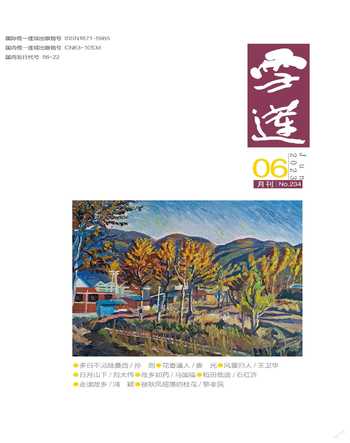花香逼人
钱春邻坐在院子里喝茶。金桂花开了几朵,稀稀落落地顶在枝头,清香在周围荡漾。他喜欢这花,简单隐逸,没有细繁的枝叶,树也干练,清清爽爽的样子,起初他只喜欢这小黄花,不喜欢那浓郁的香,来到岛城后,单位的办公室前也有两棵金桂花,在香气的弥漫下,慢慢习惯了,竟然还有些迷恋!
薛忆梅给他泡了茶,她自己炒的,只喝不卖。她把这茶看得很贵重,不舍得送人。钱春邻时常来喝,他不懂茶,口感说不上好,还有些苦。只知道每次酒后,泡上一壶,几杯喝下去,肠胃都熨贴了,有去尸还魂的意思。央求她送一点,薛忆梅不肯。钱春邻死皮赖脸地要,薛忆梅缠不过,勉强送了一罐。喝完,钱春邻不好意思再要,只能来喝。几杯茶下去,酒气散去,感觉身体舒服了,魂魄回到了身上。
薛忆梅走出来,问,想吃点什么?钱春邻说,要是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鸡蛋面就好了。薛忆梅说,还挺多事儿,鸡蛋面就鸡蛋面,有了鸡蛋还能清汤?钱春邻说,我这不是撒娇嘛。薛忆梅笑了,你还要脸不?说罢,起身去厨房。等一下老张吧。钱春邻叫住了她。薛忆梅说,不用了,他起床再说。
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个大汤碗出来,清汤上浮着绿莹莹的细碎芫荽末儿。钱春邻吸了口气说,香,真香。薛忆梅说,加了香油。钱春邻说,清汤面,当然要加香油。吃完,钱春邻一头汗,神清气爽。往椅子上靠了靠,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薛忆梅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说吧,怎么办?钱春邻说,还能怎么办?薛忆梅说,你什么意思?钱春邻说,没意思。你又打算赖着不走了?钱春邻还争辩,什么叫赖着不走,能不能有点同情心?今天就是不走了。我要是没同情心,你能舒舒服服坐这儿喝茶?薛忆梅说。
金桂花树下,做了个小桥流水的景观,曲曲折折一條小溪,从金桂花树下流过去。水路四壁长满绿藻青苔,池水看起来青黑一片。薛忆梅把鱼料撒进去,红黑黄白的锦鲤游了过来,挤成忙乱的一团。她单穿着一件小背心,下身牛仔裤,快五十的人了,依然保持良好的线条。钱春邻看着她的手臂细细地扬起来,一下,一下,又一下,真好看。
钱春邻看着她说,其实,你挺好看的。薛忆梅笑了,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好看了。钱春邻说,以前没发现,现在越来越觉得。薛忆梅说,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从来没觉得我好看过。上学时,你追的都是花瓶,还好,没一个花瓶要你。钱春邻说,也不全是,你就不是。薛忆梅一口茶差点喷出来,你什么时候追过我?钱春邻说,我没说,你就不明白了?薛忆梅说,真不明白。钱春邻说,你啊,神经比男人还大条。薛忆梅说,要不怎么和你做哥们到现在。
坐了一会儿,钱春邻问,老张怎么还没起来?薛忆梅说,不用管他,昨天喝了一天酒。你们两个,真是作死。钱春邻说,老张仗义。薛忆梅说,再仗义,你也不能跟他这么没完没了地喝了。我告诉你,逼急了我跟你翻脸。钱春邻说,别,这个城市我可就你一个朋友了,跟谁翻脸也不能跟你翻脸。
大学毕业,钱春邻和薛忆梅来了岛城。两人以前没什么关系,到岛城完全是凑巧,没一点刻意的成分。那会儿,薛忆梅在机关上班,按部就班,朝九晚五。钱春邻去了一家著名的民企,收入倒是不错,工作强度大得让人崩溃。两人见面,胡吃海喝一顿,全是牢骚。两人都单身,按说谈个恋爱挺好。奇怪的是,虽然几乎每个周末都一起玩儿,却从来没往那个方向想。有几次,两人喝多了,开了房,和衣抱着睡,更深入的却是没有。几次下来,两人都相信,彼此只有做哥们,恋爱确实是谈不起来。后来,薛忆梅就恋爱了,告诉钱春邻,他竟然没当一回事,女孩子吗?到了年龄就该恋爱。直到薛忆梅定下了婚期,钱春邻才见到了她未来的老公张辉民,钱春邻心里那个后悔呀!薛忆梅怎么找了这么个老公?心理落差也太大了,早知道她的眼光这样,那该自己表白?!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攀不上薛忆梅的!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面对钱春邻的惊讶,薛忆梅从他的目光里好像读出了些什么,她极其复杂地剜了他一眼转身而去,从此云淡风轻。
薛忆梅眼光没有错,张辉民虽然看上去老一些,但是人真的很不错,从每一件小事中都能感觉到他的宽厚、忠诚和善良,钱春邻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也庆幸,幸亏给自己留下了这片净土,要不现在的样子,他又能去哪里倾诉?
有一天,薛忆梅对他说,我真要在机关里这么混吃等死吗?钱春邻说,你这应该去和你家老张商量,怎么来问我?信任你、感觉你更靠谱嘛!薛忆梅说。钱春邻露出满足的笑容,说,我觉得没有必要。薛忆梅辞职下海。钱春邻问,为了点钱,真值得成为一台人肉机器吗?薛忆梅说,不值得。钱春邻转身也辞了职,投身岛城刚刚冒头的房地产行业。如此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桌子上摆了一碟瓜子,几块奶油蛋糕。钱春邻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三个未接电话,同一个号码,妻子唐小金的。又看了看微信,觉得闷,就把手机关了。
阳光不错,他想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一天。
这几天,钱春邻睡得不太好,老做梦。昨天,和张辉民喝了一天的酒。晚上还去了酒吧。昨晚,他和张辉民从中午开始喝到了晚上。薛忆梅说,可以了,别喝了。钱春邻说,咱们去酒吧?薛忆梅说,钱春邻,你也不想想多大岁数了?张辉民摆手说,你让他放纵一下。薛忆梅说,真想去?又问张辉民,你也想去?钱春邻说,真想。张辉民说,我得陪他。这对不要脸的!薛忆梅嘴上骂,还是开车把他们送到酒吧门口。钱春邻说,一起去吧。薛忆梅说,我又不喝酒,不愿看你们的模样。钱春邻说,你也喝点儿。张辉民说,她不去就算了。两人进了酒吧,钱春邻又蹦又跳,又喝了两打啤酒,疯了一样。
等他醒来,发现躺在床上。一会儿,薛忆梅进来了,醒了?钱春邻说,我又喝多了。薛忆梅笑了起来,昨晚你那个闹啊,要不要看看,我拍了视频。钱春邻脸一热说,不看,要脸。薛忆梅说,起来活动活动吧,舒服些。
喝了茶,吃了清汤面,钱春邻精神了。薛忆梅说,吃完午饭,我送你回去吧。钱春邻说,你赶我走?薛忆梅说,唐小金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问你是不是在这儿。钱春邻眉头紧了一下问,你怎么说?我当然说在了。她还说什么了?问你什么时候回去?薛忆梅望着钱春邻,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钱春邻说,不回去,你就让我透口气吧。
钱春邻家离薛忆梅家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钱春邻住在半岛湾,里面全是单栋别墅,家家户户都把院子围了起来,种满了各色花木,不少人还养了名贵的宠物狗。买别墅是唐小金的意思,她说,为什么不让自己住得舒服些呢?其实,钱春邻更喜欢住高层,以前的房子他很喜欢。每天早上起来,站在阳台上,看着天际线处的云彩、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他总有莫名的感动。城市独特的红色屋顶,偶尔飞过的鸽群,多么好。唐小金的意思,他没办法。搬进别墅后,一眼看过去,密密麻麻的花木,要不就是坚硬的钢铁围栏,在海边住,竟然看不见蓝色的大海。钱春邻觉得像一条狗,被关在了昂贵的笼子里。
唐小金个子不高,勉强一米六,体重不过四十多公斤。这么矮瘦的一个女人,却像一个钢铁战士。认识唐小金之前,他从来没想过会娶这样一个女人。那时,钱春邻在房地产公司做到了中层,进出也是体体面面的。薛忆梅结婚都两年了,朋友才给钱春邻介绍唐小金,唐小金是土生土长的岛城人,家世不错,祖上出过秀才,还有岛城的名商人,她在实验小学做音乐老师。
唐小金家住在大庙山,那是岛城最原始的城区,老街坊大多搬了出来,把老房子租了出去做了商业门面,一些有特色的建筑被政府收购保留古迹,开放旅游。
唐小金带钱春邻去她家,见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唐小金说,她吃着树上的石榴长大的。还对钱春邻说,等秋天结了石榴,带他回来吃。那天,只有唐小金姥爷姥姥在。钱春邻问,你爸妈呢?唐小金说,他们不住这儿,院子里的石榴树是求多子多福,可到头来妈妈是独女,一家人以前一直住姥姥姥爷家。
见唐小金带男朋友回来,姥姥姥爷分外高兴,留钱春邻吃饭。钱春邻也没推辞,还和姥爷喝了两杯。从家里出来,钱春邻搂着唐小金的腰,到了僻静处想亲她的嘴。唐小金推开他的脸说,你要娶我。钱春邻愣了一下。唐小金说,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来,给我姥爷姥姥看过,那就算是定了。钱春邻说,娶,当然娶。唐小金矮瘦归矮瘦,长得还不错,让钱春邻意外的是她居然有一对不小的乳房。结婚前,两人约会,再晚唐小金也要回家。可钱春邻的欲望蓬蓬勃勃。他带唐小金去他的公寓,想留她过夜,唐小金一听疯了一样捶打他,一副拼死反抗的样子。钱春邻吓坏了。等唐小金正常了,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了?唐小金说,对不起,我不想。钱春邻说,我们谈恋爱啊,这有什么呢?唐小金说,我也知道没什么,还是不行。钱春邻说,我娶你。唐小金说,等我们结婚了,你想怎样,都随你。钱春邻只好收手了,亲密点到即止。
把这些事说给薛忆梅听,她先是大笑,说,也挺好的,女孩子保守点没什么不好。钱春邻说,她是不是不爱我?她都二十六岁了,我就不信她没和别的男人睡过。薛忆梅说,钱春邻,你这么猥琐,有意思吗?
结婚那天,钱春邻喝多了,等闹洞房的人散了,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隐约记得唐小金帮他冲了个澡,擦干身子,把他扶上床。钱春邻努力不要睡去,唐小金还没上床,他要是睡着了,也太不尊重她了。他揉眼睛,掐大腿,使劲儿揉太阳穴,甚至还咬了两次舌头。唐小金终于上床了,关了床头灯。钱春邻伸手抱住她,她的身体微微发抖——他想爬起来,可脑子一万多颗金星在闪烁,只好对唐小金说,对不起,我喝得太多了。唐小金抱住了他,没事,挺好的。
结婚后,他仿佛成了家里的局外人。家里,规矩永远清晰有条理,所有东西都在固定的位置上,一厘米都不能挪动。他进门要换一双拖鞋,进卧室要换另一双拖鞋。如果去厨房,还要换一双拖鞋,睡衣仅限从浴室到卧室。以前钱春邻喜欢做饭。婚后,却被唐小金赶出了厨房。她说,你把厨房弄得太乱了。看过唐小金做完饭的厨房,他难以相信这里刚刚做完饭,干净整洁得像是没有人动过。再就是,唐小金是音乐老师,自然喜欢音乐,进门后,就播放轻柔的小夜曲,在流淌的音乐里营造出温柔浪漫的气氛。短短的兩三个月,他享受过这种感觉。两三个月之后,当唐小金在厨房做饭,他的茶杯放在茶几固定的位置上,他像个客人一样坐在沙发上。听着舒缓和谐的小夜曲。他想不明白,这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吗?
在薛忆梅家里,他和张辉民抽烟,喝酒。薛忆梅从来不会说,你把茶杯放好。钱春邻,拖鞋拖鞋,换拖鞋。钱春邻,你把你的衣服挂好行不行?他对薛忆梅说,唐小金怕是有强迫症吧?薛忆梅说,哪有那么夸张,小金爱干净,还勤劳,又浪漫,你一回家做个甩手掌柜多舒服,张辉民羡慕死你了。钱春邻说,你是没有看到。
钱春邻想请薛忆梅两口子来家里吃饭。唐小金说,好啊。钱春邻说,要不要准备点东西?唐小金说,你不用管,我来做就好了,一定丰盛。
周五晚上,钱春邻坐在客厅,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等着薛忆梅和张辉民夫妇的到来。门铃响了,正准备去开门,唐小金跳起来说,我去我去。薛忆梅和张辉民一进门,唐小金利索地把两双拖鞋摆在了他们面前。到客厅坐下了,倒上茶水,唐小金去厨房做菜。薛忆梅说,要不要我帮忙?唐小金说,你们先聊会儿,我很快就好了。说罢,进了厨房,随手把门也关上了。张辉民看着唐小金,对钱春邻说,你这也太享福了,地主老财怕也不会比这好了。三人围着茶几喝茶聊天,聊了一会儿,张辉民想抽烟,问,你家有烟灰缸没?钱春邻朝四周看了看,他家没有烟灰缸。唐小金受不了烟味儿。薛忆梅白了张辉民一眼说,抽什么抽?张辉民把烟塞回去,也是,不抽了。菜做好了,薛忆梅想去帮忙,钱春邻说,你坐着吧,一会儿上桌就行,她都不让我动手。
唐小金招呼他们过去吃饭,钱春邻去酒柜拿了两瓶红酒。到餐厅一看,脸上有点挂不住,桌子上摆的一次性碗筷,喝酒的杯子也是纸杯。唐小金转过脸对薛忆梅说,也没有问过你们,不知道菜合不合胃口?薛忆梅说,你看这一桌子硬菜,你这手艺——以后老张要骂我虐待他了。
唐小金做了八个菜,对虾、螃蟹、鲍鱼都有,确实丰盛。钱春邻想发火,他拿起筷子敲了敲纸杯说,你看看,这是些什么玩意儿?喝酒听不到响,喝不出感觉来。他让唐小金去拿几个红酒杯,唐小金像是没听到一样。薛忆梅说,好了好了,你就别瞎挑剔了,纸杯挺好啊。
四个人拿着纸杯喝红酒,有股莫名其妙的别扭感,张辉民讲了好几个笑话,想活跃下气氛,钱春邻压住情绪,努力地配合他。唐小金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他们说话,偶尔也插一两句,纯属礼貌应酬。薛忆梅倒是神情自若,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薛忆梅和张辉民刚走,唐小金迅速拿出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收拾了餐桌。走到门口,她停了下来,钱春邻看到她把薛忆梅和张辉民穿过的拖鞋扔进了塑料袋。此刻,那低缓悠扬的小夜曲竟然一刻也没有停。
临睡前,钱春邻对正在梳妆台前卸妆的唐小金说,为什么?唐小金扭过头,什么为什么?钱春邻说,你知道我说什么。唐小金说,我不知道。钱春邻说,我朋友到家里来吃饭,你摆出一次性碗筷,什么意思?唐小金说,没什么意思,干净卫生,收拾起来也方便。钱春邻说,你这样非常不礼貌。
钱春邻对薛忆梅说,你知道吗?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请人到我家吃过饭,太他妈烦人了,丢不起那个人,她快把我给逼疯了。
唐小金一直对钱春邻说,她想去欧洲。等到孩子上小学有时间了,唐小金开始筹划她梦想已久的欧洲之旅。一切准备妥当,飞机飞行在亚欧大陆上空,唐小金靠在钱春邻的肩上,他们回想了往事,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周围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让机舱有了国际化的氛围。在这微妙的气氛中,爱情探出头来,他们甚至还忘情地亲了嘴。唐小金说,有些东西你不喜欢,我想过要克服,也试过,可我难过死了。钱春邻抚摸着唐小金说,没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在讨论给朋友们带礼物时,唐小金掏出手机,写了礼物清单。她把手机递给钱春邻说,你看看行不行?扫了一眼,钱春邻说,挺好的,你高兴就行。给薛忆梅带瓶香水吧,她平时用香水的。钱春邻说完,唐小金的脸色变了,说,为什么要给她带香水?钱春邻说,在岛城就这么个同学,平时也玩得挺好的。唐小金在手机上补了一行字。
过了一会儿,唐小金突然对钱春邻说,你俩肯定有事。钱春邻哭笑不得,你瞎说什么,没有的事。唐小金说,我是女人,你骗不了我的直觉,你们让我恶心。钱春邻急了,我们俩要是真有什么事儿,还轮得到你。唐小金盯着钱春邻说,你知道吗?这才是最让人恶心的。你觉得配不上人家,人家不要你,你才娶了我。钱春邻扭过头说,我不和你争论这么无聊的问题。唐小金黑下脸说,不争论就是承认了,难道我赶不上薛忆梅吗?真恶心!
等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钱春邻心情糟透了,他甚至想马上买张机票返回去,只想离唐小金远远的,越远越好——在欧洲的半个月,钱春邻跟在唐小金的后面,手里提着各种各样的袋子,像个跟班的木偶。
那些天,他和唐小金话说得很少。在德国的一天晚上,不到八点。唐小金突然说,我们找个地方喝点酒吧?钱春邻抬头看了唐小金一眼说,喝酒?唐小金说,想喝点儿。唐小金说,去喝点啤酒,都说德国的啤酒好。他们去了九楼的酒吧,酒吧里多是外国人,还有几对中国情侣。喝了两杯,唐小金对钱春邻说,我并不在意你的过去,真的,一点也不在意。钱春邻说,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是同学,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你说我把她当妹妹也好,当哥们也好,反正是活成亲人了。唐小金喝了满满一杯说,你从来没有尝试理解我的痛苦,我也不指望你理解。
前几天,他们在奥地利,钱春邻临时起意,去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之前,他并不知道这场音乐会,是朋友临时告诉他,钱春邻,多少年才有一次的演出,这么有名的乐团,我都想买张机票飞过来。你一定要去听!朋友是个拉小提琴的,说这话算不上夸张。钱春邻虽不太懂交响乐,但唐小金懂啊,兴趣也已经培养出来了。他讨好唐小金说,明天我们去金色大厅听音乐吧,难得碰上的演出。意外的是唐小金竟没有感到惊喜,甚至没有兴奋,钱春邻惊呆了,这不是她最热爱的音乐嘛?!第二天,金色大厅座无虚席,每个人都很投入,看到一半,唐小金说,你听,我出去一下。钱春邻以为她去卫生间,便没有在意,谁知,直到音乐会结束,也没见她的影子。
钱春邻出来,给她打电话,关机。钱春邻慌了,再打,还是关机。在音乐厅周围找了一圈,钱春邻要疯掉了。他赶紧回了酒店,房间里没人,又去问前台,前台告诉他,唐小金没回来。钱春邻在房间里坐立不安,他甚至想要报警。等到晚上九点,唐小金回来了。一见到她,钱春邻恨不得把手机砸过去。他忍住问,你去哪儿了?唐小金答得轻描淡写,我没什么兴趣,出去逛了逛。钱春邻说,你音乐老师对音乐没兴趣?你不是每天都在家里放音乐吗?早习惯了,沒什么兴趣。唐小金依然很漠然。那你为什么关机?唐小金说,哦,没什么,我想安静一会儿。钱春邻咬牙切齿地说,你他妈的就不怕我担心吗?唐小金挑衅似的说,你会担心?钱春邻摇摇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好了,算我自作多情。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你一定要这么闹吗?钱春邻说。唐小金喝了口啤酒,钱春邻,我没闹,是你坏了规矩。钱春邻说,我怎么坏规矩了?听交响乐,我不是要讨你欢心吗?唐小金说,我们商量好了行程,那天应该是你陪我逛街的,结果,你去听音乐了。钱春邻说,就不能灵活一点,也就几个小时时间,调整一下不就行了?唐小金说,不行,我不喜欢任何不确定的东西。钱春邻没再说话。他想起了家里茶杯的位置,牙刷的位置,还有床上他枕头的位置。
一朵金桂花落在水里,两只红黄色的锦鲤游过来,撕咬着在争抢。水面荡起几串波纹,随之又恢复平静。薛忆梅坐在钱春邻对面,喝了口茶说,算了,这事儿你都说过好几遍了。钱春邻说,她是不是过分了?薛忆梅说,是,她过分了,她不知道你担心她。但你这次又跑出来三天了。钱春邻说,你怕是都烦我了。薛忆梅笑了起来,我倒是习惯了,自从你结婚后,你哪个月不到我这儿住两天,你把我这儿当避难所了。钱春邻说,谁让你是我哥们。薛忆梅说,我不当你哥们,隔三岔五,除了老张,还得伺候你。还好我家老张知道我是清白的,不然我怕活不到今天。
钱春邻第一次到薛忆梅家过夜,大概是结婚半年后。薛忆梅结婚三年多点,孩子刚两岁。大半夜,薛忆梅手机调的震动,怕吵到孩子。等她拿起电话,看到八个未接电话,都是钱春邻的。薛忆梅睡意蒙眬,不耐烦地说,你干嘛?大半夜的,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手机里静了一下,接着听到钱春邻在哭。他把薛忆梅吓到了,赶紧问,你干嘛,怎么了?钱春邻说,我他妈想死。薛忆梅赶紧坐起身,把张辉民摇醒,穿着拖鞋去了客厅。她说,你怎么了?钱春邻只是哭。薛忆梅问,你在哪儿?钱春邻说,我不知道。挂了电话,薛忆梅对张辉民说,我不放心,你去找找钱春邻。张辉民不乐意,还是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张辉民领着钱春邻回来了,他喝醉了,身上乱七八糟的一团。那时住房紧,房子面积小,张辉民把钱春邻架到孩子的床上,又把孩子抱到他们床上,孩子半夜被弄醒又哭又闹,好不容易安顿好,他对薛忆梅说,钱春邻命好,还有你这么个同学,要是没你这个同学,怕是死了都没人管。薛忆梅问,怎么了?张辉民说,你知道我在哪儿找到他的吗?薛忆梅说,我怎么知道。张辉民说,马路中间隔离带上,只见他手里死死拿着个手机,身上钱包、皮带、鞋子什么都不见了。薛忆梅说,先不管了,睡吧。
一直睡到下午两点,钱春邻才醒。洗过澡,薛忆梅找了张辉民的衣服给他,怎么回事?钱春邻说,喝多了。薛忆梅说,知道你喝多了,为什么?钱春邻说,不想说。这是第一次。接着第二次,第三次——薛忆梅恼了,钱春邻,你别一喝多就发酒疯,要发酒疯你朝唐小金发,我又不是你老婆。对钱春邻的行为,张辉民也有意见。一个男人,深更半夜喝多了老给自己老婆打电话,是个什么意思?他倒不是怀疑两人之间的关系,相信他们是清白的,问题是烦人,睡得好好的,半夜被摇醒去接一个醉鬼,换了谁会高兴?薛忆梅说,钱春邻,你要是没个说法,以后别到我家来了。钱春邻说了。薛忆梅和张辉民感到匪夷所思,就这点破事儿,闹成这样?钱春邻说,你们真的不懂,要是你们家里到处都是规矩,都是线条,你也过不下去。说的次数多了,薛忆梅也烦了,真过不下去,离婚啊,一了百了。钱春邻说,可是,她也没做错什么啊。薛忆梅说,你这么纠结,我们也帮不了你。钱春邻说,也不指望你们帮,偶尔收留我就行。刚开始,钱春邻到薛忆梅家,唐小金还打电话问问。到后来,电话也少了。多半情况下,钱春邻在薛忆梅家待一天,缓过劲儿来,还得乖乖回去。
薛忆梅夫妇对钱春邻的状态从反感到怜惜,再后来,习惯了,要是钱春邻有一两个月没来住,张辉民反倒不习惯了,他们不会有事吧?薛忆梅宽心些,能有什么事儿?谁死了,钱春邻也死不了。薛忆梅唯一反感的是,张辉民以前不爱喝酒,在钱春邻的影响下,酒量越来越大。钱春邻不再是他的对手,他成了酒鬼。
我真的想清楚了。钱春邻说,这次得离了,再这么下去,我会疯掉的。等离了,也就不会烦你了。薛忆梅说,我无所谓,你这么闹腾多少年了?你说要离婚多少次了?薛忆梅说,吃过晚饭,回去吧。她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又圆又红。唐小金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薛忆梅说,你知道她说什么了?钱春邻说,我怎么知道她说什么了。薛忆梅说,她说,梅姐,这么多年,麻烦你了。钱春邻说,我不信。薛忆梅说,我也有点意外,以前没这么客气的。钱春邻“哼”了一声。薛忆梅说,你这个混蛋,你不知道?我为你挨了唐小金多少骂,好像我是个狐狸精似的。不都过去了吗,还说?有什么意思。钱春邻说,她现在可能也怕我死了。薛憶梅说,怕没人赚钱吧。钱春邻摇摇头说,你还真是想错了,她对钱没什么要求。那晚上她还起来洗手吗?不光洗手,还擦桌子。想了想,又问,你们还一起睡吗?薛忆梅说完,钱春邻笑了,你觉得可能吗?
唐小金每次和钱春邻亲热完,都会跑到洗手间狂吐,比钱春邻喝醉了吐得还厉害。吐完,她哭着说,我不是嫌弃你,真不是,我实在受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吐。分床睡后,唐小金胖了一些。从不过问他的事情,但是他要保证周日必须回家,在家吃晚饭,宁可把苦胆水吐出来,也要和他在一起。
天色暗了,金桂花的影子影影绰绰,他实在爱薛忆梅院子里的这棵金桂花。当初他对薛忆梅说,你种棵金桂花吧,好看。薛忆梅说,我不喜欢桂花,要栀子花。钱春邻说,金桂花比栀子花内涵多得多了。薛忆梅说,种不起。钱春邻说,我送给你。他本来是想在自家院子种的,唐小金不肯,她说,我早就设计好了,该种什么花也定了。钱春邻懒得再说话了,他怕自己会爆炸。只好把愿望搬到了薛忆梅这里。种上金桂,在这里享受这浓郁的花香!
晚饭时间到了,薛忆梅叫了外卖。菜摆上桌,她笑着说,你晚饭要在这里吃不成了。怎么啦?你赶我走?钱春邻说。你的手机关着,唐小金又来电话了,她说你周日晚上都是回家吃饭的,她在家等你。薛忆梅说。钱春邻的目光突然有些漠然。张辉民特意叫了一罐四十斤的扎啤。钱春邻看着扎啤说,要不不喝了?薛忆梅瞟了他一眼,我就不喜欢你这一点,什么叫要不,不喝就不喝,果断点,不就是唐小金来电话了吗!刚说完,薛忆梅的手机又响了,钱春邻的身体突然一抖,扭头看着薛忆梅,果然是唐小金的电话,张辉民倒酒的手一下子僵在了半空,说,要不告诉唐小金,就说喝完回去,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吗。薛忆梅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钱春邻,就这么说吗?
钱春邻叹了口气,把张辉民倒了半杯扎啤的酒杯拿过来,仰头喝下去,摇了摇头说,我打车回去吧。你不是不走了吗?薛忆梅故意激他。钱春邻回头又望了一眼一桌一动没动的饭菜,无奈地说,你俩吃吧,连明天的早饭也够了。起身吸了一口浓郁的花香,感到有些窒息,但他很快消化了下去,摇摇晃晃地往外走去。这一桶扎啤我也喝不了啊!张辉民喊。你让他走吧,还不知足,这是唐小金对他的柔情。薛忆梅打断他,刚说完,薛忆梅的电话又响了。钱春邻重重地叹口气,她是认真地在等我吃饭,日子还他妈的不过了吗?头也没回,只是在空中无力地摆了摆手。
【作者简介】娄光,原名娄法矩,山东莱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小说月刊》《短篇小说》《海燕》《芳草》《朔方》《当代小说》《芒种》《山东文学》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