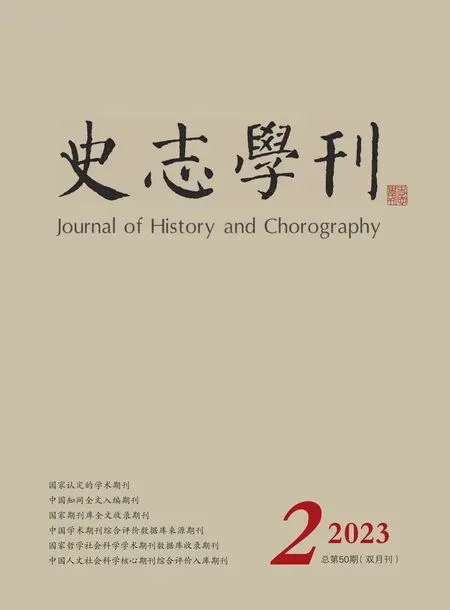东学西渐:腓尼基人对希腊城邦形成的影响
黄晓博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古希腊文明是一种经典的、纯粹的原生文明,它所代表的以自由、民主、理性等特征为基础的古代希腊社会是后世欧洲的典范和模板,这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常识、颠扑不破的真理。进入20世纪,赛勒斯·戈尔登(Cyrus H.Gordon)、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瓦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kert)、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等一批学者,结合考古发掘、文献考证、词源分析、理论批判的方法,向这一范式发起了挑战[1]Cyrus H.Gordon,The Common Background of Greek and Hebrew Civilizations[M],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1965; 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M].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John Boardman,“Al Mina and History”[J].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9,1990,pp.169-190; Walter Burkert,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M].translated by Margaret E.Pinder and Walter Burker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M].vol.I,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 Martin West,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默里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Orientalizing Period)概念,并以希腊艺术领域的近东影响为出发点,进一步考察了希腊在宗教、文字方面对近东文明的借鉴[2]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M].第二版序言:74-93.李永斌进一步将艺术领域的“东方化”一词的提出前推到1870年的维也纳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孔兹(Alexander Conze).参见:李永斌.希腊城邦兴起的几种理论与转向[J].世界历史评论,2019,(2):14.。布尔克特通过在工匠技术和文字、巫术和医学、文学史诗等方面的严密考证,详细阐释了近东文明对希腊的全面影响,乃至认为古风时代的希腊文化发生了一场“东方化革命”(Orientalizing Revolution)[1]Walter Burkert,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M].translated by Margaret E.Pinder and Walter Burker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8)。这些学者的工作都指向一个事实:古希腊文明并不像传统古典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完全原生的文明,相反,它在形成过程中汲取了地中海周围各文明的诸多养分,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产物。
对古希腊文明纯粹性和经典性更为尖锐的批判来自伯纳尔。他分析了意识形态因素对认识理解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总结出了希腊历史的两种模式——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雅利安模式强调希腊文明本质上的欧洲性或雅利安性,近现代以来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主流认知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2]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M].vol.I.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P1-38)。伯纳尔认为古希腊人对自身文明的看法是与现代古典学者不同的,他们并没有避讳自己对近东文明的学习和模仿,进而提出了古希腊文明亚非起源说[2](P1,120)。在伯纳尔看来,基督教对埃及的敌意、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印欧语系的确立促成了强调希腊文化纯洁性和欧洲性的雅利安模式的建立[2](P439-443)。黄洋也认为古希腊文明的纯粹性和经典性实际上是一场肇始于18 世纪德国的古典希腊理想化运动的结果,并针对伯纳尔所说的古代模式向雅利安模式转变的原因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在黄洋看来,“欧洲的现代性建构及其相应的起源神话的修订,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因素”[3]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J].中国社会科学,2009,(2).(P53-63,66)。陈恒、李永斌等学者也对古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考察[4]陈恒.略论古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04-109;李永斌.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图景[J].历史研究.2018,(6):105-119.。这些对古希腊文明及人们对其认知模式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古代希腊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更加凸显了文明交流的悠久历史和积极意义。
不过,学者们对近东文明影响古希腊文明的考察和反思大多集中在艺术、文字、宗教、建筑、经济等领域,对城邦政治方面的影响涉及不多。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曾简单提及,“西亚的腓尼基人,不乏可与古风和古典时代希腊的自治城邦相媲美的东西。……但是,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几乎还未起步。”[5]Simon Hornblower,“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Greece”[A].in John Dunn,ed.,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C].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2.此类研究的缺乏一方面是因为关于近东地区城邦政治的代表腓尼基城邦的史料过少,且零散分布在与其有交往的其他国家的文字记载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城邦政治一直是古典学者最引以为荣的古希腊创造,他们最不愿意承认古希腊在这方面也受到近东影响,如果说他们可以勉强承认近东文明对古希腊其他方面的影响,以城邦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层面的影响则是他们绝难接受的。本文尝试分析城邦政治在腓尼基的发展,并对比考察迦太基与斯巴达政制的异同,以论证古风时期希腊地区城邦制度的建立可能受到了腓尼基人的熏陶。
一、腓尼基人的城邦政治实验
腓尼基人(Phoenician)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版图包括自阿瓦德(Arvad)到卡尔迈勒山脉(Mount Carmel)之间的沿海平原地区,大致与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沿海地带相当[1]Mari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M].translated by Mary Turd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5)。与希腊世界的人们更经常地称呼自己是雅典人、斯巴达人等一样,腓尼基人更愿意称自己是推罗人、西顿人等。即使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们也通常称自己为“Can’ani”或“Canaanites”(二者的意思都是迦南人),而不是“Phoinikes”(意思是腓尼基人,如今表示腓尼基人的英文单词Phoenician 便由此词演变而来),即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2]Mari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M].translated by Mary Turd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8-10.关于“Phoenician”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有多种推测:一种是它来源于希腊语“Phoinos”,这是一个带着印欧语词根的单词,表示“红色”“血液”“用血染”“死亡”或“犯罪”。后来人们将这个词与紫色织物的制造和亚洲人的深色肤色联系起来,因为腓尼基人提炼出了紫色,并且将紫色织物销往各地。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开始把这一地区的居民称为“Phoinikes”,大多数现代学者支持这种说法。另一种是它的起源与同名英雄Phoinix有关,此人在神话中被认为是发明了紫色染料的英雄。参见Michael C.Astour,“The Origin of the Terms ‘Canaan,’ ‘Phoenician,’ and ‘Purple’”[J].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24,no.4,1965,pp.346-350; Mari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M].pp.5-7.。迦南人才是他们共有的可与希腊人相对应的称号。腓尼基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城市国家,如推罗(Tyre)、西顿(Sidon)、比布罗斯(Byblos)、阿卡(Acre)、阿瓦德等等,他们的文明是以这些散落的独立城市国家为基础的。这些国家大都以贸易和手工制造业为生,对海洋有着极大的控制力。自公元前16 世纪中叶起,腓尼基人便开始在地中海地区编织一个西至塔特苏斯(Tartessus)、东至亚美尼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希罗多德甚至认为他们曾进行过环绕整个非洲大陆的航行[3]Ezekiel 27: 12-24; 本文所引用的圣经文本,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NIV Holy Bible; Herodotus,Histories[M].IV,42,translated by 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腓尼基人在贸易航线附近建立了一系列商站和殖民地,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位于北非突尼斯海岸的迦太基(Carthage)。
审视腓尼基人的城邦政治实验,需要考察与城邦起源密切相关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即奴隶制经济、土地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奴隶制经济是城邦产生的基础,奴隶在社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后,公民才能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政治生活。马克思认为“亚洲式社会”虽然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但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部落共同体形式,它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由国家直接征取,所以整个社会实质上是停滞的。而更为先进的奴隶社会里有私有土地,土地所有者成为国家和更低阶层之间的中间人,城市往往由他们进行统治,这样的社会是有活力的。
虽然腓尼基在地理上位于通常所说的东方地区,但伯纳尔认为,以马克思的“亚洲式社会”和“欧洲式社会”(即奴隶社会)的划分标准,将腓尼基的社会形态判定为“亚洲式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是不合适的,他更支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奴隶社会肯定是“海岸式的”(coastal),并且区别不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而是在陆生和水生社会之间[1]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M].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351; Max Weber,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M],translated by R.I.Frank,London: Verso,1998,pp.48,155-161.。因为没有大宗粮食运输的便利,专业化的制造业经济便会因为食物不足而举步维艰。并且,大海还为奴隶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便利的条件。在海岸社会中,富人和贵族垄断了航线,奴隶被装船穿越大海,无论女奴还是男奴都失去了逃跑能力,他们的选择只有接受奴役、自杀、自杀性暴动或者混入遭受排斥的蛮族人群体。大部分奴隶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奴隶主不仅可以使用女性和丧失部分能力的男性奴隶,而且可以使用具备强劲体力的完整男奴[2]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M].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351-352)。
腓尼基无疑就是这样的奴隶社会,它的自然地理条件是海岸式的,经济模式也是海洋性的,它的社会经济对海洋的依赖程度很高。腓尼基的奴隶通常都是劫掠而来的或者在国外购买的外国人。《奥德赛》中提到一个腓尼基人拐骗了奥德修斯,并试图将其卖掉获利[3]Homer,Odyssey[M].14,288-297,translated by A.T.Murray,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19.。希罗多德的《历史》提到,进行航海贸易的腓尼基人趁着希腊妇女挑选货物的时候,掠走了伊娥和其他一些妇女[4]Herodotus,Histories[M].I,1,translated by 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不仅希腊人的记载中有多处提到腓尼基的奴役活动,以色列人的文献中也常常提到腓尼基人的奴役。《阿摩司书》中耶和华谴责推罗不顾兄弟盟约,将以色列避难者出售给以多姆(Edom)[5]Amos 1: 9.。《约珥书》中谴责推罗人、西顿人等腓尼基人将犹大人、耶路撒冷人卖给了希腊人[6]Joel 3: 4-6.。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至少在邻人眼里腓尼基人与奴隶活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从侧面反映了腓尼基地区奴隶制的发展程度。伯纳尔认为,腓尼基人的奴役活动是一种“商业奴役”(commercial slavery),并且即使不是从公元前11 世纪开始,那么从公元前10 世纪开始,这种商业奴役就主导了腓尼基的生产关系,比希腊地区商业奴役的盛行要早得多[7]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M].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55-356.古代奴隶大致可分为动产奴隶、来自特定地域的奴隶族群(类似黑劳士的奴隶)和债务奴隶三种。芬利(M.I.Finley)对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度和主奴关系进行过详细分析。参见:芬利.古代经济[M].黄洋译.商务印书馆,2020:76-105.。
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腓尼基地区已经广泛建立起了家庭土地所有制,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土地财产逐渐凡俗化,直至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的东西。《圣经》记载,一位妇女“考虑了一块地,买了下来,用她的收入栽种了一片葡萄园”[8]Proverbs 31: 16.。这似乎表明,到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土地在海岸地区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从地理条件来看,腓尼基地区极其缺乏可耕种的土地,许多海岸城市都以自己的木材和精巧物品换取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如海勒姆(Hiram)就曾要求所罗门王供给谷物以回报自己提供的松柏[1]Josephus,Jewish Antiqutties[M].VIII,53-55,translated by H.St.J.Thackeray and Ralph Marcu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土地这样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也体现了腓尼基经济的商业化程度。
公元前12 世纪末期海上民族入侵之后,许多旧的统治势力彻底瓦解了,如赫梯帝国和乌加里特等,亚述和埃及则元气大伤,而腓尼基城邦则迎来了近三个世纪的黄金时代。大约从公元前1100 年到前750 年,腓尼基城市在没有严重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维持了政治独立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腓尼基人成为了地中海地区奢侈品、金属和粮食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航海之名、商业之名在这一地区如雷贯耳,推罗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腓尼基诸城市的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逐渐组成了一个个以大家族为核心,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集团”。这些家族的首领们被《圣经》称为“商业王子”[2]Isaiah,23: 2-8.。这些大人物构成了腓尼基城邦政治中的重要一极。外部威胁或外部压力的消失,不仅促进了腓尼基经济的繁荣与扩张,还为它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这也是城邦政治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铁器的使用(赫梯帝国灭亡后,冶铁技术得以向外扩散)。与旧的宫殿经济所需的统一的全国性经济结构不同,铁器的使用极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得分散的地方性经济可以不断发展,而无需依赖青铜时代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3]Ю.В.安德列耶夫.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东方城市国家[A]//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C].时事出版社,1985.(P61-62)。
通过考察腓尼基地区的经济社会背景,可以发现此区域具备了城邦政治产生的基础条件,并且不提此时尚处于黑暗时代的希腊,便是与古典时期的希腊相比,腓尼基地区的经济结构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商品经济或商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要高于希腊世界。
一些零散的证据也体现了腓尼基的城邦政治特征。1887 年埃及当地人在古都阿玛那(Tell el-Amarna)无意中发现了三百余块泥板文书,后经学者系统发掘、整理、释读后确认这些文书大多是公元前14 世纪中晚期的一些外交书信,展示了埃赫那吞(Akhenaten)时代埃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4]William 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M].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xiii.下文提到的《阿玛那书信》均依国际惯例标注其简称EA,其后的数字为书信编号和行数。。《阿玛那书信》(The Amarna Letter/El-Amarna,简称EA)中多处提及或暗示了腓尼基城市中巨头/长老会议的存在。一封给埃及国王的效忠信中写道:“我的主人,从一开始我就想为国王、我的主人服务,但是苏姆尔(Sumur)的巨头们不允许我(这样做)。”[5]EA 157: 9-16.这表明当地统治者在重大决策上会与巨头们磋商,而且他们有很大发言权,甚至可能否定统治者的计划。伊卡塔(Irqata)的长老会议曾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埃及国王致信,并且这封效忠、求援信中丝毫没有提及当地统治者[1]EA 100.莫兰(William L.Moran)认为这是因为伊卡塔的国王之前已被人杀死。参见William 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M].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173,n.6.。图尼普(Tunip)则更进一步,以城市公民的名义向法老写信[2]EA 59: 1-4.,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没有国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20 年[3]EA 59: 13-17,43-46.关于图尼普以城市公民的名义写这封信的缘由,莫兰认为有两种可能:1.图尼普可能与伊卡塔一样,它的国王被杀了,所以没有以国王而是以公民们的名义写信;2.图尼普可能存在“共和”组织,但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参见William 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M].p.131,n.1.笔者倾向第2种观点,但不认为这是一种临时安排。因为图尼普若是专制政体,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即使国王被杀,也应很快有继任者代替,否则肯定会导致内部分歧甚至内乱,影响城邦在错综复杂形势下的腾挪,甚至给城邦带来毁灭性打击。基于同样的理由,无法想象这种公民组成的共和组织仅仅是一种临时安排,换言之,这种共和组织能够在危机时刻发挥权威、接管城邦并有效运行20年,那么它在以往平稳时刻必然也是有极大权力和威信的,否则它是无法承担这样重的历史任务的。。另外一处证据更为明显地表明,部分腓尼基城市是由公民代表组成的协商会议所管理的。一位埃及官员向法老汇报信息的信中提到,“阿瓦德的男人们与西顿的地方官(Zimredda)已经交换了反抗国王的起义誓言,并且他们装备了船只……”[4]EA 149: 54-63.这清晰地显示出阿瓦德此时是由公民统治的。
时间推进到公元前11 世纪,依然能发现这种长老会议存在的迹象。此时期的《温阿蒙报告》(The Report of Wenamun)提到,在应对追索温阿蒙的特克人(Tjeker)时,比布罗斯国王特克巴尔(Tjekerbaal)召集了“议事会”(mw’d),并站在他们正中间,然后开始询问特克人[5]William Kelly Simpson ed.,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3)。约翰·威尔逊(John A.Wilson)对此处的“议事会”一词进行了详细考证,并进一步推测这个议事会可能指的就是《以西结书》中所说的“吉布勒(Gebal)的长者和有智慧的人”[6]John A.Wilson,” The Assembly of a Phoenician City”[J].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4,no.4,1945,p.245; Ezekiel 27:9,此处译文参考了KJV Holly Bible,吉布勒即比布罗斯的别称。国内学者徐昊、吴宇虹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接见特克人的是书吏,而非特克巴尔,并且他们没有译出“mw’d”这个词,而是将特克人置于此词之前,似乎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书吏对特克人下的一个指示,而不是“议事会”。参见:徐昊,吴宇虹.〈温阿蒙历险记〉译注[J].古代文明,2010,(1):28.。
这些证据表明,尽管许多腓尼基城邦都有一个国王,但它们的君主制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国王虽有很大的威信,但并不掌握绝对权力,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更像后世的立宪君主,并且一些城邦是由长老会议或公民进行统治的(至少有时如此)。从整体上看,尽管君主制占多数,但腓尼基人的政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还存在巨头政治(富豪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等政体,而且在某些城市中还有政体更迭变化的情况发生,这与后来希腊世界里的政治状况很相像。
综上,可以看出,腓尼基地区很早便具备了城邦政治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并且残存的零散证据也向我们展示了腓尼基人城邦政治的一些特征和迹象。虽然这里有国王,但他的权力和地位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东方专制国王,在腓尼基城邦中存在着掌握很大权力的长老会议。尽管在希腊世界尚处于不断摸索的黑暗时代之时,腓尼基人的城邦政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古风时期近东文明在政治以外的其他种种方面对希腊世界的熏陶和渗透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承认,但这些只是提供了希腊人在政治方面借鉴腓尼基人经验的可能性,要想进一步证实,需要进行具体的实例考察。
二、迦太基与斯巴达政制的比较
从公元前10 世纪开始,埃及在腓尼基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推罗在艾比巴尔(Abibaal)和海勒姆的带领下逐渐强盛,打破了腓尼基城邦之间的力量平衡。海勒姆向新近崛起的以色列国王大卫示好[1]2 Samuel 5: 3,10-11.,与其结盟,借此获得了极大的利益[2]Josephus,Jewish Antiqutties[M].VIII,57-58,translated by H.St.J.Thackeray and Ralph Marcu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不久,推罗又逐渐渗透控制了另一个腓尼基大邦西顿[3]Mari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M].translated by Mary Turd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37)。公元前9 世纪中期,亚述帝国的势力扩张到海岸地区,腓尼基人为维持脆弱的政治独立,开始向亚述供奉金属原材料、白银和奢侈品等。在亚德尼那利三世(Adad-Ninari III)征服叙利亚北部之后,腓尼基人面临的上贡压力更大了。弗伦肯斯坦因(Susan Frankenstein)就认为,黎凡特人(腓尼基人生活的地区又称黎凡特)向西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是为了争得自身的生存权,而非追求荣耀[4]Susan Frankenstein,“The Phoenicians in the Far West: A Function of Neo-Assyrian Imperialism”[A].in M.T.Larsen ed.,Power and Propaganda: a Symposium On Ancient Empires[C].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1979.(P273)。也正是在这股浪潮中,推罗人在北非海岸建立了殖民城邦迦太基。作为推罗人建立的城邦,迦太基的政治形制想必有着很深的推罗政体印记,在推罗等近东腓尼基城邦政体直接史料缺失的情况下,可以将迦太基的政治形制视作腓尼基城邦政体的一个缩影。
克里特岛上腓尼基人的活动迹象非常明显,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些“飞地”(enclave),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落式社区。例如,在克里特岛南部的孔莫斯(Kommos),人们就发现了腓尼基人特有的三柱风格神殿(Tripillar Shrine)的遗迹[5]Joseph W.Shaw,Maria C.Shaw eds.,Kommos: An Excavation on the South Coast of Crete,vol[M].IV,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1)。同时,德鲁兹(Robert Drews)根据法内尔(L.R.Farnell)分析的斯巴达的戎装阿芙罗蒂特(armed Aphrodite)崇拜与腓尼基人的联系,以及该崇拜起源于塞德拉岛(Cythera)的事实推测,腓尼基人可能在塞德拉也有一个据点[6]Robert Drews,“Phoenicians,Carthage and the Spartan Eunomia”[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0,no.1,1979,p.46; Lewis Richard Farnell,The Cults of the Greek States[M].vol.II,Oxford: Clarendon Press,1896,pp.653-654.。从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区活动的一般目的来看,他们最初来到克里特和斯巴达可能是受到了两地丰富铁矿石的吸引。公元前750 年左右,斯巴达征服了欧罗塔河谷,随后与克里特人和腓尼基人有了联系。也是在这一时期,斯巴达进行了政治改革。它划分了新的部落和选区,建立了包括“国王”(archagetai)在内的三十人长老会议(gerousia),并规定要定期在巴比卡和科纳吉昂之间举行公民大会,表决长老会议提出的议案[1]Plutarch,Lycurgus[M].6,translated by Bernadotte Perrin,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14.。
虽然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对迦太基初建时(公元前9 世纪末)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亚里士多德说过,迦太基有一种良好的宪制,民众都自发地保持着对其宪法体制的忠诚,它不曾出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内乱,也没有出现过僭主[2]Aristotle,Politics[M].1272b24-34,translated by H.Rackha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波利比乌斯(Polybius)也写道:“在我看来,迦太基的宪法就其最鲜明的特点而言,在最初时候已经得到了精心的谋划。”[3]Polybius,The Histories[M].6,51,1,translated by W.R.Paton,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因此,我们可以从后来的迦太基的政治体制中大概了解其建城时的政治设计。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比较过迦太基与斯巴达的政治体制的异同。他认为,迦太基的共餐制度“赫泰瑞昂”(Hetairion)类似于斯巴达的“菲狄提亚”(Phiditia),它的“一百零四人执法官团”(hekaton kai tettaron)类似于斯巴达的“埃伏尔”(ephorois)[4]Aristotle,Politics[M].1272b33-35.translated by H.Rackha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到,迦太基也有与斯巴达相对应的“国王们”(tous Basileis)和“长老”(gerousian),在二者协调一致时,他们可以决定是否把事项提交给人民审议。但是与斯巴达不同的是,在国王和长老们没有达成一致时,迦太基的公民大会也可以直接进行审议[5]Aristotle,Politics[M].1272b37-1273a10.translated by H.Rackha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希腊和拉丁文本中对迦太基主要官员的称谓有basileis,basileis kata nomous,archontes,dictatores,reges,and sufetes(该词也写作suffetes)。德鲁兹认为,尽管古代作家们给出了这些令人困惑的各种头衔,尽管这些执政官的权力范围和任期时长可能受到限制,但我们似乎一直在与一个从最早时候到公元前146 年本质上基本不变的迦太基官职打交道,并且,希腊人称之为basileis的官职实际上就是suffetes[6]Robert Drews,"Phoenicians,Carthage and the Spartan Eunomia"[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0,no.1,1979.(P54)。“Suffetes”一词来自于腓尼基语,字面意思是“法官”,但它的权力远不止司法权,所以将其译为“执政”是较为合适的[7]吴寿彭将该词译为“士师”或“执政”。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P101)。
公元前203 年,面对西庇阿(Scipio)在非洲取得的胜利,迦太基人恐慌不已,“执政们(sufetes)——他们的权威相当于罗马的两执政(consuls)——召集了长老会议”[8]Livy,History of Rome[M],30,7,5,translated by Frank Gardner Moor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李维(Livy)将迦太基的执政比之于罗马的两执政,亚里士多德将其比之于斯巴达的国王,似乎指向了一个事实,即迦太基的执政也是两人。那么迦太基的长老会议有多少人呢?我们需要到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中寻找答案。波利比乌斯曾提到,西庇阿于公元前209 年占领新迦太基时,俘虏中有2 名长老会议(gerousia)成员和15 名元老院(sygkletos)成员[9]Polybius[M].The Histories,10,18,1.translated by W.R.Paton,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公元前149 年,罗马人要求迦太基在30 天内提供300 名人质,这些人必须是元老院和长老会议成员的儿子[10]Polybius[M].The Histories,36,4,6-7,translated by W.R.Paton,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这两个事例似乎表明迦太基有长老会议和元老院两个独立的机构。据李维所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末期,在听到西法克斯(Syphax)被罗马人俘虏后,迦太基人气馁了,再也听不到支持战争的声音了,他们派出了30 名长老向罗马人求和。李维特意对这30 名长老作了解释,强调这30 人组成了他们的主要会议(consilium),对元老院的行动有巨大影响力[1]Livy,History of Rome[M].30,16,2-3.translated by Frank Gardner Moor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将波利比乌斯与李维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李维所说的会议很可能就是波利比乌斯所说的长老会议,那么迦太基的长老会议的成员就应该是30 人。
迦太基与斯巴达不仅在基层结构(共餐制度)、上层组织(长老会议)、最高领导(国王或执政)的体系设置上几乎是一致的,而且在长老会议和执政的人数上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伊索克拉底在《尼科克里斯或塞浦路斯人》(Nicocles or the Cyprians)中所提及的“迦太基人和斯巴达人的统治管理是最好的,在国内他们实行寡头政治,在战场上则接受国王(basileis)的统率”[2]Isocrates,Nicocles[M].24,translated by George Norlin,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28.,就能更真切地了解古希腊人对二者政制的看法。迦太基与斯巴达的城邦政治的相似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德鲁兹甚至认为斯巴达曾经只有一个国王,在模仿学习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时,专门增加了一个国王,以与迦太基的双执政相一致[3]Robert Drews,“Phoenicians,Carthage and the Spartan Eunomia”[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0,no.1,1979.(P52,56-57)。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似乎也有些极端。例如,若是斯巴达如此盲目地照搬迦太基制度,为什么它没有也建立一个较大的元老院呢?为什么它的国王是终身世袭的,而不是像迦太基一样有任期限制呢?但是,这些细小的差异并不足以否定斯巴达借鉴迦太基政制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迦太基建城初期制度的认知大多是根据公元前4 世纪以后的记载倒推而来的,再加上迦太基与罗马漫长的斗争历史,也许可以推测迦太基最初是没有元老院的,这一机构是后期增补上的。同样的,斯巴达的国王没有王宫,在公共食堂就餐,且受到人民的严格监督,这样浓厚的平民色彩使得他们与迦太基的执政者们没有太大分别,世袭与否似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许只是政治改革中对斯巴达传统的一种妥协。
迦太基与斯巴达政制的比较表明,腓尼基人对斯巴达制度的影响是难以忽视的。从这一时期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社会发展的水平来看,腓尼基人的文明显然处于更高、更优越的地位,再结合他们在文字、艺术、手工技术等方面对希腊人的启发和帮助,很难相信腓尼基人在建立迦太基时借鉴了斯巴达或克里特的政治形式,相反的政治制度传播方向应该才是历史的真实。正如近现代以来西欧文明向世界各地的扩散一样,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与工业革命和科学的传播路径是一致的,不会是东方学习了西方的科技而教授了西方民主政治。
结 语
受益于两河流域、埃及、小亚文明的浸染,再加上自身独特社会经济结构的助力,腓尼基人很早便开始了城邦政治的实验。作为古代航海事业的重要开拓者,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周围不断探索,编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伴随着贸易的开展,他们不仅将字母、艺术、宗教等方面的近东成就带到了希腊,也将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安排传播到了希腊世界。通过迦太基与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斯巴达对腓尼基人政治形式的借鉴,并且这种借鉴的程度是很深的。认为希腊人在城邦政治方面学习了腓尼基人,并不意味着这种学习是一种直接的抄袭或机械的模仿,它的表现形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是全盘的系统性复制,更大的可能是局部的、有选择的借鉴,这也增大了我们发现这种迹象的难度。希腊人对腓尼基人城邦政治的借鉴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学习,从此后希腊城邦政治波澜壮阔的发展和因此而产生的文化(文学、哲学、艺术等)繁荣中,可以看到希腊人对城邦政治的新的贡献和创造远远超过了腓尼基人。希腊世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实验,希腊式的城邦政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过不断的迭代变革取得了很多成就,完全可以说是希腊人将这一政治形式的发展推向了巅峰,从而成为了它的典型代表。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将城邦政治视为希腊人的一种独立创造,而忽视希腊人在城邦形成初期对近东文明的借鉴。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极端匮乏,目前所发现的腓尼基人影响希腊城邦政治形成的证据还不多,不过,相信随着历史文献和考古的新发现,会有更多、更丰富的证据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