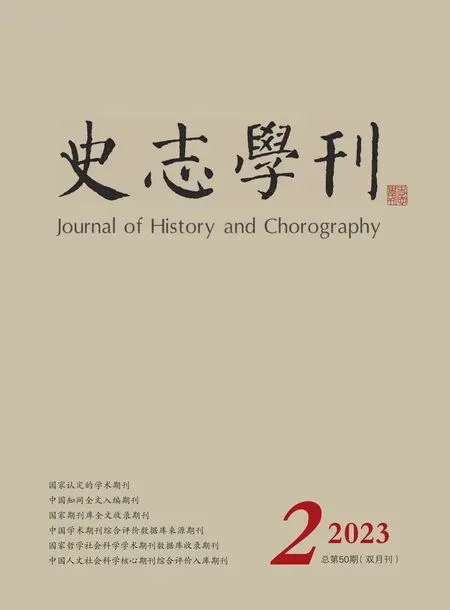以木为媒: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交往中的木刻
王海兵 王 挺
(1.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木刻是以木材为主要载体,通过刻画的方式来记录事情和表达思想的一种记事方法。广义上的木刻,其所使用的材料还可包括竹片、金属物、骨头等。木刻与标记、结绳等均属于符号记事的范畴[1]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P347)。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木刻形制繁多,流行范围甚广,其北至松潘,西南至中缅边境,南至云南腾冲地方,东至湖南省西、南两面,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南、广西、广东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涵盖汉藏语系之苗瑶、壮侗、藏缅语族以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诸民族。目前学界对西南少数民族木刻习俗关注较少,且主要侧重于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2]相关研究主要有: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王明东.彝族木刻的文化解释[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2);罗江文.谈云南少数民族记事木刻的文字学意义[J].民族艺术研究,2004,(2);邓章应.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D].华东师范大学,2007.。刻木为信是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曾广泛应用于贸易、借贷、集会、婚姻、诉讼、军事、宗教等领域。本文拟以木刻为切入点,论述西南少数民族内部社会交往中木刻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同时在族际关系的视域下,进一步考察木刻在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功能,试图从内外两个层面揭示木刻在建构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秩序以及规范社会关系、族际交往等方面的价值。
一、木刻与西南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
西南民族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字社会。彝族的“爨字为纳酋阿丁所撰,字如蝌蚪,凡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名之曰韪书”[1](清)李焜纂修.乾隆蒙自县志(卷五)[M].乾隆五十六年抄本.。其创制的时间,学界有不同意见,但不晚于唐代[2]王元鹿.中国南方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一些瓶颈[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5).。壮族的方块古壮字创制亦较早,有学者认为可能产生于唐代。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区皆然。”该书所例举的文字,与今天所见的方块壮字基本相同[3]李乐毅.方块壮字与喃字的比较研究[J].民族语文,1987,(4).。其主体文字是由汉字传播造成的。部分方块古壮字是壮族人民自造的符号,字数有限[4]王元鹿.壮族古文字的研究价值与待解谜团[J].龙岩学院学报,2014,(3).。“除了纳西族外,类似东巴文的象形文字还存在于摩梭人、耳苏人、纳木依人以及彝族、羌族、普米族和藏族之中,并形成了一个民族象形文字链”[5]宋兆麟.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探析[J].民族艺术,2010,(3).。据汪宁生称,木刻习俗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原始记事,因大多刻在或画在易朽的竹木、皮革等材料上,实物难以保存,但有一些刻画在骨、石或山崖之上的原始记事遗迹保存下来。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328 号墓中出土一套刻有缺口的骨片,这是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刻木记事的确切例证[6]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即便在文字发明后,由于西南少数民族文字主要为巫师掌握,用于传抄祖先神话、占卜、降神、咒鬼、祈雨等经书,一般民众能识者不多,用之者更少。民间社会每有记事需要,仍用木刻。甚至直到20 世纪60 年代,西南局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仍保留有木刻习俗。
木刻与古代契约概念的质剂、傅别、书契、券、莂等一脉相承[7]王旭.中国传统契约文书的概念考察[J].法治论丛,2006,(4).。明代朱荃宰认为,此即“今市井合同、夷人木刻之类耳”[8](明)朱荃宰撰.文通(卷十六)[M].天启刻本.。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借贷等活动中,木刻的使用非常普遍。《文心雕龙》载:“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缗,其遗风欤!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9](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M].黄霖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51)明代湖南卢溪县“蛮夷杂处,刻木为契,不识文字,凡有交易、借贷,以指大一木,刻其物品、日期、多寡之数于上,析而分之,彼此各藏其半,以取信”[10](明)徐学谟撰.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五)[M].万历十九年刻本.。雍正《广西通志》云:“粤蛮交易,初无文券,多用木刻,长短、大小不等,穴而藏之。其文各以事异,汉人莫识也。”[11](清)金鉷修;钱元昌,陆纶纂.雍正广西通志(卷九十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河池瑶人“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刻也”[12](清)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千四百十五)[M].雍正铜活字本.。广西一些地区的山地族群在交易时,如标识“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三日”,则于木片刻画长痕22 道,中痕10 道,短痕3 道。又如所卖者为山林,以“屮”为符号[13]刘锡蕃.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P305)。近代西康地区民众“古朴质实,几不知欺诈为何事。交易往来,以木刻示信(土人大多不识文字,每用小木,刻齿以记之。或用木条,剖分为二,各执其一,异日符合,即昭诚信)”[1]杨仲华.西康纪要(下册)[M].商务印书馆,1937.(P256-257)。
苗民传统的符契有木刻、草契等。凡是不动产之典卖多用木刻。典卖者以其中指骨节为标准,砍木为痕,授于乙。刻痕必须与骨节横纹的距离相同,另外还须划若干痕点,表明卖价及物品数量,然后剖为两半,各执其一,买者得左半,卖者得右半。苗人称此种交易之手续为“砍木刻”。草契则多用于借贷关系。若乙向甲借款,作为债务人的乙方以草1 本可借银1 两,取草结为契,以此类推。有时亦行“砍木刻”,或只凭中间人进行借贷[2]刘锡蕃.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P103-104)。因此,“殷富之家,茅草、木棍充满于其箱箧,是者所谓契券,而珍藏宝贵之物也”[3]刘介.苗荒小纪[M].商务印书馆,1928.(P24)。贵州“苗有七十二种,其散处各府州县者约有二三种。买卖田土,不立文契,但用木,约二三寸,用刀划售价若干于木上,对劈为二,各执其半以为信,日后转售,则取原主之半木合而验之,永无找绝纠缠”[4](清)顾公燮撰.消夏闲记摘钞(卷下)[M]//丛书集成续编(第9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P740)。木刻往往因材而制,并不仅限于木质。《国朝文汇》载:“苗地产人面竹,节皆具人面,七节者尤罕,以为信号,曰木刻。”[5](清)沈粹芬等辑.国朝文汇(乙集卷五十六)[M].宣统元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贵州清平县黑苗“凡买卖田土等事,用小竹割为刻数,谓之木刻,彼此剖分,各执其半,以为信,永不改悔”[6]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一[M].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云南山地族群的符契主要有木刻、裂石、结绳三种。其中,木刻系用8 寸左右的木片,“尖其一端,圆其一端,上刻各种记号。剖为二片,当事者各执其一。所刻记号,有用刀镌,有用火灼,有着色者,有不着色者”[7]谢彬.云南游记[M].中华书局,1931.(P273)。有些地区或族群的木刻为单纯的刻画符号。明代马龙州罗罗“不识文字,凡有交易、借贷,辄以片木刻其物品、日期、多寡之数于上,析而分之,彼此各藏其半,以取信”[8](明)郑颙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M].景泰六年刻本.。近代车里十二版纳的阿卡、攸乐人虽大都通晓汉语,但无本族群文字,“记数用木刻,一端刻元数(币)、尺数(度)、斤数(衡),一端刻角数、寸数、两数,前者痕大而后者小,中剖为二,各执一半,至期则合符清数,是曰木刻”[9]李拂一.车里[M].商务印书馆,1933.(P59-60)。阿佤(葫芦王地)民众“多以木刻为交往信据”。若甲买乙的田地,“则以木一块,刻有花纹和鸟兽之形,长约五寸许,剖为两半,卖者一半,当众焚毁”,“买者收存一半,作为契纸”。其他类型的交易亦用木刻,买卖双方各存一半,作为信符[10]李景森.葫芦王地概况[M].云南财政厅印刷局,1933.(P14)。
木刻也有用汉字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者,这应是刻画符号向纸质契约过渡的中间形态。清代滇南彝族“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要誓于神”[11](清)李焜纂修.乾隆蒙自县志(卷五)[M].乾隆五十六年抄本.。邓之诚曾在云南民族地区得一木刻,长约3 寸,宽1.5 寸,厚约1 分,两端呈圭形,右边刻锯5 齿,左边刻较大之2 齿,一面书买卖双方姓名、事由及价格,并保证日后不得赎取,立此木刻为据,一面书中间人姓名和订约日期[1]邓之诚.骨董琐记[M].邓珂增订点校.中国书店,1991.(P115)。民国时期,班洪“境内交易,有赊欠或期盘者,则书其值与年月于木片,当事人各执其一”,名曰木刻,其所见“有作摆夷文或汉字者”[2]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班洪风土记[M].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P47)。
刻木传信的古老习俗在西南山地族群传统社会留存最为完整,并形成复杂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具有鲜明的区域和族群特点。凉山彝族之间互相通信用“打木刻”之法,将数寸树枝或竹片,“以刀纵横砍其一方为符号,吉事涂红色,凶事涂黑色,中劈为二,一自留,一使人持往对方传语为信符,是谓木刻”。“使者至对方时,出木刻,受信者验之信,而后述主人语,并主人使命时之状态,或坐,或立,或屈一手足,或某语高声,某语低声,发某语时曾唾地,一一仿肖形容,俾受信者如见其主人焉”。若所经之地有冤家梗阻,不能直达时,使者须出资,转请冤家地方之彝人代为传递木刻。“虽易数使,而语言、状态,不敢变易,此所谓刻木为信也”[3]郑少成等修,杨肇基等纂.民国西昌县志(卷十二)[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9辑).巴蜀书社,1992.(P258)。通信木刻中有一种警示木刻,主要流行于凉山彝族社会。当彝人内部发生纠葛时,在武力解决前,“每以长一二尺之木板一个,系以麻线,表示不满而将复仇之意,预为警告。如系红线,则结怨尚浅,可以和解;蓝线则冤恨较深,和解甚难;若系以黑线,则冤仇太深,无和解可能,非打冤家不可。此种木板,系派娃子暗中送往对方,或托旁人设法转致,汉人亦名之打木刻也”[4]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M].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47.(P94)。近代西康民众识字不多,土司行政事务的传达多以木刻、金刻、石刻或竹刻,尤以木刻最普遍。如霍尔白利土司开会所用之木刻约长五寸许;遇紧急事务则用金刻,约长二寸许,棱角形,绕划二道极深之凹曲线;调兵用石刻,约长一尺许,上有五孔,孔涂蓝色;竹刻用于征粮赋,约长二尺许,以刀刻一人形,涂红色。使者携木刻等信物至各沟寨,口述土司命令。沟寨头目确认信物无误后,即按照使者传达的口令执行,用敲木梆、敲铜锣、派人口头送达等方式召集民众[5]翁之藏编.西康之实况[M].民智书局,1930.(P161-162)。
通信木刻是动员民众进行集会的重要手段。集体力量的凝聚对于处在部落状态的西南少数民族社会至关重要。当面临外来威胁或有要事需要协商时,部落酋长即“砍木刻”,“使人传示辖区各寨。急者加枯炭、鸡毛;又急者加辣椒、火绳(即鸟枪所用之燃火绳,其材料为树皮纤维质);尤急者则烧之使燃。寨目睹此,登楼擂铜鼓,召集寨民。事缓者,鼓声连续而缓,事急者,一连三遍,断而续,声急而厉。寨民若闻急槌声,无不奔走骇汗”。于是,各家派出代表1 人,随寨目奔赴指定会场集合。酋长宣布开会理由,或征求民众意见,并执行之,会众虽赴汤蹈火而不敢后退。“今此俗渝、黔、桂、云南连界之苗山有之”[6]刘锡蕃.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P89-90)。
木刻在西南山地族群战斗征召中的作用尤其显著。雍正十三年(1735),贵州“台拱苗以官吏征粮不善,苛收暴敛,激生变端,远近各寨遍传木刻”[7]印鸾章.清鉴纲目[M].世界书局,1936.(P364)。乾隆三十五年(1770),古州(治今贵州榕江县)熟苗香要起事,“椎牛飨群苗,众罗拜以次,呼为王,转相煽诱,其旁二十一寨皆响应,遂传木刻,将以五月十五日袭取下江营”[1](清)钱维乔.竹初诗文钞·竹初文钞(卷五)[M].嘉庆刻本.。嘉庆元年(1796),贵州南笼府北乡仲苗土目贺占鳌告变,“郡人共传狆(仲)苗之木刻,已过永宁州之关索岭。木刻者,狆(仲)苗调兵之符信也,以木为契,中分之,分出则壮者行,合出则老弱皆行”[2](清)张锳修;邹汉勋,朱逢甲纂.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十六)[M].咸丰四年刻本.。咸丰十年(1860),松潘藏族群众因纳粮问题,“遍传木刻起事”,至咸丰十一年,“攻陷松潘厅城一、漳腊、南坪、小河、平番、叠溪营城五、大小屯堡一百余所”,史称“庚申番变”[3]张典等修,徐湘等纂.松潘县志(卷三)[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6辑).巴蜀书社,1992.(P123-124)。同治年间,理番厅孟董屯守备穆租索朗起事之初,“曾传木刻至芦花各沟,及松潘、毛儿盖、打箭炉、瞻对边界”[4](清)吴羹梅修,周祚峄纂.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六)[M].同治五年刻本.。云南沧源、澜沧、双江、耿马、镇康、南峤各县局以及缅甸部分地区卡瓦(佤族)村落的征召信号则较为特别,其“山官对所属,号令自如,有兵事,宰牛连毛皮每村送一方,名曰散毛肉,各村接毛肉,知有兵事,即准备持武器来山官处听调遣。事急迫者,传令加鸡毛、火炭,即飞速、火速,不能停留之”[5]尹明德.云南边疆三大部族:僰人·山头·卡瓦[J].边政新报,1948,(5).。
木刻有时也用于婚姻关系,具有契约的性质。清代广西镇安府民众“婚娶不分亲疎,惟随所欲,稍忤其意,砍木刻为离书,各自改配”[6](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千四百五十)[M].雍正铜活字本.。刘锡蕃(刘介)称,“赘婿之俗,苗、狪(即侗)亦有之,但不能承受其父母之遗产;若赘于孀妇,赘婿并须先‘砍木刻’,授其未婚之妻,承认养蓄其前夫父母、子女之责任,此等手续具备后,始得与妇同居”[7]刘锡蕃.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P76)。
还有一种占卜木刻盛行于彝族社会,汉人名之为“打木刻”,彝语称为“色莫”。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文化以及鬼神信仰浓厚,巫术在彝族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巫术和宗教不但能够支配人民的动作行为和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而且统治初民的心理态度和培养传统的道德观念”[8]林耀华.凉山夷家[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P83)。占卜是预知未来吉凶从而控制命运的一种巫术。凡是婚姻、疾病、丧葬、出行、狩猎、打冤家等皆可举行占卜。彝族的占卜活动多由毕摩主持。“打木刻”属于彝族占卜的一种,多用于出行与战争。其方法系取一木条或木片,口念人名及出行方向,用刀在枝上刻画若干痕迹,并于当中划一长道,检视上下两段刻痕的单双数,以卜吉凶[8](P87)。
西南少数民族在“砍木刻”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盟誓或神誓。盟誓曾经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习俗。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盛行盟誓。规约、立信是盟誓的本质要求。盟誓的目的是参与各方通过信守共同的行为规范,从而调节、维护人际关系和群体间社会秩序。神灵、物件等是达到立誓不悔的凭借和途径。明代学者魏濬云:“夷人交易无文券,止用木刻,此意殊古然。夷人信誓、信神,交易必就神誓,故无敢爽易者。”[9](明)魏濬撰.西事珥(卷三)[M].万历刻本.据《滇略》载,云南“夷人交易尚用木刻,多在神前呪誓,故不敢叛也”[1](明)谢肇淛.滇略(卷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康熙年间,平远、大定、黔西、威宁一带的黑彝“期会、交质无书契,用木刻。重信约,尚盟誓”[2](清)田雯.黔书[M].中华书局,1985.(P13-14)。杀牲、歃血是盟誓仪式的重要内容。与“砍木刻”同时进行的一般有剁狗、杀牛、钻皮、顶经等活动。其中杀牛、钻皮等宣誓典礼之举行,大都在械斗结束或宣告和解之时。当事各方将牛杀死后剥皮,支起牛皮,从下面钻过,并各将牛血洒入酒杯之中,相互碰杯后,一饮而尽[3]魏弼周.记"雷马屏峨":一个母性中心的原始社会剪影[N].大公报(重庆),1939-01-10.。整套的仪式流程赋予木刻以神圣性。木刻有时也是神灵崇拜活动中的重要信物。四川理番杂谷脑河流域羌民在求雨时,星上上三砦民众派代表上羌民之圣山,对神许愿,并恳求取木刻召集民众。木刻藏在圣山附近的山洞内。取得木刻后返回圣山,将一半木刻留于神前,另一半由代表带下山,并依次在各砦传递。木刻所到之处,各家派人到圣山山顶集会拜神,焚香敬酒[4]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M]//石硕主编.川大史学·专门史卷(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P81)。
二、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中的木刻
木刻记事有着古老的渊源,曾被诸多民族广泛使用。辽朝“木刻子牌约一十二道,上是番书‘急’字,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本国已历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书‘永’字,其字只用金镀银叶陷成,长一尺二寸。以来每遇往女真、鞑靻国取要物色、抽发兵马,用此牌信,带在腰间左边走马,其二国验认为信”[5](宋)孟珙撰,(清)曹元忠校注.蒙鞑备录校注[M].光绪二十七年刻,笺经室丛书本.。女真“法律、吏治则无文字,刻木为契,谓之刻字。赋敛调度皆刻箭为号”[6](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19)。据宋代学者徐霆考证:“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7](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M].中华书局,1985.(P6)汉代以后,中原的木刻记事减少,而在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却长期保留木刻,尤以西南为盛。民国时期,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列举了姓氏、干支、言语、家族村舍之组合、集会、祭典、岁节与婚俗、巫蛊、契券、史事等十大证据,论证“汉蛮同族”,其中集会、契券的主要内容为木刻[8]刘锡蕃.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P263-273)。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木刻是中华民族文化同源性的重要表征。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木刻的流行与汉字推广的滞后存在密切关系。汉字早在商代即已出现,并逐渐发展出一套完善的文书系统。朱熹在《性理大全》“字学条”中指出了汉字的重要作用:“夫字者,所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百官、察万民、贯通三才,而为用大矣。”[9](明)蔡清.易经蒙引(卷十一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川纵横,层峦叠障,交通不便。中原王朝在该地的设治时间相对较晚。西汉“司马相如始建议通道,戍转相饷,耗费亡功,寻罢之,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其后竭天下力,挟平南越之威,仅乃通之,置越巂、沈犁、汶山、武都四郡。唐宋以来,西夷多没于吐蕃,南夷后割于蒙诏。元初始复汉土,而乍臣乍叛,边屡失亡”[1](清)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十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西南少数民族在与当地官府的交往中,有时使用木刻,但各地木刻的具体形制有所不同。事实上这是木刻本身所具有的诸多功能在族际关系中的体现。广西灵川县瑶族因私人间争斗,赴县府投木刻,请县官调解、处置。该木刻由一系列抽象的刻画符号组成,其象征意义尚需专人加以解释[2]陈美文修,李繁滋纂.民国灵川县志(卷四)[M].民国十八年石印本.。“献木刻”是西南少数民族归顺官府统治的重要象征。明朝天启三年(1623),四川长宁等地“各苗俱用木刻拜伏乞降,五寨悉平,乃旋师”[3](明)朱燮元.督蜀疏草(卷十一) [M].康熙五十九年朱人龙刻本.。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云南腾冲“边外各夷寨均各投献刀镖、木刻,安静就抚”[4]清实录(第31册)[M].中华书局,1986.(P471)。江心坡地区昔为中国属地,设有土司。英国殖民势力侵入该地后,江心坡民众奋力抗拒,派遣代表董卡诺、张藻札于1928 年至腾冲乞援,并带来木刻,为薄木片,上有十一刻,乃势力较大之十一山官所刻,表示江心坡人民誓属中国之意。此种木刻起着类似“保证书”的作用。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而言,木刻的信用与效力往往在官府公文之上。清人许朝在《夷歌六首》中写道:“皇古流风尚有无,结绳遗意在边隅,官符文约都无用,木刻相要信自孚。”[5](清)舒启修,吴光昇.乾隆柳州县志(卷十)[M].民国二十一年铅字重印本.因此,根据当地少数民族习惯,木刻也被官府有意加以利用。清嘉庆七年(1802),川省彝族在峨眉、雷波等处抢劫,四川总督勒保派丰绅、董教增带兵前往。据勒保奏称,“董教增等带兵至峨眉,传发木刻”[6](清)常明修,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五)[M].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由于雷波彝族外出焚掠,嘉庆十九年(1814),提督多隆武等带兵深入凉山征剿,并“发去木刻,传谕各支滋事生番,令将掳去难民献出”[7](清)常明修,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十二)[M].嘉庆二十一年刻本.。近代云南双江县府存有一个勐峨佤族送来的木刻,长约5 寸,厚约2 寸,方柱形,在木刻上面用火烙有圆圈纹2 个,并在烙印处剖为两半,勐峨佤族留一半,交给县府一半。据称,若县府在危急关头用公文去佤族地方调兵,“调几个来几个”,如果用木刻,则可全部调来救护。因此,县府非常珍视这个木刻,用手巾包裹,与铜质县印共同锁存在箱子里[8]彭桂萼.彭桂萼诗文选集[M].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P344)。
明清以降,随着统治的深入,木刻的动员、集会功能成了官府对西南民族基层社会治理的严重障碍。官府试图通过将通事置为头人、用官方符牌取代木刻,或者直接取缔木刻等手段来加强对民族社会的直接控制。苗疆治理的关键在于头人或寨头[9]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5册)[M].中华书局,1977.(P10489),因此,官府将会汉语的苗人通事置为寨头,“有讼狱应勘问者必寨头传语,而后官始悉其情,否则难以言喻也”[10](清)爱必达.乾隆黔南识略(卷十三)[M].道光二十七年刻本.。为防范土目私自用木刻征召民众,官府规定须用官颁印牌调动土练。“查土练皆系百姓,并非土目私人,非奉官调,不应擅动。历年调用土练,大抵土目自传木刻者俱多,行之日久,恐正伪不分,奸徒易于鼓惑。应请嗣后调练,务以地方文武会衔印牌为凭,不许土目擅自私调,并遍行晓谕大小村寨、乡管、头人,如有土目不奉印牌,以木刻、小票擅调乡练,即赴文武衙门具报,以凭严拿,照擅调官军律治罪”[1](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等纂.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九)[M].乾隆元年刻本.。在咸丰年间松潘庚申番变中,木刻起着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松潘厅同知何远庆认为,“番民动辄传递木刻,纠众议话,最为恶习”,应禁止土弁传木刻,“倘有不遵,即将为首起意之人送官,严行治罪”[2](清)何远庆.松潘纪略·土弁章程记[M].同治十二年刻本.。
西南民族地区在明清时期陆续被纳入卫所、郡县体制,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汉族的迁入。由于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加强,其木刻习俗也发生许多变化。据清代学者顾公燮称,“贵州汉苗杂处,苗居其九,汉居其一。汉人流寓者半系江西”[3](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下)[M]//丛书集成续编(第9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P740)。获取地权是汉人在西南民族地区安家落户的主要途径,也是多民族杂居社会形成的重要方式。在四川彝区,居于村寨的“熟夷”主动招汉人佃种田地,而“生夷地掠汉人种之,名汉人曰娃子”[4](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五)[M].光绪刻本.。贵州黎平府“自光绪初年兵燹以后,苗人田土多被汉民盘剥,日复一日,以致生计维艰。是以苗人亟欲驱逐客民,以复田业”[5](清)俞渭修,陈瑜.光绪黎平府志(卷五下)[M].光绪十八年黎平府志局刻本.。族际借贷活动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也日趋增多。彝汉毗邻地区之汉族“每多贫乏,而向夷人借债,夷人贪图大利,日积月累,致汉人无力偿还,惹起纠纷,夷人每因此种事件而向汉地抢劫俘掠”[6]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M].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47.(P94)。由于明清王朝强化了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控制,统治秩序得以全面确立,汉语逐渐成了西南多民族的通用语言,但是大部分民众仍不识汉字。湖广总督孙嘉淦称,苗人“语言文字多与华通。臣尝传集其头人而训诲之,凡臣所言皆能通晓”[7](清)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十)[M].敦和堂刻本.。另据《黔记》载,贵州古州、清江、丹江等处的青仲家“不知正朔、文字,以木刻为信”[8](清)李宗昉.黔记(卷三)[M].中华书局,1985.(P20)。即便如此,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借贷、田地租佃、买卖等方面的互动,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当地社会风气以及契约型木刻的变迁。
论者往往将书契的出现与世风联系起来。隆庆《云南通志》载,诚信不欺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种“美俗”,其“一切借贷、赊佣、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惟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如有不平,赴酋长口讼,以石子计其人之过”[9](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M].民国二十三年龙氏灵源别墅重印本.。进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简,事之大小唯结绳以识之,亦足以为治。至后世,风俗媮薄,欺诈日生,而书契不容不作矣。书文字也,契合约也。言有不能记者,书识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验之。”[10](明)季本.易学四同(卷六)[M].嘉靖刻本.贵州民风在“乾隆以前,一切礼文、日用率从简朴,不失为近古淳风。嘉庆以来渐趋于华,绅矜富户争奇好胜,不数载而家资一空,即食贫居贱之流亦皆效尤,惰弃本业,呼朋引类,吹赌游荡”。同时田土买卖也开始用书契[11]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风俗[M].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古州苗多架阁而居,曰峝家,无契券,凡田土、钱债,以片木刀刻其上,曰木刻,执此征租、索债,无敢逾时”。自汉人进入该地后,“多举放钱债,重征其息。苗无银,以禾准银,名曰脚禾,其息愈重,汉人往往操十余金入寨,不数年间即有数百金。今苗贫且刁,虽有木刻,至期亦有不偿者”[1](清)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卷二下)[M].光绪十八年黎平府志局刻本.。近代安顺“苗夷佃农之地主,大都均属汉人,租约之式样全照当地汉人流行者”。“苗夷佃农向汉人租田,先须具有担当之抵押品,与各种耕作农具及耕牛;开始时,多须找一中人向汉人或地主之管账人接洽,且须彼此熟识者,议定之后,乃立租约,俗称为‘讨田约’”[2]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3.(P142)。
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字的习得,西南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往时,改用汉字书写的木刻,甚至直接用文书。如大小凉山彝族递交给官府的呈词、保状等,多请汉人用汉字写于木板上[3]毛筠如.大小凉山之夷族[M].四川省政府建设厅,1947.(P94)。四川彝族在民国时期偶有用彝文与汉官沟通,清代时尚无此种现象。部分彝族还延请汉人教育其子弟学习汉文,但彝族内部仍以木刻通信[4]郑少成等修,杨肇基等纂.民国西昌县志(卷十二)[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9辑).巴蜀书社,1992.(P257)。
民国时期,除苗山的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还多以刻木、结草为契约外,广西其他地方的壮、瑶等族“砍木刻”风俗已被汉字书契代替。然而,改用字契后纠纷也随之增多。因苗民基本不识汉字,代笔者多为汉人,此类汉人大都以敲诈为生,苗民常被愚弄。有苗民称:“吾能识木刻而不能识字;由木刻而发生的争议,凡属苗、狪(侗)民众,类能分判曲直,若为文字,不止公断无人,赴愬于长官,或反造无穷之累。”[5]刘锡蕃.岭表纪蛮[M].商务印书馆,1934.(P107)这其实是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普遍遭遇的困境和错位,而积极兴办民族教育则是根本解决之道。
刘介指出,“苗民于诉讼、买卖、集会、订约、交际等各要件,以无文字记载之故,虽感绝大困难,然终不肯为学”。不仅如此,苗人反而以不读书为“金科玉律,遵奉罔替”,仿若“天命”如此。“吾国文字创造最古,而苗民隶吾统治亦最先,今犹以上古结绳合符之治,是谁之咎哉”[6]刘介.苗荒小纪[M].商务印书馆,1928.(P23-24)。结合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的“雇读”[7]即“少数民族视入学读汉文为当差,多愿出钱或出物作为报酬雇请他人顶替学差名额读书”。见严奇岩.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J].民族研究,2006,(6).现象,因此,弃用文字或将文字局限于特定领域,转而在族际交往中使用木刻,其中也可能存在自主选择的因素。
结 语
西南少数民族木刻按功能大致可分为契约型、通信型和占卜型三种。各种类型的木刻在不同方面维系着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木刻成了西南少数民族规范内部社会关系的重要凭借。西南少数民族在与官府的互动过程中,通过木刻进行信息传递与社会动员,同时,木刻也充当着官民沟通的工具以及官府控制民族基层社会的抓手。
木刻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结构相匹配。诚信与规约是木刻的本质特征。西南少数民族一般通过盟誓或神灵祈祷仪式,以保障木刻效能的发挥。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中,文字主要掌握在巫师、民族上层、通事等人手中,普通民众识字甚少,这是木刻长期在民间流传的重要原因。木刻上的符号以记事为主,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地区或族群中有时会有不同的解释。同一事物对应的刻画符号往往较为随意,并不固定。很多木刻符号的意义可能只有当事人知晓。这种情况极大限制了木刻在跨区域与跨族群交往中的作用。
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陆续推进,民智渐开,社会组织趋于严密,保甲机构普遍设立,民众的自卫办法已与之前迥异,保甲长取代了寨头、土目的地位,电讯、文公等成为各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同时,随着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往来日益密切,木刻基本被汉文书契取代,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木刻习俗逐渐隐退于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