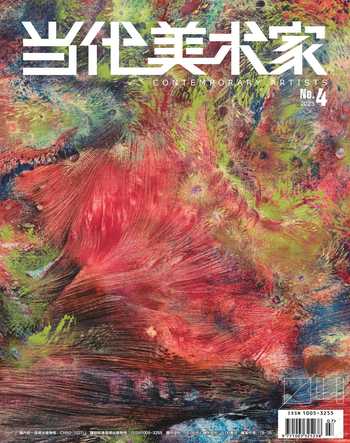东西方比较视域下赖特有机艺术论的文化积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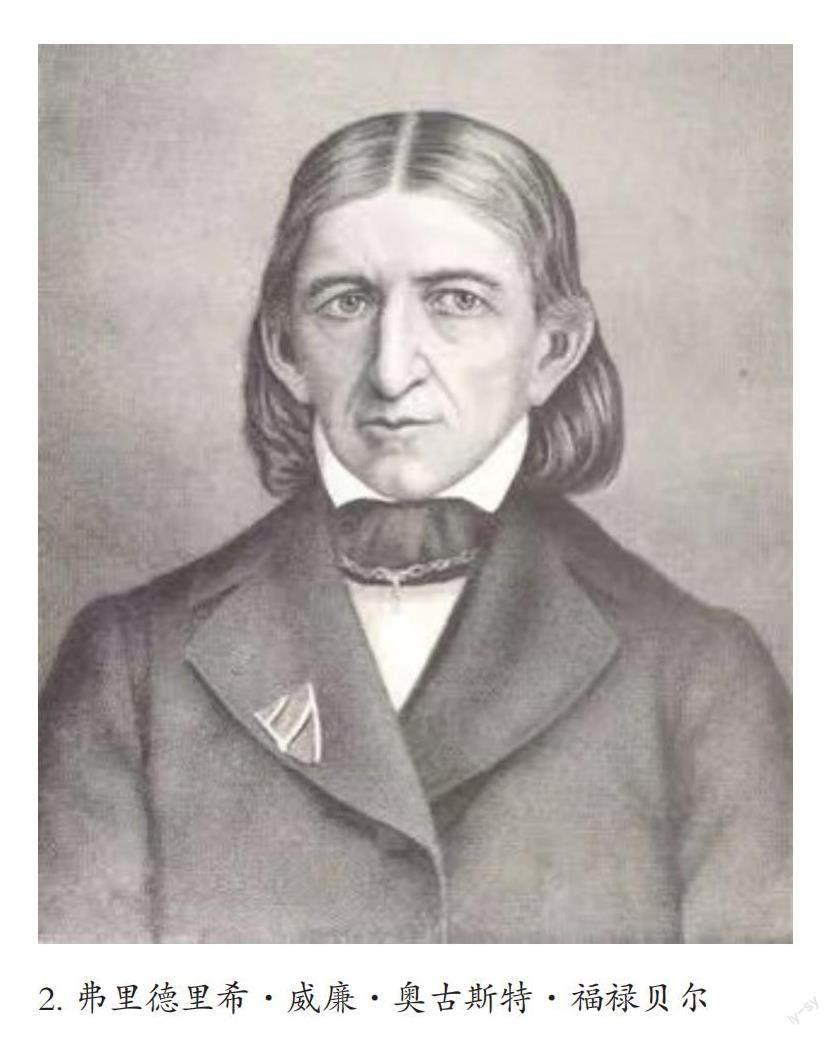

摘要: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美国最伟大的建筑艺术家,在其有机艺术论的建构中吸收并学习了以中国古典道家美学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是东西方文化走向同一轨道的典型案例,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重要文化事件。本文在东西方比较视域下,从唯一神派自然崇拜与“共生”、斯宾诺莎泛神论与“道”以及超验主义文学与“万物同一”三个方面阐明接受道家美学之前的赖特所蕴含的文化积淀与东方智慧的交融汇通。厘清以赖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家接受东方古典美学的前置思想渊薮与东方智慧的亲缘性,不仅对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为东西方美学观念交融通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赖特,唯一神派,斯宾诺莎,超验主义
Abstract: Frank Lloyd Wright i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modern western art concepts and the greatest architectural art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organic art theory, he absorbed and learned the Oriental wisdom represented by the classical Chinese Taoist aesthetics, which is a typical cas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moving towards the same track, and also an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tegration of Wrights cultural accumulation and Oriental wisdom before accepting Taoist aesthetics from three aspects: Unitarianism nature worship and “Symbiosis”, Spinozas pantheism and “Tao”, and transcendentalist literature and the Opinion “All things are the same”. To clarify the affinity of the western modern artists represented by Wright to accept the prethought of Oriental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Oriental wisdom, it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 on cross-cultural art history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esthetic concepts.
Keywords: Wright, Unitarianism, Spinoza, Transcendentalism
19世紀末期,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开拓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与东方美学结缘,由此开启了与道家思想交融的文化汇通之路。赖特并不是偶然接受了道家思想,在其有机艺术观念不断构建的过程中,西方本土的非理性思想给予他丰厚的文化给养,并沉淀出与东方美学相近的内蕴和底色。也就是说,阐明赖特生成带有东方特点的艺术观念的前置文化积淀,是理解西方艺术家汲取东方美学的重要环节。通过考察赖特的生平经历、学说著作和艺术活动,可以看到他在接受道家美学的影响之前,已经从启蒙教育、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三个层域,也就是唯一神派自然崇拜、斯宾诺莎泛神论和超验主义文学观得到了非理性思想的文化积淀。美国传记学者罗伯特·麦卡特为赖特谱写传记时曾对此提出相近观点:“在这里涉及他一生中所受到的三种重要影响:‘出身于劳埃德·琼斯家族;‘教育来自沙利文;‘信念是学习爱默生著作的结果。”[1]劳埃德·琼斯家族是赖特母亲安娜的家族,赖特在演讲和文稿中曾多次提到母亲的家族信仰唯一神派对他的思想浸润。同时,他不止一次阅读和学习爱默生的著作,在创办的塔里埃森学校中,常常让学徒大声朗读爱默生等超验主义文学家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斯宾诺莎也是赖特让学徒们研读的重要思想家,泛神论对赖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创作影响颇深。可以推见,三种思想归汇为赖特接受道家美学的思想始基,通过对赖特接受的非理性思想与东方哲思之间亲昵关系的探讨,可以窥见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接受东方古典美学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
一、信仰:唯一神派自然崇拜与“共生”
信仰作为人的精神力量的本源,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它确立了人的行动标准和价值准则,信仰迥异的人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发展方向。赖特作为唯一神派的信徒,自少年起便受劳埃德·琼斯家族的影响信奉唯一神派,根深蒂固的信仰之力既直接影响了赖特艺术观念的建构,又形成特有的内心认知和理解事物的基础,为他接受道家美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赖特拒斥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世间万物是以整体统一的特征显现出来,如他所说:“在当时混乱纷纭的教义解说中,它宣扬生活是上天所赐的礼物,只有一个至上全能的主宰,世间万物都因‘他而合为一体。”[2]“‘统一是他们的咒语。万物的统一!这正是母亲始终追求的理想。”[3]通过赖特在自传中的描述,一方面可以看到赖特的信仰来自他的家族,母亲是理查德·劳埃德·琼斯家族的一员,他受母亲家族的影响信奉唯一神派。另一方面,赖特秉承着唯一神派的思想看待自然的角度,人与自然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层层叠套并且互相包容的:“土地!它给予理查德·劳埃德·琼斯这样的拓荒者无所不包的深厚、宽广和美丽。他与田间的石头立约[4],他自己仿佛就是葱绿的山崖下露出的一块岩石。他建起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外面是一重重更大的世界。重重叠套,永无止境。”[5]在赖特看来,事物的和谐与统一展现出新的力量,人与自然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共生的。
作为美国最自由的宗教思想之一,唯一神派的教义显现出对坚固传统的强烈反叛,并为东方神秘主义思想的涌入提供了观念上的预热。纵观基督教发展史,二元论、神性论和原罪论始终被视为正统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发现,持有一元论、泛神论和人性论的异见者也是一直存在的,较为典型的聚集地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的异教徒最初在这里定居。18世纪,先定论与意志自由之间的矛盾成为清教徒面临的精神困境,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在19世纪社会迅猛发展的局势面前显得更加尖锐。具体地看,1735年左右,伴随着“大觉醒”宗教复兴运动引领的自由主义倾向以及美国文化发展带给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加尔文教的宿命论让人们感到厌倦和怀疑,其强调神本位的严格教义失去了对信众的吸引力。宗教狂热的降温使人们精神上出现了危机和真空。随着加尔文教的逐步分裂,脱胎于新英格兰公理宗教会的唯一神派形成极大的发展空间,成为美国最自由的宗教思想之一。此时,与自然神论一脉相承的唯一神论已经成为美国较为流行的思想理念,成为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信仰[6]。其作为赖特的信仰既完善了对上帝与人、人与自然的传统认知,在艺术观念中显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又为东方思想的传播和借鉴奠定了基础。
赖特是在唯一神派的氛围中逐步构建和完善了有機艺术论。他的父亲是唯一神派的牧师,超验主义文学家爱默生也曾任职波士顿地区的牧师。在超验主义时代,唯一神派在知识分子阶层信众居多,对美国的文化倾向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强调着“自然神论”的精神与信仰,为西方美学观念开拓了新视野。这里的“自然神论”是18世纪启蒙理性对神学思想进行改造而产生的,从其对美国深远的影响便可看出唯一神派思想与自然神论的一脉相承。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充斥着神秘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赖特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赖特自传的译者杨鹏在注释中为唯一神派做出解释:它的思想更接近于自然神崇拜[7]。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自然崇拜,“‘自然总是用有机的方式塑造人的性格,正如她用有机的方式塑造万物一样。”[8]实际上,此处的“自然”更接近于老子所言“道”的意蕴,饱含着人的灵魂和万物的本源与归宿。
进一步来看,赖特也遵从着唯一神派中统一与和谐的思想理念,如传记家麦卡特曾提到:“赖特是在唯一神教威尔士教派信仰的氛围中成长的,这一教派向往一种整体和谐的理想,即‘万物的统一与和谐。”[9]这使得我们必须注意到,在1819年以后,唯一神派增加的几项原则:上帝创造万物并热爱万物,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人是具有神性的,上帝存在于所有人的内心;对上帝的真正崇拜要求人们友善相处[10]。加尔文教义中的那个严厉的、谨肃的上帝已经化身为一位可敬爱可亲近的上帝,变成了具有自由意志的、凡人可以效仿的模样。总的来看,唯一神派中统一和谐的思想使人们对上帝、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新的阐释,即从服从转变为融合,为美国文化接触并接受东方思想提供了稳定而扎实的社会基础,自然万物的平等相处变得极具时代性与变革性,人与自然的纽带关系推动了道家美学思想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迅速蔓延和深远影响。
二、哲思:斯宾诺莎泛神论与“道”
哲学思想的积淀影响着艺术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作为近代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对西方现代美学有重要的理论影响,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强调的:“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首先要成为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11]。自文艺复兴以来,持续一世纪之久的启蒙运动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第二次影响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遍及社会、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是较早的启蒙理念,引起了赖特的强烈关注,是赖特常常推举并探讨的研究对象。斯宾诺莎哲学的介入使赖特完善了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其与老庄文化思想的暗合为赖特接受道家美学思想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赖特与学生的交流中,常常将斯宾诺莎的哲学设为主题,布置学生首要研读的哲学家之一即是斯宾诺莎。通过在赖特身边学习的我国近代建筑学家汪坦的记述,可以探察到赖特推崇斯宾诺莎的事实。汪坦在与妻子的往来信件中多次提到赖特“指示学生研究他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时,需读的哲人的书有老子(Laotze)、佛(Buddha)、耶稣(Jesus) 、斯宾诺莎(Spinoza)……”[12]从人物排列的顺序和提及的频率可见赖特对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重视和热情。事实上,斯宾诺莎否认了传统思想认知的人格神,将具有创世与主宰功能的上帝拉下神坛,认为“神即自然”,神与自然是平等的,主张用对待神的态度来对待自然。有学者认为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斯宾诺莎否认了宗教中神的存在。事实上,他把“神”当成“自然”的另一种说法,提出神与自然共存的理念并将神等同于一切,一切等同于神,当属泛神论的观点。这里要说明的是,斯宾诺莎经常使用“神或实体”[13]“自然或神”[14]两个术语。他把实体、神、自然并置,表达了世间万物最高因的整体与统一,是以泛神论方式表述了“神”和“自然”的含义,阐明了其中的关系:“万物都预先为神所决定——并不是为神的自由意志或绝对任性所决定,而是为神的绝对本性或无限力量所决定”[15]。他所说的“神”并不是宗教教义中传统的认知,而是接近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道”,是一切事物的内因,其存在与运行都是无形而无限、孕育在万物其中又不见开端和尽头的,“作为最高生产者,神在将万物产生和并合于自身之时,也通过万物展开和阐明自身。”[16]斯宾诺莎的宇宙观所阐释的“实体”与老子的“道”有着内在暗合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学者张岱年早在20世纪40年代发文《斯辟诺萨与庄子》论述了斯宾诺莎与庄子的相通之处。作为两者之间比较问题的最早讨论,他着重对斯宾诺莎与庄子的相通之处进行了阐发,并且关注到斯宾诺莎与老子思想的暗合,提到斯宾诺莎“这里‘上帝有些方面似乎有些类似于老子的‘道了。”[17]
在斯宾诺莎看来,由于存在是实体的本性,故实体与“道”相通是无处不在且不可能不存在的。斯宾诺莎提出一种新的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范式,即从整体和统一的角度去认识世界,这与老子的整体观念存在着近似的内在理路。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在探讨斯宾诺莎的整体性观念与老子的整体观时,提到斯宾诺莎与“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哲学家老子不谋而合,老子在《道德经》中提供了一种具有完美整体性的宇宙视角。”[18]斯宾诺莎认为每个存在都拥有、保持和发展其独特的本质,而这些本质都是上帝的表现,是自然的表现,如他所说:“我主张在自然中在这无限的力量,它作为无限的力量在自身内从观念上包含整个自然,它的思想与它的对象即自然本身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我并且主张人的心灵也是这种相同的力量(不是作为无限的和知觉整个自然)是作为有限的力量,即就它仅仅知觉人身而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人的心灵看作无限理智的一部分。”[19]在斯宾诺莎看来,人体以及人的心灵是宇宙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圆融整一的统一体。
斯宾诺莎与老子思想不仅关于世界本体或本原的探索存在相通性,对世界运行的本质规律也形成了观念上的暗合。他认为“自然本身就是上帝的力量,不过是另一名词而已。我们不明上帝的力量和我们不明自然,这两件事是相等的。”[20]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遵循着自然規律,自然与上帝是平等的,若要接近上帝,必须先了解自然,如他所说:“自然的效能与力量就是上帝效能与力量,自然的法则规律就是上帝的指令”[21]。依照老子的说法,世间万物便是依照“道”的规律自然而然地行动与发生。老子主张“无为”,指不过分地行使自己的能力,由万物自然的生发和展开,不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世间万物,通过领悟的方式让人发生内在的变化。道家所说的无为而为则是依照自然规律作为,保留自然的状态,斯宾诺莎与老子对待万物运行规律的态度是相近的,这也成为赖特理解、体悟和学习东方美学的基础和前提。
三、理念:美国超验主义文学观与“万物齐一”
作为美国重要的文学思潮,超验主义思想以本土文学的特殊身份对赖特形成精神洗礼,加深了他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感受和体悟。赖特十分推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曾多次言及爱默生对他的思想启示,并于“辞世前一年发表《活着的城市》(The Living City),书末附录了爱默生的论文《耕作》,平时谈话中爱默生是经常提到的前辈之一,可谓终身服膺。”[22]
爱默生作为美国精神的开创者,被誉为“美国的孔子”[23],他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随着超验主义文学思潮的蔓延,东方精神逐步融入了美国文明的血液中。爱默生借东方精神以弥补西方文化上的不足,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实体与东方道家有着内在的思想契合,思想杂糅着鲜明的美国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元素。尽管他并没有直接研读过《道德经》或道家理论书籍,《道德经》的英译本出现在爱默生逝世九年以后[24],但据研究者介绍,如果爱默生阅读过道家思想相关内容,极有可能是通过阅读儒家思想书籍的注释而获得。[25]这并不影响东方文化对爱默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在建构超验主义体系时吸收了中国孔孟、印度佛陀、波斯文明与阿拉伯的文化给养,通过阅读东方典籍来获取灵感和智慧,以整体性思维认识事物的方法对美国文学与艺术产生了新的启发。早期的爱默生已经开始关注东方典籍,按照理查森(Robert D.Richardson)的说法,爱默生在1840年已经有读研东方典籍的习惯[26]。1843年,他主编的《日晷》期刊中专设有《异国文化经典》(Ethnical Scriptures)系列专栏以介绍孔子、佛陀等东方文化思想。事实上,爱默生对东方思想的关注,是渴望在异域文化中寻求某种精神上的共通以及文化上的认同。
爱默生所探讨的核心范畴“超灵”(Over-Soul)与老子的“道”都在说世界本体的问题,也是世界统一性和整体性的问题。爱默生在《论超灵》中言明人要承认“更高起源”(higherorigin)——“陌生的力量”(alienenergy)的存在,他把这种力量称为“超灵”,涵盖了“至上存在”(Supreme Being)与“精神”(Spirit)的范畴。爱默生的“超灵”宇宙观与老子“道”极为相像,其本身不能显像却投射于人与万物之中,对世间万物发生作用并使人感悟到它的存在。从爱默生对超灵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它与道家思想的暗合,诚如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提到:“如同爱默生笔下那些直觉感悟式的精彩段落一样,老子的隽语警句闪烁着智慧的光芒。”[27]又如理查德·格罗斯曼(Richard Grossman)所言:“爱默生的作品实际上使老子获得了新生,他那清晰有力而又地道纯正的英语使老子的思想熠熠生辉。”[28]
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爱默生断然否定了传统,重新提出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他对“自然”一词进行了两种意义上的界定,阐释“自然”的词义是应对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所在。在爱默生看来,“自然”一是指自然界,二是指非我(Not Me)的部分。非我的部分言明,除了自我的心灵或灵魂以外,其他都属于自然,学者余静远曾提及“爱默生对‘自然的定义不同于前代的任何一位哲学家。”[29]爱默生对自然的界定启发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对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主客关系的思考,即从整体和谐的视域出发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说道:“‘精神,即至上存在,并非在我们周围建立自然,而是让自然穿过我们的身心,正如生命之树从旧的毛孔中伸展出新的枝叶一样。”[30]在他看来,“每一种自然现实都体现了某种灵的现实”[31]。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的角度被拉近成为通感的审美体验,爱默生认为人与自然的精神达到物我同一的生命境界。
依前所述,19世纪上半叶的超验主义思潮将人的身份与自然并置,它的兴起显示出人对自然秉持着近似宗教的虔诚与崇敬。作为美国文化的布道者,爱默生为赖特带来了饱含文学性的审美体悟,对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思想观念上与道家学说的暗合为美国文化带来了新的理念思路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四、审美辩证法:有机建筑论与“有无相生”
在接受了这样的前置思想的浸润下,赖特接受和吸收了道家美学,对建构有机艺术论提供了丰厚的理念铺垫和思想滋养。其中,最为显著的理论特征即是对道家“有无相生”观念的学习和借鉴。他在演讲中说道:“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老子的思想。一天,我从工作室的花园走进来,看到一本驻美日本大使送给我的书,在这本书里,看到了我向你们提到的建筑理念。它简洁地表达出我心中所想和我一直在建筑上所做的努力:‘建筑的实质不仅仅是墙和屋顶,它还包括建筑中的居住空间。”[32]这位日本大使送给赖特的书便是《茶之书》。道家哲学虽然是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想,但在他看来,老子美学是空间营造乃至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赖特不仅将“道”视作“虚实相生”空间观的最高诠释,更把“道”看成具有独特魅力的东方智慧。
赖特领悟老子“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这种关于空间的理解不仅与他一直以来所构建的有机建筑论亲和相通,并且对进一步丰富有机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成为有机艺术审美经验的理论指导和核心特质。赖特模仿东方习惯,在建筑上注以文字说明其艺术理念,他刻注在西塔里埃森墙上的文字即为《老子》之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并将此视为校训名言。[33]赖特眼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已经超越了建筑领域,成为体悟宇宙、自然与生活的至理名言。与此同时,《老子》是赖特在教学以及宣讲时常常与学生们讨论研究的藏书之一,其中有无相生论是他最为重视和推举的美学观念。《老子》中记载:“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王弼注:“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34]在老子看来,房屋内在的空间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部分,真正的可用之处在于“实”营造出的“虚”的空间。老子对房屋空间“有”与“无”的论述道出了建筑空间创作的实质,揭示了“有”与“无”在对立之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虚的空间可以容纳万物,在“虚”之中,空间才有可能流动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无相生理论浸润下,赖特曾多次前往日本寺庙和庭院,十分关注葆有着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法式的建筑群样貌。建筑和庭院的“虚”“实”境界对赖特的艺术观念产生强烈渗透。建筑群的围合,将围合空间呈现出人与天地相通的联结状态,人在其中与天地交融,空间的流动和弥合消解了三者之间的边界,构成实中有虚的环境场所,生活空间被赋予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显现出“无”的审美境界。梁思成早年曾拜访赖特,梁思成回忆说:“我这次在美特去访问美国建筑界老宗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他今年八十多岁,而仍是美国建筑界最先进的一个,他于本世纪初已设计‘合理的建筑,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然而现在看来,仍不愧是最近代的建筑。”[35]在访问过程中梁思成问及建筑理念时,赖特对他说:“中国的建筑师只要了解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几句话就行了,著名的道德经上曾说过:‘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牅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36]老子的这段论述被赖特奉为理解建筑精神的真谛。[37]
在长达七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赖特十分注重空间的流通性,不断调整和改善对空间的处理手法,营造出有无相资的美学意蕴。有无相生理念对赖特影响之深远,从其早期“草原式住宅”(PrairieHouse)到后期古根海姆博物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均有跡可循。赖特将空间内部关联起来,只做必要的功能区分,空间结构的布局不是用墙体进行生硬的分割,而是将功能与形式完全统一。“草原式住宅”完全符合了美国中西部草原的地貌特征,在结构设计中摒弃维多利亚式的“盒子”空间,摆脱传统欧式建筑的束缚,通过对传统折衷主义建筑空间的反叛,逐渐形成美国本土化的建筑艺术样态。赖特阐明了有机建筑的表现形式和深远意义,从传统建筑注重实体转向关注空间,从独立的静态空间转向连续的流动空间。与此同时,赖特在罗比住宅(RobieHouse)实现了十英尺深的悬挑,挑檐给建筑带来了更开阔的视觉延伸,满足了赖特对表现形式大胆的需求,营造出更为丰富的空间层次,室外到室内的空间转换中增加了过渡部分,丰富了居者的切身感受。有学者指出“拉肯大楼是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方形的筒,具有纪念性特征,它有真正的建筑空间,正如公元前中国老子提出来的虚空的认识。”[38]质言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39],空间的“有”与“无”“动”与“静”“阴”与“阳”在“道”的世界中不断转化,相互依存,赖特认为建筑只有互通有无、虚实结合才能真正地反映出世界的生机与灵动,只有诗意的永恒流动才能使建筑充满生气、意味弥远。
结语
综合来看,赖特在接受道家学说之前存在着三个关键的西方思想因素,即唯一神派自然崇拜、斯宾诺莎泛神论以及美国超验主义文学观,这为其有机艺术论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同时为他向东方文化寻求精神给养奠定了丰厚思想基础。事实上,以道家美学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渗入西方现代社会并非偶然现象,正是由于不同层域的思想归汇,才得以形成接受东方美学的文化沃土,最终产生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传播和接受、交融和互通。通过梳理和阐释其与东方美学的暗合互通,以有无相生为核心的有机艺术论为对象,言明赖特有机艺术论的文化积淀与思想始基,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以及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柳思如,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东北大学博士。研究方向:艺术教育,跨文化艺术史。
注释:
[1] [美]罗伯特·麦卡特:《赖特》,译者:宋协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4-75页。
[2] [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一部自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译者:杨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3] 同上。
[4] 《圣经·旧约·约伯记》5:22,“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天理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
[5] 同[2],第12页。
[6] 参见左少峰:《爱默生的神人一体自然观与美学观》,济南:山东大学,2012年,第55页。
[7] 同[2],第8页。
[8] 同[2],第77页。
[9] 同[1],第15页。
[10] 陈奔:《爱默生与美国个人主义》,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第88页。
[11] [美]威尔·杜兰特:《哲学简史》,译者:梁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118页。
[12] 汪坦:《1948年生活在赖特身边》,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13]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译者:贺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
[14] [荷兰]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译者:洪汉鼎、孙祖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9页。
[15] 同[10],第91页。
[16] 吴树博:《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性原则及其对近代哲学中主体性的批判》,《世界哲学》,2019年第4期。
[17] 王珍:《东西方无神论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18] [英]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译者:宋玉波、朱丹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19][英]罗斯:《斯宾诺莎》,译者:谭鑫田、傅有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8-89页。
[20] [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译者:温锡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页。
[21] 同上,第91页。
[22] [美]查尔斯·E·阿瓜尔、贝蒂安娜·阿瓜尔:《赖特景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景观设计》,译者:朱强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6页。
[23] 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8, p.219.
[24] 马丽媛:《爱默生思想中的东方元素新探》,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第1页。
[25] 姚亚芝:《论爱默生与老子之“道”》,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1期。
[26] 小罗伯特·D. 理查森:《爱默生 充满激情的思想家》,译者:石坚、李竹渝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3页。
[27]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Laotse, 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48,p.5.
[28] Richard Grossman, The Tao of Emerson,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2007, p.21.
[29] 余静远:《释爱默生的〈论自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0] Brooks Atkinson ed.,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0, p.33.
[31] Porte J, Morris S, Emersons Prose and Poetry,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35.
[32] [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有机建筑论》,译者:陈琦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33] 参见汉宝德:《建筑母语:传统、地域与乡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页。
[34]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页。
[35] 梁思成:《建筑市镇设计的新观点》,大公报,1947年12月8日,第六版。
[36] 同上。
[37] Frank Lloyd Wright, Bruce Brooks Pfeiffer, ed., Frank Lloyd Wright Collected Writings Volume 5 1949-1959, New York:Rizzoli lntem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1995, p.127.
[38]荊其敏,张丽安编著:《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39] 宋伟:《审美视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从纳德勒的评价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