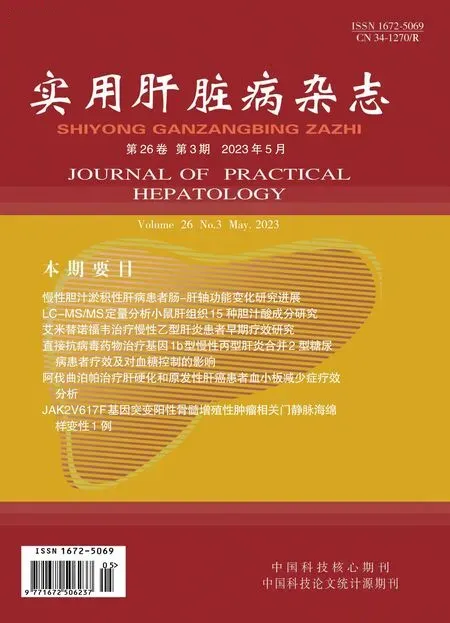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肝细胞癌
苏佩华 综述,宋枚芳,赵彩彦 审校
尽管随着乙肝疫苗的普及和母婴阻断水平的提高HBV感染率呈下降趋势,但目前全球CHB负担仍较重,WHO估算全球慢性HBV感染者约有2.57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种与遗传环境应急等相关因素相关的以肝脏脂肪沉积、肝小叶内炎症与窦周纤维化为特点的临床病理综合征,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OS)是其发生的核心机制,其疾病谱包括单纯的肝脂肪变性(nonalcoholic fatty liver,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随着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流行,NAFLD的患病人数逐渐增多,其全球发病率约25%。在CHB患者中,合并NAFLD的患者也越来越多。CHB患者中肝脏脂肪变性的患病率已上升至25%至30%[1]。慢性HBV感染和NAFLD均是导致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病因,CHB合并NAFLD可能增加HCC的发生风险,本文就其相关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CHB对HCC发生的影响
1.1 HBV基因突变 HBV基因突变可以改变病毒的生物学行为和致病性,促进肝细胞癌变。慢性感染、HBV基因组的特殊结构、核苷(酸)类似物(NAs)广泛、长期和不规范的应用,以及宿主免疫应激均可导致HBV基因的相关突变。HBV中的YMDD突变,又称M204V/I突变,是由YMDD基序中的缬氨酸或异亮氨酸替代蛋氨酸引起的,分别称为YVDD或YIDD变异。既往认为拉米夫定是YMDD突变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在没有接受过抗病毒药物治疗的CHB患者中也检测到自发的YMDD突变。HBV基因主要为B型和C型,自发性YMDD突变更可能发生在C型菌株中,感染C型菌株的患者发生YMDD突变可能会增加HCC发生风险[2]。另外,HBV基本核心启动子(basic core promoter,BCP)区的A1762T和G1764A双突变与基因B或C型携带者HCC的发生密切相关[3]。相关数据表明,位于HBV基因组X/preC区域的8个关键突变(G1613A、C1653T、T1753V、A1762T、G1764A、A1846T、G1896A和G1899A)的累积是HCC发生的危险标志,而BCP双突变和8个关键突变的组合与HCC的发生显著相关[4]
1.2 HBV DNA整合 病毒DNA整合到宿主基因组是HCC发生的重要分子机制。HBV DNA与宿主基因的整合往往不完全,使得宿主和HBV基因破坏,甚至基因序列的重排,导致病毒蛋白的异常表达。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的HBV DNA序列包括X、C、增强子和S基因,整合的病毒DNA可以导致突变和截短的HBV X蛋白(HBV X protein,HBx)、HBsAg及HBcAg蛋白的持续表达。其中,C端截短型HBx可通过抑制硫氧还蛋白相互作用蛋白促进肝细胞增殖和重新编程细胞代谢[5];其还可以调节小窝蛋白-1的转录,稳定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6,维持β-连环蛋白的激活,增强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促进HBV相关HCC的进展[6]。X基因整合还可以直接激活癌基因(如Myc、Ras和Src),抑制抑癌基因(如p53和Rb)的表达,从而促进HCC的发生。此外,HBx基因启动子、C基因启动子和增强子可以整合到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基因或附近的调控区域,启动子的重复整合增加了TERT的表达[7],从而触发细胞的克隆性增殖,导致恶性转化和HCC发展。
1.3 HBx HBx是由154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链,具有N端负调节区和C端反式激活结构域,分子质量为17kDa,其存在于HBV感染肝细胞的细胞质及细胞核中,调节细胞转录、凋亡、增殖和蛋白质降解,在HCC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HBx可以抑制由p53、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Fas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诱导的细胞凋亡,还可以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Akt)、Janus蛋白酪氨酸激酶1(janus kinase 1,JAK1)/信号转导子与转录激活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Wnt/β-连环蛋白(Wnt/β-Catenin)以及氧化应激等信号通路,均与HCC发生密切相关[8]。HBx与CREB结合蛋白(CREB binding protein,CBP)/p300相互作用,协同提高磷酸化的环腺苷酸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的转录活性;CREB不仅在肝脏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参与HCC的发生[9]。损伤DNA结合蛋白1(damage-specific DNA binding protein 1,DDB1)是一种参与DNA修复和细胞周期调节的蛋白质,HBx通过与DDB1结合干扰S期进程诱导有丝分裂异常,导致多极纺锤体形成、染色体分离缺陷、中心体复制异常以及多核细胞出现,促进HCC发生[10]。端粒酶在保持端粒稳定性、基因组完整性、细胞长期活性以及持续增殖潜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HBx可上调端粒酶活性,导致肝细胞恶性转化[11]。
1.4 免疫抑制 HBV对天然和获得性免疫细胞的抑制作用导致病毒识别和清除障碍,从而加重HBV诱导的慢性炎症,促进肝细胞的恶性转化。HBV特异性CD8+T细胞通过产生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和TNF-α或直接杀伤受感染的宿主细胞发挥抗病毒作用。持续高水平的HBV DNA载量增加抑制受体的表达,损害HBV特异性CD8+T细胞的功能。研究发现,HBV特异性CD8+T细胞表面高表达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导致HBV特异性CD8+T细胞维持部分耗竭状态,无法有效控制HBV复制[12]。但这些细胞有助于维持中等水平的炎症,可能有利于癌变发生。此外,CD8+常驻记忆T(tissue-resident memory T,TRM)细胞在HBV感染的肝脏中富集,导致部分免疫应答。然而,在HBV感染的HCC中,TRM细胞也可以通过过表达抑制受体(如PD-1)而被抑制和耗竭[13]。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是CD4+T细胞的亚群,CHB患者Tregs增多,通过抑制CD8+T细胞的增殖、活化和细胞因子分泌促进HCC发生[14]。NK细胞通过产生INF-γ、TNF-α和其他细胞因子参与早期抗HBV过程。持续HBV感染诱导产生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和TGF-β,可能抑制NK细胞的成熟,导致其产生INF-γ和TNF-α减少,无法有效抑制HBV的复制[15]。
2 NAFLD对HCC发生的影响
2.1 代谢失衡 NAFLD中过多的脂肪堆积和肥胖导致肝脏和外周IR和高胰岛素血症,进而通过PI3K和MAPK通路激活胰岛素受体信号,导致代谢失衡,扰乱肝细胞周期调控。研究表明,IR和高胰岛素血症增加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1,IGF-1)的表达[16];IGF-1与其受体相互作用激活PI3K和MAPK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增殖和抑制凋亡。PI3K通路通过细胞周期蛋白D1、双微体2(MDM2)/p53、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影响细胞周期调控、细胞凋亡以及细胞生长,参与HCC的发生发展[17]。MAPK通路的激活导致包括c-fos和c-jun在内的几个原癌基因转录上调,最终激活Wnt/β-catenin信号级联,导致肝纤维化和癌变[18]。
IR造成肝脏中脂质过度堆积,即能量代谢的不平衡增加肝脏的脂毒性,导致游离脂肪酸的产生增多,其在线粒体中经β氧化产生大量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ROS的过度产生引起呼吸链断裂和线粒体功能进一步缺陷,继而释放细胞色素C、触发凋亡死亡信号。ROS和OS诱导的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RS)导致 Ca2+过度释放。过量的钙水平导致线粒体和溶酶体通透性增加,进一步增加线粒体ROS的释放,激活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3(caspase-3)和9(caspase-9)相关的凋亡,促进肝脏炎症和癌变的发生。ROS的产生、OS和ERS与细胞死亡机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与HCC发生发展有关。NASH是NAFLD的严重类型,被定义为5%以上的肝脏脂肪变性,合并炎症、肝细胞损伤,伴或者不伴纤维化。肝内铁蓄积增加与NASH进展为HCC有关。研究显示,与NASH患者相比,NASH相关HCC患者的肝脏铁储存水平更高[19]。NAFLD患者的代谢紊乱可能诱导肝内坏死性炎症和OS恶性循环,间接影响肝脏的铁储备。过量的铁在肝细胞内积聚,通过产生ROS导致肝细胞损伤。
2.2 免疫失衡 IR、线粒体OS不仅促进脂肪堆积和ROS的产生,而且通过免疫学机制促进HCC的进展。细胞因子信号通路、信号激素(包括瘦素、脂联素)和免疫细胞等与NAFLD进展为HCC有关。IR和OS刺激IκB激酶β(inhibitor kappa B kinaseβ,IKKβ)依赖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存活[20]。OS促进TNF-α、IL-6等细胞因子的释放。TNF-α通过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amino-terminal kinase,JNK)和IKKβ激活原癌通路,促进转录因子激活蛋白-1和NF-κB的合成;IKKβ的磷酸化和降解导致NF-κB的核进入,触发炎症级联反应,加速NF-κB的活化,而NF-κB参与肝细胞的癌变过程[21]。另外,IL-6可激活STAT3,STAT3是一种癌基因转录因子,可诱导激活细胞增殖和抗凋亡途径,在NASH相关HCC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OS还会改变瘦素和脂联素等脂肪因子的水平,肥胖和NAFLD的典型特征是高瘦素和低脂联素。瘦素促进IR和肝脂肪变性发生,并通过激活TNF-α和IL-6信号促进纤维化形成和血管生成。瘦素与其受体结合可激活多种致癌信号通路,包括JAK2/STAT、MAPK和PI3K/Akt,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22]。瘦素还可上调TERT,导致肿瘤细胞永生化[23]。另一方面,脂联素下调炎性细胞因子并抑制血管生成,其还减少STAT3和Akt的激活,抑制HCC发生[24,25]。在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脂联素水平降低,从而减弱其抗炎和抗肿瘤作用。免疫反应对NAFLD相关HCC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作用。与其他游离脂肪酸相比,亚油酸诱导的线粒体功能损伤会导致更严重的氧化损伤,导致CD4+T淋巴细胞丧失,损伤机体免疫监视能力并促进癌变发生[26]。研究表明,胆碱缺乏的高脂饮食诱导肝内CD8+T细胞、NKT细胞和炎性细胞因子的激活,促进NASH和HCC的发生[27]。
3 CHB合并NAFLD与 HCC发生
单纯CHB和NAFLD均会引起肝纤维化、肝硬化及HCC,两种疾病同时存在可能对HCC发生起协同作用。对270例CHB患者进行了平均79.9个月的随访,其中107例患者合并NAFLD,结果显示同时合并NAFLD使CHB相关HCC的发生风险增加了7.3倍[28]。基于1089例CHB患者组成的大型队列研究也显示,活检证实的NASH与临床结局(如HCC和死亡)显著相关(HR=3.06)[29]。CHB和NAFLD导致HCC的机制不同,CHB的基础上合并NAFLD,HBV感染和肝脂肪变性对肝脏造成双重影响,可能促进肝纤维化、肝硬化和HCC的发生。除了如上所述两者对HCC发生的影响机制,CHB和NAFLD均会影响肠道菌群以及细胞自噬,进而促进HCC的发生。此外,细胞损伤可触发Hedgehog(Hh)信号通路,该信号通路参与细胞分化、器官形成、癌变和肿瘤转移;研究[30,31]发现HBV感染的肝细胞和NAFLD中气球样变性的肝细胞产生和释放促纤维化Hh配体增加,可能导致疾病的进展和HCC的发生。
4 CHB合并NAFLD的管理
4.1 NAFLD对CHB患者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 NAFLD是否会影响CHB患者对抗病毒治疗的应答,目前结论尚未统一。既往研究认为,在接受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α-2a(PEG-IFNα-2a)或NAs治疗的CHB患者中,合并NAFLD对完全病毒学应答无明显影响。但是,对226例接受PEG-IFNα-2a治疗的CHB患者进行为期24周的随访,结果显示肝脂肪变性程度越重,完全应答和病毒学应答率越低[32]。研究结果发现,在接受恩替卡韦治疗的267例CHB患者中,合并肝脂肪变性组HBV DNA清除率和HBeAg血清学转换率均较低[33]。此外,ALT复常率在24周和48周时也显著降低,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肝脂肪变性是恩替卡韦治疗应答不佳的独立因素。病毒学应答不佳可能是由于肝脂肪变性导致抗病毒药物与肝细胞之间接触面积减少,药物生物利用度降低。因此,为了提高抗HBV的疗效,建议CHB合并NAFLD患者应注重NAFLD的防治。
4.2 CHB合并NAFLD患者抗病毒药物的选择 NAs能够有效抑制HBV复制,并且抑制肝脏炎症、减轻纤维化程度、降低HCC发生风险,对于CHB合并NAFLD的患者仍推荐应用,尤其是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和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enofovir alafenamide fumarate,TAF)。Yao研究表明,拉米夫定(Lamivudine,LAM)、恩替卡韦(entecavir,ETV)或阿德福韦酯(adefovir dipivoxil,ADV)可增加CHB患者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内脏脂肪面积。TDF可通过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剂激活受体上调肝脏CD36来调节脂质代谢,可能与肝脏过表达CD36可减轻肝脂肪变性和改善IR有关。与口服ETV治疗的CHB患者相比,TDF可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脂蛋白水平。对CHB患者的研究发现,合并或未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应用TAF后虽然体重和BMI增加,但是其可以改善代谢功能障碍、降低血清ALT水平、促进ALT复常。因此,TDF和TAF在有效抗病毒的同时可以调节CHB患者的脂质代谢情况,更适用于CHB合并NAFLD患者。与NAs不同,干扰素具有抗病毒和免疫调节双重作用,诱导的先天免疫反应可以在病毒复制周期的不同时间点抑制HBV复制;其还可以诱导宿主产生多种抗病毒蛋白,特异性地抑制HBV复制并降解cccDNA。相比于NAs,IFN和PEG-IFN治疗后HBe和HBs血清转换率更高。此外,干扰素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增殖实现其抗肿瘤作用。基于IFN-α的治疗在降低HCC发生风险方面优于NAs。另外,干扰素的治疗常伴随有体重下降,对NAFLD有益。1例CHB合并NAFLD患者经Peg-IFNα-2a联合NAs治疗实现HBsAg、HBeAg、HBV DNA的转阴以及NAFLD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