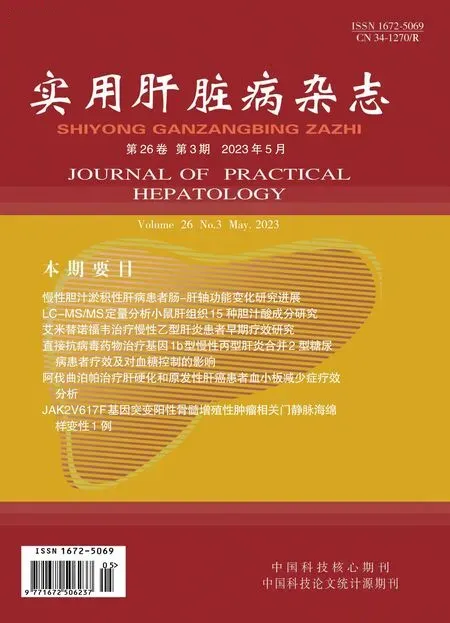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患者肠-肝轴功能变化研究进展*
陈慧婷,周永健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和解毒中心,能够分解代谢营养物质和毒性物质,阻止有害物质进入循环系统,而肠道是机体防御的最前线,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与肝脏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肠-肝轴(gut-liver axis),肠道中的营养成分、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而肝脏中的物质通过胆道系统排泄入肠道。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肠粘膜屏障、细菌移位和胆汁酸代谢是肠-肝轴的关键特征[1]。肠道菌群紊乱可导致肠道中有害物质增加,有益物质减少,肠道屏障功能受损,肠道来源的细菌产物和代谢物可暴露于肝脏,通过肝-肠循环诱发肝细胞损伤和肠道炎症的发生,并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而肝病的进展又会进一步加重肠道菌群的失调,最终导致肝病加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保持肠道的健康稳态,对于维持正常的肝脏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胆汁淤积是指免疫、遗传、环境等因素造成胆汁形成、分泌和排泄障碍,胆汁不能正常流入十二指肠而进入血液循环的病理学状态,患者可出现黄疸、尿色加深、乏力、瘙痒等。各种原因造成肝脏病变导致胆汁淤积性疾病统称为胆汁淤积性肝病(cholestasis liver diseases),主要包括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和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胆汁淤积性肝病起病隐匿,早期常无明显症状而仅表现为血清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转肽酶(GGT)和免疫球蛋白IgG升高,疾病进展后可出现高胆红素血症,且具有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肝衰竭,甚至死亡的风险。目前,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病因仍不清楚,研究表明肠-肝轴的失衡是胆汁淤积性肝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1 肠-肝轴
肠道和肝脏通过门静脉、胆道系统和体循环进行双向交流(crosstalk),其中肠道菌群对于维持肠-肝轴的稳态至关重要。肠道微生物群不仅影响着肠道局部功能,而且对全身免疫系统的成熟和维持、物质代谢等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肠道微生物种类繁多,包括细菌、古生菌、真菌和病毒等。肠道细菌主要由厚壁菌、拟杆菌、放线菌和变形杆菌四个门类的细菌组成。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受到宿主内在遗传(如基因型)和外在环境(如饮食、运动、寒冷暴露、感染和抗生素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紊乱是包括肝病在内的许多疾病发生的基础,肠道微生物紊乱导致肠道通透性升高和细菌移位,称为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PAMPS在血液循环中识别肝细胞中的免疫受体,进而激活炎症级联反应,进入门静脉循环,导致肝细胞损伤、肝纤维化和肝硬化[1]。此外,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如胆汁酸的变化会影响肠道和肝脏的生理功能。肠内胆汁酸分布的改变可以改变肠法尼醇X受体(FXR)活性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15/19表达,对胆汁酸体内平衡至关重要[2]。反之亦然,肝脏通过胆汁系统和体循环释放胆汁酸和炎症介质,如细胞因子等参与肠道沟通。
2 肠道屏障与细菌移位
肠道屏障由单层上皮细胞形成,上皮细胞由肠上皮细胞、杯状细胞、潘氏细胞、Tuft细胞和肠嗜铬细胞等组成。肠细胞由连接蛋白紧密连接在一起,并与肠腔中的粘液、抗菌肽、免疫球蛋白、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的共生菌等协同作用,保护肠道免受病原微生物群的伤害[3]。肠道屏障对于维持肠道和宿主内部微生物之间的物理和功能隔离是十分重要的。在正常情况下,物质有选择性地通过肠道上皮细胞,而当存在肠道屏障功能障碍时主要表现为肠漏(leaky gut),即肠道通透性增加和细菌移位等。受损的肠道屏障使得微生物/代谢产物和PAMPs通过门静脉到达肝脏,并通过激活肝脏枯否细胞、肝窦内皮细胞、肝星状细胞等,导致炎症级联反应[4]。在肝脏疾病,特别是肝硬化患者,可以观察到细菌移位增加是一种受细菌过度生长、淋巴组织缺陷、免疫系统对微生物和PAMPs的异常反应影响的病理生理发生机制。
3 胆汁酸和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肠-肝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胆汁酸和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肠道细菌可以将初级胆汁酸代谢为次级胆汁酸改变胆汁酸的信号特性,维持粘液层和紧密连接的完整性,进而改善肠道屏障[5];反过来,胆汁酸也可以通过胆汁酸受体直接或间接地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6]。胆汁酸通过肝脏和肠道中的FXR和膜结合G蛋白受体5(TGR5)传递信号[6]。胆固醇合成初级胆汁酸,后者在肝细胞中与牛磺酸或甘氨酸结合后释放到肠道中,吸收脂质和脂溶性维生素,大多数在末端回肠被主动重吸收,少部分(约5%)转化为次级胆汁酸,被被动重吸收或排出。初级和次级胆汁酸在小肠和大肠中被重新吸收,并通过门脉血返回肝脏,每天完成4~12次的肠肝循环[7]。肠道微生物包括拟杆菌、梭菌、真杆菌、乳酸杆菌和大肠杆菌等菌群产生的胆盐水解酶(BSH)[4,8]和7α-脱羟基酶可促进初级胆汁酸向次级胆汁酸的转化。FXR通过调控胆汁酸转运和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促进胆汁酸的肝肠清除,其活性受胆汁酸调节,间接影响肠道菌群。胆汁酸依赖性FXR激活还可防止胆汁淤积大鼠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细菌移位。FXR激动剂已被证明可以预防胆汁淤积症、肝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和炎症性肠病(IBD)的炎症反应[7]。奥贝胆酸(OCA)是FXR激动剂,可调节胆汁酸稳态、脂质代谢、糖异生和炎症纤维化过程,抑制内源性胆汁酸合成,使小肠中厚壁菌门的比例增加。
4 肠-肝轴与胆汁淤积性肝病
PSC患者常同时伴发IBD。在肝移植前进行结肠切除术可以降低供体肝脏PSC复发的风险[9,10]。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肠道和肝脏之间的联系似乎在PSC中更加明显[11],提示肠-肝轴是PSC发病的重要因素[2]。多个队列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比,PSC患者粪便菌群多样性显著降低,并伴有一些特殊物种的丰度改变[2],即共生细菌的相对丰度降低,潜在致病物种丰度增加,主要表现为韦荣球菌、梭状芽孢杆菌、链球菌属、乳杆菌属和肠球菌属等的丰度增加,而粪杆菌属和粪球菌属的丰度降低[1]。一项招募了10例PSC-IBD患者的临床试验表明,粪菌移植(FMT)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得到显著改善,其中3例患者血清碱性磷酸酶降低了50%以上[11]。另一方面,微生态失衡会导致肠道通透性改变并损伤肝脏。肺炎克雷伯菌改变了PSC患者的上皮屏障,导致细菌移位,肝脏T辅助17细胞(Th17)诱导的免疫反应导致的肝损伤与肠道通透性相关[1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PSC和PBC患者肝组织胆管上皮细胞具有异常高浓度的内毒素水平[13]。总而言之,以上研究提示肠道通透性增加和细菌移位是PSC病理生理学的关键特征。目前,还没有完全阐明肠屏障功能障碍是在疾病发展之前还是之后,但可以推断肠屏障功能障碍和炎症可以作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促使疾病进展。因此,改善肠屏障功能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治疗策略。
在PBC,肠道菌群、肠通透性增加和细菌移位也是重要的发病机制[1]。与PSC相似,与健康对照人群比,PBC患者肠道微生物组的特点是细菌α多样性降低,链球菌属、乳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丰度增加,而健康人群则是产丁酸盐的粪杆菌属的丰度增加。此外,与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应答者相比,UDCA治疗无应答者粪杆菌丰度有所降低[14]。上海交通大学马雄团队[15]也评估了UDCA治疗初治PBC患者的肠道菌群,发现血清次级胆汁酸水平与PBC患者肠道中富集的菌属呈正相关,而与健康对照组中富集的菌属呈负相关,表明次级胆汁酸水平可能取决于微生物组的组成。此外,他们还发现UDCA显示出可以通过减少嗜血杆菌属(Haemophilusspp)、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spp)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spp)丰度,增加在健康对照中丰度比较高的拟杆菌属(Bacteroidetesspp)、Sutterellaspp和Oscillospiraspp的丰度,部分恢复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16]。在长期暴露于细菌抗原的情况下,BALB/c小鼠肝组织学特征的发展与PBC相当[17]。临床上,PBC患者胃和小肠通透性增加[18]。与丙型肝炎患者比,脂磷壁酸(lipoteichoic acid,LTA)作为革兰阳性菌的一种细胞壁成分,在PBC患者的肝组织胆管和血清有所增加[19]。PBC患者血清LPS水平高于健康对照[20]。总之,这些发现表明 PBC患者肠道屏障功能障碍。
5 靶向肠-肝轴治疗胆汁淤积性肝病的可能策略与展望
靶向肠道菌群的治疗措施包括益生菌、抗生素和FMT等。调节肠-肝轴的进一步治疗策略还包括FXR激动剂,后者可以治疗胆汁酸代谢障碍、抑制细菌过度生长、改善肠屏障功能和肝组织炎症。在治疗PSC方面,小样本PSC-IBD患者使用含4种乳酸菌和2种双歧杆菌属的配方治疗3个月未显示明显的疗效[21]。抗生素治疗,如万古霉素和甲硝唑,可降低PSC患者血清碱性磷酸酶和胆红素水平,Mayo PSC风险评分下降,但机制尚不清楚。利福昔明治疗对PSC无明显疗效[22],但服用米诺环素超过一年可使碱性磷酸酶水平和Mayo PSC风险评分降低[23]。如前所述[11],小样本临床试验提示FMT后PSC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得到显著改善。UDCA被广泛用于治疗PSC,但缺乏对包括死亡在内的长期临床疗效的益处分析。治疗PBC的基本方法是促进胆汁酸代谢,而UDCA的一线治疗通过诱导胆汁酸流动,增加胆汁酸排泄。除了用于治疗瘙痒症的利福平外,目前暂无关于使用抗生素、益生菌或FMT治疗PBC的明确报道[1]。
综上所述,针对肠-肝轴在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病理生理学方面的作用和转化研究以及研发靶向肠-肝轴治疗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策略,如功能菌群的分离培养、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的功能鉴定、肠屏障模型的体外构建、菌群与疾病的因果关系验证、临床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等,是当前临床科研的前沿命题,值得广大研究工作者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