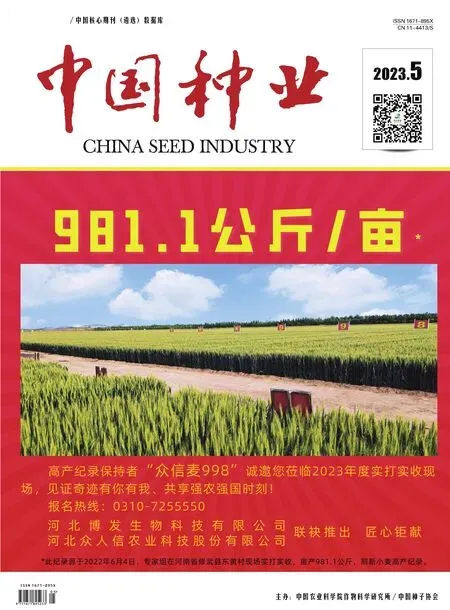育种产业中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的衔接
钟 辉 郝 佳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北京 100160)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育种产业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对助力种业核心技术攻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植物育种技术创新研发活跃,迫切需要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完善植物育种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为植物育种科技创新提供知识产权的最大保护[1]。
我国于2001 年12 月加入了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 协议》)是加入WTO 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义务遵守的国际公约,其中第27 条规定了能够获得专利权保护的主题,该条第3 款(b)规定“除微生物之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了非生物方法和微生物方法之外本质上为生产植物和动物的生物方法”可以排除其可专利性,并且同时规定了“缔约方应以专利方式或者一种有效的特殊体系或二者的结合对植物新品种给予保护。”作为《TRIPS 协议》缔约国,中国通过植物新品种权对植物品种进行保护,通过专利权对育种方法等进行保护。
1 中国植物品种相关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1.1 植物新品种权植物新品种权的立法宗旨在于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植物新品种权是指完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依法享有的排他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近年来,植物新品种权相关的司法和行政实践日趋完善、逐渐加大对育种者的保护力度,农业农村部每年发布年度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类型涉及新品种权侵权相关的司法案例、行政执法案例、确权相关的行政审批案例。尽管如此,仅通过植物新品种权仍难以有效保护育种者权益。主要体现在以下4 点。
第一,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时效滞后、保护不及时。植物品种的育种过程耗时持久,植物新品种审定确权的客体是已育成、产业上已经推广应用、较为成熟的植物品种,无法对新制备或新发现的植物育种材料或种质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
第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客体局限、不保护尚未形成品种的育种材料。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对象必须是列入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以下简称保护名录)中的植物种属,并且需要符合授权条件,由此可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对象是保护名录中已育成品种的植物品种,而不保护名录外或未育成的中间育种材料。
第三,植物新品种权难以保护育种过程中关键智力贡献。在植物育种中往往通过生物工程、诱变、远缘杂交等手段获得具有新性状的植株或育种材料,其他的杂交、回交、轮交等传统育种方法均为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综合性状表现优良适合作为亲本的已知商业化品种也容易替代,因此,在最关键的、具有新性状的植株或育种材料无法通过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情况下,仅提供育成植物品种的新品种权保护容易被规避。
第四,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行政处罚空转。由于植物新品种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糅杂、行政处罚和假种子处罚重叠,导致了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行政处罚实质上被架空[2]。
1.2 植物品种相关的专利权《专利法》的宗旨在于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与植物新品种权不同,专利权涉及各学科技术领域而并非仅涉及植物育种技术。
由于中国《专利法》排除了植物品种的可专利性,因此植物品种相关技术在国内的专利布局,主要涉及功能基因、检测方法等上游技术或边缘技术,难以为育种者的关键智力劳动成果提供有效的专利权保护。通过专利权维护植物品种成果的司法和行政案例也极为罕见。植物育种者客观上难以通过专利权有效保护关键的育种成果。
2 中国植物品种相关技术知识产权的客体对象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享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基于目前中国植物新品种权、植物品种相关专利权的二元保护体系未能充分保护植物育种者权益的现状,首要的是从两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条件进行研究,分析育种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原因。
2.1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客体条件植物新品种是实施育种方法和完成育种过程得到的结果,而不是育种过程和育种方法等如何培育植物新品种的技术方案。1997 年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品种权的内容和归属、授予品种权的条件、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品种权的审查与批准、期限、终止和无效、罚则等进行了规定。其中,授予品种权的条件包括:(1)属于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物的属或者种;(2)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3)具备适当的名称,并与相同或相近的植物属或种中已知品种的名称相区别。202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5 条规定,对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内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第90 条中对品种、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等的含义进行了规定,其中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
由此可知,中国植物新品种权受理和审查的客体仅限于保护名录内列举的植物属或者种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权所述的植物品种,为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因缺乏一致性、稳定性而未形成植物品种的植物群体、植株或其繁殖材料则不能通过植物新品种权进行保护。
2.2 植物品种相关技术的专利权保护客体对象《专利法》第25 条第1 款第(四)项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属于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专利审查指南》将植物群体、植株个体、繁殖材料均归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植物品种,从而对排除于专利权保护之外的植物品种进行了扩大化解释,不仅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植物品种,还扩展到了未形成植物品种的植物群体、植株以及植物繁殖材料。这就导致了目前植物品种相关技术专利权保护的客体仅限于生产植物的非生物学的方法。
2.3 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的客体对象未能有效衔接在我国,植物品种相关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种类主要包括植物品种权和专利权,如二者能有效衔接,就能为育种者提供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根据植物新品种权和专利权的制度设计,育种者的智慧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分为以下3 类:(1)新的优良植物品种由专门的植物新品种权进行保护;(2)通过非生物学方法生产植物品种的方法由专利权进行保护;(3)通过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生产植物品种的方法,由于其缺乏人的技术介入、或人的技术介入对于所述方法达到的目的或效果未能起到主要控制作用或决定作用,因而不能被授予知识产权。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和确权程序中对于授权客体的植物品种采用了严谨的解释,而专利权的授权和确权程序中又对专利权排除客体的植物品种采用了宽泛的解释,从而留下了植物品种相关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空白。
3 我国植物品种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建议
3.1 将植物新品种权的行政审批权归由同一部门管理,取消植物种类的限制,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客体延及至所有植物种属,而不限于保护名录中列举的种属随着我国植物育种科技的进步,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不仅是响应育种者对自身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也是为应对未来加入UPOV 1991 年文本做准备[3]。目前《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通过保护目录将植物新品种权根据种属的不同分别由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两个部门各自独立进行审定授权,然而,中国幅员辽阔、植物遗传资源丰富,有产业价值的植物品种不限于保护名录中列举的植物种属,保护名录难以覆盖全部的植物种属,不能对所有具有产业价值的植物品种进行有效保护。此外,两部门根据植物品种客体的不同对植物新品种进行平行审查也不利于实践中新品种权授权标准的一致。
从国外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的规定来看,无论是UPOV 公约、还是美欧植物品种保护制度都没有根据植物种属由不同的部门独立审批,也没有对植物品种权客体的植物种属进行限制。因此,将植物新品种权的行政审批权归由同一部门管理、取消保护名录的限制也有助于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与国际接轨。
3.2 在方法专利延及所述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一般规定下,针对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设置例外,增强专利法体系内部的逻辑严密性,避免法条之间相互抵触《专利法》第25 条将植物品种排除于专利权之外,《专利审查指南》中明确了排除的植物品种包括植物,同时还规定生产植物的非生物学方法不排除于专利权之外,这就造成了植物品种相关专利只给予生产植物的非生物学生产方法而不保护任何植物。然而,由于《专利法》第11 条规定了方法专利权延及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因此对于生产植物的非生物学方法专利权,根据《专利法》第11条则能够使植物主题通过所述方法专利获得保护,这就导致了《专利法》第25 条和第11 条之间的逻辑不严密[4]。
中国的专利制度是在借鉴欧洲专利公约(EPC)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专利体系中,在方法专利权的保护延及所述方法直接获得产品的一般原则前提下,对于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还进行了特殊规定,从而解决了不排除植物非生物学生产方法而排除植物品种、方法专利延及其直接获得的产品二者之间的逻辑抵触。中国同样可以借鉴欧洲专利法的上述规定,通过设置特殊规定完善《专利法》第25 条和第11 条之间的逻辑。
3.3 将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中植物品种的含义统一,加强二者之间的衔接,避免植物育种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真空目前植物新品种的两种权利形式呈现出融合、并存的趋势。品种权与专利权融合、并存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或扩大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要么以专利权保护为主、品种权保护为辅,植物新品种相关专利涵盖植物新品种相关的所有发明创造;要么以品种权保护为主、专利权保护为辅,植物品种相关专利只给予品种权客体之外的发明创造[5]。《专利审查指南2010(2019年修订)》中解释了专利权排除植物品种的原因在于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给予保护,因此《专利法》排除植物品种的立法本意在于使植物品种相关技术在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之间相互衔接。然而,在实践中专利权排除的植物品种采用了扩大化解释,而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植物品种则采用了严谨的解释,导致二者之间的衔接脱节,造成了产业上具有育种价值、最能体现智慧贡献的植物群体、植株以及植物繁殖材料无法获得任何知识产权的保护。
4 结论
我国的植物育种技术和育种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育种相关的知识产权体系初步建立,然而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尚未能有效衔接,无法充分发挥植物育种相关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的优势。突出的问题在于具有较高育种价值、但尚未形成植物品种的中间育种材料既不能受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也不能受到专利权的保护。此外,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受到保护名录的限制,专利保护体系中也存在《专利法》第25 条和第11 条之间逻辑不严密的疑问。针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植物育种相关的知识产权体系的措施和建议。从立法层面,完善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相关法律,增强其相互协调性;从行政审批层面,对植物新品种权的审定进行统一管理,专利审查中对涉及植物品种条款的执行标准进行优化。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