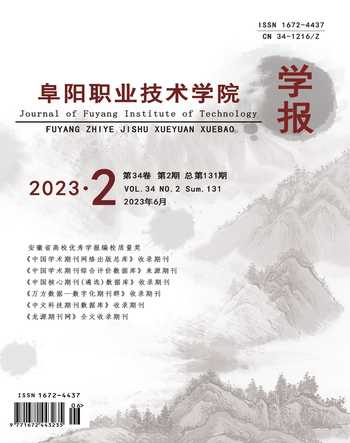《悦耳的猪叫声》中历史记忆下的个体命运书写
刘恒
摘 要:达蒙·加尔古特的《悦耳的猪叫声》再现了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女性的个体命运,同时又以个人历史书写的方式映射了南非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从囿于“女性奥秘”的家庭主妇,到打破“美貌神话”的独立女性,再到屈从父权体系的白人妇女,埃伦在父权制社会的妥协—抗争—妥协揭示了南非白人女性的生存困境。文章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探讨埃伦在种族隔离时期由遵从女性性别角色、重构女性身份认同到追寻自我归属的嬗变。
关键词:《悦耳的猪叫声》;父权制;“女性奥秘”;“美貌神话”;达蒙·加尔古特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3)02-0071-05
达蒙·加尔古特是南非小说家和剧作家。《悦耳的猪叫声》问世于1991年,是加尔古特写作生涯中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第一部获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泰晤士报》盛赞该小说为“一部心理观察与政治分析同样巧妙的作品”。该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在20世纪80年代的南部非洲,此时纳米比亚(旧称西南非洲)的种族隔离正被逐步废除,殖民主义正在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行将就木。小说围绕主人公帕特里克展开,故事的主体部分发生在1989年纳米比亚举行历史上首次自由民主选举的前一周,叙事中穿插着帕特里克对童年时光、家庭往事和军队服役的回忆。帕特里克曾是一名驻扎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边界的南非白人士兵,在非正义的南非边境战争①中,他不仅亲身经历了残酷血腥的丛林战争,还痛失了他在军队中的唯一挚友拉皮斯,这给他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最终不到一年就因精神崩溃而退伍。退伍十个月后,他陪同母亲埃伦去纳米比亚见她的恋人戈弗雷,再次踏上了这片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土地,并且目睹了它即将走向独立的历史性时刻。
《悦耳的猪叫声》是加尔古特的早期作品,学者们分析了作品中的后殖民性、人的动物性、男子气概和双重人格等,研究对象往往集中在男性人物上,而对女性人物的研究寥寥无几。作为帕特里克的母亲,埃伦是小说里最主要的女性人物,她的人生经历具有典型性和悲剧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女性的社会生存困境。因此,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讨埃伦在种族隔离时期面临的性别角色、身份认同和归属追寻问题。
一、陷于囚笼的家庭主妇与母亲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是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白人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拥有支配性特权。父权制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不鼓励女性独立,希望女性依附于男性和家庭存在。白人女性虽不同于黑人与有色人,属于南非的统治阶级,但在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仍然受到一定的压迫和歧视。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和从前比起来,现在的社会风俗即使对女人的约束较小,这种消极的放任并不能彻底改变女人的处境,她还是被拘囚在附庸的地位。”[1]1125 埃倫是一位阿非利卡②农场主的女儿,20岁时因怀孕而辍学,嫁给了霍华德,成了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马尔科姆与帕特里克。结婚之后,“她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母亲,一个家庭缔造者。”[2]8
埃伦在大学里学的是戏剧,尽管后来也确实尝试过一些表演工作,但她从未真正拥有过自己的事业。不仅如此,她还按照霍华德所期望的形象重新塑造自己。霍华德是英裔南非人,他对埃伦乡土气息浓厚的阿非利卡出身感到羞愧,为此她练就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另外,她将培养自己都市阶层的志趣和价值观作为本分,竭力融入新的社交圈子。等到帕特里克出生的时候,埃尔莎·德·布鲁因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埃伦·温特:一个或许是出生在康斯坦提亚的人。作为交换,霍华德给予她丰厚优渥的物质生活。她曾对帕特里克气愤地说:“我是匆匆忙忙长大的。”[2]9从埃尔莎·德·布鲁因到埃伦·温特,这不仅仅是姓名的改变,更暗含了在父权文化下霍华德完成了对埃伦的控制与塑造。霍华德通过剥夺埃伦的阿非利卡文化身份,对她建构新的价值理念,使她成为了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的家庭主妇。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批驳了“女性的奥秘”——盛行于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贝蒂认为,通过大众传媒、性别教育、商品营销等方式,“女性奥秘论告诉人们,女人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3]35 埃伦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女性奥秘”价值体系的影响,她致力于完善自身的女性特征,使自己符合它所宣扬的女性形象。“她晚上会坐在书房里的一张真皮扶手椅上,手里忙活着织锦、缝纫或者写信。她说话时轻声细语。”[2]11 她“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很优雅,手臂伸展,紧贴在身旁。”[2]10 然而步入婚姻后,“女性奥秘”给广大妇女带来的并不是充实美满的家庭生活,而是令她们烦恼苦闷的“无名的问题”:“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3]1 于埃伦而言,婚姻与家庭已然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最终她从身穿深色连衣裙、扎着两条辫子、缺了颗门牙却咧嘴大笑的阿非利卡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年轻苍白的妻子,“她的过去被永远褫夺,在一个美丽的真空中打旋。”[2]20
埃伦在成为家庭主妇的同时,还拥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母亲。艾德里安·里奇认为母亲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压迫女性的父权制度,但如果允许女性定义与践行母性,那么母性就有可能赋予她们权力。她在《生于妇人》中写到,“我试图分辨母亲身份的两种意义,两种相互重叠的意义:女性同其生育能力与孩子的潜在关系;以及这种制度,它旨在确保上述潜在关系和所有的女性处于男性的控制之下。”[4] 然而埃伦在母性的体验中并未与其孩子建立紧密的情感纽带,也未能摆脱母亲身份的内在桎梏,在性别角色与父权机制的双重压力下,失去了自我,沦为家庭生活的附属品。埃伦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麻木的。空虚无助的生活使她的情绪像她的脸一样平静而茫然,她非常安静,经常独自坐在椅子上,沉浸于冰冷的幻想中,听着时钟弥漫在整个空寂房子里的滴答声。在帕特里克的记忆中,“那些年她没怎么笑过。我记得那是一张沉着冷静、若有所失、毫无血色的脸,眼睛又大又黑,睫毛很长。还有她那硬邦邦的嘴,嘴唇有点儿太薄,不太性感。这本可以是一张冷酷的脸,但是在她身上却感受不到一丝冷酷。”[2]9 在母性的驱使之下,即使面对霍华德的出轨,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也选择了隐忍与妥协。她有且仅有一次在睡梦中叫喊了出来,那是一声悠长、缠结且痛苦的呻吟:“霍华德…霍伊…你到底做了…什么…?”[2]11 可是埃伦在婚姻里的一味忍让使她变得愈发压抑与绝望,马尔科姆在20岁时的意外死亡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马尔科姆死后不到四个月,她就与霍华德离了婚,带着帕特里克搬出了那豪华的三层别墅,住进开普敦的一个小屋里。
埃伦深受父权制下性别角色的羁绊,落入了“女性奥秘”编织的“幸福的家庭主妇”之网,为深沉的母性和母亲身份所困,终究成了为家庭与孩子自我牺牲的“殉道者”。
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身份认同
离婚后的埃伦挣脱了父权制的枷锁,成为了独立的女人,如获新生,开始探求身为女性的自我价值。帕特里克回忆说:“我的母亲也变了,变得如此彻底,如此突然,但是与我父亲的改变截然不同。”[2]19 她曾经是个全心全意、温柔顺从的妻子,如今卸下了作为妻子所承载的重负,仿佛这个角色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在与帕特里克搬出霍华德住宅的几天后,埃伦向帕特里克吐露了心声,“我第一次找回了自我,帕特里克。在此之前,我的一切都不过是在表演罢了。”[2]20 她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但是此刻的她究竟是谁,是个连她都无法触及的谜。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她却在二十载的婚姻里痛苦地停滞不前,对家庭之外的广阔世界浑然不知。“她总是坐立不安,彷徨四顾,四处走动。”[2]20 由静到动,不仅隐含了埃伦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且预示着她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对生活的使命感的萌发。
家庭不再是埃伦唯一的生活与生存领域,她开始踏足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这是她从私人领域迈入公共领域的表征。她疯狂地投身于各式各样的时尚和运动,参加各类俱乐部和协会。此外,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政治产生了高涨的热情。她先是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她为动物权利奔走呼号,不惜冒着雨站在街角,手举醒目的标语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后来她从动物权利转向人权,既反对霍华德所代表的父权制资本主义,也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先后加入“黑肩带”组织③、终止征兵制运动和被拘留者父母声援委员会(DPSC)。
埃伦诉诸于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同时,还抛却对“美貌”的执念,进行着对父权文化无声的抗议。娜奥米·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中写到,“‘美貌像金本位制一样是一种货币制度。同任何经济一样,它是由政治决定的,并且在现代西方社会,它是最后也是最好的一套捍卫男性支配地位的信仰体系。根据文化建构的体格标准,在纵向等级制度中赋予女性价值,这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表现,在这类权力关系中,女性必须近乎反常地相互争夺男性已占为己有的资源。”[5] 在沃尔夫看来,“美貌”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操控下成为了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而对于“美貌”的崇拜使女性无形之中成为父权制的同谋者。在“美貌”效应的催化下,男性通过规训和凝视实现了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埃伦在离婚前一直生活在男性的凝视之下,帕特里克坦言道:“我以前从未见过她脸上的皮肤,没见过它细微的斑点。”[2]21 离婚之后,埃伦不再化精致的妆容,不再刮腿毛和腋毛,这正是她对男性凝视的消解,坦然接纳身为女性的自己。与“美貌”息息相关的服饰话语也对女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服饰是身份的表征,它可以表明女性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正如波伏娃所说:“服饰具有社会的意涵,所以女人可以借着穿着打扮来表达她在这个社会的立身态度。”[1]912 埃伦当霍华德妻子时穿的衣服全部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牛仔裤、运动鞋以及饰有标语的T血衫。她借助服饰话语来反抗父权话语体系,以此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身份,塑造了一个打破社会陈规、积极进取、生气勃勃的现代女性形象。
在感情方面,她几乎和霍华德一样频繁地更换伴侣,但二者的动机却判然不同。对霍华德来说,她们全是埃伦的替代品,每一个都是光彩夺目、短暂的匆匆过客,只为填补他内心情感的缺失。离婚后,霍华德追忆着与埃伦的昔日时光,对埃伦脱离他掌控的事实感到伤感。“我父亲以前从来没和她如此分离和疏远过,现在远远地注视着她的一切。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问我关于她的事情。”[2]22霍华德从离婚前的漠不关心到离婚后的殷切关注,折射了他中心地位的丧失以及他与埃伦之间权力关系的转换。“他为她的离去悲伤无比,而我的母亲从未回头。”[2]21 过去是作为客体存在的家庭主妇,如今埃伦的情感抽离凸显了她的主体性,她以无言的方式瓦解了霍华德的男权话语。埃伦的自我解放和对性的寻求并非是对霍华德婚姻背叛的报复,而是出于女性自我满足的需求。她交往的恋人有嬉皮士、会计、激进分子和学生等,不全是男性,但唯独没有像霍华德一样油滑的商人。在事业方面,她又开始尝试表演了,重拾为婚姻所扼杀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但是她不够自信,或者说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以至于她只能得到一些小角色。然而生活的独立也需要经济自主的保障。因此,在纳米比亚一所学校里担任讲师的老朋友邀请她去那里暂时代替别人上一学期课的时候,她当即接受了。去温得和克(今纳米比亚首都)教授戏剧解决了她在经济与事业上遭遇的困境。对她来说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改变,而此刻的她正对改变如饥似渴,这也为后来她从女性身份认同过渡到自我归属追寻埋下了伏笔。
结束与霍华德的婚姻让埃伦突破了父权制的束缚,激发了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并由此展开对父权话语体系有声与无声的反抗。通过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与对生活的使命,埃伦实现了从家庭主妇到独立女性的嬗变。
三、游离于黑白之间的白人女性
为了寻求事业的发展,同时为了谋求经济的独立,埃伦来到纳米比亚,开启了短暂的戏剧教学生涯,也正是在此期间她与戈弗雷相识以及相恋。戈弗雷是她所教的一个五人班里的学生,當时是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她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戈弗雷的存在,但不是因为他很有魅力,而是因为他对她的态度粗鲁,令她厌恶。她上课时,他总是极力展示着他的无聊与烦闷:打哈欠、动来晃去与四处张望。不宁唯是,他还上课迟到,一直盯着窗外看,将她视如草芥。他的这些行为让她愤怒不已,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她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埃伦终于忍无可忍在课上与他对峙,而他在下课后面对她时却一反常态,与平时判若两人,“说真的,他人很好。有一点点害羞,也有一点点温柔。”[2]44-45 他请求埃伦给他“单独补习”,因为他跟不上埃伦的课。她对他的意图一清二楚,起初并未答应,但后面被他持之以恒的精神所打动。“她最终还是让步了,邀请他到她房间里上‘额外的课,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无可避免了。”[2]45 帕特里克曾这样描述埃伦离婚后的情感经历:“这些年我看见很多恋人从我母亲的卧室里走过: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男的,有女的,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在她生活中的转瞬即逝。我母亲的每一段风流韵事都很短暂。”[2]43 帕特里克以为埃伦回到南非后,她的激情会很快消散,和戈弗雷通话几周后就会心生厌倦,她会另觅新欢,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此结束。然而他们的通话持续了一年半,为了见他,她再次去往温得和克。
埃伦虽然乐于尝试,坦率开明,但在认识戈弗雷之前从未与黑人交往过。同她之前所有的恋情一样,她在寻找戈弗雷所代表的理念。在她看来,黑人是非洲大陆的原住民,是白人与非洲大陆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戈弗雷是一个光芒四射的理念,与他交媾是一种“政治行为”,可以建立她与非洲大陆的连接,成为真正的非洲人。“她最近一直在谈论自己是非洲人,谈论与非洲大陆的紧密相连。”[2]43 埃伦试图重新审视她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在瞬息万变、风雨飘摇的社会中找寻一份归属感。纳米比亚即将实现国家独立和种族解放,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大厦将倾,为了摆脱新的身份危机,她不惜再度沦为父权制下“美貌”的“囚徒”。在温得和克再次与戈弗雷见面之前,埃伦花了很长时间做精心的准备。她穿的是白色的衬衫、绿色的裙子和一双凉鞋,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她不仅化了妆,喷了香水,还刮了腿毛。可是在与霍华德离婚后,她发誓往后不会再使用化妆品和香水,也不会再刮腿毛和腋毛。成为独立女性后的埃伦为了消解男性凝视,毅然决然抛弃了“美貌”,然而如今,为了迎合男性凝视,她又重拾了“美貌”。埃伦对“美貌”再次转变态度也折射了她与戈弗雷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她第一次去纳米比亚时,纳米比亚仍处于南非的殖民统治之下,但种族隔离制度日渐式微。她是白人和教师,戈弗雷是黑人和她的学生。然而她第二次去納米比亚时,纳米比亚即将成为一个由黑人当家作主的独立国家,她不再是老师,戈弗雷也不再是学生,而是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④效力的激进分子。他们久别重逢时,不难看出两者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戈弗雷被赋予了权力话语,在他和埃伦的权力关系中占据主体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由最初的和谐融洽逐渐发展为矛盾丛生与针锋相对。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戈弗雷对埃伦控诉道:“你认为你现在与其他白人不一样。你觉得自己很激进、很了不起。为什么?就因为你在睡一个黑人?你以为你能把历史抹得一干二净吗,埃伦?你是这样想的吗?……休想让我闭嘴。我不是你的黑仔,明白吗?你好好听我说。我来告诉你这里发生了什么。我来告诉你关于强制搬迁的事情。我来告诉你何为班图教育⑤。以及库武特⑥的行径,军队在边境的所作所为。我来告诉你——”[2]92 此时根植于戈弗雷内心深处的种族仇恨跃然纸上,同时将埃伦奋力融入黑人社会的理想彻底击碎。种族隔离给黑人族群造成的伤害使戈弗雷不可能真正接纳埃伦,埃伦也不可能完全融入黑人世界。“这次的离开凛若冰霜。像她以满腔热情从事的崇高事业一样,他开始在她眼中变得暗淡无光……他不再是个理念;他太真实了。” [2]113-114
埃伦终究还是选择了与戈弗雷分道扬镳,这意味着她从白人社会转向黑人社会找寻归属的失败。对此,莎拉·纳塔尔在《文本,理论,空间》中这样评价埃伦:“对她来说,与非洲的关系引发了一场身份危机,并导致一个自由主义斗争的故事。她设法融入非洲大地,但未能成功。‘背井离乡,缺失过去,不过她仍然是非洲人:这片畸形大陆的产物。她虽然渴望归属,但是不知归属在何处。她在岩石中寻找她的根。”[6]与戈弗雷决裂后,埃伦转身投向在纳米比亚相识的迪尔克·布拉奥。一行三人返回南非的途中,迪尔克邀请埃伦和帕特里克去他位于南非西海岸的农场。尽管小说以他们三人入境南非为结尾,但是从埃伦对迪尔克邀请的欣然接受、她对他的态度以及两人之间的暧昧,可以推断出他们接下来会发展为恋人关系。然而迪尔克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和男权中心主义者,除了不是油滑的商人外,他几乎与霍华德别无二致。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重回父权制的牢笼,这无疑是时代与命运对埃伦的捉弄。在非洲大陆寻求归属的过程中,埃伦在离婚后所形成的女性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消失殆尽。
作为一名白人女性,埃伦在种族隔离制度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际积极探索与非洲大陆的关系,竭力融入黑人社会,渴望成为真正的非洲人。但是横亘在黑白种族之间的仇视与偏见使她只能在白人社会寻求归属,最终她再次步入父权制的樊笼。
四、结语
加尔古特的书写紧扣南非特殊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以个人历史书写的方式映射南非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探索个体在历史巨变中的身份认同,同时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或种族主义遗留问题进行着反思。他的作品均是以男性人物为主线进行叙事,女性人物往往是陪衬性质的“功能型”角色。但是在男性叙事中充分挖掘女性人物的个体命运,更能勾勒出一幅清晰完整的历史画卷。对《悦耳的猪叫声》中埃伦的研究便是如此。从囿于“女性奥秘”的家庭主妇,到打破“美貌神话”的独立女性,再到屈从父权体系的白人妇女,埃伦对父权制的妥协—抗争—妥协揭示了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女性的社会生存困境。陷入苦闷彷徨的家庭主妇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和对生活的使命才能走出“女性奥秘”的陷阱。另外,女性应当抛却对受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操控的“美貌”的执念,并借助服饰话语来表明自身的主体价值和文化身份,消解男性凝视,反抗父权话语体系。然而埃伦寻求在非洲大陆归属的过程中,再次回到父权制的囚笼,这暗示了南非白人女性在种族隔离时代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不可能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因此,只有当南非实现真正的种族和解和性别平等,白人女性才能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权力、独立、自由与归属。
注解:
①南非边境战争(The South African Border War),又称纳米比亚独立战争,在南非有时称安哥拉丛林战争,是南非为维护其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于1966年8月26日到1990年3月21日在纳米比亚、赞比亚及安哥拉发动的非对称战争。
②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指以17至19世纪移民南非的荷兰裔为主,融合法国和德国移民后裔形成的白人民族,说阿非利卡语。
③“黑肩带”(The Black Sash),是于1955年在约翰内斯堡成立的非暴力抵抗组织。该组织主要由南非白人妇女组成,其成员身披黑肩带以示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抗议。
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成立于1960年,领导了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被认作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自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以来一直是该国的执政党,简称人组党。
⑤班图教育(Bantu Education),根据1953年颁布的《班图教育法》,南非政府将种族隔离制度引入教育领域,推行针对不同种族的教育体制,对黑人进行奴化教育,意欲培养廉价的劳动力。
⑥库武特(Koevoet),纳米比亚独立前南非殖民政府支持的搜捕人组党解放军的警察部队。
参考文献:
[1]西蒙·德·波娃.第二性:第2卷[M].邱瑞鑾,译.台湾:猫头鹰出版社,2013.
[2]Damon Galgut,The Beautiful Screaming of Pigs[M]. London:Atlantic Books,2015.
[3]贝蒂·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4]Adrienne Rich,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M].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1995:13.
[5]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2:12.
[6]Kate Darian-Smith, Liz Gunner, Sarah Nuttall.Text, Theory, Space: Lan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and Australia[M]. London: Routledge,200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