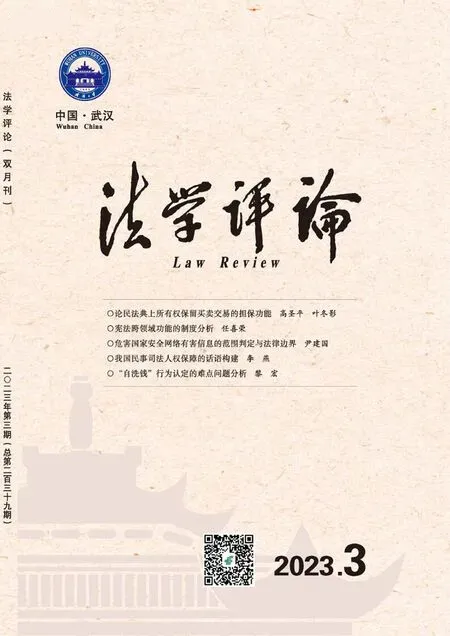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与法律边界*
尹建国
导 言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往往与煽动分裂国家、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仇恨等问题紧密相连,直接威胁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之基石,是世界多国均高度警惕并重点打击的有害信息类型。缘于国家安全概念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并基于不同国家面临的不同历史传统、制度背景、文化特征和社会共识,各国对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内涵与外延之界定并不一致,并在具体判断标准和边界勘定方面存在较多模糊之处。对我国而言,作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践行有别于西方政党制度和政治道路、尚未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已进入各类国家安全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爆发时期。新形势之下,亟需统一、明确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围,这不仅体现着我国网络信息规制的口径和网络法治发展的程度,更是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国家安全权益的客观前提和基本保障。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主体,以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为补充的维护国家安全和规范网络言论表达的法律体系。但缘于规范类型的多元化、条文设计的粗放型等特点,相关立法在统一性、明确性、合理性等方面,尚存一定欠缺。(2)参见尹建国:《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由此导致相关法律在适用时也呈现较多争议和困境:一方面,适法者难以确立统一、明确的解释和具体化规则,有损裁判结论的说服力、公信力,会增加权力滥用的风险,或导致恐惧禁言的“寒蝉效应”。另一方面,裁判标准和说理论证过程的缺失,为敌对势力基于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事后攻击留下了“口实”,当指责似是而非时,容易产生迷惑和煽动的负面后果。
鉴于此,本文拟重点以《网络安全法》第12条、《国家安全法》第2条等相关规定为切入点,意图通过理论分析、法律解释、实证研究、比较观察等方式,就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类型建构、法律范围和排除规则等提出相对明确、统一的意见与建议。具体而言,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从理论上揭示“国家安全”概念之内涵,并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界定其外延;二是梳理和归纳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在实际执法和司法案件中的现实表征和基本类型;三是比较观察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法律原则和微观标准,并讨论确立符合我国国情之明确判准的正当性和可行方式;四是基于平衡表达自由、国家安全等多元权益之立场,反向确立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典型排除情形。
一、“国家安全”概念的核心内涵与现时外延
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之范围,首要前提在于明晰“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与现时外延,这是后续判定标准赖以确立的基础。
(一)国家安全概念的主要学说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具有相对普适性和稳定性,但也存在国域差异及历史变动性。欧美各国一般对国家安全定义持“状态说”(3)See Paleri, Prabhakaran, National Security: Imperatives and Chall enges, New Delhi:Tata McGraw-Hill, 2008, p. 52.和“能力说”(4)See Harold Brown,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Dangerous World,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83, p. 4.两种观点。在我国,学界界定国家安全核心内涵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其一,“能力说”。该观点将国家安全归结为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某些能力,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控制边界以及防止外力击垮其特质、体制和统治等“能力”。(5)参见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采用单一“能力说”界定国家安全概念的方式已不多见,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坚持这种观点。
其二,“状态说”。该说认为,国家安全一般指“一国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国家权益有机统一性、整体性免受任何势力侵害的一种状况。”(6)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持该说的国内论者数量较多,且学界对于这种状态的属性还存在“客观一元说”与“主客观二元说”的争论。(7)参见刘跃进:《国内关于安全是否具有主观性的分歧和争论》,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其中,前者认为,国家安全仅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8)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后者则主张国家安全是客观状态和主观认知的结合。(9)参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相较而言,“客观一元说”目前拥趸更多,即认为安全属于客观存在,而主观的安全感因人而异、虚无缥缈且难以外显、外证,放大主观特性将进一步增加国家安全概念之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三,“利益说”。该说认为,国家安全之本质是国家利益问题。(10)参见甘培忠、王丹:《“国家安全”的审查标准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市场准入视角》,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5期。并且,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其他具体利益得到保障从而免于损失威胁的元利益”,是“国家的第一需要。”(11)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这种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利益、军事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科技利益、生态利益、外交利益等。“利益说”揭示了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但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一样属于高度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本身也具有模糊性。(12)参见杨宗科:《论<国家安全法>的基本法律属性》,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
其四,“综合说”。该说兼采多种观点,从多方面综合界定国家安全范畴。我国现行《国家安全法》第2条规定,国家安全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此种界定方式将“重大利益”“状态”“能力”等要素有机结合,是以“综合说”界定国家安全概念的典型表现。
(二)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科学界定
比较观察相关立法和学说,可以发现,“综合说”较为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安全概念的核心要素。这种界定相较于偏重一隅的其他观点,既避免了僵化地审视安全状态,又避免了过分强调安全能力的弊端,能够实现“国家安全状态与国家安全能力的有机平衡”。(13)参见李文良:《国家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故宜将“综合说”作为界定国家安全概念的最佳选择,同时也应兼采其他相关立法、政策和学说的科学要素,以准确、全面、充分揭示国家安全之内涵与外延。
第一,国家安全是一个法律概念,应立基于现行权威法律文本界定其内涵与外延。整体上,我国《宪法》第1条、4条、28条、29条、52条、54条等,对我国政体、国体、政党制度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国家安全、国家荣誉和利益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奠定了其他领域国家安全立法的基础。我国《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刑法》相关条款则对通过网络发表和传播有害信息作了整体限制性规定,上述立法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与内容治理的基本依据。其中,2015年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第2条首次相对明确地界定了国家安全的法定概念,且采取了“综合说”的界定方式。《刑法》则从相对狭义角度对国家安全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其概括为“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即限于《国家安全法》第15条所列举的“国家政权安全”部分。显然,作为专门法,《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内涵之界定和外延之揭示,更为全面和准确。故科学界定国家安全之内涵,应首先立足于《国家安全法》之全面和广义规定,仅在涉及刑事领域的国家安全类犯罪之出入罪问题时,方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采行《刑法》中的狭义界定。
第二,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外延具有历时变动性,当前必须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一致。当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各界对国家安全局势会有不同的认识,对国家安全概念内涵、外延之认识则与主体所持“国家安全观”密切相关。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已从最初的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军事安全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安全观逐步转变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合作对话为手段的“总体国家安全观”。(14)参见杨宗科、张永林:《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道路七十年探索:历程与经验》,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而应当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多方面的内容。(15)参见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在网络时代,以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为主体的网络安全还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影响。(16)参见杨蓉:《从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到算法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网络法律治理》,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将跟随时代继续演绎变化,并会以开放的态势发展得更加丰富和全面。
第三,国家安全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利益,前者的内涵和外延均窄于后者。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国家安全利益是其他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前提,但国家安全无法包括全部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国家安全只是其中的基础性、前提性和最核心构成部分。(17)参见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因此,不能将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两者混同,更不宜因之“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概括而言,国家安全具有鲜明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特征,当前可在学理层面将我国国家安全之内涵与外延科学界定为:国家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客观状态,以及保障国家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其以人民安全为根本目的,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构成内容和要素,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和最核心构成部分。
在国家安全上述构成内容中,有些安全类型主要受行为威胁,言论对这类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这在涉及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领域体现的较为明显。发生于这些领域的国家安全事件,往往是具体的行为,言论信息在其中往往起伴随性、次要性或工具性的作用。同时,国家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风险主要指一国面临的市场信息安全、交易安全、金融安全等风险威胁。(18)参见何杰等:《网络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治理研究——一项基于指标体系和安全数据的区域比较研究》,载《情报杂志》2019年第1期。该风险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受不实信息的误导与欺骗,二是遭遇信息泄露。(19)参见曾润喜等:《网络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载《电子政务》2019年第3期。这两类安全风险与网络有害信息均有一定关系,尤其是前一风险系直接由网络虚假性有害信息所引起。但这类违法案件往往同时侵犯企业、消费者或其他交易主体的商誉权、商标权或财产权等具体权益,在实践中多以民事侵权或操纵证券价格、刑事诈骗等类案形式呈现,根据我国《民法典》和《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等足以对该类信息进行打击和治理。在各界对网络犯罪本已普遍“降维打击”的时代,(20)参见刘艳红:《网络犯罪的法教义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0-151页。不宜将其“升格”为危害国家安全类案。
综上,在科学界定“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之上,可将“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之范围,主要界定为危害一国政治制度、政权稳定、国家统一、党的领导、国家荣誉和利益、政治意识形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等利益的网络虚假性、诽谤性或煽动性言论信息。其危及的国家安全利益集中于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并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思想文化等方面。
二、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类型建构与表现样态
基于上文对“国家安全”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概念界定与构成内容认识,笔者认为,当前环境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主要包括危害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三大基本类型,其在实践中则主要演绎为六种具体违法样态和典型类案。
(一)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基本类型
1.危害政治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处于“根本地位”。(21)参见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政治安全的首要问题是政权安全,其表现形式是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不受污辱,统治权力坚实稳固,其核心要义是坚定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2)参见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中共二十大报告等纲领性文件,将“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等列为新时期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任务。
当下,危害我国政治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主要体现为两种类型:第一,宣扬渗透、颠覆、暴力恐怖和分裂活动、宗教极端主义的网络有害信息。第二,宣扬诋毁、破坏、否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的网络有害信息。这两类有害信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集中体现为攻击、否定和破坏我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否定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党的先进性、合法性等方面。
2.危害文化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
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联系紧密,政治安全决定了文化安全的本质属性,文化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由之形成与构建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体系。(23)参见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法制建设:国家政治安全实现的根本保障——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法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丑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散布和传播网络有害信息方面,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文化安全实施的侵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和政治制度差异,就涉藏、涉疆、涉台、涉港等议题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第二,利用“学术自由”外衣,系统推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分权等政治制度判断标准和“新冷战式”学术解释标准和科研、教学评价指标,抢占理论与话语权标准,试图压制和颠覆中国文化创造力和优越感。(24)参见温铁军:《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再版序言”第17-31页。第三,有组织地歪曲历史、否定党史、丑化英雄人物及事迹,推行历史虚无主义,意图瓦解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向心力。
3.危害社会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
社会安全是社会系统能够稳定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最小化不安全因素及其影响、各个群体能够通过社会建构稳定持续地得到安全保障的能力和机制。(25)参见王龙、霍国庆:《社会安全的本源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实证研究》,载《管理评论》2019年第11期。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社会安全事件与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并列。学界则认为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26)参见戚建刚:《中国行政应急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具有较为强烈的主观故意、“人为痕迹”。(27)参见杨海坤、马迅:《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应急法治新视野——以社会安全事件为视角》,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
新常态之下,我国社会安全的威胁因素主要集中于:第一,因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造成重大社会安全危机。(28)参见王国华等:《重大社会安全事件的微博传播特征研究》,载《情报杂志》2014年第8期。第二,因群体性事件导致社会动荡和恐慌。(29)参见郭强:《论新形势下的社会安全》,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2期。第三,因贫富差距、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受教育程度差异等造成社会割裂,进而导致公共事务讨论中的群体对立、攻击与谩骂。在这些社会安全威胁及相关事件中,通过网络发表虚假、错误、极端、煽动性言论,往往不可避免。这种有害信息之“危害性”,主要体现为威胁或破坏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表现样态
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三种安全类型,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交叉重复之处。故对大多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而言,其实际侵犯的国家安全类型可能同时包括两种或多种。这些有害信息在实践中的具体表征,可类型化为如下几种典型形式:
第一,通过网络散布、传播虚假、煽动、反动性言论,意图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面临多股分裂势力的侵扰和破坏。一是“藏独”势力,典型如“藏独”组织利用“哲瓦在线”网络对中国网民进行的煽动蛊惑和渗透策反等。(30)参见周光俊:《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挑战与应对》,载《情报杂志》2019年第7期。二是“疆独”势力,典型如“东突”组织长期利用“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等网站大力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害信息等。(31)参见王军:《观念政治视野下的网络空间国家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三是“台独”“港独”势力,典型如港台分裂势力利用“颜色利器”CloudFlare、Firechat、Code4HK等网络媒介和工具大肆发布、传播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各种虚假、煽动性信息等。(32)参见徐晓迪:《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香港“占中”事件反思》,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第二,通过网络发表和传播虚假、歪曲、污蔑性言论,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例如,马某某自2022年3月以来,充当境外敌对势力代理人,歪曲捏造事实,传播各类谣言信息,并逐步升级着手制定反宣纲领,筹备成立“大陆临时国会”,宣称要“借助境外的力量推翻中国政府”。(33)参见杜洋:《马某某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关情况》,载《法治日报》2022年5月5日第3版。
第三,通过网络发表和传播暴力恐怖言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如果说政治问题是言论自由的命门,是最醒目的红线,那么,民族宗教问题就是言论自由的雷区,是最敏感的神经。”(34)刘玉安、玄理:《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平衡》,载《东岳论丛》2015年第12期。而通过网络等媒介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暴力恐怖主义却一直是国家安全案件的典型样态,这在藏人受蛊惑自焚事件(35)参见程刚:《揭秘达赖集团蛊惑藏人自焚内幕 受美机构资助》,载《环球时报》2013年1月24日第5版。等典型案件中均有集中体现。
第四,利用信息网络发动意识形态战争,意图通过观念渗透威胁国家安全。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采取不同政治道路的国家,我国是西方意识形态攻击的重点对象。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运用“网络自由”等战略,一直对中国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封堵围截、恶意抹黑。(36)参见尹建国:《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机制及其对我国之启示》,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自由幌子之下的虚假陈述、歪曲误导,正是西方的“软性武器”和惯用手段。
第五,网络盲动力量受蛊惑或基于对现状不满,通过网络发表错误、片面、极端言论,诋毁和动摇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网民规模庞大,其中的部分主体或因确有冤屈,或因受到蛊惑和收买,会自行或煽动他人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缘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其真实意图和身份难以逐一判断。并且,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均衡问题客观存在。(37)参见蔡宝刚:《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法治理论》,载《法学》2022年第1期。有些个人与群体将社会落差归因于政治制度,不当放大具体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的问题,进而通过散布不当言论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客观地讲,这种言论的出发点可能“恶性”有限,因其寄希望于批评、揭露、抨击以实现公平与正义,但当这种言论超过必要界限并汇聚成整体力量尤其为外部势力所利用时,其危害性可能产生质变。
第六,通过网络发布歪曲、虚假信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歪曲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38)《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以所谓探求事实真相等名义诋毁英烈名誉、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等有害言论,在洪振快污蔑“狼牙山五壮士”案、(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第99号指导案例“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仇某明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权案(40)参见《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网民“辣笔小球”被批准逮捕》,载光明网,https://m.gmw.cn/baijia/2021-03/01/130213981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8日。等案件中均有体现。这些案件看似分散且并不触及抽象、宏观的国家安全问题,但点滴个案一旦串联形成合力,则可能瓦解国人的历史荣誉感、文化自信力和民族认同感,会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危及国家安全,不能不引起重视和警惕。
总之,作为一种“言论”,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所威胁的国家安全类型主要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三类,其在个案中往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推翻党的领导、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形式呈现。但是,由于此类信息大多属于“公共言论”,识别和治理此类信息也需兼顾国家安全和表达自由等多种权益之平衡。尤其是对那些致力于促进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改进党政机关工作作风、探求客观历史真相、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有益言论,即使言辞激烈甚至有所错误、偏颇,也应依法予以甄别并将其从“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中排除。这也为我们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围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初步类型化基础之上,还需辅之以探求更加深入、细致的判定原则和法律标准,对案涉信息予以“个殊化”地精准评估与识别。
三、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判定原则与具体标准
如上文所言,为在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等权益间寻求平衡,在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法律范围时,在初步类型化基础之上,还需进一步确立宏观的判定原则,勘定微观的判定标准。
(一)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基本原则:以比例原则为中心
根据消解法律概念不确定性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在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时,理应遵循明确性、平等对待等一般性法律原则。(41)参见尹建国:《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以下。此外,由于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主要涉及作为“国家法益”的国家安全与作为“个人法益”的表达自由间的冲突和竞合,故应受公法上比例原则之调整和影响。比例原则是在个案中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类有害信息时,应恪守的最重要、最能体现适法效果的核心原则。
根据比例原则,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之必要而须对表达自由等进行限制时,应尽可能选择侵害自由最小的手段,且所造成的利益侵害不得超过行为之目的所欲追求的价值。比较法上,运用比例原则以平衡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等权益之典型案例和学说见解屡见不鲜。在美国,在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个人权利保护问题上,其并没有基于人权保护而冒牺牲国家安全的风险,而是调整了寻求合理平衡的规则,灵活地采用着比例原则。(42)参见韩大元:《论中国宪法上的国家安全与人权的关系》,载《人权》2019年第5期。相关判决还以比例原则为基础,演绎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实质恶意”等诸多微观判准。在欧洲,比例原则肇始于德国公法,在需权衡言论自由、人权与国家安全等权利与价值时,往往依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以兹衡量。(43)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8-69页。德国对比例原则的理论与司法运用进一步影响到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欧洲人权法院往往将比例原则之下的适当性原则,作为平衡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案件的基本审查原则,并在该原则之下区分情况分别适用“人权保障优先”和“国家安全优先”两种分析和权衡模式。(44)参见荆超:《平衡国家安全与人权:欧洲人权法院适用适当性原则的分析模式及其运用实践》,载《人权研究》2021年第3期。
在我国,根据学界共识,比例原则已经由本体论迈向了方法论,成为一般化的法益衡量方案之中心。(45)参见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尤其当基本权利间发生冲突时,权利之间普遍性的位阶次序并不存在,此时需通过个案权衡寻求微观解决之道。(46)参见尹建国:《基本权利冲突视角下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载《法学》2023年第1期。在个案权衡以做“综合考量”之时,引入比例原则可以明确解释基本权利之保护范围,进而确定“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比例原则此时构成利益权衡的关键倚重手段。(47)参见王锴:《基本权利冲突及其解决思路》,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在事关国家安全的言论审查案件中,主要涉及作为“公共利益”的国家安全与作为“个人利益”的表达自由之冲突与均衡,比例原则无疑不可或缺。这不仅为学理所证成,也为我国《国家安全法》第66条所明示,(48)我国《国家安全法》第66条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还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案”(49)参见秦前红、黄明涛:《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5期。等经典案件中得到鲜明体现。
我国公法学界对比例原则具体内容之认识,向有“三阶论”(50)参见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等。和“二阶论”(51)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6页。之争,近年还发展出“四阶论”。(52)关于“四阶论”之提出和商榷,参见刘权:《比例原则适用的争议与反思》,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等。但整体而言,无论是哪种理论,均认为必要性原则乃是比例原则的基础,合比例原则(即均衡性)则属比例原则的“心脏”,代表在目的与手段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的精髓。(53)See Jeremy Kirk,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Characteris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1, no.1 1997, pp.1-61.简言之,比例原则对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之调整和影响,主要集中于必要性和合比例两个层面。
一方面,对言论进行限制具有必要性,即相关言论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已达到一定程度且不具备可豁免情形。笔者认为,证成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信息予以限制具有必要性,主要应考虑言论性质、言论价值和危害后果三方面要素。其中,就言论性质而言,对“禁止性言论”予以限制之必要性大于“限制性言论”;就言论价值而言,对“低价值言论”予以限制之必要性大于“高价值言论”;就危害后果而言,言论本身的内容、发表的时间和场域、发表的主体等均为影响因素。基于这三方面的考量并运用三层次的论证结构,可以判定案涉信息是否达到需予限制之必要,并充分支撑和回应必要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另一方面,相较于限制措施所侵犯的表达自由等利益,限制相关言论所欲实现的国家安全利益更大,两者应“合比例”。那么,如何判断限制手段产生的损害与目的追求的利益之大小及是否“合比例”呢?有学者通过剖析域内外司法判例,归纳出以“数字公式”判定是否“合比例”的特别方法:不限制危险言论的机会成本(OC1)×此成本兑现的可能(P1)是否大于限制危险言论的成本(OC2)×此成本兑现的可能(P2)。仅在OC1×P1>OC2×P2时,对言论的限制才满足合比例原则。(54)参见吴昱江:《试论比例原则在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平衡下的使用——以美国司法判例为鉴》,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3期。
数学和量化的方法固然直观并在形式上具有说服力,但难点可能在于如何确立成本的具体数量及可能性之准确比例的问题。确定这些数值仍需裁判者综合多种情节和因素加以系统研判,裁判者的主观意志仍不可避免。为防止因主观因素而使个案处理沦为武断与反复无常,需要裁判者在个案权衡和论证时,既要在程序上受制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一般性的说明理由程序限制,(55)参见尹建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说明理由》,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同时又在实体上最大限度考量、还原和回应相关立法条文、条文背后的立法精神与目的以及现时的国家安全环境与时局背景。论证“合比例”的“数学公式”,则可作为说理工具,并因循其提供的一套论证进路。
基于上述认识,在适用合比例原则判断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之范围时,离不开对我国独有之国情和阶段性的国家安全环境与任务之考察。我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但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却在日趋严峻。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个并不安宁的风险时代、动荡局势之中,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因素甚嚣尘上,近在咫尺。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在国家安全审查案件中,在对比例原则之口径把握上“适当趋严”,阶段性地倾向重视“国家安全利益优先”问题。因为暂时性的权利让渡和克制,乃是为更为长久、坚固的安定繁荣、民权保障争取空间。另外,在进行利益均衡时,必要之时需考虑在个案中引入《国家安全法》第56条明确提出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即在重大典型个案中组织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代表等,通过“一事一议”的个案风险评估形式,(56)参见汪全胜、宋琳璘:《政府信息公开中危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司法认定——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典型案例为考察对象》,载《网络空间安全》2020年第6期。据实确立案涉言论的危害后果,以专业评估方式,确保合比例子原则能在判定与审查过程中落到实处。
(二)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具体标准: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双阶理论”“双轨理论”及其演绎为主线
在比例原则的调整和框架之下,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还需辅之以构建更为微观的审查标准,以填补和充实比例原则的具体内涵与指向。
就言论审查标准而言,为各界援引和讨论最多的,无疑当属“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在言论审查案的司法发达史中,绝大多数审查标准均是围绕该标准而展开,该标准确立的考量因素、权衡方法和论证框架,是判断公权力干预和限制言论之合法、妥当与否的主线和基石——尽管对它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由两项要件构成:一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二是严重的危险。(57)See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 S. 379-380(1927).从发展历史看,该标准在美国的适用客观上存在历时变动性。但近年来,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以国家安全为名对信息等予以审查再次成为美国主流,这在针对中国的系列“特别关注”事件中表现得尤为鲜明。(58)参见刘岳川:《投资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及法律对策》,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在输出美式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之时,无不是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进行的。相关审查和限制,明显具有国家安全审查意识形态化特点,其不仅未限缩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反而明显降低了其适用条件。整体而言,“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为言论审查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标准。我们并不能将该标准视为平衡言论自由与言论限制的“金科玉律”,但该标准及其演进过程所体现的、为言论自由设定尽可能明确而清晰法律边界之努力,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59)参见刘玉安、玄理:《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平衡》,载《东岳论丛》2015年第12期。
除“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等审查标准之外,与比例原则相配套的还有著名的“双阶理论”和“双轨理论”,这两种理论系对限制言论做出的进一步细化、分层审查机制。其中,“双阶理论”将涉及言论内容的审查标准区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并对前者采用严格审查基准;对后者则依言论类型与所涉利益再次细分,仅在特定情况下加以限制。(60)See Geoffrey R. Stone, Louis M. Seidman, Cass R. Sunstein, Mark V. Tushnet& Pamela S. Karlan, The First Amendment(2nd ed.), Aspen Publishers, 2002, pp.139-280.“双轨理论”的核心是将对言论的规制区分为“基于内容的规制”和“内容中立的规制”,并适用不同之审查标准。(61)参见龚艳:《仇恨言论法律规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98页。一般来说,法院对前者采“严格审查基准”;对后者则强调审查和限制限于言论表达的时间、地点与方式等,一般不涉及言论内容。(62)See Clark v.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466 U.S.789, 805(1984).“双阶理论”与“双轨理论”为言论审查提供了更为精细的标准,是司法技术更臻成熟的表现。
上述审查标准虽然纷繁复杂,但仍体现出一些共同规律和稳定主线:一是比例原则之下,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应重点审查言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是否严重”“是否紧迫”,而判断“是否严重”的标准主要由言论的内容决定,“是否紧迫”的标准与言论的内容、发表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均有关联。二是言论审查标准和口径之把握,具有历时变动性,要结合现时社会背景、政治需要、舆论环境等“据实确定”。
基于对比例原则内涵之认识和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双阶”“双轨”理论之参照,并结合前文将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类型化为六种典型表征的归纳,笔者认为,可将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区分为两大类:(1)构成“禁止性言论”的“低价值言论”,主要包括四类:一是“藏独”“疆独”“台独”“港独”等势力散布、传播的意图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虚假、煽动、反动言论信息;二是意图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虚假、歪曲、污蔑性言论信息;三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言论信息;四是意图进行观念渗透、意图发动政治意识形态攻击的言论信息。(2)构成“限制性言论”的“(相对)高价值言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网络盲动力量受蛊惑或基于对现状不满,发表的错误、片面性言论信息;二是否定传统文化、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以及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虚假性言论信息。
这两类信息的差别是明显的,第一类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是明显的、即刻的、现时的;后一类对国家安全之威胁过程是持续的、相对缓慢的。但这并不是说两者的危害后果有明显区别,更不表示后者一定比前者危害小。只是因第一类信息的危害是明显的,基于“严重性”,故应允许适法者采取更迅速手段,在利益衡量时更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利益。由此导致认定该类信息违法之判准就“相对宽松”,若出现误判,毋宁把矫正和救济机会留给事后。但对第二类信息,由于其起作用过程相对缓慢,决策过程中有相对充分的审查、甄别和论辩时间,故认定其违法之判准就应“相对严格”,以尽量减少“误判”和“误杀”。
基于此,可在二分的基础上,对两类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设置和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1)对属于“禁止性言论”的第一类“低价值言论”,判定其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危害时,宜采“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并坚持“国家安全利益优先”倾向予以判定和治理。(2)对属于“限制性言论的”第二类“(相对)高价值言论”,应更多基于“内容中立的规制”标准,更多地从言论发布的主体、主观动机、发布时空、影响范围、实际危害后果等角度对之予以进一步的甄别与区别对待。相对而言,仅在这类信息发布主体影响力较大、发布和传播范围较为广泛、发布者主观有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攻击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等恶意、发布时空敏感而不合时宜、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或政治秩序产生严重危害等情形之一时,方可认定为符合法定标准的危害国家安全之有害信息。否则,应根据本文第四部分的“排除规则”,不将其“升格”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有害信息,而按一般的不良信息加以惩治、教育。
综上,比例原则是平衡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等权益的核心原则。比例原则指导之下,通过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以及“双轨”“双阶”理论,可将我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六种信息划分为两大类,并设置类型化的审查标准,这是据实判定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具体范围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径。
四、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排除事由与典型类型
在各界对网络违法与犯罪普遍进行“降维打击”的时代,为尽量减少对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误判”“误杀”,除正面归纳其基本类型和判断原则与标准之外,也有必要从反面排除和豁免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实质危害的网络“疑似有害信息”。
(一)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排除与豁免的法理和实践基础
将不在实质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疑似有害信息”加以排除和豁免,这种做法和态度的法理和实践基础是多元而充分的。
第一,其理论基础在于言论自由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在基本权利体系中,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属最高的一类。”(63)秦前红、李少文:《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言论自由具有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保障真实、增进幸福等多重价值。(64)See Robert Bork, “Neutral Principles and Some First Amendment Problems”,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47.1971, p.1.在国家利益面前,言论自由虽应受到一定让步和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当是谨慎和有限的。因为宽容不是纵容,审慎只为平衡,这不仅源自对言论自由基本价值之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本身的必然要求。
第二,其还具有尊重和保护网络政治表达、促进民主的特殊价值。人的个性和潜能发挥以政治表达自由为政治基础,而网络作为特殊的公共场域,能更好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协商、对话和社会共识的形成。“在一个社会中把言论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也就在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民主。”(65)[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1页。故在对网络公共言论进行控制时,应该把握好“度”,应尊重和保护网络政治表达之特别需要和宝贵渠道。(66)参见杨嵘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
第三,对大多政治性言论而言,法律惩治的基础往往不在于言论自身,而在于该言论会产生“严重后果”。判断抨击时政类公共性言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准在于,言论是否具有煽动或诱发集体反动行动的可能性。如果当事人既缺乏煽动或诱发集体反动行动的能力,又缺乏煽动或诱发的故意,还缺乏煽动或诱发的客观局势条件,就不应该将其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归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即便这种言论可能以较为激烈、不太理性、过于情绪化等方式表达。
第四,危害国家安全是较为特殊和严重的罪责和指控,往往与民族大义、爱国主义等紧密联系,一旦错误指控、强行加罪,恐构成当事人“难以承受之重”,故不能将侵犯一般法益的网络有害信息混同、泛化或“拔高”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国家安全涵盖多个方面,其对应的法益覆盖着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多个层次,但三者并不能混为一体。(67)参见李凤梅:《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范缺失及立法补正》,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某一具体领域或层面的安全问题,可能也会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但不能因此就将其定义为国家安全问题。
(二)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排除与豁免的典型类型
在上述理论与方针指导之下,笔者认为,在实践中至少有如下几种典型的“疑似有害信息”,应从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围中排除或豁免:
第一,表达政治性意见时的过激或抱怨性言论。“有关公共事务的辩论往往是言辞激烈、尖酸刻薄的,有时还包括令政府和官员不悦的尖锐攻击,但是这种辩论应该是不受约束的、活跃的和完全开放的。”(68)New York time v. Sullivan, 376 U.S. 254(1964).伴随激烈情绪的政治表达,仅为参与政治生活、发表政治意见的一种形式,不一定具有积极煽动危害国家政权等目的追求。究其本质,判断“有害性”,主要应看言论是否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观目的和现实可能性。很多政治表达中的过激、抱怨性言论,并不以推翻现有政权或分裂国家为目的,针对的仅是具体政策、制度或事件;目的是主张权益或表达现时看法、意见和思想,本质上不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性。(69)参见曾白凌:《国家权力与网络政治表达自由》,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因此,应将其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区分开来,不能动辄归责甚至归罪。
第二,属于学术问题的公共评论甚至错误观点。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会涉及政治、文化问题,不可避免会提出对现行政治、历史、法律、制度等的批评和商榷意见。这种意见系出于完善政策和制度、还原历史真相等理性和良善目的,而非意欲煽动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否定国家文化、瓦解民族共识等危险行为。此时即便有偏激、不当之辞,也不宜轻易上升到“法定有害”程度。同时,学术批评、艺术评论、知识探讨、思想交锋等学术言论往往被视为“可供公评之事项”,行为人对这些问题所为之评论,理应受到更大的宽容对待。(70)参见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我国有司法判决也旗帜鲜明地指出:“从促进学术争鸣以及净化学术风气角度而言,司法应为学术批评设定较为宽松的环境。”(71)参见周宁、申楠:《耿美玉诉饶毅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载《经济参考报》2021年12月14日第8版。换言之,学术观点本身是允许错误和不正确的,如果在法律上不允许偏激、错误、不当的观点,学术研究将畏首畏尾,最终的结果将是创新凋敝,满盘皆输。故在网络空间中,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72)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不应对涉政治及文化问题的学术讨论言论,施以严苛禁锢。
第三,部分失实或夸大的公共性言论。众多公共性言论均与作为一国生存与发展之基石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但其中也不乏大量针砭时弊、呼吁社会变革、践行公共辩论的有益言论。这类信息受制于虚拟时空并囿于发表者自身的各种局限,出现部分虚假、夸大、不全面、不理性之辞,恐在所难免。但因其发自公心,事关公益,故在将其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有害信息时,理应适用严格标准。诚如有学者所言:“当公民的言论关涉政治、公共管理、公众人物等公事时,基于言论自由的民主自治价值,即使该言论具有一定的虚假或者夸大成分,其可罚性也受到必要的限制。”(73)刘艳红:《网络犯罪的法教义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9页。
第四,针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性言论。针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性言论,在网络上大量存在。因这类批评“不好听”“刺耳”“有损形象”,被以违法犯罪甚至危害国家为由实施制裁的案件也有不少。“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即是典型代表,该案之所以先被公诉后又被撤回起诉,前后处理结果大相径庭,(74)参见宋识径:《陈平福发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案撤诉》,载《新京报》2012年12月18日第A12版。主要原因在于陈平福发表、转发的批评言论虽然刺耳,但并不具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恶意和客观危害。在现代法治社会,容纳针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言论,不仅是法治本身的应有之意,也是推行民主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75)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5页。因此,对于针对具体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言论——包括一些可能不正确、与事实不符的指责,也不宜轻易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
五、结语
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际、国内国家安全局势暗礁丛生、空前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7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全面、准确甄别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基本范围和法律边界,是新形势下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网络法治的必然选择和时代要求。而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所危害之国家安全利益,应当是国家排除内外威胁、保障持续安全的状态和能力,其主要危及的国家安全类型集中于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三个方面。判定此类有害信息,应遵循明确性、平等对待等法律原则,尤应奉比例原则之下的必要性与合比例原则为圭臬,并在个案中灵活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双阶”“双轨”等具体判准。在实践中,还应基于个案权衡,明示危害国家安全网络有害信息的排除与豁免情形,以在国家安全维护和表达自由等权益保障间寻求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