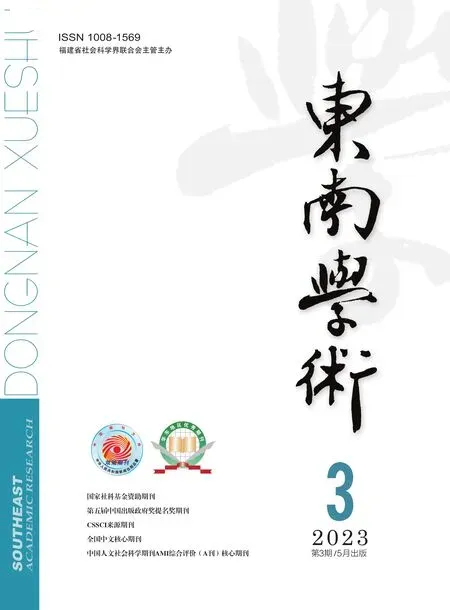知识翻译学视域下强制阐释的三个动因
陈开举
近十年来,随着对强制阐释的深入讨论和批评,以及公共阐释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中国阐释学研究呈现出日益繁盛的局面:主题突出、热点聚焦、成果丰硕。 这些研究的主线基本上沿着阐释的标准问题展开:一方面,无视文本的整体性而肢解文本,“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且将此意强加于文本,宣称文本即为此意”,①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 期。从而形成强制阐释;另一方面,以文本为归宿的阐释本身具有开放性,即阐释具有无限性,它们共同指向公共阐释,即“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②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 期。阐释的公共性、公共理性,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性,公共阐释的本质特征等一系列重大基础性课题的研究,为中国阐释学派的建构奠定了基础。③参见孙麾、陈开举主编:《中国阐释学的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前言”,第1-2 页。
阐释过程中,违反语言规定性会导致对文本基本语义意义的错误理解和阐释,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①关于话语理解中的基本意义问题,详见陈开举:《从语境看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6 期。基本语义理解正确,但是将阐释者自己先有的主观立场、观点乃至结论借文本之名阐释出来,则会导致强制阐释。 然而,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要动因从何而来,或曰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强制阐释的发生,既有研究还较少有专门的探讨。 本研究综合运用阐释学理论,聚焦作为阐释的典型形式之一的翻译实践,考察在翻译阐释过程中强制阐释最明显的三个动因,进而讨论译者应该如何规避干扰,克服可能形成的强制阐释性译文。
一、阐释、翻译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便于讨论,这里首先厘清两组基本概念。 其一,阐释与翻译。 阐释(hermeneutics),其英文词根中的Hermes 是希腊神话中神—人间的信使,他在神—人两重世界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转换中,相当分量的工作就是信息的语码转换,即是说,他所司职的阐释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翻译,跨越神—人两重世界的语码转换以实现意义的理解与传播。 这一点在阐释学教材中基本都有专门论及,如帕尔默的《诠释学》②理查德·E. 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 页。和潘德荣的《西方诠释学史》③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 页。等。 阐释学和翻译学界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了较多辨析,甚至直接提出翻译即阐释、阐释即翻译的观点。④杨宇威:《浅论“翻译即解释”在普遍诠释学时期的含义》,《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6年第12 期。如阐释学翻译理论家斯坦纳明确指出:理解即翻译,翻译即阐释,阐释即翻译。⑤乔治·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 页。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源流,翻译学界已有不少专门研究,在此不赘。⑥这方面的成果如杰里米·芒迪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和谢天振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本文聚焦翻译学近年来最新的知识翻译学视野,讨论强制阐释的三个动因。 知识翻译学是从整体上研究翻译的性质、内涵与特征的新兴翻译理论。 对于翻译的本质属性,该理论的倡导者杨枫说:“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翻译使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成为世界公共财富。”⑦杨枫:《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6 期。
其二,阐释与阐发。 阐释是围绕文本展开的,对文本的理解和意义的阐释总归要受到文本本身的束缚,即阐释必须以文本为归宿。 虽然超越文本本身的解释也普遍存在,但正如陈嘉映所说:“阐释虽有发挥,但仍以文本为归宿;阐发以文本为起点,以自己要说的为终点。”⑧陈嘉映:《谈谈阐释学中的几个常用概念》,《哲学研究》2020年第4 期。文本有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两大门类。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文本的意义是直显的,解释者的任务是对其中的意义加以说明,典型的如操作或功能说明书,对其中的意义的说明一般不存在争议。 然而,精神科学文本中一般除了字面意义之外,往往还蕴藏着作者不愿意或不能直接表达的意义,如曹雪芹寄寓在《红楼梦》中的“其中味”。 文学文本往往是作者暗含意图最多的文本形态,加上修辞手法等多重审美技巧的综合运用,文本字面意义外的蕴含意义十分丰富,为读者的欣赏、理解和解释提供了广阔空间。 愈是高明的作者愈能娴熟运用各种艺术技巧,藏思于文,吸引后人对其作品源源不断地阅读、欣赏、阐释,即是说,经典的文本必然引发无限的阐释。
文本的生产也好,对文本的理解也罢,操作的核心乃是通过文本传播意义。 文本生产和阐释的两端都出自作者和阐释者高度自觉的理性活动,寄寓在该活动之中的必然有着当事人意欲通过文本实现的自己的意图。 没有白说的话,也没有无寓意的故事,要透过话语或文本理解背后说话人的意图,这一点即使是很多生活阅历不多、知识积累尚浅的小学生也常常能明白,如:
(语境:学生没做家庭作业,撒谎说忘记将作业带到学校。)
老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学生(红脸):老师,别讲了,我是没有做家庭作业。
这里,学生的回答蕴含了一定的趣味:显然他准确理解了老师要讲的故事之基本信息,这是表面的、通俗的乃至无趣的;真正的趣味在于没有明说但是蕴含在文本字里行间的暗含意义,即言者/作者意图。 合格的理解和阐释必须将言者/作者意图抓取出来,换言之,言者/作者意图乃是判定阐释效度的标准。 又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 页。
就字面意思而言,这段引语给人以“狂人疯语”的感觉。 然而,没有直说的作者含义之丰富、深刻、辛辣,才是这段文字的精髓,才使得整个作品具有了中国文学文化史上革命性佳作的意义。 “研究”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上的“仁义道德”本质上却是藏在“字缝里”的“吃人”,本来清楚的意思却只能借助“狂人”的“日记”才有表述的机会……可见,只有围绕作者藏在文本中的意图进行阐释,才可能抵达文本含意的精妙之处,才具有阐释价值。
从个人的生命历程来看,广义的阐释无所不在,是人的自证行为,即是说,人只要活着,只要做事,总是要落实其意图,即把他的脑文本中的计划通过语言和行为诠释、解释、兑现出来,亦即阐释出来。 从社会整体上看,文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过程,也是人和社会的重要主题得到不断深化、反复阐释的过程。 对于经典文本的今译、批评与阐释,对于其他文化体中经典文本的翻译、评介和阐释,越来越成为社会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高投入的集体性研究实践。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思想、信念、宗教等社会宏观层面上,对于构成文化内核成分的典籍文本的阐释和翻译,从来都是社会公权力明确支持的学术内容,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组织性学术活动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 如在当代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基础性经典文献外译与译入已成为投入较大、研究力量越来越强、成果成批量增长的领域,为社会的持续发展进行着必需的知识经验之交流、学习和互鉴。 可以说,这股力量是推动思想、文化核心价值文本之翻译的最大社会动因。
在由各种行会组织、企事业机构等形成的社会中观层面上,译入目标文化中具有优势竞争力的知识技术文本,以提高文明文化本体相应的生产、服务水平,乃是由于实用性催生出的文本翻译、阐释的原生动力。 它追求的是直显的功能主义阐释效果,以改善自身技能技艺、夷平对手的竞争优势为目的,奉行的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功能性原则。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机构和组织是这类文本翻译与阐释的主要推手,文本范畴主要是自然科学及其相关学科。 当然,现代社会以来,自然科学的强势发展及其衍生技术的广泛使用,形成了科学至上的宰制性力量,其扩散开来,决定性地影响并形构了现代精神科学。 这类文本的翻译和阐释以追求对等的功能为旨归。
在阐释者个人的微观层面上,其生命体验、职业经验和审美趣向综合作用形成的他本人对文本风格、审美要素的诉求,是第三类动因。 首先,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会影响其对文本的独特理解,这种独特性既体现在他与其他读者理解的差异性,又体现在他自己每一次阅读文本都可能产生新的不同的理解效果,而好的文本往往具有一种特质,鼓励着读者引人入胜的丰富而不同的理解。 其次,个人对文本风格的偏好既会影响其对要翻译或阐释的文本的选择,更会影响其在翻译和阐释过程中对文本内容的取舍。 最后,不同译者或阐释者对于文本中的思想、意境、意象等审美范畴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性。 这种动因往往最容易导引着翻译或阐释结果突破文本,形成强制性或者阐发性的解释。
二、影响翻译标准的三个动因
第一种动因是社会历史使命感的驱动。 信息差异性促成交际和交流,这是人之见贤思齐的本质属性使然。 社会层面上,人们认识到其他文明文化尤其是文化核心的思想、信念、价值观方面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便会克服重重困难去学习和借鉴。 如唐玄奘克服千难万苦历时十余载拜取佛经;二十世纪初众多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甘冒危险,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 这类社会层面的动因根本在于改善本文化的生存与竞争能力,属于神圣的民族英雄主义情怀,取经者、译者和阐释者受到神圣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的驱动。 为丰富和发展本文化思想、信念、价值观而作出树德立言之贡献,乃是该群体中有识之士的共同梦想,它驱使着译者和阐释者对于经典文本的反复重译和重新阐释。
对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文本的“取经”与翻译,大多出于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资助的安排,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投入力度越来越大。 这些发生学意义上的交流和翻译动因会影响翻译过程中对于文本处理的目标、方法和标准。 一方面,对于所选取的源文化思想、信念、价值观的崇敬,使得译者在文本翻译和阐释过程中保持着对作者和文本的虔诚敬仰,体现在翻译中莫过于翻译界长期奉行的“信达雅”信条;另一方面,社会迫切的现实需求要求在一定时效期内完成翻译和阐释,更由于源文化中的宗教、思想、信念在目标文化中空缺,巨大的信息差产生强大的势能,迫使翻译、阐释要克服困难,通过硬译、比附、格义等异化策略,尽快将翻译和阐释文本传递给受众。 所谓格义,指的是“一种类比之理解方法,用来解释和理解跨文化背景的概念,与之同义词是‘配说’或‘连类’,近似英语analogy(类比)”。①华满元:《重识“格义”》,《外国语文研究》2016年第2 期。源文化与译入文化之间的知识鸿沟,决定了译入的诸多概念、思想、信念,需要经过长期的消化、吸收、融合等归化处理,才能真正被吸收成为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丰富和改变本文化。 如日本对中国汉唐文化以及其明治维新前后对西方文化的引入、翻译、消化、吸收进而发展的日本文化,中国文化中对佛教的译入、融合、发展而成的禅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等。
关于翻译的标准和社会对译文的认可度,新的思想和知识从源文化引进之初,社会对译入知识的迫切需要决定了其对译文知识的较高接受度,并将译文推崇到公共阐释的地位。虽然格义、硬译会产生诸多晦涩难懂的异化效果,如格义法带来的“佛陀”“菩萨”“阿弥陀佛”等实际上只是就发音硬译的权宜表述,让缺乏相应背景知识的读者在很长时间内处于懵懵懂懂、一头雾水的状态,但是由于最先的翻译缺乏可资借鉴或比较的平行译本,故不会影响先行译文的公共阐释地位。 后续每个时代的重译也基本是由最优秀的学术、财力、出版等方面资源合力完成的,其译文和阐释版本吸收已有版本的优点,改进和完善不妥之处,形成替代此前的公共阐释,即新的所处时代的公共阐释。
第二种动因是传播红利的驱动。 社会各行业出于对行业知识技术的现实需求,组织力量收集、翻译和阐释相关文本,这些知识技术的传播会很快改善其生产生活水平,故我们将这种动因称为传播红利的驱动。 这类文本的翻译标准首先体现在实用性上,即文本能使读者提升自身的行业知识技能即可。 在翻译学中表现为对等、等效翻译理论,研究内容先后涵盖了源文本与译本之间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的对等或等效,科勒甚至将等效关系细分为外延、内涵、文本规范、语用、形式五个方面的对等。①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李德凤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66 页。当然,其最终宗旨在于使译文能够帮助读者学会源文化中相应的知识技能,提升自己的竞争水平。 大量的技术类文本、经济合同以及商务信函等源文本要求信息表达准确,无需文采,一般也没有作者蕴藏在文本中的其他意图。 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许多日常语汇,由于在译入文化中缺乏对等内容,也会出现音译、硬译、格义的译法,例如英文中的“kang”(炕)、“kungfu”(功夫)、“wok”(锅)、“kowtow”(磕头)等,就是以音译方式创造新的词汇来表达源文化中的新奇内容;汉语中音译引入的西方语汇如坦克、吉普、阿司匹林等也属于这一类型。 翻译中新造的词汇用得久了,人们可能会习以为常地将它们当成本语言文化中的成分,即是说,这些词汇的翻译成功地化为了公共阐释。 当然,在文学文本的翻译上也有类似情形,典型的是在诗歌翻译中从形式和内容上做到对等乃属难能可贵,翻译时适当侧重于形式或内容应该不算是强制阐释。
受传播红利的驱动,对源文化中的内容进行碎片化处理,断章取义以满足目标读者群猎奇的心理,就容易产生强制阐释的译本。 为了照顾读者的喜好,汉学家霍克思承认有时候要对原作作出一定的改动。 他辩解说:“如果这样的改动超出了一个译者的职责范围,我只请求注意我为西方读者考虑之心。”②David Hawkes 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盛君凯译,朱振武等:《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 页。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如将“饺子”译成“dumpling”,将“筷子”译成“chopsticks”;③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饺子作为食材实际上精致、营养、味美,岂能译成“dump(倾倒)+ling(小东西)”? 另外,筷子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器物,译成“chop(削)+sticks(棍、枝)”太过粗鄙,虽然这一英文译名已经广为接受,但还是值得批判的。 限于篇幅与主题,在此不赘。文学翻译中的例子如将《水浒》译为猎奇性的《105 个男人和3 个女人的故事》,将《西游记》译为“MonkeyKing”;等等,简化得失之偏颇。 当然,如果译者本来就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则很容易造成对源文本带有偏见的翻译处理,如笔者在与多位西方同事讨论“鸦片战争”的翻译时,他们通常反对用“The Opium War”,而是坚持用“The War for the Balance of Trade”——当然,这里的争论已经不限于翻译了,而是对待这场战争的两种对立立场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阐释和表述。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意识形态通过长期传播已经内化为“常识”“知识”状态,译者、阐释者在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警惕的批判精神,抵制可能的种族中心主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势利歧视等倾向造成对源文本的强制阐释。
第三种动因是译者或阐释者的个人审美趣向的驱动。 翻译和阐释终究是个人行为,因此一定会受制于个人学识、阅历、审美趣向等要素,这些要素是个人长期学习和习得的,已经先在地内化于每个译者和阐释者的职业素养中,十分隐蔽。 这些要素决定了译者或阐释者的视域,即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所“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①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 页。正是由于阐释者之间的视域不同,才出现了对于相同的文本,不同的读者和阐释者见仁见智,甚至出现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 越是经典的文本,其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巧妙的运思越是能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理解的空间,即为阐释提供无限的可能。 阐释学翻译理论强调译者自身对源文本的理解,以及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各种译者主体性抉择。
当然,阐释的无限可能性或曰阐释的开放性并不是说对具体文本的阐释可以随意进行,甚至在阐释开始之前已经有了某种清晰的个人意图乃至既定立场,只是借用对某文本阐释的名义抒发出来,将文本本身工具化处理,成为佐证自己意图的材料。 若如此,则是典型的强制阐释:“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②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 期。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译者的个人因素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坚持以源文本为出发点和归宿,以避免翻译中的强制阐释。
三、翻译过程中如何克服相应的强制阐释?
我们从发生学的视角分别讨论了社会宏观、行业中观、阐释者微观层面上翻译阐释的动因,分析了这些动因可能导致的强制阐释性译本。 知识翻译学作为翻译学近年来发展的新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置身于更高更广的平台,从总体上看待翻译,探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规避强制阐释。 综观古往今来的翻译,可以概言之,翻译无非是通过译出不同语言文化中的知识,以利于交流、传播、改善文明文化体的生存和运作状态。 总体上讲,“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翻译使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成为世界公共财富”。③杨枫:《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6 期。
知识翻译学强调知识的地方性和个体性差异。 在第一种动因的作用下,翻译和阐释的先行者的译文或阐释版本当然地成为公共阐释。 当然,后来的版本可以对已有的公共阐释版本进行修正,形成新版本的公共阐释。 在思想、文化核心价值内容最初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只能依据目标文化中的概念硬性表达译入内容,但是由于常常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其难免采用格义、硬译等权宜策略,故其译文也难免存在晦涩难懂之处,如硬生生借来的“阿弥陀佛”“般若波罗蜜”“涅槃”等音译语汇。 有趣的是,这些生僻的词语用得久了,人们不再在意它们的根本意义,转而不自觉地运用它们,这正应和了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起将语言与意义的本质关系认定为约定俗成的(conventionalized)而不是逻辑的(logical/motivated),即否认词语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这里还需要简要讨论一下“格义”“硬译”是否造成“强制阐释”,以及应该如何看待其中晦涩难懂的表述问题。 一方面,这类文本的译者一般出于对文本的虔诚敬畏之心而参与了文本的遴选,翻译过程中虽然常用“牵强附会”的策略,但是基本是以翻译和阐释源文本意义为宗旨,而不是借文本阐发本己意图,所以不属于强制阐释。 另一方面,译者和读者对于外来文化的核心思想、信念、价值观等的认识和借鉴,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适应、深化和全面理解的过程,如20 世纪初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以及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诸多知识和概念的翻译、重译与完善就是如此。 限于篇幅,仅以science 和democracy 的翻译为例,从初期的“德先生”“赛先生”到后来的“科学”“民主”的译文发展,充分彰显了包括译者在内的受众群体对译入思想、知识、术语认识的深化、发展和完善历程,作为公共阐释的内容丰富了译入文化,而这正是翻译和阐释发展演变的理想路径与结果。
基于第二种动因即实用性驱动的翻译,基本以项目的形式展开,其目标主要侧重翻译对象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译出需要的内容,该项目也就完成了。 这在知识翻译学上十分简明:达到知识传播的目的即可。 不过,在实践中也可能出现译者借其所翻译之文本阐发自己意图的例外情况,如严复借自然科学文本《天演论》的翻译,类比性地阐发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对社会变革的观点随之成为社会广为接受的公共阐释内容。
对于先有既定的立场,强以文本之名征用文本片段佐证自己的观点,形成强制阐释的,学界应该展开持续的批评,将强制阐释中译者或阐释者先有的各种偏见和立场与文本本身的意义剥离开来,争取改进的空间,使得译本或阐释版本向着优化的公共阐释版本方向衍化。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阐释文本的同时,应保持对可能的偏见的警惕性,对于失之偏颇的理解适时展开纠偏,这种批判与质疑精神是翻译和阐释界、批评界以及受众都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 实际上,任何文本都是对于某些或某种知识的阐释,读者和评论界在理解与欣赏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不论有无问题都当作真理全盘接受。 关于这一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权力批判,赛义德对西方文学中的“东方主义”批评等,可谓纠偏性的批判范例。 近年来,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如BBC 对中欧班列、“一带一路”倡议的系列报道充满了嘲讽和“污名化”,甚至将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歪曲地解释为“秀肌肉”(showing muscle)的新型殖民行为,其在采访报道过程中主要是找一些对建设项目不满者发表意见,以支持BBC 既有的偏见性认识。 在固化了的偏见如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白人至上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的长期影响下,西方左翼党派难以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其文化基因中的偏见往往促使他们臆想式地歪曲阐释中国的社会主义。 这类与事实相悖的文本和话语其实是赤裸裸的强制阐释,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当然不必等到翻译的阶段。①对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和批判,详见Zhou Suifang,Zheng Danni,“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Neo-Colonialism or Cosmopolitanism? A Cultural Critique Based on a Hong Kong Newspaper Articl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Studies,2022,vol.8,pp.120-133。至于具体文本的翻译,尤其是对于经典文本的翻译,译学界每年都有大量针对已有译文进行评述和批评的研究,涤除强制阐释内容,促成公共阐释性译本。
第三种动因即译者或阐释者的个人偏好,也会促成对源文本的翻译或阐释。 由于个人的知识和偏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内在化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自然”与“无意”之间,实则最可能出现“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②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 期。的强制阐释版本。 实际上,“本己之意”是任何文本创作、阐释与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这里的第三种动因,专指主要由个人意向推动的翻译或阐释。 这种现象又可以细分为如下情况:借整理和阐释其他文本之机,在筛选、编辑、解释文本的过程中充分阐释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其思想、观点和立场成为对典籍的公共阐释之形式和内容,以实现自身意图的最佳阐释和传播。 虽然这种方式名义上可能是“述而不作”,但是实际上已经完完全全地实现了著述——而且是以经典的名义。
前述的“东方主义”的偏见性阐释,实际上还存在着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文化现象。 如诸多反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以专门描写、阐释丑陋面为手段来对标赢得国外某些奖项,获奖后再回到本土市场赚取受众市场份额。 其阐释的强制性在于,在先有的文化自卑心理的影响下,选取非主流的负面文化要素,并将之进行艺术性夸大以博取国外评委、专家的眼球从而获得奖项,这种功利诉求视野选择性地看不到主流文化。
在文本的翻译中,译者除了要具备深厚的源语语言文化和母语语言文化功夫外,还必须始终保持对源文本作者和文化的尊重,抓住并创造机会考察核定其对源文本中语言与文化难点的理解。 如汉学家白亚仁(《聊斋》的英译者),“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白亚仁一向不吝啬自己来华交流访学的时间,每有会议或是朋友相邀共商学术,他总是欣然前往,尔后满载而归”。①罗丹:《今古文学我为路,中西文化译作桥——白亚仁的译介历程》,朱振武等:《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第71 页。汉学家蓝诗玲为了核准对《马桥词典》的理解,专程来华与作者韩少功实地考察“马桥”,亲身体会作者的思想和作品背景,她强调:“以归化策略为主,注重中英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忠实性再创造’。”②唐春蕾:《文学翻译添薪火,英伦汉学焕诗情——蓝诗玲的译介历程》,朱振武等:《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第103 页。
影响翻译的三个动因相互之间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也可能存在一些别的影响要素。这里我们强调的是,这些要素最终将聚焦作用在译者身上,影响其翻译工作,从而可能形成强制阐释的译本。 一方面,“任何翻译都带有翻译者的诠释学‘境遇’和理解‘视域’,追求所谓的单一的真正的客观的意义乃是不可实现的幻想”。③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译者序”,第13 页。即是说,对于文本的翻译和阐释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存在完美的译本或阐释版本,瑕疵也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坚持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归宿,可以规避强制阐释性译文进而指向公共阐释。
结 语
从知识翻译学视角看,任何文本的翻译都是由思想观念等社会宏观层面、社会诸行业的中观层面和译者自身知识素养与文艺追求的微观层面的力量推动而成的。 当然,各种推动力本身会影响文本的翻译和阐释,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译文或阐释版本之中。 社会文化和译者个人先有的立场或成见构成的阐释者的主观动机,可能在这些推动力的作用下被放大,形成脱离文本本身的强制阐释译本。
强制阐释批判理论和公共阐释理论有助于提高译者和阐释者的意识,使其更好地贯彻以文本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原则,聚焦源文本信息与作者意图,向着公共阐释的方向推进对文本的翻译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