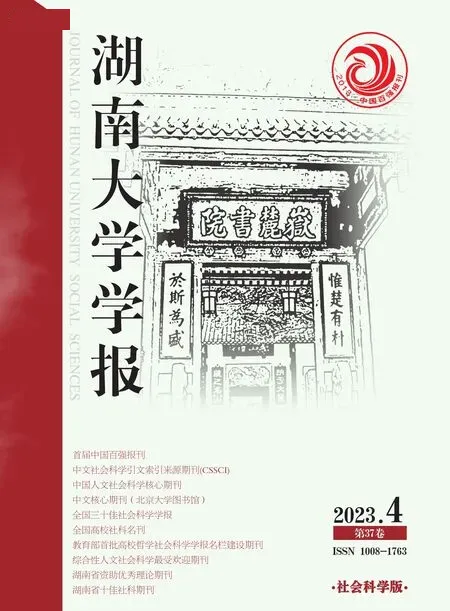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理论辨正与立法回应
——兼论《民法典》第1168条的解释*
唐绍均,李生银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属于大陆法系侵权法连带责任在适用范围扩张过程中正当性基础得以相应扩张的产物[1]79,被我国理论界借鉴并用于解释我国民事立法中所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责任适用范围扩张的正当性,导致相应法条中有关“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解读争议一直悬而未决。针对理论界聚讼纷纭的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本文在检视其概念分歧与立法现状的基础上,评析其民事立法的学理解释争议,从分类逻辑的确立、样态种类的识别两方面对其予以理论证成,并分别就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模式与立法表达提出建议,以期推进我国《民法典》第1168条的解释与适用。
一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问题检视
(一)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淆乱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所称的“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与“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区别在于数个侵权人的行为具有“客观关联共同性”。虽然共同侵权行为早在罗马法时期就有相应雏形,但是罗马法仅将共同过错作为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并无共同侵权行为“客观关联共同性”的理论萌芽。从现有文献资料看,1913年日本大审院就提出将“客观关联共同性”作为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基础[2];1972年日本法院在“四日市公害案”判决书中进一步将“客观关联共同性”区分为“较强的客观关联共同性”与“较弱的客观关联共同性”,并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关联共同性”仅包含“客观关联共同性”[3]。1977年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在“例变字一号”判决书中将“客观关联共同性”作为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基础。此后,理论界还形成了共同侵权行为的“主观说”与“客观说”融合发展的“关联共同说”(实质上就是共同侵权行为的“折衷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不仅包含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还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4]。
尽管理论界早已提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这一概念,但就何谓“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统一的概念界定。归纳而言,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有学者将其界定为“数个行为人事先并无共同的过错,但是各个行为在客观上偶然结合在一起,之后导致同一个受害人遭受同一损害的侵权行为”[5](以下简称“界定一”);第二,也有学者将其界定为“数个行为人事先并无意思联络,各加害行为原因力结合在一起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6](以下简称“界定二”);第三,还有学者将其界定为“数个行为人事先并无意思联络,在客观上数个行为人所实施的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是被害人因此所生损害之共同原因的侵权行为”[1]83(以下简称“界定三”)。
细辨之,前述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三种概念界定尚处于“淆乱”状态,不仅存在“相同点”,也存在“差异点”,还存在“忽略点”。前述概念界定的“相同点”在于:从行为上看须为“数个行为”,从结果上看须为“数个行为造成的损害同一不可分”。前述概念界定的“差异点”在于:对“客观”的认定不同。详言之,“界定一”将“客观”认定为“无共同的过错”,即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界定二”和“界定三”均将“客观”认定为“无意思联络”,但两者还略有差异,“界定二”将“无意思联络”表述为“无共同故意”,“界定三”将“无意思联络”表述为“无‘共同故意+共同认识’”。前述概念界定的“忽略点”在于:第一,忽略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应根据主观过错与客观表现细分为不同的样态种类;第二,忽略了原《侵权责任法》与现《民法典》均已将无主观关联前提下“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数人侵权行为单列为“分别侵权行为”,若再将其界定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则必然存在体系性冲突。
(二)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含混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作为大陆法系侵权法连带责任在适用范围扩张过程中被用以诠释共同侵权行为正当性基础的理论成果,经由日本、我国台湾传入我国大陆,被我国大陆学者用于解释共同侵权行为的相关民事立法。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在我国大陆被先后用于解释原《民法通则》第130条、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原《侵权责任法》第8条及《民法典》第1168条。详言之,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先被用于解释原《民法通则》第130条,有学者认为其中规定的“共同”指“客观关联共同”,即数个行为之间有牵连,各行为均为损害的共同原因[7];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后被用于解释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有学者认为其中“无共同故意与共同过失但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实质上就是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还被用于解释原《侵权责任法》第8条及沿袭该条内容的《民法典》第1168条,有学者认为该条中的共同侵权行为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尽管我国的民事立法至今尚无直接、明确规定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法条,但是理论界已通过运用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将前述法条解释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实质上是指理论界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作学理解释时所援引的法条。
梳理前述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我国有关民事立法均有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但均未明确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包含其中,导致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一直处于“含混”状态。原《民法通则》第130条虽然首次将“共同侵权”写入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该条规定并未对“共同侵权”的具体含义予以细化规定,导致理论界对该条中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学理解释形成了“客观说”“关联共同说”“主观说”等迥异观点。“客观说”“关联共同说”认为该条中的共同侵权行为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而“主观说”却认为该条中的共同侵权行为不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未能对该条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作出统一的学理解释,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原《民法通则》第130条中尚处于“含混”状态。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细化解释了《民法通则》第130条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共同故意侵权行为、共同过失侵权行为与“行为直接结合”型共同侵权行为,其中的“直接结合”是指“数个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区分各个行为对损害结果在因果关系上的原因力大小”[8]。尽管有学者将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涉及的“行为直接结合”型共同侵权行为解释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但该解释也仅为部分学者的学理解释,从理论源流上可被视为“客观说”或者“关联共同说”基于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而作出的延伸解释,并未根本改变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立法的“含混”状态。原《侵权责任法》第8条并未将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加以法律确认,仅将原《民法通则》第130条中的“共同侵权”变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现行《民法典》第1168条沿袭了原《侵权责任法》第8条的内容,修正后的2020年版《人损解释》已将原《人损解释》第3条第1款删除,导致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现行立法基本上已“回归”原《民法通则》第130条,对“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法条解释争议虽几经发展演变,却又重新回到解释原点,但始终未变的是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一直处于“含混”状态,不仅使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种类未能得以厘清,也使共同故意侵权行为、分别侵权行为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常被混淆使用,进而导致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被一些法院不当认定。譬如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王毅鹏等财产损害赔偿案(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13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均将共同故意侵权行为不当认定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宋金龙与徐高文、陈子祥等财产损害赔偿案(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人民法院(2019)新4223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将分别侵权行为不当认定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二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理论争议
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势必导致理论争议的产生[9],由于我国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一直未能明确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包含其中,因此围绕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民事立法的学理解释,理论界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尽管“肯定说”与“否定说”表面上是在探讨“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共同侵权行为”,但实质上却是在争议“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一)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已经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此类行为应当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文所指的用以学理解释我国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民事立法的“肯定说”实质上包括“客观说”与“关联共同说”。“肯定说”的支持者认为,不同于刑事责任重在“惩罚主观过错”,民事责任侧重于客观损害的赔偿,若损害的发生是各行为人所实施的共同行为而导致,即便各个行为人之间无意思之联络,也应将这类侵权行为认定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并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10]。为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当各加害人经济力量、负担能力不一致时,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可增加对受害人的赔偿几率”[11],有利于避免受害人“不能证明侵权人之间存有意思联络而遭受难于求偿的风险”[12],使受害人“不应当因为不止一个人对损害负有责任而遭受不利”[13],很明显“肯定说”具有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实用主义倾向。
(二)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未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此类行为不应当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归纳而言,“否定说”的支持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一,“否定说”符合“责任自负”原则。“责任自负”原则是指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而不应让未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其他人承担该责任。[14]“否定说”的支持者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未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此类行为不应被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而应根据侵权人所实施的行为对损害结果在因果关系上的原因力大小承担责任,如此才符合“责任自负”原则。相反,如果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已经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将其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则无论侵权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单独足以导致该损害,受害人即可向造成同一损害的数个侵权人中的任意一个行为人主张全部损害赔偿,还可以向其中的几个行为人主张全部损害赔偿,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共同侵权行为的范围,不合理地让其中无“主观关联”、行为仅对损害结果提供部分原因力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15],有违“责任自负”原则。理由二,“否定说”能够契合法条的体系解释。“否定说”的支持者认为,从体系解释角度看,由于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中“肯定说”所称的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已被纳入原《侵权责任法》第11、12条(现为《民法典》第1171、1172条)并按照分别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即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须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须承担按份责任),因此原《侵权责任法》第8条(现为《民法典》第1168条)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并不包含“肯定说”所称的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三)对理论争议的评析
1.对“肯定说”的评析
由于“肯定说”中包含了“客观说”与“关联共同说”,“客观说”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仅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关联共同说”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既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还包含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对“肯定说”的评析不宜笼统进行而应分别展开。第一,“客观说”从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角度看存在“顾此失彼”的弊端。所谓“顾此”是指“客观说”为了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而主张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包含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一方面扩大了责任人的范围;所谓“失彼”是指“客观说”将传统意义上的狭义共同侵权行为——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排除在外,导致虽与他人存有“主观关联共同”而未实际实施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16],另一方面又缩小了责任人的范围。第二,虽然“关联共同说”从充分保护受害人权益角度看能够实现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彼此兼顾”,但从共同侵权行为区分角度看“关联共同说”却未能实现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泾渭分明”,即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分类标准欠周延,既未能准确揭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辨识要件,也未能明确细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样态种类,导致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界限未能得以厘清。
2.对“否定说”的评析
“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并不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虽然也符合“责任自负”原则和能够契合我国民事立法相关法条的体系解释,但是“否定说”所具有的以下两方面的弊端却使其难以逻辑自洽。第一,“否定说”在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认识层面存在“以偏概全”的谬误。“否定说”仅以“数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已被纳入原《侵权责任法》第11、12条(《民法典》第1171、1172条)为由否定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虽能将“数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之外,但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除包含主观共同侵权行为外,并非只包含“数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否定说”并不能将无主观关联的“数人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在内的既非主观共同侵权行为也非“数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排除在外,因此如此学理解释显然存在“以偏概全”的谬误。第二,“否定说”必将导致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划分出现逻辑断裂。“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未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基于主观与客观是一对逻辑周延的哲学范畴,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即两者属于对立统一关系[17],因此“否定说”在哲学范畴层面否定了客观,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主观的否定。循此逻辑在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已被否定的情势下,作为其对立范畴的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自然难以独存。若“否定说”在否定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基础上仍承认我国民事立法中涉及的共同侵权行为包含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势必导致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划分出现逻辑断裂,不能在哲学范畴层面形成“闭环”。
三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证成进路
由于“客观说”在保护受害人权益上顾此失彼,“否定说”在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认识上以偏概全,在对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型划分上逻辑断裂,因此前述理论观点均无法用于学理解释我国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由于“关联共同说”虽无法实现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泾渭分明”,但能够达致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彼此兼顾”,因此本文拟从分类逻辑的确立与样态种类的识别两个层面对“关联共同说”予以完善,希冀能够用以学理解释我国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
(一)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分类逻辑的确立
立足于“关联共同说”,若要证成我国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就亟须首先实现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泾渭分明”,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然离不开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分类逻辑的确立。所谓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分类逻辑是指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从我国共同侵权行为民事立法中予以划分所应采用的方法论。由于侵权行为涉及主观过错与客观表现两方面因素,因此根据前述两方面因素所能确立的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分类逻辑不外乎“主观”“客观”与“主客观结合”三种方法论。所谓“主观方法论”是指仅将共同侵权行为主观上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作为逻辑起点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客观方法论”是指仅将共同侵权行为客观上的表现(加害行为+损害结果)作为逻辑起点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主客观结合方法论”是指将共同侵权行为主观上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与客观上的表现(加害行为+损害结果)两相结合作为逻辑起点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从我国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民事立法的学理解释看,目前仅有“关联共同说”将“客观方法论”作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分类逻辑,尚无采用“主观”“主客观结合”两种方法论作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分类逻辑的学理解释。鉴于“关联共同说”将“客观方法论”作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分类逻辑时仅将客观上的表现(加害行为+损害结果)作为逻辑起点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划分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时又仅将主观上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作为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分类逻辑,如此划分势必导致“关联共同说”在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时忽略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故意或过失),在划分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时忽略侵权人客观上的表现(加害行为+损害结果)。前述“两个忽略”业已成为“关联共同说”难以实现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划分“泾渭分明”的真正缘由。“主观方法论”虽未在我国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民事立法的学理解释中被采用,但是若采用“主观方法论”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进行划分,仅将主观上的无过错(故意或过失)作为逻辑起点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势必出现“两大弊端”——不仅会导致“客观关联共同”的核心要义难以在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中得到充分体现,也会导致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无法实现与其他无过错(故意或过失)侵权行为间的严格区分。由于“主客观结合方法论”不仅有助于避免出现“关联共同说”将“客观方法论”作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分类逻辑时的“两个忽略”,也有助于避免出现采用“主观方法论”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进行划分时可能产生的“两大弊端”,因此笔者拟摈弃“主观方法论”与“客观方法论”,采用“主客观结合方法论”,既从共同侵权行为主观上的过错又从共同侵权行为客观上的表现来划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以期实现主观、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泾渭分明”。
(二)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样态种类的识别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证成,不仅需要确立其分类逻辑,还亟须识别其样态种类。尽管原《民法通则》、原《人损解释》、原《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中均有涉及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但仅有《民法典》现行有效,且其中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具有代表性意义,因此本文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样态种类的识别仅以《民法典》相关规定为依据进行展开。此外,由于共同侵权行为在《民法典》中属于“数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下位概念,因此本文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样态种类的识别以“数人实施侵权行为”为切入点,分以下三个步骤予以展开。



从图1可知,在“数人实施侵权行为”的12种情形中,根据《民法典》第1171、1172条有关分别侵权行为的规定,第1168条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以及第1169、1170条有关教唆、帮助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再结合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与客观表现,X5、X8、X11这3种侵权情形只能被认定为分别侵权行为,X6、X9、X12这3种侵权情形理应被认定为单独侵权行为,X1、X2、X3这3种侵权情形理应被认定为主观共同侵权行为,前述侵权行为均不属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样态种类。而X4、X7、X10这3种侵权情形在客观上具有“关联共同”的特征,理应属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样态种类。

图1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样态种类
1.不属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样态种类
第一,X5、X8、X11这3种侵权情形在主观上的过错并不相同,分别为“分别故意”“部分故意+部分过失”“均为过失”,在客观上的表现均为“分别实施”+“同一损害”,由于满足《民法典》第1171、1172条涉及的分别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同一损害”,因此这3种侵权情形只能被认定为分别侵权行为。第二,X6、X9、X12这3种侵权情形在主观上的过错并不相同,分别为“分别故意”“部分故意+部分过失”“均为过失”,在客观上的表现均为“分别实施”+“不同一损害”,虽然这3种侵权情形满足《民法典》第1171、1172条涉及的分别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但是造成的却是“不同一损害”,并不满足前述条文规定的“同一损害”构成要件,因此这3种侵权情形不能被认定为分别侵权行为,鉴于这3种侵权情形是“分别实施”且造成的不是“同一不可分损害”,因此理应被认定为单独侵权行为。第三,X1、X2、X3这3种侵权情形在主观上的过错均为“共同故意”,在客观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分别为“共同实施”+“同一损害”、“分别实施”+“同一损害”以及“分别实施”+“不同一损害”,由于这3种侵权情形的行为人通过意思联络形成了共同追求或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意志,即具有共同故意,在主观上形成了“关联共同”,其中无论是部分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还是行为人分别实施的行为抑或共同实施的行为均应被视为全部行为人所作出的行为,其所导致的损害结果的责任理应由全部行为人连带承担,因此X1、X2、X3这3种侵权情形理应被认定为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2.属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样态种类
X4、X7、X10这3种侵权情形在主观上的过错并不相同,分别为“分别故意”“部分故意+部分过失”“均为过失”,在客观上的表现均为“共同实施”+“同一损害”。很明显,由于这3种侵权情形既不满足《民法典》第1171、1172条涉及的分别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满足第1169条涉及的教唆、帮助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还不满足第1170条涉及的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更不满足单独侵权行为关于相当因果关系的“相当性”认定要件,因此要认定其为“分别侵权行为”“教唆、帮助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以及“单独侵权行为”均不可能。虽然这3种侵权情形的行为人并未通过意思联络形成共同追求或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意志,即不具有共同故意,并未在主观上形成“关联共同”,但是由于这3种侵权情形的行为人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且导致了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在客观上具有“关联共同”的特征,因此理应被认定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
四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回应
尽管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理论证成可分别从分类逻辑的确立与样态种类的识别两个层面得以实现,但是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还须分别从立法模式的选择与法律规范的表达两个层面得到立法回应。诚然,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实质上就是要实现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的“辨识性嵌入”,既通过立法模式的确立彰显其立法技术性,也通过法律规范的表达增强其立法可操作性。
(一)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模式
1.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
从理论上讲,立法缺陷可以通过对现行法律进行立法修订、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予以解决。由于我国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一直处于“含混”状态,从可辨识性角度看也应属于立法缺陷,因此这一立法缺陷亦可尝试通过对现行民事法律进行立法修订、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予以解决,既实现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辨识性嵌入”,也使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立法不再处于“含混”状态。从立法缺陷的解决方式看,立法修订模式、立法解释模式与司法解释模式均可成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立法的可选模式。第一,立法修订模式。立法修订模式就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法典》”,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168条中的共同侵权行为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第二,立法解释模式。立法解释模式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将《民法典》有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含混”规定作为《立法法》所称“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情形制定立法解释。第三,司法解释模式。司法解释模式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第1168条制定共同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增加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细化规定,以实现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辨识性嵌入”。
2.司法解释模式的确立
相较于立法修订模式与立法解释模式,司法解释模式在立法目的可实现性、制定成本的经济性方面更具优势,更适宜被确立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模式。第一,立法目的的可实现性优势。立法目的的可实现性一般包括立法目的的“部分”可实现性与“全部”可实现性,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目的在于增强该类侵权行为在《民法典》第1168条中的可辨识性,由于立法修订模式与立法解释模式仅具有立法目的的“部分”可实现性,司法解释模式具有立法目的的“全部”可实现性,因此司法解释模式在立法目的的可实现程度上更具优势。立法修订模式主要用于应对法律条文与社会诉求之间的脱节,使法律的适应性缺失得以弥补[19],立法解释模式主要用于实现法律规定具体含义的明确。采用这两种模式,即便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第1168条进行立法修订,明确该条规定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第1168条进行立法解释,明确该条规定中“共同”的具体含义不仅包括主观关联共同,还包括客观关联共同,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细化规定仍然需要进一步通过司法解释才能得以实现,可见这两种立法模式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目的均仅具有“部分”可实现性。司法解释模式主要用于解决司法审判中涉及的法律具体应用问题,不仅可用于明确《民法典》第1168条中包含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还可用于明确该类侵权行为规制的细化规定,对该类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目的具有“全部”可实现性。第二,立法成本的经济性优势。相较于立法修订模式与立法解释模式,司法解释模式往往因协调成本低、制定周期短而具有立法成本的经济性优势。首先,司法解释模式的协调成本低。从三种立法模式的协调成本看,立法修订模式涉及的主体除包括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还可能涉及代表团、专门委员会、委员长会议、主席团及国家主席等主体;立法解释模式涉及的主体除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还可能涉及法律委员会、委员长会议等主体;司法解释模式涉及的主体主要为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各个部门,相较于立法修订模式与立法解释模式,司法解释模式的协调难度相对较小,协调成本相对更低。其次,司法解释模式的制定周期短。从三种立法模式的制定周期看,法律修订既可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还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法律解释仅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全国人大的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一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若采用立法修订模式或者立法解释模式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在制定周期上势必稍欠灵活性。而司法解释草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中的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即可。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召开并无时间限制规定,相较于立法修订模式与立法解释模式,司法解释模式的制定周期相对更短,制定效率相对更高。
(二)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表达
如果说立法模式的确立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辨识性嵌入”提供了宏观指引,那么立法表达的优化将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辨识性嵌入”构建出微观方案。从前述“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证成进路”部分的分析可知,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表达应将“无共同故意+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共同作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辨识要件,即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表达应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证成进路一样,也必须遵循“主客观结合方法论”。
“主客观结合”的立法表达既表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辨识要件必须同时包括主观过错要件与客观表现要件,也表明单独的主观过错要件或者客观表现要件均无法实现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准确描述。首先,若仅从单独的主观过错要件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进行描述,由于“无共同故意”的侵权行为除了包括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外,还可能包括分别侵权行为、教唆帮助侵权行为、单独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因此仅凭侵权人“无共同故意”尚不能从主观过错要件层面实现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精准辨识。其次,若仅从单独的客观表现要件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进行描述,由于同样具有“共同实施”的客观行为要件的侵权行为还可能为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同样具有“同一损害”的客观结果要件的侵权行为还可能为分别侵权行为,仅凭“共同实施”与“同一损害”尚不能从客观表现要件层面实现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精准辨识。
综上所述,仅将主观过错或客观表现单独作为辨识要件均不能实现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精准辨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立法表达应将“无共同故意+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共同作为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辨识要件。在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司法解释模式下,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第1168条制定共同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宜将该条中的“共同”解释为客观关联共同与主观关联共同,并将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与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一体纳入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在该司法解释中,建议进一步将“无共同故意”细化解释为各行为人之间并未通过意思联络形成共同追求或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意志;将“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细化解释为各行为人仅对“实施的行为”存在“一致意思”,各行为人的行为主动自愿共同作用于同一个客体上,而非偶然结合在一起;将“同一损害”细化解释为“损害同一不可分”,并与《民法典》第1171、1172条中“同一损害”的意思保持一致。“同一损害”的本意不是指只有一个损害,也不是指造成损害的性质必须相同,而是指各行为人造成的损害不可分割,即使数个行为人造成的损害只有一个或属于同一性质,但若造成的损害可以分割,则不属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规制的范围而应按照单独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损害同一不可分是从事实层面上进行的考量,而非基于法律技术层面的同一不可分”[20],还应当“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角度上进行判断”[21],且仅须判断各个侵权行为是否均对损害后果具有原因力,确立“若无,则不”判断规则。
五 结 语
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尽管早就于20世纪80年代经由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传入我国大陆,被学者们广泛用作我国民事立法中关涉共同侵权行为之法条解释的学理依据,但是其不仅在理论层面缺失明确、统一的概念界定,在立法层面也未获得明确的法律回应。有鉴于此,本文从问题检视、理论争议、证成进路和立法回应四个维度对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展开研究,不仅对其现存问题进行了充分揭示,而且对其完善进路进行了深入探讨,期冀通过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理论辨正与立法回应进一步厘清主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与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之间的界限,实现客观关联共同侵权行为构造的体系化与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