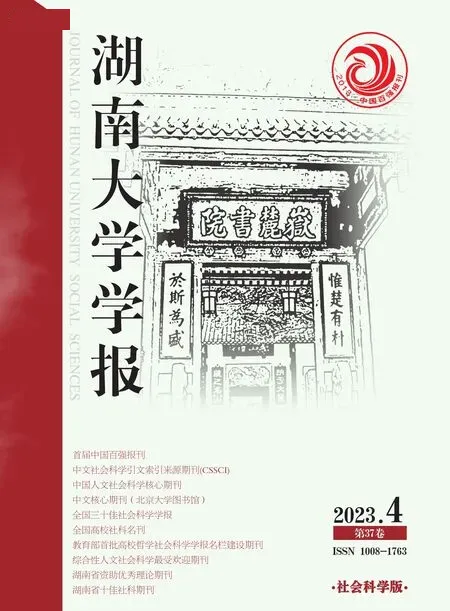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陈 树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尚书》流传过程曲折复杂,是一部文字最有争议的经籍。《尚书》先秦古本经秦焚书和秦末战火而亡散。汉初,伏生传授《尚书》二十八篇,用隶书书写,世称今文《尚书》。武帝时,破孔子宅壁,得《尚书》四十五篇,为先秦古文书写,世称古文《尚书》。孔安国用隶书摹写古文,成隶古定本。经西晋永嘉之乱,汉传今古文《尚书》相继亡佚。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上孔传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与今文《尚书》相同,另多出二十五篇。此本存隶古定字,唐玄宗时为便于阅读,令卫包将全书改为通行的楷体今字,这就是今字本,《唐石经》即据此刊石,宋以来版刻今字本皆源于此。
《尚书》历代传本颇多歧异,除了有文本篇目内容的差异,还有历代传本的字体变迁。随着字体的转换,文本的样貌发生变化,文字容易出现讹误。因此,清理《尚书》历代文本形态和异文及其传承关系,成为《尚书》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是,在前赴后继的历史浪潮中,众多的古本被新的文本所替代而湮没于历史的封尘中,使后世学者很难对《尚书》文字的演化进程做清晰完整的探究。
有清一代,经学大盛。众多学者曾对《尚书》文本的流传史做过各方面研究。其中有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他在阎若璩等清儒考辨二十五篇为伪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对其余三十一篇《尚书》文献进行考订,致力复原出汉代“真古文”本《尚书》。但因材料欠缺,段氏对中古时代的《尚书》文本问题认识有局限性。他说:“古文三十一篇字因天宝、开宝之旧,是以唐之今文《尚书》乱之也。”[1]1段玉裁既未见“天宝改字”前的隶古定本,也未见开宝前的唐本《释文》,所以对卫包怎么改字和陈鄂如何改《释文》具体情况并不清楚。阮元集合众儒校订《十三经注疏》,其中《尚书注疏》多以版刻为主,又引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但是阮元对山井鼎参校的古写本价值持怀疑的态度,他说古本:“乃日本足利学所藏书写本也。《物观序》以为唐以前物,其经皆古文,然字体太奇,间参俗体,多不足信。”[2]13由此看来,能否发现《尚书》唐写本成为解决中古时代《尚书》流传问题的前提和条件,而这个突破是由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罗振玉来实现的。
罗振玉所处的时代国势衰弱,政府对祖国文化遗产漠不关心,任其散佚海内外。罗氏“夙抱传古之志”[3]6,汲汲于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其中,他对古写本《尚书》的搜求、保存、整理、刊布、研究孜孜不倦,成就斐然。
一 罗振玉辑刊的古写本《尚书》考述
罗振玉搜求《尚书》古写本始于44岁。在这之前,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石室甫开,缥缃已散”[4]357,1907年藏书遭英国人斯坦因盗劫,1908年又被盗于伯希和。至1909年,罗振玉始从友人董康处听说伯希和窃运敦煌古卷轴之事。当时伯希和赁宅北京苏州胡同,罗振玉得见伯希和身边所携敦煌古写本,“一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4]357。他首次见到敦煌写卷,就对其中《尚书·顾命》残页非常注意。其后罗振玉在当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介绍《顾命》残页的形制和特点:“仅尺许,然异文不少。此页以糊经帙后。”[5]他同伯希和商量影写《顾命》及其他十多种敦煌写卷,1909年11月出版《敦煌石室遗书》,并撰《隶古文尚书顾命残本补考》。
当时京师大学堂筹设分科大学,罗振玉充农科监督,1909年5月曾赴日本调查农学。在考察途中,他还得以访求传于日本的古写旧刻。回国一年后,田伏侯从东京某故家为他购得《古文尚书传·周书》中的五篇残卷,即《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罗振玉见称:“书法朴雅,果千年物也。”[6]1他校订该写本,发现与《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所引的孔安国传十合八九,著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周书》一卷。
1910年,罗振玉获得伯希和邮寄的敦煌写卷影照,包括《夏书》中的《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四篇。他将之与传世及《考文》诸本进行校对,记录异文,著成《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他又将伯希和的敦煌写卷《商书》部分同杨守敬所影写的日钞本《商书》进行对勘,撰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商书》。这两部著述后收录于《群经点勘》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罗振玉应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伯和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教授等人邀请,东渡日本。留日八年间,罗振玉集聚和刊印了不少《尚书》古写本。1913年,罗振玉将法国伯希和三年来陆续邮寄的敦煌写本影片十八种辑为《鸣沙石室佚书》,存有《尚书》之《夏书》四篇、《商书》八篇,以及之前《周书·顾命》的残卷。他极为重视敦煌写本的文献价值,将敦煌藏经洞发现“古遗宝”与晋太康初年的汲郡出竹书相比,在目录提要中提及古本:“均为未经天宝改字,犹是魏晋以来相传隶古定之原本也”[4]361,“得借是确证宋以来传本之伪”[4]363。
1914年,他又将搜集的日本古写本刊入袖珍本《云窗丛刻》,第一册为《影写隶古定尚书商书残卷》,是从杨守敬处借来抄写,包括《盘庚》《说命》《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等《商书》九篇。第二册为《古写隶古定尚书周书残卷》,即之前田伏侯所购,日本学者岛田翰之旧藏。1915年夏,京都收藏家神田香严携所藏古写本《尚书》至罗振玉处,有《泰誓》《牧誓》《武成》等五篇,罗氏见之十分惊喜。神田香严欲印行此古本,请罗振玉为之作弁言。今上海图书馆藏大正四年(1915年)《唐写本尚书》一册,末有罗振玉和内藤湖南的尾跋。1916年,罗振玉借得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所藏敦煌本《尚书释文》残卷影本,印入《吉石盦丛书》中,罗氏著《敦煌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包含《尧典》《舜典》的陆德明《释文》,为宋开宝未删改之前的写本,弥足珍贵,为探讨《尚书释文》演变提供了新材料。
1917年,罗振玉在《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中陈述他已辑刊的古写本《尚书》情况,同时也表达了想要搜集更多古本的志向。他说:“盖英伦所藏尚有《洛诰》《大禹谟》《泰誓》(1)英人斯坦因所藏《洛诰》有斯6017号;《大禹谟》有斯801号、斯3331V、斯5745;《泰誓》有斯799、斯8464号。,东邦岩崎氏得唐写本,予曾见《禹贡》及《盘庚》上中下,闻尚有《周书》数篇则未之见也。又阅杨舍人《日本访书志》记所藏,尚有古写本第一、二及第七至第十三凡九卷。”[7]209而且,他从日本林浩卿博士处获悉内野本古写《尚书》全帙,希望能够有机会影印内野本和岩崎本,整理成唐古本《尚书》全书。虽然罗氏这些理想后来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也为后世《尚书》古写本的汇集留下了线索。
1928年,罗振玉63岁时,将以前收集和陆续影印的各种敦煌本和日钞本《尚书》古写卷汇聚成《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今上海图书馆藏东方学会影印本)。该汇编除了将之前敦煌本《夏书》四篇、《商书》八篇、《周书》一篇,以及日钞神田本《周书》五篇加以重新影印,又补充有岩崎氏藏本,包含《夏书》一篇、《商书》九篇、《周书》四篇。这是对他多年努力所得成果的较为全面的一次总结,也反映了他对古写本《尚书》价值的重视。
《永丰乡人行年录》云:“乡人居日本八年闭户著书外,惟务访求海东秘籍,影印流传,冀拾黎、杨之遗。”[8]36-37中华典籍在日本流传时间长,范围广,许多在中土散佚的珍本秘籍在日本珍藏且保存完好,成为接续文脉的重要资料宝库。在罗氏赴日之前,光绪初年黎庶昌曾任驻日公使,杨守敬作随员出使日本。黎庶昌委派杨守敬积极搜罗汉籍,刊印《古逸丛书》。但所采多为刻本,《丛书》所印《尚书释音》用日本景钞宋大字本,为开宝删改之后的本子,其版本价值与敦煌本《尚书释文》不可同日而语。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记录他所见《尚书》四种,《尚书正义》单疏本、《尚书正义》注疏合刻本、《尚书释音》各一种,均为宋本,只录有一种《古文尚书》古钞本。此钞本及他所影写的元亨本,后均被罗氏收录进《云窗丛刻》。与黎、杨相比,罗氏将更多精力放在日本古钞本上,在古写本《尚书》资料搜集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古钞本的来源较为复杂,可能是唐代原钞本,也可能是后世传钞,只有以出土的真正唐代写本为参照才能判定古钞本面貌的时代距离,敦煌藏经洞写卷的发现为罗振玉重估传世《尚书》写卷价值提供了机遇。此外,罗氏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在搜集古写本之前,罗振玉已经收藏有甲骨金石等众多出土材料,使得他对新材料、新史料有一种学术敏感,这是他作为近代收藏家最成功的地方。而且丰富的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经验,磨炼了他独到的收藏眼光和出众的文献价值判断能力,罗氏关注到《尚书》古钞本数量少,反映的文本状态更早,日本许多世家代代流传的古写本比版刻的价值更高。
其次,罗振玉对《尚书》古写本付出诸多心血。他不遗余力,穷尽各种方式去搜集资料,有的是花费重金去购藏,有的是借得摹写,还有的是朋友馈赠照片,逐渐聚沙成塔。罗氏交游广泛,与学、政、教各界人士熟悉,尤其是他在日本寻访的古写本,相当一部分由他交往的日本学者提供。罗氏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受益于学友颇多。
最后,罗振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收藏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不是古董赏玩。所以,他一获得珍稀古本,立即编次成书,尽快刊印,“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7]4,嘉惠学林,促进了古本《尚书》的传布和研究。
二 罗振玉对古写本《尚书》价值的发掘
罗振玉所收集的古写本《尚书》包括敦煌本和日钞本的《古文尚书传》残卷,以及敦煌本的《尚书释文》,势必促进诸多问题的探研向纵深发展,对《尚书》学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些稀世珍本对了解《尚书》在中古时期的形制、样态及内容,梳理《尚书》传本嬗变脉络,分析《尚书》文字演变歧异都有重要意义。罗振玉对所得文本进行细致的考校,撰成跋或校记,从多方面研究古写本《尚书》。
(一)探寻文字源流
罗振玉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在考释文字时,善于将多种字体作比较,阐明文字演变的渊源关系,这对分析《尚书》的字体有借鉴意义。
古写本《古文尚书传》中的孔序及经文有许多是隶古定字。孔安国《尚书序》:“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孔颖达疏:“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2]11伏生本为隶书,壁中本是古文字,孔安国以伏生书考定,且以隶体写之。则此古文与孔壁古文有所不同,会有许多唐玄宗所说的“奇字”。分析古写本《尚书》中隶古定字,以及它的来源是罗振玉的一项研究任务。例如:

敦煌写卷和日钞古本文字类型构成复杂,往往是别体、俗字和隶古定字夹杂在一起。《经典释文序录》云:“范宁变为今文集注。”[9]32东晋范宁把隶古定《尚书》改为用今字写的《尚书》,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有“《今字尚书》十四卷”[10]913,说明民间在唐以前已有了今字本的《尚书》。顾廷龙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唐写本和日本古写本隶古定《尚书》中,隶古定字已经不多,有的已经改用了通行的正体字,这是由解决隶古字难认的需要而形成的。”[11]前言14在由古转今的字体转换过程中难免有一些讹误。例如:
相协身居。身者,氒之讹。《说文·氏部》:“氒,读若厥。”《玉篇》:“氒,本也。今作厥”,《汗简·氏部》引《书》“厥”作“氒”,《考文》本《太甲》篇“厥”亦作“氒”。《广韵》:“氒,古文厥字”。[6]2
今按:罗振玉发现此处“身”是别字,并且分析原因与“氒”形近致讹,他引《说文》《玉篇》《汗简》《广韵》说明“氒”字有来源,并引《考文》本的《太甲》篇“氒”作为文献使用的证据。
除此之外,罗振玉善于运用积累的古文字材料,分析写本的用字现象。例如用金文证《说命下》“旁招俊乂”,“俊”当作“畯”;分析古写本《洪范》“惟十又三祀”,“又”字符合金文用字习惯。这也反映出罗振玉对出土材料的熟稔,以及良好的古文字学素养。
(二)校订异文讹误
典籍之传抄,鲁鱼亥豕,在所难免,罗振玉利用古写本存古的优点校正传世刻本的误夺衍倒,以实证方式还原经典的原貌原义。林平和曾分析罗振玉所撰《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乃罗氏据敦煌写本伯2533号隶古定《尚书孔传·夏书》四篇残卷以校今注疏本、唐开成石经本、相台岳本、《七经孟子考文》引古本与足利本、宋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与《史记集解》所引等,凡得一百一十三条一百二十八异同正误者”[12]121。
罗振玉在《日本古写本古文尚书周书残卷跋》中指出岛田本的价值“可是正今本者,指不胜计,多可补阮氏《校记》所不及”[7]345,例如:
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孔传》:“经营求之于外野”,十行、闽、监、葛本俱脱“营”字、“外”字,岳本、《纂传》均有,与此同。[13]13
今按:阮元十行本为“经求之于外野”,《校勘记》:“闽本、明监本、葛本同。岳本、《纂传》‘经’下有‘营’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2]148阮校对勘出异文,但是没有下断论。罗振玉在此基础上依据古写本,判定十行本“营”“外”为脱字。
阮元集合众多版刻进行对勘发现某些用字的不正确处,但是由于缺乏古本的确证,故而在《校勘记》中多用“疑”等字,阙疑而不敢作定论。这时候罗氏所搜集的古写本往往能体现出一定的证据优势,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例如:
《洪范》“于亓亡丑子”。今本作“于其无好德”,案,阮氏《校勘记》曰:《疏》云“‘无好’对‘有好’”,又云“《传》记言‘好德’者多矣,故《传》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见之本经无‘德’字,至《传》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无恶’者,疑误耳。盖谓经文‘无好’,定本作‘无恶’也。”玉案,《史记·微子世家》引正作“于其毋好”,亦无“德”字,《集解》引郑注“无好于女家之人”,是郑本亦作“无好”矣。[6]7
今按:阮氏《校勘记》对于今本“无好德”,参考孔颖达《疏》怀疑本经当作“无好”。罗振玉不仅用日传古钞本为阮氏《校勘记》分析的正确性提供了版本支持,而且还引用《史记》及郑注加以分析论证,论据充分,比较可信。
(三)勾稽文本联系
罗振玉之友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14]2。该思想其实是王氏日积月累长期学术实践的结果,尤其是他在1911年同罗振玉赴日本,罗王共同考释汉晋木简时形成。可以说,罗振玉既是该思想的贡献者,也是践行者。面对来源和成书问题较为复杂的日传《尚书》古写本,他以出土的敦煌写本为参照,判定其时代和价值。
罗氏所影写的杨守敬藏《商书》九篇,起《盘庚上》迄《微子》,伯希和所藏敦煌《商书》则前缺《盘庚上》一篇,又《盘庚中》之上半,而此下至《微子》均无损佚。罗振玉“就两本并存者勘之,虽略有小殊,而经、《传》之见于古籍所引,与胜于宋以来诸本之处,则两本靡不隐合”[7]346。例如:
《盘庚中》“女分猷念以相从”。《传》“群臣当分相与谋念”,今各本“分”下皆有“明”字,此与敦煌本均无有,《正义》言“汝群臣当分辈相与计谋念”,是孔本亦无“明”字。[7]347
今按:传世诸刻本的《孔传》解释“女分猷念以相从”之“分”为“分明”,但是孔颖达《正义》疏解是“分辈”,令人费解。罗振玉发现敦煌本和日钞本的《孔传》“分”后均没有“明”字,这样就理顺了《传》与《疏》的关系,同时也说明日钞本不同于传世诸本的讹误,具有与敦煌本同样的存古特征。
通过大量的对勘,罗振玉认为“此皆远胜于宋以来各本者,而两本正吻合。然则日本古写本为卫氏未改字以前真本,信而有征矣”[7]347。在确认了日本古写本的时代特征后,他把它放到与敦煌本同样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在汇集古写本《尚书》时,将敦煌藏隶古定《尚书》夏、商、周书各篇与居海东所见之古钞,一起荟为《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刊印。
不仅如此,罗振玉还看到日钞本具有篇幅比敦煌残卷更长更完整的优势,他说:“敦煌本为世重宝,此本虽出影写,得与参照,且可补唐写本之缺者一篇有半,亦人间之秘笈矣。”[7]348在罗振玉看来,出土和传世的材料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可偏废。因此,在分析写本文字的时候,他往往将西域和海东的写卷联系起来,相互印照。例如:

(四)考辨文本真伪
罗氏利用古写本《尚书》在文本真伪方面主要澄清了两个问题:“宋代传本为伪,东邦所传者为真”[11]附录437,突破了清代乾嘉学者的局限,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序》曰:“自梅赜献孔传而汉之真古文与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别,《新唐书·艺文志》云:‘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说者谓今文从此始,古文从此绝。殊不知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以后又别有古文也。《隋书·经籍志》有《古文尚书》十五卷,《今字尚书》十四卷,又顾彪《今文尚书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2]13阮元分析,盛唐以前其实同时有古字本和今字本在流传。《册府元龟》载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后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典谟无乖于古训,庶遵简易,有益于将来,其旧本仍藏之书府。”[15]13唐玄宗见到古本上有“六体奇文”,所以要改用今体字便于认读。日钞本保留有许多隶古定字,应当是保存了唐代古本的样貌,但阮元却因《考文》本所引用的足利本“字体太奇”认为“不足信”。
罗振玉在《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序中分析:“日本《七经孟子考文》中尚载古本,阮氏又疑其多俗书,不足信。予频年以来,见日本所传隶古定《尚书》唐人写本残卷,计《商书》九篇,《周书》□篇,其文与薛书大异,而与《考文》多合,始恍然悟,薛书自伪,而《考文》所据自真,学者犹未以为信。及去年秋见伯希和氏所得敦煌石室中唐写本《顾命》残篇,其中古文与日本所传古文《尚书》唐写本一一吻合。今年冬又影造在敦煌石室中所得二残卷见寄,则益得证成予说。”[16]1罗振玉从日钞本与《考文》对勘中获得感悟,再以敦煌本证实《考文》古本可信。
天宝改字对《尚书》的传本影响很大,官方废弃隶古定本,后来开成石经都是用今字本。虽然在民间有可能还有隶古定本流传,但是通行本中楷书字体取代隶古定字是必然趋势。所以陆德明《尚书释文》对晋宋古本校订时,仍录有隶古定字。但是,宋代“开宝中诏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本驳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17]17。南宋初,出薛季宣撰《书古文训》,所用古文与《说文》《玉篇》《汗简》等书相合。罗振玉说:“予曩一披览,满纸异字,与陆文《释文》条例所谓古文无几之说颇戾,疑为伪托。段茂堂先生亦斥为不可信,顾无确证以折之。”[4]362也就是说段玉裁并无文本确证,断定其为伪书。
罗振玉将所获敦煌本《顾命》残卷同薛季宣《书古文训》、山井鼎所引足利本《尚书》对比发现用字差异,如“上宗曰嚮”,“薛本作丄宗曰亯”等。据此罗振玉曰:“以薛书与此残本相较,其隶古文同者仅七字,其不同者则三十有七,疑薛书乃采集诸家字书所引,益以《说文解字》中之古文以成之,非卫氏改定以前之旧本,不言所自出,知即《宋志》所录晁氏所刻与,抑薛氏自写定也。金坛段氏谓薛书之不可信,其洵然矣。然使不得此十行者,亦乌乎知之?”[4]17-18罗振玉为清儒段玉裁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
罗振玉学术精湛,博稽深考,运用古写本《尚书》新材料校正刊本之讹衍,疏证先贤之校注,考辨古籍之真伪,刊补前修之缪缺,为《尚书》研究开辟新途径,见解超越前人,取得丰硕成果。
三 罗振玉古写本《尚书》研究的影响
王森然评价罗振玉的学术影响:“先生学综内外,卓然儒宗,其著述风行海内外,为学术界所推重。”[18]169例如他的《敦煌石室遗书》刊行后,日本汉学界开始闻知敦煌遗书内容,遂有1910年秋派遣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六教授来华考察之举。在古写本《尚书》研究方面,罗振玉的研究成果对后世研究有着开拓与奠基作用。
19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着手编辑《尚书文字合编》,汇集历代不同《尚书》本子为一编,旨在正本清源,探索文字变迁之踪迹,其中古写本《尚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935年朴社出版预告中,提及“唐写卷子,虽作真书,尚留古体,即所谓‘隶古定’者,其结构亦至参差”[11]附录485。但后来由于战乱及各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直到1982年才重新整理编纂。1996年出版的《尚书文字合编》写本资料引用了较多的罗振玉所收藏和刊印的古写本。
敦煌本引用“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一九一三年影印本,用伯希和编号”,以及“罗振玉《吉石庵(盦)丛书初集》,一九一六年影印本,用伯希和编号”[11]引用资料2。
日钞本引用如:“岛田本,日本写本,残。岛田翰旧藏。一九一四年罗振玉《云窗丛刻》影印本。”“上图本(元亨本),日本元亨三年(一三二三)藤原长赖手写本,残。上海图书馆藏,原件后间有脱佚,据罗振玉《云窗丛刻》影印杨守敬本配补。”[11]引用资料3当年罗氏所获岛田本已不知所踪,罗振玉刊印的《云窗丛刻》本成为存世的珍稀之本。古写本赖以流传,从中可以看出罗振玉当初积极刊印古写本的真知远见。为了清晰地了解顾氏《尚书文字合编》与罗氏所集《尚书》古写本篇目之间的继承关系,特整理如表1。

表1 罗振玉所集古写本与《尚书文字合编》篇目版本对照表
从表1来看,罗振玉所搜集的资料篇幅覆盖《尚书》30篇,超过总篇目的一半。其中敦煌写本4种,涉及15篇;日钞本有岩崎本、神田本、岛田本、元亨本4种,涉及24篇;二者重合的篇目是《禹贡》等9篇,可以相互对照。这些材料成为《尚书文字合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合编》中引用了斯坦因藏敦煌写卷和内野本,这些在罗振玉的《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中都有所提及。
《尚书文字合编》还引用“上图本(影天正本),日本影写天正六年(一五七八)秀圆题记本,有松田本生印记,全”[11]引用资料4。今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古文尚书》十三卷,影钞日本天正本,每半页9行,行约20字。卷首有叶景葵跋:“此即《日本访书志》所载,上虞罗氏惜为人藏俱亡者,今得此覆写本,借以见古文真面目,不胜欢喜。辛未正月景葵书。”罗振玉《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说:“又阅杨舍人《日本访书志》记所藏,尚有古写本第一、二及第七至第十三凡九卷。舍人在往昔未尝以告予,今舍人亡,所藏不啻与之俱亡,可慨也。”[7]209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记录了情况:“此古文《尚书》古钞本存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末有天正第六六月吉秀圆记,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以森立之《访古志》照之,此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二册,即容安书院所藏,其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二册则守敬从日本市上所得之,相其笔迹、格式的为一书,不知何时义落其中。”[19]第九册29罗振玉未曾见到的是杨守敬从日本市上购得的古本。再查日本江户后期文献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云:“旧钞本,求古楼藏。卷末有天正六年六月吉日秀圆题记及花押。每半页九行,每行字数不同。容安书院又藏零本五卷,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卷末有经注字数,又有天正六年秀圆记,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注双行。”[19]第一册44-45在这里,森立之介绍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全本,该本行款与末后的题记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天正本相合。第二种是容安书院藏的残本五卷二册,杨守敬购得四卷二册,上图所藏全本共六册,卷数属册与杨氏所记相符,他所未见的是第二册(第三、第四卷)和第三册(第五、第六卷)。罗氏虽然未见杨所藏天正残本,但也可为《尚书》古本汇编提供线索。
四 结 语
罗振玉研究古写本《尚书》,“以学术存亡为己责,蒐集之,考订之,流通之。”[7]1王国维曾盛赞罗振玉的学术成就:“《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7]4他在《尚书》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学术贡献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罗振玉为学术界提供了众多真实可靠的《尚书》古写本新资料,丰富了学者们研究的内容,开辟了新的路径,从而奠定了现代《尚书》文本汇集和研究的基石。发掘有价值的新史料,这是罗振玉功劳最大的地方,也是他作为一个近代学者最成功的地方。罗振玉研究古写本,一方面继承清代乾嘉学者精深考据的优良传统和学术精神,校订文献异文讹脱衍倒,致力还原文本原貌。另一方面,勇于开拓,掌握更为丰富的出土材料,来追溯文字源流;利用新材料辨证真伪,突破陈说,推动了《尚书》学发展。
1925年,王国维在接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的演讲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33他认为近代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内阁档案,四者之一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20]33“新的发见”除了为学术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资粮,更重要的是带来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式的变革。罗振玉在研究古写本《尚书》过程中,运用二重证据法,注重将“东”“西”古本联系沟通,采用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方法,使得《尚书》文本研究跟上近代学术转型的步伐,于《尚书》学实有继往开来之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