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隐者”也是译者的最佳状态
赵小斌

陈英的翻譯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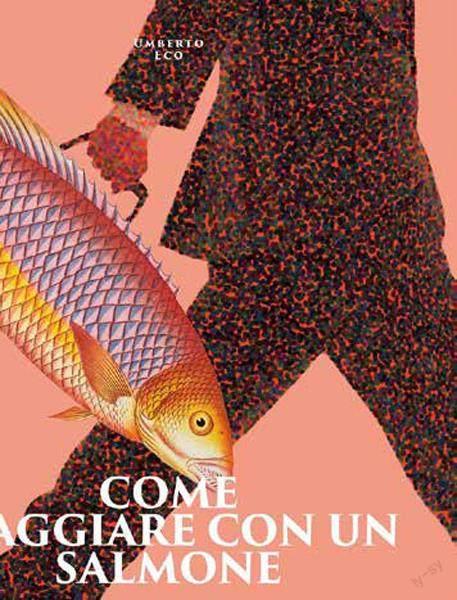

翻译家陈英。
如果说陈英成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译者算作偶然,进入文学翻译领域本身则是某种必然。她的文学翻译事业始于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小说处女作《愤怒的城堡》,那还是在她十几年前读研究生时。后来博士期间兼职为北京一家摩托用品工厂做商务翻译,直到毕业后前往高校教书,课余才有更多空闲时间。这时有位同事介绍了巴里科的最新作品《一个人消失在世上》来翻译,而这本书与陈英当时的文学品味非常贴近:巴里科在书中飘逸和逃避的人生态度,营造出一种极其惬意的空间感。于是俩人一拍即合。
之后是课业相对繁重的两年,最忙碌时陈英要同时上七门课,从文学到经贸再到翻译。好容易理顺之后,她开始着手翻译意大利犹太作家亚历山德罗·皮佩尔诺的作品《迫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初她对这套书在世界范围内的畅销还比较惴惴,因为与自己惯常的文学风格并不一致,想介绍给调性更契合的师兄,但出版方坚持要用女性译者,她便硬着头皮地接了下来,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像一条路走到头一样成了费兰特所有作品的中文译者。
最开始是比较艰难的,因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文学类型对陈英而言也是全新的尝试。费兰特的小说是比较沉浸于肉欲和世俗的,她将女性的欲望、情感和日常生活描写得非常细致,沉向生活实质的层面。巴里科的小说则是尽可能与世俗脱钩,往精神层面走。如果追根溯源,巴里科的哲学背景,讲究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这一理念对他的写作影响是从头至尾从上而下的,体现在作品和人身上也都是超然世外的。费兰特则是古代文学专业出身,她的写作有对文学先辈如艾尔莎·莫兰黛等人的沿袭,语言文字上有明显的古典文学倾向,是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探索。这种差别对译者而言需要比较大的转变,好在这也与陈英当时的状态吻合:日渐从一个相对飘忽的人向现实层面转变,其实也是一种成长,从少年气向现实世界的成长。
所以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完成后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来自读者的反馈也表示进入状态比较艰难,但从第二本《新名字的故事》开始就相对得心应手,好评如潮。而当时的陈英也正好在教翻译课,通过这套书的翻译,教学和生活也算很好地结合起来,互相成就。
如何理解费兰特的“隐者”心态?
在日常生活中与费兰特同样有着教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等多重身份的陈英,对她的“隐者”心态深表理解。陈英认为“隐者”也许是费兰特的一种心态或状态,但其实更像是她的创作和决定,换言之,她在1991年创作小说《烦人的爱》的同时也一起创造了小说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并且会一直维系和创造下去。
费兰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不是在隐藏自己的写作,而是写作隐藏了她。说明她对自由创作的需求高于一切,因此她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感,为此不惜放弃一切在前台抛头露面的机会,隐入幕后,而且特别坚定。或许这其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碍。
在文学态度上,费兰特认为文学作品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并无必然联系,例如荷马与莎士比亚的身份成谜丝毫不影响《荷马史诗》与莎翁戏剧的伟大,于是索性割断了这种难免流于世俗八卦和花边新闻的眼球效应,让作品直接与读者对话。故而作为译者,陈英也没有主动和费兰特进行过邮件沟通,因为同样觉得并无必要,对文本吃透就已足够,作者要的空间,不论是出版方还是译者或读者,都应该充分理解和尊重。
最好的译者也是“隐者”
陈英曾多次在接受采访和公开讲座时表示,译文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不能过度引起读者注意,注意到译者就是一种失败;好的译者要藏在译文背后尽量诱发读者对原作的阅读欲望,同时切忌不能带入太多自我,否则会很痛苦,译文风格也趋于单一。在她看来,翻译本质上是工匠,要做好的首先是工艺,而非情绪,所以应该精益求精,但不能过多创造。
不过在“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翻译上,陈英表示自己的存在感还是稍微多了一些。一方面是因为最初翻译时为了体现意大利语与那不勒斯方言的区别使用过汉语方言,引起了读者关注,成了译者用力过度的表现。后来在译文中就不再使用汉语方言,而是用语体来提示:“她用方言说……”,至于高雅或低俗,完全通过语体来掌握。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者费兰特的“隐者”身份,推广她一系列作品的工作就天然落在了译者和出版方身上。陈英也就无法做一个纯粹的“隐者”,反而要花不少精力在小说的背景上跟读者有更多交流和沟通,所以最终呈现出来也不仅仅是译者的角度,还包括对意大利历史、文化、城市和人文知识背景的普及,这无形中也让陈英成了读者在译文文本之外理解作品和作者的一座桥梁。
尽管这样的存在感有悖于陈英的“隐者”理念,但她后来慢慢发现自己所做的这些加法,会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影响,比如让读者在某些事上更加坚定,或者因此做出一些重要的选择和决定,这种良性互动也为她收获不少成就感。
选择译作的标准是“好”
在今年做完费兰特所有已出版作品的中文翻译后,陈英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在接下来选择翻译作品时,她不再设置任何标准,除了必须是自己喜欢的“好”作品这一条。比如从翻译生涯伊始时就很钟爱的巴里科,他另外两本代表作《海上钢琴师》和《丝绸》的新译本已经交稿,年内可以和读者见面,与此前的《愤怒的城堡》《一个人消失在世上》合在一起终成完璧。
还有切萨雷·帕维塞,陈英觉得与这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声誉斐然的诗人、小说家在精神和灵魂的状态上比较接近。作者通过对虚化的情结、诗意和哲学含义的对话,探讨了青春、生命和死亡的意义,甚至在作品中预演了自杀。只是他的作品应有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在中国还未得到展现,陈英希望通过对帕维塞的翻译,让读者了解并喜爱上他。
再比如对古典名著《十日谈》的重译。陈英日常就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单论诗词和文言文的精准、洗练和优美,其实与意大利文学殊途同归。不论是卡尔维诺还是埃柯,其现当代文学的根子也在古典上,而《十日谈》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經典。不过陈英重译的初衷并非为了超越谁,更多是译者自己的个人情结:一方面为了提高古意大利语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她作为女性译者的态度。陈英认为《十日谈》过往在翻译时最大问题是男性视角和被指以“色情”的污名化,重译时发现很多所谓“色情”之处不过是有意处理,偏离了原文相对的隐晦和克制。她的重译将尽量贴近原文,且不改变原风格。

电影《海上钢琴师》改编自亚利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述了一个被命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由陈英翻译的《海上钢琴师》新译本已经交稿,年内可以和读者见面。

陈英的翻译作品。
对于现在炒得火热的人工智能软件,陈英也做了使用和尝试,比如她试过用“ChatGPT”来翻译《越女采莲》,呈现的结果是“越南的女子”,摘的则是莲花。所以至少在文学翻译领域,普通的人工智能连“信”“达”都不能保证,更不要说像巴里科这样充满飘逸、空灵甚至禅意的作品和他将行为艺术文字化的小说,比如一个人消失在世上的过程也是找回自我的过程,那种辩证和“雅”的味道是AI翻译不出来的。但它确实可以做很多基础、重复和机械的辅助工作,然后把人解放出来。
至于将中文典籍翻译成意大利文,对译者的要求则更高。意大利文书面语和口语差别较大,这就加大了对写作和翻译的难度。陈英认为翻译的能力本质上是写作的能力,翻译的成就更多取决于母语水平。这方面她比较推崇林语堂,他用英语写的《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等书,在当时成功地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尽管这里也有历史的机缘巧合,但林语堂本人中英文写作功底之深厚,令人钦佩。此外,写作受生活环境和周围语境的影响也很大,陈英希望如有一天可以到意大利生活一段时间,对她意大利文写作水平的提高应有很大帮助。
(责编:常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