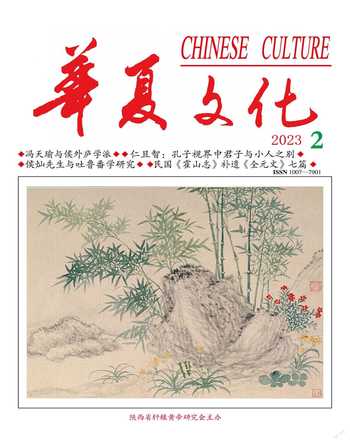冯天瑜与侯外庐学派(下)
三
方克立教授曾说:“形成学派首先要有‘学,就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它还不是一般性的创新思想,而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思想,能够形成系统的学理和学说,对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一个学派开宗立派的代表人物就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学识与人格,对于这个学派的气象和规模、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方克立:《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载《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天瑜教授无疑堪称这样提出足以开创学派之学说思想的宗师型学者。尽管他对我说,长期学术研究中受到外老思想和侯派影响并略有申发,这是事实,但完全谈不上开宗立派。而在我看来,某一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在继承发展中另外形成起具有新的学术个性和思想风貌的学派,这正是这学派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显现,这种生命力又必然会对学术、思想文化繁盛性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譬如王阳明集心学思想之大成而创姚江学派,在他身后,其亲传弟子心斋王艮开门授徒,以“百姓日用之学”为思想宗旨而建构平民儒学,开创泰州学派,这就既彰显了阳明心学的内在生命力,同时又有力推动了晚明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促成了儒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
由此而使我想起了刘泽华教授。他青年时代曾前往中山大学,师从杨荣国先生进修中国思想史。杨先生是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合作者之一,是“侯外庐学派”第一代代表性学者,因此,在学术师承上,泽华教授与外老和“侯外庐学派”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而天瑜教授与外老和“侯外庐学派”则并无任何师承关系存在,但由上述的三点浅见来看,他与外老和侯派更多有着的是治学方法和基本思想观念上的内在关联性。天瑜教授说他长期受到外老和侯派前辈或同辈学者的教诲,相互间建立起深厚的学术情谊。而侯外庐学派的学者对天瑜教授则一直有着高度评价,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外老的重要合作者之一并为《中国思想通史》贡献了所能贡献出的一切,堪称“侯外庐学派”第一代中的重要人物和引领了第二代的邱汉生先生,就对天瑜教授的文化史研究称颂不已,在《<明清文化史散论>序》中说:“解放前,柳翼谋先生著有三卷本《中国文化史》,史料翔实,断制谨严,观点虽是旧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冯天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治中国文化史,成就自当超过前人,即以书中引据浩博而论,已足以与柳先生方规。”因此,吴光教授说:“有不少受到侯外庐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刘泽华、冯天瑜、萧萐父等,是广义的侯外庐学派。尤其是冯天瑜,他写的《明清文化史散论》,深刻论述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新民本思想,颇有外老遗风。”(吴光:《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载2013年5月13日《北京日报·理论版》)
当然,犹如泽华教授“在长期教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政治权力支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等级的人,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必然导向君主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具有以‘阴阳组合结构来支持君权的绝对性,又用仁政、德治、王道、民本、均平、尚贤、变革等理论来对君权作限制、调节、缓冲、缘饰的特点,这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解释体系,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和思想史观”(克立:《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以此为思想要旨而形成发展起着重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的“刘泽华学派”;天瑜教授在继承发展侯外庐学派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显示出自身的学术个性,在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上创新性发展外老学说思想,形成起他自己的学说思想体系。他所提出的“文化生态”说、“元典精神”说(天瑜教授认为晚周为中华文化生成之“轴心时代”,此时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他称之为“元典”;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一部中国文化思想史,实际就是依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华元典形成过程、内在结构及其常释常新的诠释历史)等重要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史解释系统,或者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史观,为科学探讨中国文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范式。以他为核心,以他本人及他与合作者们的一系列著作为标志,形成发展起了着重研究中国文化史并体现出21世纪时代精神的“冯天瑜学派”。在外老过世以后,“刘泽华学派”和“冯天瑜学派”的相继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显示出真正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流派的强大生命力。
说到天瑜教授与泽华教授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不能不论及他们的历史观。泽华教授受马克思名言“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启发而从“王权主义”视角重新审视、评估中国历史,“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与‘王权意义相同的还有‘君权、‘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等等”(引见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年,第51页),揭示“中国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断变动,而其结构却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第2页);“自殷周以来,中国就是君主专制政体。商周是以氏族为基础的以分封为形式的君主专制,春秋时期官僚行政君主专制开始萌芽,战国时期形成区域性官僚行政君主专制,到秦汉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冯天瑜:《“封建”论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天瑜教授并不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是王权专制的社会,而是认为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的中国社会,曾经存在过“宗法封建”的分权政制,王与贵族共治天下,完备形态就是文、武、周公创定的保有若干原始民主遗意的“周制”。但周秦之际以降,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指出:“与欧洲、日本相比,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专制王权的早熟与长期延续。”(《“封建”论考》,第404页) “中国的帝制与专制相共生”(《“封建”论考》,第404页),而“以公元前221嬴政(前246---前211在位)称制‘始皇帝为端绪,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7---1912在位,年号宣统)逊位止,专制帝制历时2132年,共有492个皇帝登极。此间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势是中央集权于涨落间愈趋强化”(《“封建”论考》,第403页);“秦汉以下,中国的王朝频繁更迭,但专制君主制却传承不缀,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又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秦政式的专制君主政制,在君民关系上,务在‘弱民,本在‘制民;在君臣关系上,力行‘君尊臣卑。此种绝对君权,两千年间愈演愈烈”(《“封建”论考》,第408页)。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中,他又申论道:
周秦之际以下,中国政制既与尧舜时代的“众治”揖别,也同三代宗法封建的“礼乐之治”渐行渐远,帝王日益专权,不仅未曾出现古希腊雅典式的城邦民主制,亦罕见西欧、日本式的中世纪贵族政制,统驭万民的是掌握生杀予夺之极的君王。这种“王权决定社会”的体制规约下的政治观念,包括极端尊君论(为“秦制”作则)和民本----尊君论(为“周制”作则),呈现以周制为表、秦制为里的基本格局,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式皇权制度的一体两翼。这一延传两千余年的政治文化,战国初萌,秦汉定型,唐宋得以完备,明清强化到极致,近现代余韵犹存。(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下册,第509页)
他还揭示了周制与秦制對文化的不同影响,说:
殷至西周是宗法封建时代,文化权掌握在宫廷,所谓“学在王官”;至东用(春秋、战国),与诸侯为政相适应,发生从“学在王官”到“学在私门”的转变,进入一个因学术下移而多元发展的阶段。此为周制对文化的影响。
秦并山东六国,建立一统帝国以后的两千余年间,除分裂时期相对松动外,学术文化受到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的控摄、支配,形成“大一统”的学术格局。此为秦制对文化的影响。(《“封建”论考》,第521页)
他更依据详尽的历史资料,揭示中国皇权政治具有起点早、持续久,植根碎片化的小农社会,君主政治理论早成而完备,“君权神授”与“民为邦本”,与宗法制结合,君主集权趋于强化,“君本位”与“官本位”,“贵”---“富”互动等特点。应该说,天瑜教授和泽华教授所论,虽未必完全一致,但基本观念和思想精神是相通的。这种历史观绝非异想天开的虚构,反映出的乃是中国历史的事实,诚如萧公权所说:“中国之君主政体,秦汉发端,明清结束,故两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也未有逾中国者。”(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47页)至于钱穆《国史大纲》所以为的中国帝王并不特别专制则只能是书生臆想之见。
泽华教授指出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在于“王权支配社会”,天瑜教授强调自秦至清末,皇权专制贯串了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始终,但他们绝非历史虚无主义者,都没有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或皇权专制传统予以简单的全面否定,而是都充分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在某些方面对历史的进步起过有益作用的一面,如中华民族的形成,地域的扩大,某些有利于经济恢复(相对于它的破坏而言)和发展的措施等。并且,泽华教授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并不是纯任专制君主宰制的羔羊,而是天然的民主派,他们从维护自身生存利益出发孕生出民主意识,甚至在他们的现实社会中还将民主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如民间结社即为显例。天瑜教授则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专制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制约皇权的因素,如“天----理”、“礼----法”观念就在形上意义上制约着皇权,“受命于天”说固然为皇权政治赢得合法性,至高无上、大公无私的“天道”又对皇权起着制衡作用,礼俗、家法、祖制、律法亦约束帝王言行;而贵族阶层、官僚体制以及乡绅起中坚作用的民间自治则成为制约皇权的社会结构因素,如即使在皇权达于极致的朝代,帝王意志也难免遭遇朝臣的封还、清议的批评。当然,这些制约因素缺乏法制规范,对专制皇权的制衡力有限。
在行将结束本文时,我还想就天瑜教授有关“封建”概念的辨析及其取得的成果忆述两件事,从中或亦可见真正学者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是先师黄公宣民先生在临终前亦注意到天瑜教授对“封建”说的质疑,他曾嘱我一定留意天瑜教授这方面的论著。他说外老根据“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路径,并指出中国的“封建化”(实质是前近代性的转化)也有自身路径和特色。天瑜教授作“封建”辨析,不是要为专制主义辩护,而是意在指明人类社会历史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多样性。史家之职就在于要担当起揭示出这多样性的责任和使命。惜乎黄公过世太早,他没能够撰文论析。二是泽华教授曾对我说,究竟用什么来概括秦以来的传统社会,这可以充分讨论,但(一)肯定不是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天瑜教授的辨析是对的,很有必要;(二)肯定有个社会形态类型;(三)权力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是剖析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锁钥,但这不是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概括。他说自高度关注了天瑜教授 《“封建”考论》后,因没考虑好用什么术语概括传统社会形态,行文中常沿用习惯了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但一定括注“姑且使用这一术语”,以示自己并不赞同这概念。
另,泽华教授曾注意到2010年《文史哲》杂志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上学者专家对秦至清末社会形态形成的重要共识:“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从秦至清末中国古代社会这一真正的历史基因出发,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用诸如‘皇权社会、‘帝制时代、‘帝国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等多个命名来取代‘封建社会的主张。”他说:“从报道看,出席会议者都是当时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共识显然不是临时动议,而应是多年来学术界积累的升华。”(刘泽华:《八十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78页)我想,在这样一个“多年来学术界积累”而终于升华形成“共识”的过程中,泽华教授从“王权主义”视角重新审视、评估中国历史,天瑜教授对“封建”的考论以及明确指出的既然贯穿秦至清的是“宗法制”、“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地主制)以及“专制帝制”,那末,“秦至清主要时段宜命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参见《“封建”论考》,第390-411页)这样一种历史观,无疑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天瑜教授和泽华教授都是从外老学说中汲取思想滋养,承继外老精神遗产而发展出富有自身学术个性的理想主义型的史学家。泽华教授坚信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并非单纯地引进西方文化就能成功,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弘扬传统文化就会实现,而是要否定和摆脱那些至今还阻碍我们现代化进程的思想重负。民主主义、公民意识和自由观念需要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痼疾消肿之后,才会在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的建构中生根发芽。天瑜教授则说:“中华民族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中贡献过震惊全人类的文化,又没有在近代的挫折中甘于沉沦,而是顽强地摸索重新崛起的路径。可以确信,有着如此雄健的生命活力与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垦殖新生产力的丰厚土壤,汲取科学世界观的阳光雨露,一定可以重新赢得文化的原创性动力,创造出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现代世界的新文化。”(《中华文化史》,第1180页)他们这种思想认识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作者:天津市西青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邮编:300380)
【作者简介】陈寒鸣(1960-),男,江苏镇江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泰州学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