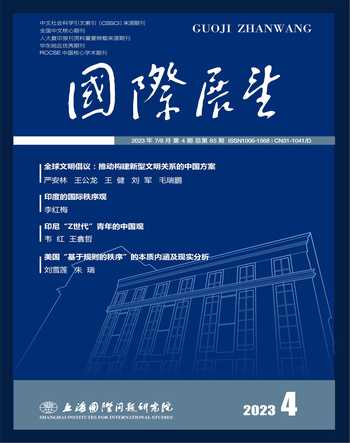中国倡导“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价值、内涵与路径
【内容摘要】 航行自由是全球海洋秩序的核心内容,美国为维持世界霸权,宣扬“海洋航行自由”论并付诸行动。这种单方面曲解海洋法规则尤其是歪曲航行自由制度的主张和行为严重威胁海上安全和海洋秩序,引发国家间海上活动争议和冲突。中国应倡导“开放包容、安全畅通”“和而不同”“和平、合作、和谐”等具有航行自由特质和中国文化元素及时代要素的航行自由观,这是协调各国立场和权益、兼顾自身经验和时代特点的中国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倡导的这种航行自由观,不仅开启海洋法规则体系完善进程,成为与西方强国在国际法规则、航行自由解释话语权方面进行斗争的重要标志,也符合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目标。在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挑战和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既可为海洋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也可为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 航行自由 海洋新秩序 国际法治 海洋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金永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青岛 邮编:266100)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4-0102-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4006
航行自由是现代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兴海洋大国以及最大的南海沿岸国,一贯重视和维护国际法上公认的航行自由。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以“非法限制航行自由”为由攻击中国正当的海洋权利主张及相关国内立法。 这实际上反映出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同中国在“航行自由”这一重要命题的内涵认知上存在明显分歧。针对航行自由问题,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外国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制度上的分歧:自由使用论与事先许可(通知)论之间的对立,以及直线基线的适用争议。 主流的观点和公正的主张是,外国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应遵守沿海国关于领海的法律和规章,法理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30—31条。 其次,针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争议:自由使用论和事先许可(通知)之间的对立。即在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测量、联合军事演习、谍报侦察等军事活动,在性质上属于与经济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对其管辖权归沿海国还是使用国之間的争议(即剩余性权利归属争议),在原则上表现为自由使用论和事先许可论之间的分歧。 其涉及对《公约》第58条第1款“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解释上的对立和分歧。由于《公约》并未规定“军事活动”的概念,即使从“海洋和平利用”“海洋科学研究”视角也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只能通过有关国家的双边对话包括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加以解决。
在航行自由方面,受到普遍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航行自由年度报告》(Annu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port)。美国自1979年以来,依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所谓法律立场,在其他国家的管辖海域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这种挑战很多国家的海洋权益及立场、谋取自身私利的主张和行为,严重威胁航行安全,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对。
中国应在吸纳国际法上公认的航行自由的本质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系统阐明针对海洋航行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倡导并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元素及时代要素的航行自由观(简称“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这种航行自由观对完善海洋秩序、海洋治理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价值
中国适时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启动海洋法规则体系完善进程,并对西方强国开展涉及国际法规则包括航行自由话语权斗争的重要标志。这也符合在全球海洋秩序面临挑战和全球海洋治理变革的背景下,使中国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融入海洋法的规则和制度的需要,并能为呼应全球海洋治理理念升级作出中国贡献。
(一)价值之一:提升参与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话语权的重要标志
作为国际规则中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获得了中国有关主管机构和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学界,国际法学者更加认识到中国对于推动当代国际法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国际法的立场、态度、主张和贡献引人注目,并越来越具有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以欧美国际法为代表的西方国际法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处于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对于国际法领域的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在国际法领域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有学者指出,国际法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仍然是大国制定规则、小国承受规则。
在国际海洋法领域,主要表现在近20年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沿海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海洋强国对《公约》中涉及航行自由的若干规则所进行的不同解读及由此引发的立场和实践上的明显对立。 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和“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rules-based maritime order)自居,以本国或少数国家对某些国际海洋法规则的片面、甚至完全错误的解读取代《公约》以及公认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习惯。 另一方面,中国在2009年和2019年分别提出“和谐海洋”理念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己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
因此,究竟未来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将继续由美国等西方传统海洋强国主导,还是将由以中国为代表的真正维护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为广大沿海国家谋利益的发展中国家主导,要素之一取决于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对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变革有关的话语权斗争。为此,在海洋航行自由问题上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理阐释,是获取国际话语权并丰富和发展国际海洋法规则的切入点和重要契机。
中国如能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洋强国在关于航行自由问题的交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得到广大发展中沿海国的支持,在国际法的道德高地和法律战上占据有利地位,就可以在国际海洋法领域进一步提升、巩固中国在相关国际问题治理领域和国际法领域的大国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在现阶段表明针对航行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并依据海洋航行自由的特质倡导和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符合中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变革的战略目标。
(二)价值之二:助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提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不仅有利于提升自身在世界沿海国家中的号召力、影响力,有利于在同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的博弈中获得制定新型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深化。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利用海洋的认知态度尚无法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与管辖权的桎梏。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纷纷加强对海洋空间和资源的控制与开发利用,《公约》因多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在创设及分配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先天性的制度设计缺陷和不足,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蓝色圈地运动”。因此,在海洋治理方面,国际社会需要新的理念以及在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制度,其中包括完善与发展国际海洋法。 而与航行自由有关的规则博弈作为《公约》制度的基石,历来是各国为获取海洋空间和资源、控制海上重要战略通道以及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角力场。
合理、有效地解释和运用《公约》中涉及与航行自由有关的规则,不仅可以发挥维护、巩固中国既有海洋权利主张的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法律战上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积极斗争,逐步改变由个别国家基于私利来片面解释航行自由相关制度的不利局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积极运用航行自由制度,对解决中国海洋权利维护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解读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国际法规则,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适时提出“新时代的航行自由观”,可以为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基础和重要保障。
二、“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核心内涵
如上所述,以美國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主张的“航行自由论”(尤其是“军事航行自由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明显问题,是对传统航行自由制度的片面甚至错误解读,服务于其维护世界霸权的需要。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不仅侵害了沿海国管辖海域(尤其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权益,而且片面解读了与海洋法有关的海洋自由规则。因为海洋法(尤其是《公约》)规定了不同海域的航行自由制度,各国在行使航行自由时受到多种限制和约束,所以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不是横行自由和威胁自由。美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和主张,自然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坚决反对,各国需要批驳美国的认知和行为。要客观、全面阐述中国针对航行自由的立场和观点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就必须明确与航行自由有关的若干原则或属性。首先是基本立场。提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并不是舍弃传统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而是基于传统国际法上航行自由制度的特点和性质进行正确解读,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因为只有正确理解航行自由的本质,才能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制度进行准确演绎。其次是重要理念。提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需要结合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形势,包括及时融入中国倡导的国际法理念,特别是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原则和精神,与时俱进地发展航行自由制度,更好地实现公正、公平目标。再次是实践要求。提出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需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并与“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法治蕴含的宏观理念和价值相符。因此,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需要立足全球治理视野和国际法治精神,通过提出“中国方案”、制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重点解决现实航行自由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为此,本文拟从航行自由的本质、和平解决与航行自由争端有关的立场、构建和谐与合作的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三个方面,阐释“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核心内涵。
(一)航行自由的本质:开放包容,安全畅通
上文已述及,航行自由是国际法上久已确立的一项权利,且被视为海洋自由的核心。 该项权利能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是因为它始终致力于在各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等个体利益同贸易、航运利益等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间寻找最佳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了航行自由的本质,即开放包容、安全畅通。这也是倡导“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所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
第一,开放包容是航行自由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航行自由与海洋本身属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 航行自由自身的进展就是与人类对贸易自由的追求相伴而生的。 它带来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实现了全球经济的大融合,因而传统的航行自由特别强调海洋自身的开放性。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试图通过封闭海洋和瓜分海洋将海洋占为己有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例如,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曾于1493年得到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发敕令的授权,准予两国瓜分世界海洋,但随即遭到法国、荷兰等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从未真正有效地对它们各自“拥有”的海洋行使“主权”。
在当代国际海洋法体系(尤其在《公约》)中,航行自由开放包容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各国船舶在各类海域中有不受阻碍的航行自由权。例如,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公约》规定了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航行自由(第87、58条);在沿海国的领海、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公约》也规定了各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以及群岛海道通过权(第17、52和53条);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规定了外国船舶的过境通行权及无害通过权(第38、45条)。
同时,为实现各国依航行自由原则享有的航行便利与沿海国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 船舶在上述海域的通行权也受到《公约》条款的若干限制。例如,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它受到“适当顧及”(due regard)原则(第87、56条)和“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第88条)的限制。外国船舶在领海内的通过应严格遵守沿海国关于无害通过领海的法律和规章,如不得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不得从事“有害”活动或与通过本身无关的活动(第21、19条)。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过境通行的外国船舶不得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得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第39、40条)等。总之,航行自由的开放包容属性在《公约》体系下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而《公约》规定的这些合理限制并未影响各国行使正常航行的权利。
第二,安全畅通是各国享受航行自由的必要保障,这对于国际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中强调了保护海上贸易路线安全的重要意义。 在当代,重要国际航道的安全依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来自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所以,如何确保国际航道乃至整个世界海洋的安全畅通,在当今全球海洋秩序下依然是一个“旧原则面临新挑战”的重要课题。
此外,《公约》虽对海盗罪行、海盗船舶以及外国军舰的登临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第100—107条),但对在位于沿海国管辖海域内发生的、沿海国因自身能力有限而无力惩治或管辖的海上抢劫行为,或对在公海上以政治目的而并非为私人目的从事的海上抢劫行为,仅凭《公约》规定的上述条款无法实现治理的要求和目标。为此,1988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其中引入了“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概念,并将《公约》规定的海盗罪行未能覆盖的其他威胁航行安全的行为列为缔约各国均可管辖处置的罪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约》在海上安全方面的缺漏。 但该公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国际社会在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活动上仍任重而道远,保障世界重要海域和海上通道的航行安全依然是各国真正实现航行自由的前提条件。所以,从航行自由的本质来看,“安全畅通”依然是航行自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和平解决与航行自由争端有关的立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如果说开放包容、安全畅通是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必须坚持的传统航行自由的本质,那么“和而不同”则凸显了“新时代的航行自由观”内涵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事实上,与航行自由有关的问题是1973—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各国激烈交锋的议题之一。 在《公约》“一揽子交易”(one pakage deal)的审议程序下,为顾及《公约》的完整性、权威性、普遍性,《公约》的最终文本中没有直接凸显各国之间关于航行自由问题的激烈矛盾,而且《公约》本身也明文禁止缔约国对《公约》条款进行任何保留。 但这并不代表各国之间(特别是西方海洋强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航行自由的诸多争议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实际上,对于《公约》未予明确规定的与航行自由有关的事项,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发表了非条约保留性质的解释性声明。 显然,自《公约》诞生以来,各国对与航行自由有关的问题就充满争议和分歧。为此,倡导并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就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在承认存在争议和分歧的基础上,各国努力秉持诚意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尝试解决这些争议和分歧。
第一,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要实现和而不同,就需要在保证开放包容和安全畅通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而不是像西方海洋强国那样实施零和博弈。特别是西方海洋强国对属于“灰色地带”的海上军事活动强调所谓的自由, 而这与争端各方遵从的和平、和谐、和解的准则背道而驰,无益于它们在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体谅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一方面,要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洋强国之间在航行自由若干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要努力协调、化解分歧;另一方面,应当将分歧和矛盾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因航行自由问题引发直接对抗并造成重大损害。部分西方学者亦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例如,欧克斯曼(Oxman)和墨菲(Murphy)就曾表示,“无论是沿海国还是海洋大国,只要将自己对法律的解释‘强加给另一方,就是一种挑衅行为;在确定权威的解决方案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应被迫放弃自己的立场,争端双方都应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对方作出暴力反应的可能性。” 这也说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的国际争端所必须秉持的原则或理念,应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海洋强国之间解决航行自由方面的争端。
第二,坚持加强沟通和协商解决争端的态度。习近平指出,“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各国应该秉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的态度。“有事”意味着在各方之间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存在持续的争端。对于航行自由问题,中美两国之间就存在争议乃至对立,属于“有事”情形,但“有事”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必然会爆发冲突或对抗。“商量”指通过沟通和协商力求消除分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联合国宪章》第33条规定了谈判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出现争端时,相关方应该保持对话、交流而非冲突、对抗,应当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与航行自由有关的争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对立与分歧。中美双方应秉持善意和诚意来解决相关问题。为避免争端升级,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一方违背另一方的意愿,利用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漏洞而单方面诉诸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国际社会应正视争端,并对争端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
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特征:和平、合作、和谐
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应反映“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价值和精神,体现“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特征。
第一,和平是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的本质特征,也应被视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和平的海洋航行秩序,一方面,体现在任何国家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船舶都应以和平使用作为行使航行权利的指导性原则上。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挑衅性、危及沿海国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的行动。这就要求有关国家,特别是拥有强大海军实力的海洋大国和海军强国严格依据《联合国宪章》《公约》的原则和制度行使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和平解决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国际争端是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重要内涵,有关航行自由的争端,应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二,合作是促进各国形成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的必由之路。当前,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在多处重要的国际航道威胁着航运安全,确保航行自由内涵要义之一的“安全畅通”,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确保在本国海域内的所有船舶的航行安全以及悬挂本国旗帜的船舶在其他海域内的安全,离不开各国政府及海军之间开展各层面的广泛合作。“增强互信、平等相待、深化合作”是各国之间应对威胁航行安全问题的必然选择。
第三,和谐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各国友好、互信地共同使用海洋的愿景。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从根本上体现的是“平等相待、和而不同、诚信正义、立己达人”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 对于航行自由,和谐意味着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对于国家管辖海域内航行权利的行使必须互相遵守“适当顾及”的义务。一方面,沿海国不应利用国内立法对其他国家船舶的正常航行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应在沿海国管辖海域内从事与航行无关且影响沿海国主权及主权权利行使的“有害”及“不友好”的活动。
三、“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实现路径
未来,要实现“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为航行自由争端的解决提出中国方案,就需要以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以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全球海洋秩序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合作共赢为指引,善于运用政治、外交和国际法等手段,适时、合理地在有关外交场合正式提出该倡议,并推动各国付诸实践,使中国的合理倡议成为各国行动的指针。
(一)适时正式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
如前文所述,以欧美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垄断了国际法的话语权,并时常凭借其传统海洋强国地位曲解以《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规则体系,在航行自由问题上更是以“军事航行自由观”谋求维持海上霸权。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仅对西方国家这套打着“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的幌子行海上霸权之实的逻辑予以批判,而不提出系统性主张,那么对于全球海洋秩序改革的意义将不明显。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双边及多边外交场合适时正式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海洋治理中涉及航行自由的问题作出贡献。
从技术上说,虽然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发布政府白皮书的形式正式提出对于某个国际法问题的立场态度, 但是通过双边及多边外交场合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观则更为适宜。因为航行自由问题不仅关乎一国自身利益,还广泛涉及周边海洋邻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属于世界各国共同关切或关心的事项。事实上,中国历来重视运用多边及双边外交场合阐明自身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问题的重要立场和态度,并且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和高度认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在双边外交场合,可通过访问、会晤等形式,在双边磋商和对话中阐明中国对于航行自由问题的主张,正式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并以发布联合声明的形式表明两国对于航行自由问题的共识,以诠释“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丰富内涵,从而使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写入双边外交文件,并向国际社会发布。
第二,在多边外交场合,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无论从霸权国家制定国际规则的已有经验,还是从当前国际规则的运作和改革实践来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多边渠道都是制定国际规则的舞台, 所以,灵活运用传统外交方式,特别是通过多边外交阐述中国针对航行自由问题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具体而言,中国可运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国主办的多边会议等渠道,积极将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推向区域乃至全球。
(二)推动航行自由领域的国际合作
从自然属性上看,作为全球公域,海洋整体功用大于部分功用, 这就决定了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的“独角戏”,客观上也就必然要求中国推动各国在航行自由领域加强合作。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應当包括关系到海洋法治重要议题之一的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多边治理、危机管控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改良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就实现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而言,中国应在以下两个涉及航行自由的问题上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
第一,中国应继续加强同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航行安全合作。众所周知,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航行自由(特别是航行安全问题)历来是中国以及各国关注的重要方面。这是由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南海也是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全球50%的商船和1/3的海上贸易航经该海域,每年10万多艘商船通过该海域,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从来不是问题。 同时,为应对相关海域威胁航行安全的海盗和武装劫持事件,中国应继续在《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机制基础上,在协调军舰巡逻、商船护航、打击海盗、引渡海盗罪犯、信息通报与分享等具体事宜上主动寻求同该条约缔约国的合作,为保障南海及东南亚国家周边海域航行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实际上,中国持续加强了保障航行安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的国际合作。截至2023年6月8日,我国已派遣海军舰艇编队44批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在亚丁湾海域开展护航行动15年来,中国海军已累计派出100余艘次舰艇,完成7 0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解救、接护各类船舶近百艘,其中外国船舶占50%以上。 而2021年2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八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海警有权依据中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对等、互利的原则,开展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际和地区海洋公共安全和秩序。
第二,中国应加强同其他重要国家的海洋航行安全合作,推动与航行自由有关的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这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门签署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这是中美两国对于航行自由可能引发海空意外冲突事件而加强管控合作的有益尝试。但是,由于该备忘录没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且适用范围有限,因此在实践中并未发挥预期作用。 所以,中美双方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相关制度。此外,自2013年8月以来,中国开启了同东盟各国就“南海行为准则”(COC)进行磋商谈判的工作,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今后需在适用范围、法律拘束力、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和一致意见。 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离不开创设一套令各国可以接受的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套机制不仅应反映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所包含的“和而不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内涵,还应真正起到保障航行自由与安全的积极作用。所以,创设行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本身,必然离不开相关国家间真诚、善意的多层面、多维度海洋合作。
(三)合理运用国际法手段维护国际海洋法治下的航行自由
形成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同样离不开以《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规则体系及相关国际法制度的保障。 具体而言,中国可从两个方面入手,维护国际海洋法治下的航行自由,推动全球海洋秩序有序变革。
第一,在《公约》缔约国会议上阐明中国对于航行自由的立场和主张,并提交相关问题的建议案和改革方案。中国在提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同时,一方面要对西方海洋强国的“军事航行自由观”予以批驳,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寻求同《公约》其他缔约国开展航行自由领域的合作,争取获得广大发展中沿海国的全面支持。在必要时应会同其他国家联名提出针对航行自由问题如“统一解释”或“共同声明”之类文件,以推动《公约》框架下航行自由争议问题的澄清和解决。
第二,可有效运用“第二轨道”,即通过中国国际法学者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向全球国际法学界“发声”。中国国际法学者群体在2016—2017年间批驳所谓“南海仲裁案”时,已积累了“法律战”经验, 所以中国国际法学者完全可以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发挥作用,提升话语权,发挥影响力。当前,可由相关主管部门或机构牵头,组织、邀请国内精通国际海洋法(特别是航行自由问题)的专家、学者,以“航行自由的中国视角”为主题,撰写和编著学术性质的文集,并将其译成多种外文,向境外国际法学界推介;还可邀请外国学者赴华参与主题论坛,讨论与航行自由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对外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团结支持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外国学者。同时,要大力鼓励、支持学者通过在境外出版书籍和发表论文的方式同西方国际法学者进行学术辩论,开辟并拓展航行自由领域的学术争鸣阵地,传播中国主张,真正将“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推展至全球,争取外国学界的关注和更多支持。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的发展,进而使之演绎为阐释海洋航行自由的新规范和新制度。
结束语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传统海洋强国仍然凭借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及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打着维护全球海域航行自由的旗号,实际上在采取谋求军舰“横行自由”的行动。这种包括“军事航行自由观”在内的“海洋自由论”的主张和做法,既不利于推动国际贸易与航运,也不利于维护以《公约》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海洋法规则体系。这种状况要求当今全球海洋秩序实现变革、突破和创新。
为此,基于海洋航行自由的特质,有必要形成“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反映中国对于航行自由这一国际法经典命题的独到见解。中国适時提出构建具有“开放包容、安全畅通”“和而不同”“和平、合作、和谐”等丰富内涵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可以体现中国对于新时代全球海洋秩序的立场和态度,目的是捍卫传统国际法上航行自由的基本价值,摈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强国企图继续维持海上霸权而刻意曲解《公约》的原则和制度、实施“横行自由”的“军事航行自由观”,最终为维护广大发展中沿海国的航行利益和安全利益,构建和平、和谐、合作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中国方案。这不仅有利于解决针对航行自由问题有关的争议,有利于营造和平、合作、和谐的全球海洋秩序,更有利于推动海洋领域的国际法治。所以,形成并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既有其适应形势、符合国际法发展趋势的积极立意,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构建“新时代航行自由观”,一方面,应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进行各种理论上的准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与海洋航行自由有关的国内法治和话语环境; 另一方面,为了推动中国倡导的“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走向世界,需要积极开展诸多重要的研究性、解释性和传播性工作。这些工作的综合开展,有助于“新时代航行自由观”被国际社会所认识、理解和拥护,并融入新时代全球海洋法治体系,成为处理和解决与航行自由有关争议的新原则和新制度。
[责任编辑: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