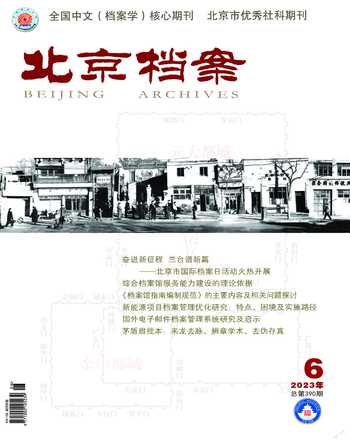梁启超与晚清西学翻译
伍媛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史学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启新风气的一代大师,面对中华民族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提倡西学,极力推动外国著作的翻译,以期“兴民权”“开民智”。值此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特根据晚清档案记载,追记梁启超致力西学翻译的历史片段。
一、译印书报的倡议宣传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源于强学会对译书的重视与提倡。1895年前,我国翻译的西学主要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甲午一役失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军事技术的落后,而是政治体制落后所致。于是,他们主张学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进行政治改良。为了号召更多有识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1895年11月在北京创办了强学会。强学会倡导西学,主张译印图书,传布要闻;出版报纸,刊布新闻;购置图书,设图书室。在这期间,梁启超“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1],从而引发了对译书的关注。
强学会在遭到清廷的封禁后,梁启超深感时局维艰,风气未开,于是将注意力转向办报,以开民智。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共同创办《时务报》,汪康年和梁启超分任经理和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60篇慷慨激昂的文字,“他利用这一宣传阵地,较全面而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内容和具体思路”[2]。该报为旬刊,每期3万余字,设有“西文报译”“域外报译”“英文报译”专栏,广译五洲近事。梁启超在其中多次呼吁学习西方文化,如刊登于《时务报》第8期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对中国近代译书史做了系统梳理和研究,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3]。在《时务报》第45期中,梁启超撰写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再次提到“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4]。他将兴西学与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认为此举必将影响深远。
二、大同译书局的实践尝试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廷掀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其主张之一就是创办西式学堂,培养外语人才。最初,清廷仅有同文馆及江南制造局等几处译印西学之书,所译之书仅数十种,“且皆二十年前之陈编”[5],不敷使用。1897年9、10月间,梁启超在多方努力下,于上海南京路创设了大同译书局,康广仁任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称,此举是促成维新变法的关键一步,“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曾翻译了大量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著作,加之清政府于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梁启超认为,译介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从日文间接翻译是一条捷径,他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翻译宗旨,具体方法为“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来变法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6]
大同译书局在开办第二年奉谕改为官书局,后因戊戌政变失败而被迫停办,但在这一年中陆续出版了《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意大利侠士传》《日本书目志》等书,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时局提供了精神食粮。
三、变革中拟定《译书局章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光绪帝诏书里强调,“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7]
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上奏,向光绪帝举荐“维新救时之才”,他提到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忠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各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该省风气为之大开”,建议“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著效甚速。”[8]当日,光绪帝谕令“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9]。总理衙门察看后,认为梁启超“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礼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10]
与此同时,设立译书馆以开风气启民智已然成为一些朝中大臣的共识,如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认为,“言学堂而不言译书亦无从收变法之效也”,他提出,将泰西、日本各学精要之书可尽译之,“而天下人士及任官者咸大通其故,以之措政,皆有条不紊”。[11]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请旨“开馆专办译书事务,遴调精通西文之翻译数员广购西书,分别门类,甄择精要,译出印行,以宏智学”。[12]对此,总理衙门议奏,肯定了译书的必要性,“今当更新百度之始,必以周知博采为先”,同时也提出,如另设译书局,“易致复出,徒费无益”,建议北京的译书局“可与上海联为一气”,由梁启超办理,“所有细章皆令该举人妥议”。[13]
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梁启超向光绪帝提出了开启民智的方案,光绪帝赏予其六品官衔,并令其办理译书局事务。8月16日,梁启超拟定《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折》[14],由吏部尚书孙家鼐代奏。在这份奏折里,梁启超对译书的原则、译书局的设置及经费来源都做了规划。
一是译书原则,梁启超认为以往所译之书,多为兵制、医学类的图书,学者并不能真正悟出西方富强之本,他提出译书应“先政而后艺,先总义而后专门,庶几条例本末粲然具见。”梁启超将翻译图书种类按轻重缓急的次第顺序做了规划:第一,“西国富强由于内政修明,今当首译其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律例学各书”;第二,“西国富强由于变通尽利,今当多译其史志,以观其沿革得失之迹,其各国名人传亦当搜译”;第三,“西国各省各部之章程皆屡经损益,密之又密,今当广搜多译,俾他日欲办某事,即可酌照某事之章程施行”;第四,“富国之学全恃开源,今当广译农政、矿政、工政、商政之书,以资取法”;第五,“各种艺术皆以格致为根本,天文、地质、声光化电各书,旧有译本,今专采其新出者译之”;第六,“各国蓄志積虑窥伺东方,今当取其论中国情形各书尽译之,悉其阴谋,借以自警”。因日本已译出西书六十余种,他建议“先由东文转译,其事更捷,至一年以后然后译英法各文”。
二是设立译书局的内部机构,包括“总办一人,坐办二人,总翻译一人,东文翻译四人,英文翻译四人,法文翻译二人”。在译书局之外,另设翻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学堂“设总教习一人,其分教习即以各翻译兼充,校勘六人,钞写十人,司事四人”。学堂设东文、英文、法文三馆,其学生分为两种。对“中学颇深,曾多阅译出各西书,而未通东西各文者”,则教授东西文。对“已通东文、西文,中学尚浅者”,则教授中学,梁启超认为,“两途并进,则成就译才自易”。
三是译成图书的使用,梁启超提出,译出各书拟写书目提要,加以装潢。图书分为三类,首先“进呈御览”,其次“呈送军机处、总理衙门、大学堂各一份”,最后送各省督抚、学政各一份,“以备考试调阅之用”。对于各省新设有藏书楼的学堂,也加送一份,“其余则减价出售”。梁启超同时提出,译出各书当仿照东西各国之例,不准坊间翻刻,以杜伪误。
四是译书局的费用。梁启超提出,每年年终,要将一年译印书数量、所需费用开列清单,呈报总理衙门备查。因译书局为官商合办,如遇经费不足的情况,“即依原奏招集股份,以竟其成”。
光绪帝充分肯定梁启超对译书局的构想,亲笔御批“尚切实,即着依议行”。光绪帝认为,梁启超提出此事,应为“经久之计”,而不是草率迁就。为确保译书局的经费,光绪帝还大大增加拨款,特批: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着再加给银一万两;常年用项,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二千两。自七月初一日起,“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15]
然而,1898年发生的“百日维新”不久就以“戊戌政变”的失败而告终,康有为、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日本。梁启超早期的翻译事业至此暂告一段落。
维新变法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在此影响下,中国近代翻译也实现了由单一器物翻译向自然科学翻译与社会科学并重转变,开启了中国近代翻译的新境界”,梁启超则“在思想上为这次转向发挥了领导作用”[16]。他提出译当译之本,尽译西国章程之书等观点,打破中国封闭保守的文化状态。正是他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使得中国的翻译事业迎来了清末民初的学术重心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日文书籍得到翻译出版,其中以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广智书局、教育世界出版社最为有名,“对时人曾发生极大之影响,受其启发而研究西学者接踵而起”[17],推动了近代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翻译的潮流。
注释及参考文献:
[1][6]汤志钧,汤仁泽.梁启超全集:第4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9,271.
[2]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4.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3.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52.
[5]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为开馆译書事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档号:03-5615-0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7]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档第1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为密保梁启超等维新救时之才请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事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档号:03-9446-0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9]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谕档第2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遵查广东举人梁启超学问淹通究心时务询为有用之才请酌予京秩并特赐召对事奏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档号:03-9446-0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11]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为译书智民其功至大请总署议行事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档号:03-9446-0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12]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为开馆译书事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档号:03-5615-0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1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遵旨议复责成梁启超办理京师编译局事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档号:03-9447-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14]呈举人梁启超所拟译书详细章程清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档号:04-01-38-0029-0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
[15]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上谕档第1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4.
[17]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75.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