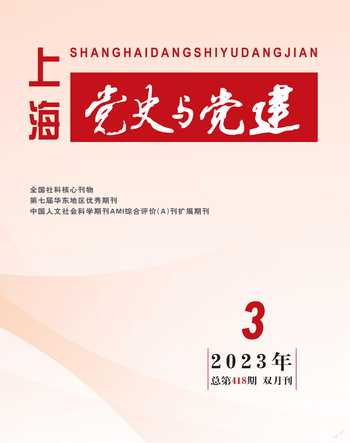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社会主义”主要问题的探讨
肖建平
[摘 要]
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思想理论界同一线干部群体以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方式,合力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势体现、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加以思考和探讨,这对系统解决理论上的偏狭、政策上的偏差、工作中的偏激具有积极影响;还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助力推进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由于有的看法超前和有的观点偏执,在广获赞誉的同时也引发质疑和批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经验和教训再次表明,如何掌握好意识形态战线收与放、严与松的张力,保持理论与决策、务虚与务实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论题。
[关键词]理论工作务虚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K27;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3-0049-08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外越发注重以实践效果而非主观臆断作为检验路线方针政策的准绳,并由此汇聚成一场思想大解放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的洗礼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触动下,广大思想理论工作者和一线领导干部中的精英人士借助1979年1—4月中央层面理论工作务虚会,结合具体实际和亲身体悟,对社会主义主要理论问题开展思考总结,有效助力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策是非的拨乱反正。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
制度优越性的探讨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历经理论的混杂和实践的失误后,重新厘清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改革之初首次开诚布公地探讨该课题的中央级别会议,发挥了破冰和探路作用。
(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讨。务虚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对事关重大但并未完全厘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发表看法。多位代表直抒胸臆,指明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内涵、本质、界限等存在混乱而模糊的提法。中国社科院董代表的发言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干部和群众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往往把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并且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致使思想更加混乱,政策越发错位。
至于造成复杂局面的原因,与会人员从多个角度作了思考。有的归咎于不法之徒,林彪、“四人帮”使得“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康生却在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常识的问题上,一再制造混乱”。有的归因于个人因素,“毛主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看法。这套看法和他原来的想法不同,也和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不一致”。这些判断略显粗糙。与其说是个体的责任,不如说是领导集体的责任,是中共在力图独立探索一条优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产生的困境。
与会人员还就尽快解答该课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展开交流。一方面,有的代表提出这是理论工作正本清源的内在要求。国务院研究室林代表谈到:“我们很需要向青年人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事实上在这些问题上有许多糊涂观念,不仅年青人分不清,有的老年人也分不清。这就需要大家下一番功夫,进行一些研究。”在第二阶段会议中,一些干部提出:澄清理论认识是一项前提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现在连这个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许多正确的东西还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有其特质和评定标准,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有明显界限。但这个界限在哪里、社会主义的评判细则是什么,受实践程度和认识深度所限,并未完全厘清,决策层同理论界相互之间及其內部之间都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有的代表提出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尽快解答该课题。国务院研究室于代表认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亟待解决。理论指导实践,解决这个问题不论对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是很重要的。”在第二阶段会议上,邓小平就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发表讲话后,不少代表据此进一步延伸。中央党校韩代表谈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四人帮当政时有的地方一个农民种三棵自留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种两棵树以下就是社会主义,不弄清楚是不行的。”
与会代表均认为,“左”的指导思想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央,放大了“修正主义”的危害、缩小了“社会主义”的空间;在地方,人为设置了“社会主义”的量化标准,如“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就是资本主义”;在基层,社员自留地、集贸市场、家庭副业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取缔;总体呈现层层加码的递进逻辑。代表们的讨论意见助推此后全党长时间不间断地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课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从理论到实践都带有一些问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前30年经验教训和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引导思想理论界与中央决策层开展良性互动,最终科学解答了该课题,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探讨。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密切关联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足基石。可对广大青年人来说,对优越性存有很大困惑,“他们往往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四人帮宣传的那种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尝够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苦头,他们看不出这种‘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这种质疑看似轻巧,实则隐患丛生。正如国务院研究室林代表所说:“当前有一个很急迫的问题,就是要向青年人讲清楚为什么这十几二十年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这不仅要从理论上来说明,而且要用实践来回答。”1980年,中宣部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提交的《汇报纲领》,重点谈到“制度优越性”问题。倘若纠“左”的同时对群众民生福祉及社会右倾思潮不重视或不能及时有效加以解决,无疑将陷入新的泥潭。
关于如何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少数代表提出要加强正面宣传和鼓劲,“大家还希望今后多刊阅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有助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顾大局、识大体的先进人物的文章和报导,使理论宣传武器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更多代表注重从具体方针探寻有效方案。中国社科院王代表、赵代表建议清除个人迷信,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迎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春天,使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中联部廖代表提出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加快发展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社会生产力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个问题应当由实践来回答,应当用事实来回答”。阶级斗争从严重扩大化到纲举目张之“纲”,一再将社会意识拔高到脱离社会存在的地步,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必须痛定思痛、彻底纠偏,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调整生产关系基础上推动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彰显的根本保障。对此,务虚会已达成基本共识。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
主要矛盾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讨论时常被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党的八大前后达到高峰。党的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左”的认识相互交织、更替递进。在理论务虚会上,思想理论工作者根据实践效果和当前形势对固有认识进行反思,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认识的匡正扶偏。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盲目地对共产主义实现路径作出预言,而是希望通过无限丰富的社會实践来解答。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还要不要再划分阶段?如果不要,原因是什么?如果要,如何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过往的宣传口号是否有缺陷,为什么会长时间急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当前属于哪个发展阶段?这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存在分歧的理论问题,理论务虚会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第一,科学分析原有发展阶段理论的误区及其成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个过渡时期。但对“过渡时期”怎样理解及是否细分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间存在分歧。毛泽东也曾主张分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又提出在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急于过渡的理论依据。《人民日报》社的苏绍智代表和国务院的冯兰瑞代表就发展阶段问题提出困惑,“怎么能不分阶段呢?漫长的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你就老是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两人认为不划分阶段,“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在理论上,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在实践上,不能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正确地确定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认为不分阶段论,“会把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当成几个阶段共有的现象”,“还会把下一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才能办的事,提前到上一个阶段来办”,如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结果适得其反。两人还提出:“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些理论观点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表示赞成,也有人以该文“质疑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为由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准备大加批判。1979年7月,中宣部受命处理这场“阶段论”风波。经多次讨论,认为两人观点虽不够严谨,但论点和论据站得住脚,不宜上纲上线。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更多声音支持两人的文章发表,认为中国当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属于不发达或者说不完善或者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对国外情况相对了解更多的江春泽代表在务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其建议在国际比较中寻求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即兴发言引起热议。“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的体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开展比较研究,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我还建议,在学术界创立一门中国的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这将有助于推动思考如何在借鉴和扬弃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标准细化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浙江省委宣传部程代表结合地方状况提出疑问:“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有什么标志?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有没有一个发展过程,有没有发展阶段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混淆阶段常易导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式的提前过渡。前述苏、冯两位代表在发言中还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中联部廖代表表示赞同,认为“应当从生产力的发展方面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作必要的补充说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即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本上是由生产力发展落后所规定的”。因此,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理应聚精会神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强调生产力革命的优先地位,“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党的中心工作由原来的三个(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二个(抓革命、促生产)调整为一个(经济建设)。
务虚会上还对把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下限理解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我国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不需要划分阶段的历史时期且这一时期始终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固有认识进行反思,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进而为之后不断丰富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初步思想资源。
(二)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探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不仅偏离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一直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理论根源。改革开放之初,思想理论工作者力图从学理层面作出全面剖析。代表们纷纷思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什么关系?一个时期是多个中心好还是一个中心好?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否一成不变?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实践中的巨大危害?推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否应当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务虚会通过民主讨论,得出以下意见。
第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而会发生转移。由于对漫长的社会主义时期不再划分阶段,所以武断地认定整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对立。《人民日报》社何代表和外交部李代表先后分析了这一论断的理论缺陷,“一个历史时期有很多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不能始终只是一个。主要矛盾不发生变化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是违反客观现实的”;三大改造完成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但落后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的改造任务依然艰巨,因此“这里势必要分阶段发展,各个阶段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一定会有变化。决不能用简单公式去套一切,或适用于一切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误判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或者不实事求是地更正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都是错误的。在总体目标方向指引下,发展阶段“不变”与主要矛盾“变化”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無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社会生产滞后于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显著矛盾。党的八大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关系作出了清晰界定和科学概括,遗憾并未贯彻始终。务虚会上,有的代表谈到了将阶级矛盾视作主要矛盾的悖论所在,即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而主要矛盾作为基本矛盾的充分体现和集中表达,理应与基本矛盾的立场和导向相一致,“既然如此,为什么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又是非对抗性的”,换言之,基本矛盾倾向于安稳谋发展,主要矛盾却强调对抗斗争,背道而驰。正如胡乔木所说:“每天都革命是人民受不了的,结果只能破坏生产。任何事物的发展,在一定阶段都必须有它一定的稳定性。”纲举才能目张,一个阶段当以一个中心工作为宜,同时兼顾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主要矛盾的解决推动时代进步。与会人员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推进了关于该问题的正本清源,为端正思想路线奠定重要条件。根据代表们新的看法、意见和建议,邓小平在3月30日讲话的第三部分就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作出答复。会上,“有的同志也试图作一些新的概括,但又觉得没把握,不知道哪一种概括更科学、更稳妥”,有的建议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以四个现代化为纲”,但务虚会毕竟属于理论探讨而非作出决议的会议,因而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暂时沿用党的八大论断。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作出修订,到党的十九大时又适时对主要矛盾作出新的概括。
三、关于社会主义阶级划分和
阶级斗争的探讨
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是革命取得成功的“看家本领”,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明显失灵。思想理论工作者群体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寻根问源。在务虚会筹备期间,胡乔木在中宣部碰头会上曾就阶级斗争问题发表亮点纷呈的讲话,该讲话摘要作为会议印发的8个材料之首,发给各与会代表。胡耀邦在务虚会前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也谈到这个问题。两者的讲话拋砖引玉,鼓舞与会人员积极讨论阶级斗争相关问题。湖南省委宣传部王代表谈道:“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胡乔木同志提出了许多问题,我都赞成。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些问题也需要研究。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阶级?什么时候有?是不是始终存在?划分阶级到底是几个标准?除了经济标准还有没有政治标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个概念要不要提?过去抓阶级斗争有很多教训可吸取。”归纳起来,代表们重点从3个方面展开讨论:阶级划分的标准是什么、能否按照政治思想标准来划分阶级?持续20多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和教训有哪些、如何重新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国当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地位有了什么新变化?务虚会经过民主探讨,得出3点新认识。
(一)明确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是生产资料而非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多位代表坚持唯物史观,反思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的理论,强调阶级存在和划分的根源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什么叫阶级?是以经济标准来划分阶级还是用经济和政治两个标准来划分阶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应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是否剥削别人,即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用两个标准,把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之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存在的根源是所有制。三大改造完成后,所有制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剥削阶级基本消除。但随着“继续革命”论的兴起,又以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作为新的主要划分标准。对此,有代表反思认为:消灭对立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消灭其经济基础一样,都是必要的,但不能本末倒置,陷入唯心主义,“要消灭一个阶级,不但要推翻这个阶级的政权、消灭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而且还要消灭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绝不是说,可以不按人们的经济地位,而按人们的思想状况来划分阶级。以思想状况决定阶级的划分,这是一个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标准”。在激进路线驱使下,对阶级划分标准和阶级形势的判断越发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成为越发“左”的重要依据和助推力量。在政治思想上求纯粹求绝对是一种片面化、静态化的观点。思想理论界要求以经济而非政治作为阶级划分的根本依据同要求学会算政治账、从政治上看问题并不冲突,而是针对不同事项在不同语境中发表的不同意见。
(二)强调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教训深刻。有代表对其过程和原因作了分析。如中国人民大学宋代表所说:在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之争思想推动下,“不断开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斗争对象“从党外发展到党内、军队内;从群众发展到干部,阶级斗争被极大地扩大化了”,这是“企图要用专政的办法来为消灭专政创造条件,用加强阶级斗争的办法来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党内分歧并不都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必须区分党内思想分歧与社会阶级斗争。中联部廖代表提出:“如果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解决上述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问题,那就是人为地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那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关于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有益指导,历经波折后更显思想光辉。廖代表还将反右派斗争视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源头,并对其深刻教训作了探讨,“扩大反右派的结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就随即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鸦雀无声的沉闷空气。……这是我们党走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道路的开始”。也有代表从原因和危害中得出教训。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曾代表、赵代表提出:在反对扩大化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长期性、激烈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历史研究》杂志社丁代表提出要尤为注意“左”的错误,“多年来我们党警惕了抹煞阶级斗争的右倾危险,但是忽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危险。这种‘左倾,和那种右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因而对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作出合乎实际的考量、界定和处理。
(三)建议重新认识和审慎判断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地位。如何定位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趋势、地位事关长治久安,“现在,下面干部群众思想比较混乱的是阶级斗争问题。过去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但当前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哪些是阶级斗争?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思想领域的资产阶级侵蚀等是不是阶级斗争?对一些阶级斗争的表现应该怎么对待?如此等等,好多人感到无所适从”,亟待纠正过往成见,进一步明确阶级斗争的内涵与外延、尺度与边界。中央编译局王代表提出此前一些论断带有唯心主义倾向,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或始终存在,这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四川省委宣传部沈代表谈到该省近期召开的务虚会上的一些意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是绝不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强烈”,“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不都表现为阶级矛盾,……一般地也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决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建议“我们还是要以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导,要回到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上来”。其他多位代表同样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理论是宝贵遗产,至今仍具指导意义。也有代表反思了“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说法,重新思考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主副关系。
会上还对与阶级斗争密切关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多数代表对该理论持否定态度,“我们应当抛弃这种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说法,而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来”。这种意见为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吸收,并在2021年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加以坚持和巩固。还有代表对“革命”的多重含义进行探讨,“一种是社会革命,包括改变生产关系、夺取政权等等;再有是相对改良而言的:革命优于进化,质变优于改良;还有是作为政治界限提出来的: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有,革命是一种精神,是相对于保守精神的进取精神,等等”。
在社会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务虚会进一步从理论上对遭遇挫折的表现、过程、原因、教训等作出探讨,提出必须改变以政治思想划线、以阶级斗争妨碍经济建设、以扩大外延和放大细节方式运用阶级分析法等操作。不过,在反思之余对党内外忽视或取缔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重视不足。尽管也有极个别如天津市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代表所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消灭”,但相对而言,一些与会人员在纠正过去片面化之时自身也陷入了局限性。因而,邓小平在第二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予以说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坚持熄灭论、过时论同扩大化、绝对化都是错误的。
四、结语
改革开放伊始,思想理论界同一线干部群体以务虚和务实相结合方式,合力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哪些、制度优越性何在,发展阶段如何区分、主要矛盾是什么,新形势下阶级如何划分、阶级斗争如何开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加以重新认识和深入反思,这对于系统解决理论上的偏狭、政策上的偏差、工作中的偏激等问题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务虚会还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进一步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区和固化守旧的思维,推进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然,除了内容上略显粗浅外,理论务虚会主要缺点有二:一是有的看法超前,引起强烈震动。沈宝祥认为:在僵化半僵化极为严重环境下,“却有一个先锋队走得太快的问题,快到连某些领导人的思想都跟不上的地步”。二是有些观点偏执,存在矫枉过正倾向。如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完全错误的,提出“新民主主义补课论”等;力求绝对性和彻底性的思想理论界不自觉地陷入“理性的自负”“片面的深刻”的误区。这就给企图走改旗易帜邪路的力量以某种程度的利用和支持,给要求走保守僵化老路的力量以批判的口实和把柄,引发对务虚会的各种质疑和批评,流传“务虚会是胡闹会”“愈开愈乱”,甚至称务虚会是“戊戌会”,有的“认为社会上的错误思潮和闹事现象,是解放思想‘解放出来的,是发扬民主‘发扬出来的,是理论务虚会‘务出来的”。此次务虚会的经验和教训再次表明,如何掌握好意识形态战线收与放、严与松的张力,保持思想理论界与党政决策层、务虚与务实的良性互動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论题。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22CDJ034)和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理论工作务虚会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21YJC770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