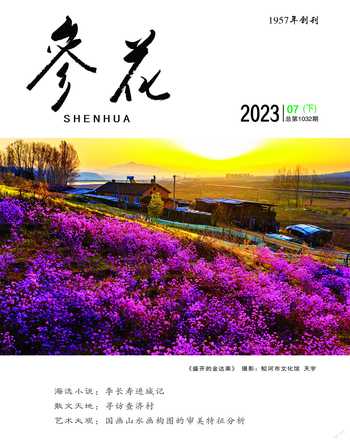探析徐渭书画中表现主义之渊薮
徐渭是明朝书法、绘画、剑术、诗歌、戏曲、文章皆通的一代奇才,他于书法中宣泄情感之所向,花鸟间吐露内心之所感,他所开创的大写意画派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创作的杂剧、戏曲也别出新意,不落俗套。笔者将对徐渭在书画中所透露出的表现主义进行客观研究,望能从中窥探文长先生的美学思想。
一、师承关系
徐渭出生于浙江绍兴,受当地名家杨珂、陈鹤的感染,擅长楷体和草体,草体学书于怀素,楷体属晋人一脉。杨珂长于草书,且喜作“狂书”,属恣心所欲一路,徐渭深受其教化。亦曾言小楷学于钟、王,以徐渭留给我们的风格印象来看,师法钟、王一脉似乎让人有些不解,但是仔细想来,无论是徐渭欣赏的“宋四家”,还是甚为称赞的倪瓒都是无法跨越钟、王两道门槛的,钟、王对徐渭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徐渭欣赏苏、黄、米、蔡,他的行、草书学黄庭坚、米芾面目较多,常采用米芾八面出锋的方法,与此同时又掺以黄庭堅的笔意,盘旋环绕,欹正互参,粗细变化自如,尽显妍态。无论是章法还是结体,都可以看出受米、黄二人影响较大。但仔细对比,徐渭的书法相比米芾,更为刚毅苍劲,较之黄庭坚,更显纵情潇洒。大草受怀素、张长史、祝枝山影响颇深。[1]
二、书法中的表现主义——以《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轴》为例
《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轴》初看点画纵横狼藉,章法疏疏密密,再观水墨浓淡掺杂,流畅自然,变化丰富,整篇气势磅礴,犹如黄河之水倾泻而下,奔腾入海。[2]例如第一句中的“淡”字被夸张拉长,第二句中的“高”字被省略,瞬间落笔的点画是书者情绪迸发的表现,情到深处,全然忘记语句是否通顺,字形结构是否合理。第三行中间部分“不劳钟鼓”的“钟”字右面部分与第二行“阶面青苔”的“阶”字左面部分拉扯十分胶着,而“钟”字本身左右两部分却离得极远,从“钟”开始一直到“浣”,六个左右结构的字连在一起,这样一个组合与前后两行的间隔又离得很近,这也体现出徐渭对于空间张合的掌控能力。该诗轴绝非二王一路的中和淡雅,亦不是张旭、怀素的狂放自由,其中字结构被破坏,有的长拉,有的勾连,字的可识性降低,局部的精致被弱化,作品旨在创造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是一种无声胜有声地宣泄。其书法用笔之狂逸,风格之奇肆,是同时代的书者绝无仅有的。出锋或涩笔的加入,更增添了用笔的丰富性,使得作品的层次感更强烈,视觉效果更加震撼。徐渭能做到点画狼藉而又散而不乱,足以反映出他对驾驭整篇作品的技术之精湛。
徐渭欣赏祝枝山和王维的作品和人品,追求“自然”“游戏人生”的态度,认为强加修饰的作品往往有矫揉造作之嫌,信手拈来,率意而为方是佳品。书法在古代还是作为教化世人的一种实用性需要而存在的,但到了徐渭这里,实用性大大降低,无法再用行或列来欣赏它,前人也有突破行列之间规则的尝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徐渭这般彻底的打破,以至于我们对于其作品的识读变得很难。所以欣赏徐渭的作品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部位,应该就其所给出的空间看整体感觉,把他的作品当成一幅图来进行欣赏。例如多个点画并列的情况,可识读性会变得困难,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是用传统笔法所书写出来的一种抽象性的图案,那这便是超越艺术之外的艺术。徐渭在《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轴》为我们所创设的情境中,一点一线都无法置换,一气呵成的状态下完成的点、线、面、空间布局,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是凌驾于技法之上的直指神采气韵的一幅作品。徐渭在经过传统积累、技法磨炼和人生百态的锤炼下,能够将用笔的方圆虚实、抑扬顿挫很好地表达出来,夸张笔根与笔尖的使用,利用提按顿挫,呈现出菱形或者三角形的锐利线形,与之互补的是作品中常常加入篆籀之气的浑厚笔画,形成鲜明对比。基于对传统和技法的掌握,所以徐渭在书写创作的时候才会更加随心所欲地将笔锋使转、跳宕,从而表现出浓淡、干湿、长短、欹正、疾徐的效果。
三、绘画中的表现主义——以《墨葡萄》为例
“以神写意”摆脱了局限于物象的创作观念,而追求利用笔墨宣泄情感的方式。徐渭的大写意画法与以往的追求形神兼备的画法相抵牾,将“神韵”提到了绝对高度,注重突出事物内在特质,不再一味追寻惟妙惟肖地重现事物本身,而是更加注重主观情感的表达。徐渭本身极强的个性,加之能灵活运用泼墨、破墨等表现手法,以书入画的创作理念也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生机和视点。笔下之画纵横奔放,不求形似,但又意蕴横生。《墨葡萄》作为徐渭大写意风格的代表性画作,其藤条横扫三分之二的画面,低垂错落,斜伸而下,枝干、树叶、葡萄都是寥寥几笔,泼墨晕染,真正应了那逸笔草草之意,墨色变化丰富,层次分明,营造出风中飘飘然的枝条动感给人以空灵之美。画中留有大量空白,中间大面积留白呈斜势的倒三角形,右下角小面积留白,右上角留白与题画诗相对应,这种布白结构会使画面更加富有灵气,整体和局部配合得相得益彰,既区分明显,又暗生情愫,使得画面整体感很强。这种奇妙的构图,用“密不透风”来形容很是恰当,右侧叶子和葡萄紧密集中可以例证这一点,而这种构图用“疏可走马”来比喻也不为过,左侧的叶子疏朗灵动,中间留大面积空白,这种大开大合的张力控制是十分考验功力的。徐渭的用笔看似似断似续,其实内部之间互相咬合。用墨方面乍看随意涂抹,实则每团墨色之间循序渐进,妙趣萦绕。虽不是形似,但徐渭着重借水墨葡萄抒发自己的内在感受,又将大写意画的表现力提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格局。徐渭的写意画,兼收各家之长,大胆创新,以书入画,不落前人窠臼,代之以水墨纵情晕染,相互渗透。古代绘画,常常是诗书画印应有尽有。徐渭常常用画笔直接即兴题跋,《墨葡萄》中的题画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字里行间狂放不羁,欹斜跌宕,磊落不平之气悄然于纸上,前两句交代创作时间是晚年,末两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的幽怨与无奈之情。[3]
像徐渭这样的文人画家,文学功底深厚,而题画诗也是画画的一种延伸,可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和思想高度,文学性的象征和书画的结合将一个物象的世界与画家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徐渭曾在《答许口北》中指出:“试取所选之者读之,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由此看来,徐渭所追求的正是一种随心肆意,使人醍醐灌顶的艺术理想。写意画可以让作者的情绪一吐为快,故直到今日,我们还依旧可以感受到徐渭当时的情绪起伏状态。[4]
四、徐渭书画中的表现主义对后世的影响
徐渭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代奇才,他的美学思想可以说十分具有前瞻性。不必说对朱耷、石涛、郑板桥等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人们都受益匪浅。徐渭强调:“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一味地去模仿古人,只会“随人作计终后人”,要带有想法地去临摹,去思考,不局限于一家的风格,宽泛地去探索各家背后的艺术渊源,最终达到能对多种线条、风格融会贯通的目的。绘画重“神”,不求形似不是说可以随意涂抹,只是基于对事物外象的了解,人们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它的“神韵”,这时候是不受外物所牵绊的。应学习传统,化融古法,但又不囿于前人,应以古法助我,随学随化。
徐渭跌宕起伏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作品,书法线条或温润流畅,或苍劲粗獷,或古拙老辣,或率意放达。线条是徐渭书法艺术的生命,在徐渭的笔下,线条被赋予了感情,拥有了多种表现方式。如《秋兴》诗八首,初始风格温润儒雅,随着书写节奏加快,情绪越来越激昂,书至高潮处,跳宕感呼之欲出。再如大幅作品《七言律诗》,我们可以深刻地被其所体现出的茂密古朴、大气恢宏的书法风格所震撼,作品乍看狼藉一片,然仔细观摩,愈见其精到之处,全篇气势磅礴,有摄人心魄的效果。这样的风格面目一扫书坛时习,对晚明书风熏沐良久。徐渭从不因袭固守,运笔方式也与前人相异,结字章法追求险中求胜,局部动荡不影响整体平衡,真正达到了书者精微布置而又了无布置之痕。徐渭对字的结构进行变形改造这一创举对后来的傅山、郑板桥有极大的影响。徐渭行草书掺以章草笔意,与他学习索靖是分不开的,这种独辟蹊径的方法,为郑板桥、黄道周等人指明了前路。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画派,为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明末清初的朱耷更是将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绘画作品《杂花图卷》,画中有荷花、牡丹、石榴等十三种花卉,十余米长,气势奔放、酣畅淋漓、一挥而就。这种体制经朱耷、石涛、郑板桥、李鱓、李方膺等人的丰富和发展,演变成了近代大写意画派。又如《榴实图》,本是画史上不被人提及的山石榴,经过徐渭画笔的勾勒、渲染,便向世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仿佛其自身命运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对于传统或古法的研究是基于理性下的徐渭,那么满纸挥洒,天马行空就是基于非理性之下的徐渭了,但总的来说徐渭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更为全面客观。他的狂并不是狂妄放纵之狂,更多的是身处乱世浮沉中不知何以为家的自我麻痹,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傲姿态,抑或是入世不达的愤懑,尘世难托的遗憾。徐渭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不再是传统的赏心悦目,而是一种让人难以抗拒地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一种力量,能直击人的心灵从而引发思考,这是徐渭创造的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具有推进和启蒙的意义。给明代以降、清代、近现代的艺术大家们如朱耷、汤显祖、石涛、郑板桥、齐白石等人的美学思想注入了营养和活力。在他故去后的二十年,袁宏道四处搜集徐渭的作品文稿,对其进行研究并且宣扬其艺术主张,后来著成了《徐文长传》,一直流传至今。书中袁宏道评价道:“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这句话很中肯地评价了徐渭的艺术成就和豁达豪迈的性格。
徐渭的“本色”观贯穿于他艺术生涯的始终,不断影响着后来者,对当代的书法艺术理论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厢序》云:“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呴呴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这里所说的“本色”与“相色”,“正身”与“替身”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徐渭以“相色”和“替身”作婢,形容他们如婢作夫人般浓妆艳抹,矫揉造作。徐渭驱散了“文必秦汉”的伪复古阴霾,开启了明代艺术新风尚。[5]正如袁宏道所说:“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艺术是顺情而至,有感而发,我们要善于把握住瞬时的情感,利用笔墨将真情流露于纸上,这样就会进入徐渭所言:“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的境界了。在今后的创作当中,人们也应当扎实自己的学识修养,丰富作品的思想性,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境地。
五、结语
总而言之,徐渭尚个性、重情感的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史以及近现代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现主义书风在晚明愈演愈烈,使得书法渐渐脱离了实用性的目的,进而成为书家表达个人情感的手段,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美化生活。正是因为这些人对传统的继承与反叛,才开辟了新的书风。徐渭深知将创新建立在传统之上才是有源之泉,抒发真我才能独出新意,艺术之路才会更长,这也为后世带来了振聋发聩的启迪。
参考文献:
[1]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徐渭.徐渭画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3]敬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M].济南:齐鲁书社,1989.
[4]秦炳娟.徐渭书法风格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5.
(作者简介:徐丽丽,女,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书法美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