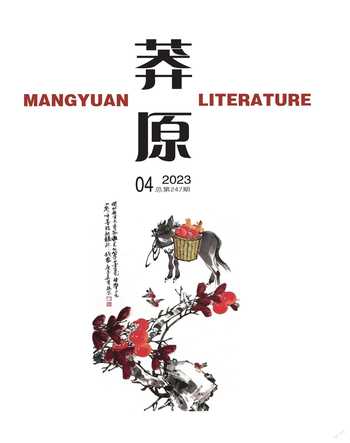母亲
2023-07-12 03:03:07郑因
莽原 2023年4期
郑因
1953年,一个身高1.72米、剪着齐耳短发的姑娘,身着蓝卡其布双排扣的列宁装,腰扎黑亮的宽皮带(皮带上别着小巧的手枪套),白手套,白力士鞋,昂首挺胸在一个万人大厂的门前执勤,成为那家大厂一道青枝绿叶的风景——那是我18岁的母亲。
母亲19岁结婚,20岁生下我哥哥,22岁生下了我。同年,我的父亲成了右派,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那时候,母亲的耳根每天都响着“离婚”“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之类的聒噪。终于有一天,母亲对我的外公外婆说,她准备退职,带上两个孩子去农场照顾劳动改造的丈夫。
外婆赶紧把户口簿藏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说她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母亲的艰辛和不易。外婆一辈子就母亲一个女儿,说只要母亲退职去农场,她就和母亲断绝母女关系。外公到底理智些,拿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母亲不忙退职,先去农场看看,然后再决定。外公胸有成竹——农场是血吸虫重灾区,沟河湖汊钉螺比泥沙还多;夏天,蚊大如蝇,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下雨天,烂泥巴让你无处下脚,任你再牢靠的鞋也给你拔下来;冬天,河沟里结冰,担水得带上斧头。外公想他女儿实地体验后,一定会彻底地打消去农场安家的念头。
1962年元旦,27岁的母亲背着我,拉着哥哥,顶着漫天大雪去了农场。半路上,我们乘坐的小木筏子夜间停靠在内荆河一个叫夏家台的地方,冰冻裂开了船帮,水满船沉。幸亏水不是很深,一个姓夏的农民救了我们。我们在他家里住了
猜你喜欢
保健与生活(2019年7期)2019-07-31 01:54:07
学苑创造·A版(2019年12期)2019-01-10 08:23:43
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18年11期)2018-12-05 03:14:22
文苑(2018年19期)2018-11-09 01:30:28
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18年9期)2018-10-08 02:29:42
高中时代(2016年7期)2016-09-21 16:42:39
三月三(2016年7期)2016-08-23 23:47:33
公民与法治(2016年4期)2016-05-17 04:09:39
小青蛙报(2014年5期)2014-03-21 21:24:57
河南科技(2014年22期)2014-02-27 14: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