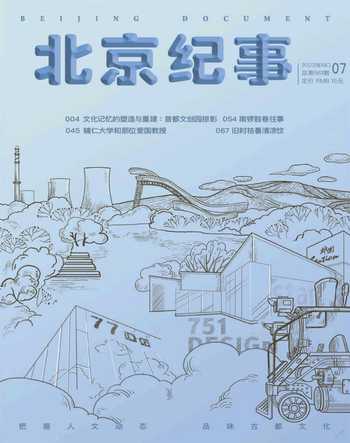老北京中药铺的独门小药“避瘟散”
一
老北京的中藥铺,通常都有自己的独门小药。这种小药不值钱,也治不了大病,但平常有个头疼脑热,皮肤痛痒,吃了或抹上这类小药,立时能减缓一些痛痒,“避瘟散”就属于这类小药。
说起“避瘟散”,上岁数的北京人一准忘不了这个小药。它属于闻药。谁有个头疼脑热,花两枚铜子,买盒避瘟散闻闻,顿时会觉得神清气爽,“瘟”病跑了一半儿。所以,那会儿的人家里一般都备这种小药。
闻“避瘟散”特别有意思,不是把药对着鼻子直接闻,讲究的主儿,闻“避瘟散”像闻鼻烟那样,打开盒盖儿,张开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八字形,把盒里的药倒在“虎口”上一小撮,然后在鼻子下边抹个“花蝴蝶”,闭口深吸一口气。哎,就闻这么一鼻子,您会觉得一股凉爽之气沁人肺腑,身上顿时觉得痛快、舒坦。这就是“避瘟散”的“神功”。
老北京装“避瘟散”的盒也有意思,盒有一元硬币大小,形状是锡制的八角形扁盒,小巧玲珑,携带方便。盒里是个小纸袋,“避瘟散”是装在这个纸袋里的,纸袋上印着个慈眉善目抱着八卦图的道士像。
您可能要问“避瘟散”,干吗要印八卦图和老道的像呀?敢情这里有一段中日两国药商斗法的故事。
二
您知道仁丹吧?这也是一味提神醒脑的小药,但仁丹是日本人发明的。您看过反映抗日战争的老电影,就会知道当年在中国的城市乡村,到处贴着日本仁丹和宝丹的广告画,上面有个头戴黑礼帽、翘着两撇八字胡子的东洋人头像。
没错儿,就是这种广告画,不过,这种广告宣传画并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才有的,早在清末民初,许多日本的药品就已经开始倾销中国,当年也贴得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很多人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但这些广告画却惹恼了一个老北京人,谁呢?
此人姓孙,名崇善,号三明。孙三明的爷爷叫孙振兰,祖籍山东省招远县,是当地有名的郎中(中医大夫)。清乾隆末年,孙振兰摇着响铃,来北京闯荡,靠着自己的医术和精明,他在前门外大街长巷头条,开了一家门脸不大的药铺。
这个小药铺除了丸散膏丹之外,还卖当时颇为流行的闻药,买卖不大,生意还不错。孙振兰信奉老子的《道德经》,讲仁义,卖的闻药虽然价格不高,但在原材料的炮制上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所以直到老人家去世,药铺也没有发大财。
孙振兰死后,药铺由他的儿子孙学奎接着经营。同治二年(1863年),孙学奎生了个儿子,他就是孙三明。
说起来有些怪,孙学奎本想让儿子学习中医,这样对经营药店会有好处,但孙三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却偏偏痴迷于道教。
他不到20岁结了婚,婚后不久便在房山的一所道观受戒,当了在家修行的火居道士。后来,他在永定门外买了几亩地,修了一个道观,取名“长春观”,后来,他把孙家的药铺也改了字号,叫“长春堂”。
自己也蓄发梳鬏,每日都穿道袍,见人也行道礼,一副仙风道骨的做派,所以人们见了他也叫他孙老道。
三
这位孙老道,虽然每天打坐练功,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他内心却有正义感,也很爱国,看到日本人除了宣传仁丹,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凉闻药宝丹,他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
孙老道想:药王爷可是中国人,华夏乃中药材的故乡,难道连个仁丹和宝丹都生产不了吗?让日本的这些药耀武扬威?
因为“长春堂”也卖闻药,但日本的仁丹和宝丹在北京大行其道以后,他药铺里的闻药便成了滞销品。为此,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心想无论如何也要研制出一种闻药,跟日本人的仁丹和宝丹叫板。
自打有了这个心眼儿,孙老道睡觉不踏实了,他成天琢磨研制闻药的事。
他在观里打坐,朦朦胧胧觉得有股香气飘过来,吸了几鼻子,感到神清气爽,他揉揉眼睛一看,原来是神像前燃着的两炷香散发的气味。他顿开茅塞,决定在香料上打主意。
最初,孙老道自己动手,试着把香条研碎试闻,但粉末粗糙干燥,闻着不是味儿,也起不到提神的功效,一连试了两个多月,他不得要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在北京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药剂师蔡希良。
蔡先生经常到“长春堂”买药,跟孙老道是老朋友。孙老道把自己研制闻药的事跟他说了,没想到,听说孙老道的初衷是跟日本的仁丹和宝丹叫板,他对孙老道心悦诚服,答应帮他这个忙。
蔡先生是药剂师,懂得怎么调药,他给孙老道提供了几味中药,同时选用大栅栏云香阁出产的优质香。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调整,最后他们在香面里加进了薄荷、冰片、朱砂、麝香和甘油等十几味药材,终于在1914年研制出了“避瘟散”。
孙老道有意与那位“八字胡”抗衡,在“避瘟散”的盒上印出自己蓄发梳鬏、身着道袍的头像,并以八卦图作为商标。
“避瘟散”问世后,受到北京人的青睐,人们觉得它比仁丹和宝丹的效果好,经过几年的宣传,“避瘟散”在国内成为知名的小药,改变了日本仁丹和宝丹独占市场的局面。在后来全国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孙老道的“避瘟散”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长春堂”的发展却一波三折,原来孙老道把“避瘟散”研制成功后,过了十多年就病故了(1926年),“长春堂”由他的内侄张子余接手当了经理。

张子余在白云观受戒,也是一位火居道士,但他比孙三明要精明得多,脑瓜灵活,善于交际,经营思路也多。“长春堂”是1914年试销“避瘟散”的,从老铺的账底子上看,从1921年到1923年,平均每年生产销售也就是三四万盒。但是张子余接手“长春堂”后,销量年年提升,到1933年,销量高达250万盒,不但涵盖国内各大城市,而且远销泰国、缅甸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当年孙老道经营“长春堂”时,店里的伙计只有五六个人,到了1930年的时候,店里的员工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且还有自己印包装的印刷厂,做锡盒的铸造车间。
此外,以合股或独资的形式,长春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店、东升木材厂,在地安门开了“仁和堂”药店,加上外地的“长春堂”分号,他开了8个买卖店铺。靠小小的“避瘟散”发迹,张子余后来成为京城商界的“四大巨子”之一。
但是“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长春堂”的“避瘟散”遭到了日本人的打压。日本宪兵队不但限制“长春堂”对外省的邮寄,而且寻找借口,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长春堂”的经理张子余逮捕,強迫“长春堂”用200两黄金赎身。
这波灾难刚躲过去,谁能想到没多久,“长春堂”着了一把大火,把店铺里的东西烧得精光,而且大火还殃及了华乐戏园子(即后来的大众剧场),把富连成科班的衣箱和舞台道具付之一炬。
这场大火让“长春堂”伤了元气,不但老店损失惨重,而且还赔了华乐和富连成几十万。日本投降后,张子余又一次遭到国民党军统的逮捕,关押了九个月,最后张家花了300两黄金,才把这位张老道给赎出来。
看来老道不能发财,发财就要倒霉。不过,从孙老道那儿开始,“长春堂”就办善事,他将“长春观”腾出一个套院,开办义学。以后,又在永定门外和左安门外增办了“二小”和“三小”。
张子余接管“长春堂”后,接着办这三所小学,学校的一切费用都由“长春堂”负责,学生不但免交学费,所用的书本笔等文具,甚至校服都由“长春堂”包了,三个小学加在一起有近二百人,“长春堂”没少积德。
张子余倒霉是因为所处的那个社会黑暗,那年头,“吃大户”是恶势力的一种手段,没辙。几经折腾,到了北平解放之前,“长春堂”衰败。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字号“长春堂”才又获新生。在有关方面的关心下,“长春堂”店址从长巷头条搬到了前门外大街路东,它的门脸比原来大了许多,变成了大药房,经营的范围不光是丸散膏丹中药,也卖水剂片剂等西药。
当然,“长春堂”卖的药品种再多,依然没忘卖自己看家的小药“避瘟散”。这个小药不起眼,却一直是“长春堂”的招牌药。
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到夏天,家里的老人便张罗着买几盒“避瘟散”备用。当然,不光是我们一家,街坊四邻都拿“避瘟散”当备用药。
那会儿,我们家住西单附近,西单周边的中药店和西药店不少,但有时买不到“避瘟散”这味小药。这时,家里的老人会说:“到前门的‘长春堂买去呀!”
于是,我便骑着自行车奔前门,到“长春堂”,在“长春堂”,什么时候去,都能买到这味小药。
“长春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卖中西药为主,自己的药厂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就逐渐没了。到1960年以后,他们卖的“避瘟散”,都是别的药厂生产的。
这味小药虽小,但配料却挺复杂,而且成本大,利润低,又加上跟它疗效差不多的新药很多,所以,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味小药就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连它的发明地“长春堂”也不卖“避瘟散”了。
2003年,北京城暴发了“非典”,因为没有特效药,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这时,有人想起了“避瘟散”这味小药,建议有关方面恢复生产,但是,限于各方面的情况,这件事最后沦为空谈。
“避瘟散”这味小药的处方是:将檀香、零陵香、香排草、片姜黄、甘松、玫瑰花、公丁香、广木香、白芷这九味药碾成细粉。再备以下五味药:人造香、朱砂粉、冰片、薄荷冰、甘油。将人造香研成末,冰片和薄荷冰研成液体,用朱砂粉把前面说的粉和液体调研均匀,兑入甘油,研匀后装缸密封,半年后开封装盒。
您瞧,“避瘟散”的制作是不是并不复杂?殷切希望有识之士,让这味小药有一天能起死回生,重新造福老百姓。
刘一达,老北京人,笔名达城,著名京味儿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能咂摸出味儿来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编辑 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