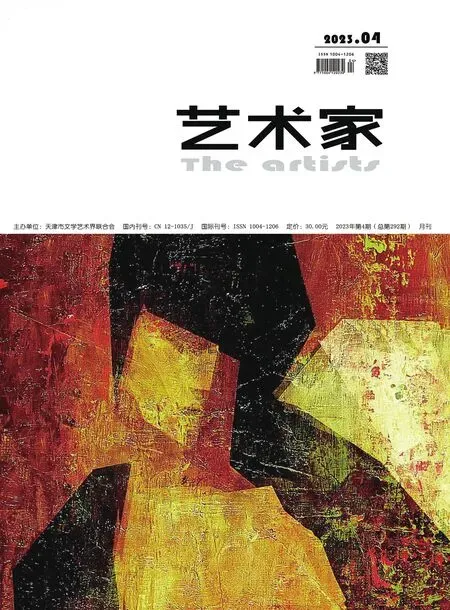关于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实践探讨
□ 关丽颖
唱好中国作品对于每一位学习美声唱法歌者来说都责无旁贷。中国民歌蕴含着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民族音乐特色,应当被所有学习西洋美声唱法歌唱艺术的中国人传唱和研习。同时,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本文就以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意义,对演唱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具体探讨与分析。
一、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意义与相关演唱历史回溯
在众多的中国声乐作品中,中国民歌蕴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多彩传统文化以及浓厚民族情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值得每一位声乐学习者去认真研习。在音乐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上,中国民歌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中,部分民歌更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我们中国音乐文化与音乐创作的“根”。把美声唱法这个“世界声乐的国际语言”运用到中国民歌作品的演唱上,无疑是我们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直接途径。
关于我国运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早期历史实践,在我国美声唱法的“开拓者”们身上就有所体现。老一辈歌唱家喻宜宣先生早在1940 年在兰州演唱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1974 年她又在南京独唱音乐会中以一曲四川民歌《康定情歌》引起巨大轰动,将此民歌传唱到国外,受到了西方观众的喜爱。她的唱片里还收集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国早期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就曾演绎过安徽民歌《凤阳花鼓》,虽然他演唱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已无从查证,但是他的演唱实况视频在当下的互联网上仍然引起热议。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也曾演唱过东北民歌《五朵花儿开》,并在1959 年由人民唱片厂出品了黑胶唱片。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的中国作品专辑中也收录了她演唱的《二月里来》《绣荷包》两首作品。改革开放后的美声歌唱家们更是非常注重中国民歌的演唱,许多在国外开音乐会的歌唱家都会选择几首经典的中国民歌作为表演曲目。同时,这一实践也被外国歌唱家采纳。1997 年,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二的卡雷拉斯、多明戈在北京举办音乐会并用中文演唱了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二、关于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方法问题
美声唱法起源于意大利,在声音的审美与发声规格上有着自身的艺术规格与特性,在国内也称为西洋唱法。而中国民歌是建立在我国各民族民间,通过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口头传唱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歌曲艺术。当西洋的美声唱法与中国的民歌相结合演唱时,演唱者首先需要确定的便是方法问题。部分观点认为,中国民歌具有中国特有的音乐形象与特色,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必须在发声上借鉴中国传统民间、戏曲的方式方法,走美声民族化路线,这样民歌的韵味、特色和民歌风格才得以展示。
笔者认为,美声唱法在演唱中国民歌时应当以美声唱法对声音的规格和审美原则为前提,再去诠释音乐风格和歌唱语言。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在针对美声唱法演唱中国作品时就曾明确地指出:“每一个声乐工作者都应该对祖国语言、音乐有精深的了解,但是作为表演工具的‘乐器’则不能‘变种’、不能‘改型’。”笔者的导师是周小燕先生的学生,她曾和笔者分享过一个关于她的演唱经历。有一年,她参加一个国际声乐比赛,周先生希望她能演唱一首中国民歌《沂蒙山小调》,她演唱结束后,周先生问她为何突然“夹着嗓子”唱,为何不用她唱外国歌剧时“美丽的声音”来演唱,这使她有了很深的感悟,这正是周先生对演唱中国民歌时不改变美声发声原则这一重要思想的最直接体现。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就曾经以西洋乐器小提琴来演奏中国作品《梁祝》,并被大家熟知且誉为经典之作。如果把美声唱法比作西洋乐器小提琴,那我们在演奏中国民歌时是否应该把“小提琴”更换为二胡或琵琶?如果说美声唱法就只能唱西洋作品,民歌就只能用民族的声音演绎才能体现它的民族化,那世界艺术文化何以呈现多元化?一个音乐作品是可以通过不同的乐器演绎的,同样,我们不应该因为演绎不同的音乐作品而改变我们的乐器。事实上,对于一个学习美声唱法的歌者而言,如果在唱民歌时仍然能在唱法上不改变音色、音质,并做到吐字清晰、对音乐风格把握准确,也很好地说明了他对美声声乐艺术的本质规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把握。
三、具体实例探讨——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槐花几时开》两首中国民歌为例
(一)无词歌唱练习
在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练习中,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先把我们的“乐器”塑造好,固定成型。在学习美声唱法之初,许多教师都提倡将歌曲看作练声曲,先去掉歌词,以单纯发“啊”的方式来进行歌唱练习,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除去了吐字的干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怎么唱好每一个乐句,唱好每一音符,感受我们的身体在歌唱时以怎样运动的方式进行。但是一般我们在演唱中国民歌的过程中,都缺少这个“啊”过程,大多数人在一开始就带词练习,缺少练声的过程,加上中国的汉字吐字具有复杂性,直接唱词脑子会因为反应不过来而直接去唱“字”而不是音符,不但影响了乐句的形成,还很容易出现歌唱中吐字影响发声的问题。皮埃尔·弗朗切斯科·托西在他发表的著作中就提及关于歌词和吐字的观点:“如果教师不够谨慎小心,在学生尚未完全掌握练声法就叫学生用歌词唱的话,他将毁掉学生的终身。”因此,在练唱中国民歌时,我们应该先把字去掉,单独练唱歌曲的旋律,这对演唱发声中后期吐字的加入起到稳固基础作用。
(二)字腹(元音)延长
在演唱中进行吐字处理,我们首先可以将字腹的元音延长,在这点上美声唱法与中国传统民歌演唱的处理方式是相同的。从大的范围来说,世界各国语言虽然在结构上会有所不同,但是主要分类还是元音(韵母)与辅音两种。我们知道在歌唱中,元音发声中声带很好地持续稳定震动,声波也比较均匀和规则,一般在歌唱里,我们称元音发出的声音为乐音,辅音发出的声音为噪音,人的声音发出来可以延长的基本都是元音,只要有声音就会有元音。在演唱中,意大利美声以元音发声为主,同样,在我国的各个唱法中也都以延长字腹为主,美声唱法更是如此。因此,在演唱前我们可以尝试先对每一个汉字的歌词元音进行分析,以民歌《槐花几时开》为例(如图1)。

图1
这首经过作曲家丁善德改编的四川汉族经典民歌属于山歌类,最初的音乐旋律取自四川宜宾《神歌》,曲调婉转悠扬,通过妈妈与女儿的对话,体现了姑娘对情郎的盼望与情窦初开的羞涩,为数不多的四句歌词却清楚地交代了演唱的情景背景、人物事物以及人物内心动态。
在演唱前,我们应该对第一句歌词进行元音字腹的分析,“高(gāo)”字在韵母中存在两个元音的情况,这种属于韵腹加韵尾结构,字腹元音为“ā”母音,“o”母音则属于字尾归韵,我们在演唱时声音应当在“ā”上占有更多的时值,如果在元音“o”上延长,则会出现归韵过早的情况,演唱中的“高高山上”很容易听成“蝈蝈山上”的感觉。“山(shān)”字歌唱元音应以“a”“n”为韵尾,延长的元音同样为“a”母音,“上(shàng)”字除掉韵尾“ng”,演唱也在“a”元音上延长。在后面歌词中的语气词“哟”和“啊”的演唱选择上,美声演唱中一般唱“哟”,“哟”字元音为“o”。在练习时,我们可以把这一小句的元音都单独挑出来,a-a-a-a-o 进行和旋律结合进行元音的连唱练习,这种方法既可以很好地吐好汉字的韵母,同时对声音的连贯性也有很好的帮助。
(三)关于声母(辅音)
辅音之所以称为辅音,是因为辅这个字在汉语中有“辅助、辅佐”的意思,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辅音为辅助发音,辅助元音发音。根据声母阻碍方式分类,先对塞音为声母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句中的“高(gāo)”字,发声母塞音“g”时,气流可以冲破舌根与软腭接触形成的闭塞,顺势爆发辅助发出后面的韵母“ao”,使声音响亮且富有不同的色彩。因此,在演唱时不可忽视和弱化,但是对于吐字力度,我们应该在平日练习中通过经验去定度,否则多了影响发声,少了影响歌词字义。
对于声母为擦音或擦塞音的一些字,像声母中的擦音和塞音f、t、s、sh、d、k 的辅音,在演唱时,或许我们可以借鉴演唱德语时的吐字技巧,德语中的辅音就存在许多擦音还有爆破音,通常声乐指导会让我们把辅音提前吐出,通过气流与嘴唇、牙齿间的摩擦力度,来提高字头声母的清晰度,不影响元音的发声。例如,《槐花几时开》中的“树(shù)”字,让字头辅音“sh”在意识上提前,并发出相应的气流的摩擦声音,吐完后让声音快速到元音“u”的位置上,这样既有了清晰字头,又不影响声音的共鸣和音质。
(四)关于归韵
归韵属于演唱中国民歌时吐字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在中国传统戏曲演唱领域被看作一种演唱规范,处理不好会失去中国语言特有的音韵美,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为例(如图2)。

图2
这是一首由向音收集改编的陕北民歌,歌词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姑娘在经历了对情哥哥数月的等待而苦闷和伤感,音乐表现缠绵,曲调简谱朗朗上口,歌词为四句体,相应做出押韵的处理,体裁属于典型的“信天游”类,在写作结构上运用了再现的手法,表现出人物情绪的对比。
在美声演唱民歌中,字尾为“n”和“ng”的鼻韵母结束的字叫收音(归韵),在收音时,把握不当会让声音听上去有断错感。因此,在演唱时,演唱者应该在音快结束处轻巧发出,不可提前占用字符(元音)的时值。在这首民歌中,歌词涉及许多字尾收音的情况,像第一句歌词中的“牵牛儿开花羊跑青”的“青(qīng)”字,在演唱中占两拍,韵尾“ng”不能在第一拍就收音,这样会使声音得不到很好的延展,我们可以选择放在结束前大约四分之一处轻轻吐出“ng”。
(五)歌词的吟诵
在对中国民歌演唱的发声与吐字练习上,我们可以效仿古人对诗词的吟诵方式,在演唱民歌前可以对它的歌词加入四声进行“拿腔拿调”的吟诵练习,并结合歌词对应的实际拍值去拉长字的发音时值。在演唱学习中,几乎所有教师都会强调要读词朗诵,但是在朗诵中国的词时,我们很习惯地按音节朗读,因为中国汉字为方块字,发声中也是一字一音节的,如果一字一字朗诵,哪怕是四声对了,也和歌唱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民歌韵味和特色除了体现在音乐中,还体现在语言上。歌曲的旋律都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好的作曲家往往会根据说话时声音的语调中的抑扬顿挫进行旋律的编创。因此,在演唱前,我们要对歌词进行如同古人读诗般的吟诵,通过加入声调以及拉长发音的吟诵歌词进行吐字练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歌唱发声的流动性并与歌曲的旋律进行更好的协调,同时增强演唱中乐句的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