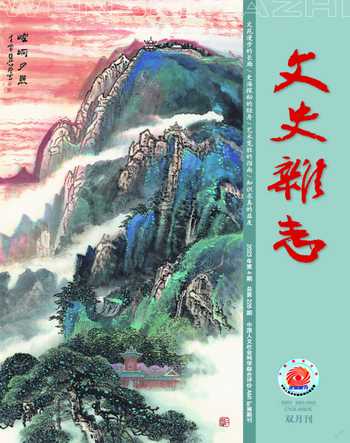关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步探讨
张宣逸
摘 要: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有五个要素起了重要作用:一、农业有一定发展,出现社会分工;二、出现阶级分化;三、出现中心城市;四、出现地区间上层精英的互动;五、出现最初的国家。这五个因素是今后研究文明形成的“中国模式”需要考虑的重点。
关键词:中国模式;五要素;文明形成
传统观点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关于“国家”的标准,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城市、冶金和文字的文明“三要素”,曾被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如果套用西方学者“三要素”来探索和表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未免有些机械化。因为就世界文明而言,世界各地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也不同,因此文明形成的进程和表征也不尽相同。就中国而言,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1]中华文明从文明表征上讲,诸如中国的祖先信仰、尚玉比德、天文历法、农耕务实、治水文化[2]等,都是其他文明所不及的。从文明物化形态上讲,中国文明的演化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3],尤以前青铜时代的“玉石文明”[4]阶段为中国独有的模式,这种模式被叶舒宪先生称之为“玉教”或“玉石之路”。从文明形成的时空角度上讲,中华文明的特性“不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最先最早,而在于其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5],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特征”[6]。因此,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应当根据中国自身的考古材料,结合以下五要素,提出文明形成的“中国模式”。
一、第一个要素。农业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社会分工。有一部分人能专门从事手工业,手工业得以精细化,比如制作精美的玉器、陶器等。以盛食器“陶豆”为例,早期的陶豆普遍比较矮、粗糙(如跨湖桥文化中的豆就像是在盘钵碗底下加个底座),目的是用以盛放“辅食”。随着稻作农业不断发展,满足温饱的主食粮食越多,盛放辅食的陶豆逐渐精细化、多样化。马家浜时期的环太湖流域水稻栽培逐渐成熟,如草鞋山、圩墩、绰墩和马家浜,而后的崧泽和良渚时期更是出现了大型的水稻田。从马家浜崧泽再到良渚,原本粗糙的陶豆造型纹饰变得越来越丰富,部分陶豆豆柄不断升高,三段式样更加明显,出现镂空圆形、近方形或弧三角形纹饰,部分豆柄部甚至出现复杂的兽面纹等等。这些变化都与稻作农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有关。
二、第二个要素。出现阶级的分化,贫富差距悬殊。一部分精英掌控军事、宗教,拥有王权或神权。马家浜时期文化的墓葬中,各墓随葬品并不丰富,也不是很悬殊。但到了崧泽文化时期,如东山村遗址中大型墓葬和小墓葬随葬品差异明显,大墓中有玉器、石钺、大口尊等象征财富、身份、等级的随葬品,小墓随葬品则以日用陶器为主。[7]良渚文化更是如此,良渚以玉为尊,其中玉琮、玉钺、玉璧三种大型玉器一般出土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这些大型玉器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作为拥有它们的墓主人,则是掌握部落祭祀天地大权的军事贵族。再如距今5300多年的凌家滩墓地,大中小型墓分布在不同区域,大墓随葬品玉器最多(且玉器精美、图像具有宗教色彩),石器相对少一些,陶器最少;小墓中随葬品则以工具为主,玉器较少。随葬品数量、品质的悬殊,说明了阶级分化的明显。
三、第三个要素。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逐渐出现。出现以大型聚落为中心、周边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类似;也有学者称之为“古国”。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以及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的出现。岀现明显的城乡分化”。早在马家浜时期,就已经出现依自然环境而建的壕沟,明显具有保卫聚落中心城市的防御功能。姜里遗址发现的古河道宽约8米、深约1.6米,河道内发现有陶片、鹿角和水生动物的骨头,房址距离河道不超过20米。古河道不仅可以提供水源,满足生活、排涝和生产的需求,还可作为防御屏障,是聚落的依托和组成部分。[8]新岗遗址新农村地点也发现了环绕遗址半圈的壕沟。壕沟内有居住区和墓葬区,居住区与墓葬区相距不远。壕沟显然是用于聚落生活、生产和防御的设施。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高大土台的外围更常见“环壕”,用以划分功能区或者区别不同等级的人群。相关研究表明:距今约5000年前的良渚都城遗址,在筑城之前,良渚社会统治者集中了大量劳动力,“利用自然地势的起伏构筑起长十几公里、高数米的多段水坝,整个水坝分为高、低坝系统”[9]。这一水利系统兼有防洪、蓄水、灌溉等功能。在修建巨型古城之前,良渚社会的统治者还组织劳动力,在城内中心位置堆筑起长630米、宽45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足球场)、高近十几米的高台……又以高台为中心,在周围修建起南北1900米,东西1700米,城墙墙基宽20—150米,高约4米,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相当于4个北京故宫)。[10]在内城城墙之外,还筑有“宽数十米的壕沟”[11]。
四、第四个要素。各地区上层(权力层)的密切“互动”和“关注”。上层精英“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12]这些“互动”和“互通”,为“最初中国”的形成,创造了前期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如何判断不同区域存在着上层交流互动呢?我们大致可从“连续”与“断裂”两个方面来谈。就“连续性”而言,不同地區的一些陶器上出现了相似的“刻画符号”,这些特殊符号可能是上层交流互动的媒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的复杂的刻画符号系统”[13]。比如“五”字符、“八角星纹饰”“十字纹”“对三角纹”,这些符号不仅存在于史前不同区域文化中,而且还具有“延续性”。有些符号如“”(“五”字符)本身就兼有“图像符号”和“文字记录”的双重特征,从史前一直延续到六朝,甚至更晚,明显具有“连续性”。而用以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天圆地方观念”[14]的“八角星纹饰”在史前不同区域同时流行,最后成为在历史上长期使用的装饰纹样,甚至在现代少数民族服饰中依然常见。就“断裂”而言,在马家浜时期,一些葬俗流行到一定的时间就突然中断,而且这种中断几乎是在同时期进行的。这表明不同地区的上层精英在丧葬仪式上可能进行过交流和沟通。比如在马家浜文化中,用陶钵、陶盆、陶匜类圆形陶器覆盖或承托死者头部的葬俗,在新岗遗址、圩墩遗址、草鞋山遗址都有发现,且不专属于环太湖地区“马家浜—崧泽文化系统”;这种葬俗也出现在淮北的“大伊山”“二涧村”等遗址中,亦即“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中;江淮东部的“龙虬庄遗址”中也有红陶钵覆面情况。这种葬俗在马家浜之后突然消失了,这或许暗示了某种上层交流的一致性。
五、“国家”[15]的形成和最初的“文明”。虽然“国家”和“文明”是两个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但在考古学看来,“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16]。所以,只要有足够充分的能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起源”[17]。“文明形成”是物质文化、精神信仰、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的演进又往往具有“渐进性”“延续性”,而“国家”的出现正是这种“渐进延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质变升级,是标志文明形成的外化形态。考古材料显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可能就是“尧都平阳”的所在,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国家。一是因为陶寺遗址中出现了都邑性城址,礼制性建筑。从陶寺遗址宫城城墙上延伸出的“阙楼”式门址,成为后世宫阙的典型范式。二是陶寺遗址中发现的陶文,能与文献记载的“尧舜之都”互为印证,表明陶寺都城遗址是最早的国都,使得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可以成为信史。三是陶寺文化中带有彩绘“龙纹”图案的陶盘仅见于最高等级墓中,显然是社会上层专享的高级用器;而龙图像更是高级身份的象征。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龙文化在国家形成初期,便与地位、权力、尊贵等相联系。四是陶寺文化表明其时“天圆地方”观念和“地中”概念已经形成。一些研究者看重的陶寺圭尺1.6尺(或接近1.6尺)“地中”刻度,首次表明最早“中国”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诞生最初“中国”的陶寺时代,正是贫富悬殊严重、阶级矛盾凸出的时代。这说明,在新石器晚期,为缓和阶级冲突产生了最初的“国家”,而这恰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综上所述,这五个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这是今后研究文明形成“中国模式”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注释:
[1]参见赵辉:《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人民日报》2022年8月8日。
[2]文献《尚书》中记载了五帝时代的治水事件和圣人治水精神。其中《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记载距今4000年的大洪水和治水活动,客观呈现出了治水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禹浚九河,治水成功,舜帝让位于禹,于是夏王朝由此产生。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但目前考古资料显示距今约5000年前,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外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水利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这恰恰是判断良渚先民们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依据之一。
[3]陈胜前:《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4]考古资料显示,早在9000多年前中国玉文化的水平已经比较成熟。小南山文化中大量精美玉器发现,也充分说明了这里的手工业和社会形态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王巍认为“玉礼器的发明,是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玉石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起源当中极为重要的独特文化现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也认为:“不同于西方文明将玉作为装饰器,中国玉器作为礼器,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
[5]谭佳:《从人文学科深耕文明探源的中国性问题》,《光明日报》2022年8月6日。
[6]柴雅欣:《文明探源工程:诠释“何以中国”——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6月15日。
[7]参见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编著《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141页。
[8]参见郑铎:《马家浜文化聚落形态研究》,《东南文化》2020年第5期。
[9][10][11]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12]参见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13]参见李新伟:《中华文明起源语境下的文明标志》,《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1期。
[14]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78页。
[15]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专指古代国家形态的出现,以国家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16]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求是》2022年第14期。
[17]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附记:本文为笔者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暨“太湖流域史前文明起源研究”座談会上发言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作者单位:常州市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