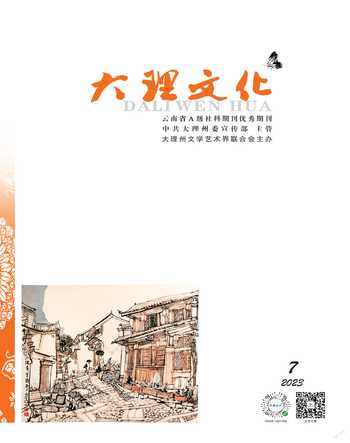凤眼莲(组诗)
莫独

网
扯开
鱼腥味和陈旧
晒在岸上。风
一阵阵撞上
几个洞,大小不一
随便开在网眼间
怎样的经历
是鱼的挣扎,浪的撕扯
还是时间的撞击
抑或,是岁月的松懈
让握紧的时光
从不经意的地方,相继开裂
滩 涂
时间的创口,被返回的季节
从伤痛的身上,重新忽略
泥土又瘦了一圈
深深浅浅的水塘,大大小小
各自为国。零落的水草
青黄交错,一次次地冲刺
却不成气候
其实,热爱从来不缺
鸟们三三两两地起落
牛羊刚刚回去
风,主动慢下来
小小的水塘,微澜粼粼
浮着一层还没散尽的哞声
那只大鸟在暮色覆盖之前
再次飞临,看看
走几步,默然而立
几片荷叶,贴水绿着
不惊,不动。近在咫尺
鱼的残骸,散落在石堆下
顽固地呼唤,自己溺死在
水中的人生
黄 昏
此时,水面趋于宁静
趋于向西。晚风轻微
三天前的雷鸣、电闪
裹挟着雨水的风暴、迷雾
像是传说无意翻开的前世
夕晖、霞光、渔网、水中的石墩和暗草
水鸟在天上飞翔
步履轻盈、明快,宛若初来乍到
甚至被那条水边的死鱼炸起的惊叹
亦情不自禁。此时
午后和我们一起,被喧嚣临时遗弃
被水公开歌颂,相信每一次落日
都是一次辉煌
连续几个电话,只顾得回一条短信
——涌泉湖。是的
我们的湖,我们的黄昏
那群水鸽子,一次次
从红映的天边,急切返航
仿佛每一次,都是最后一趟
靠 近
微波泛蓝。从你的方向
我加快靠近
稻香醒来
鹭鸶在低空舞蹈、盘旋、下滑
在黄昏之前一步,靠近草色
用什么,可以把时间抺掉
只见得到风中静止的翅膀
慢下来,慢到百年前的时光
慢到火车的第一记
长笛前。不经世事的青春
再也无以避让,那份隔世的爱
有更多靠近水的方式
你仰面躺在斜坝的草地上
红霞满天,照水、照草、照鸟
照对岸的村庄,照迷恋云天的你
长 堤
歲月的一道痕
拦截,还是切割
一条鱼,被山河分割自由
一只船,被航线切断前程
一蓬水草,看着一掬前世的水
在体内徘徊、惆怅,找不到出路
风水,是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
亦是当下的,装饰成风景
长桥的名下,堤坝长长
雨水走了。风,依然当作跑道
当作自己的运动场。我们,初来乍到
凤眼莲
从哪一幕,烈焰再起
舞台重启,所有的场次
一一出镜。那条回家的鱼
左冲右突,最终
倒毙在花朵密集的艳蓝里
一堤之隔,宛若隔世之隔
香蒲正好。我们坐在岸头
面对密密匝匝的凤眼
沉默、发呆、各怀心事
沟头,空出小小的空
水,在张嘴大口呼吸
传 说
时间的卡上,火车的汽笛声
锈死在哪个齿。一湖水
已被揭去一层皮,还强求一滴水
交出早晚
夕阳燃烧。有多少黄昏
可以一起坐在坝上
回不去的时光。竹子刚刚栽进去
由远而近的,是鸥鸟,还是白鹭
那时的蔚蓝,一朵
就大过今天的一座海
风,已经无能为力
传说转身,毅然回到民间
湖 名
别说,不是
在自己的名字里
一颗心,就是一座湖
在村边。牛羊随意抵达
渔舟随便入水
一眨眼,视野就跑到了对岸
干净的水,在自己的湖名里
收好自己的波涛和汹涌
在今生的湖名下,写下前世的
蔚蓝和云朵
鱼 摊
就在坝上。转个身
就撞了个扑鼻
就在村庄与湖水之间
一个点,窄窄的,就在船头
湖,浓缩成一盆水
生活,在盆水里呼吸
高高低低的时光
一围,就是半天
风,不屑于围观
漏过指缝的水
还能否回到脚下的湖里
一条船归岸。湖
又吐出了一颗核
伤,又被掏空一寸
痛,又收紧一尺
荷
是否把比例缩小到
几亿分之一、几十亿分之一
乃至几百、几千、几万亿分之一
湖,就是一片荷叶
粗粗、细细,勾画命运的纹
落水的风,踩着荷叶
轻轻逃离水面
谁突兀地叫到莲的名字
那是荷生死相随的名啊
闭落的前世,被那位水边的女子
在自己的裙裾上,徐徐打开
荷花已谢。或者,从未开过
堤上的车
骏马无影
掠耳的嘶鸣声里
那些盛满湖水的蹄印
在水草遥远而奢侈的记忆里
开成不谢的花朵
任青色枯萎
任鸟声在萎缩的叶片上越开越少
时代的马匹,板着各自的面孔
不屑于靠近草地
堤坝长长
一些停驻,以为就是新的风景
一些呼啸而去,企图超越前面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