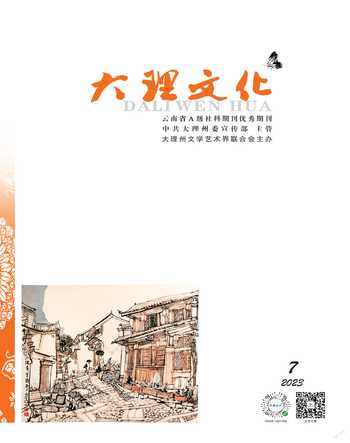千古文章一良师
2023年1月10日,当我从张焰铎老师给我发的一首诗中得知张乃光老师去世的噩耗时,我懵了。我给张老师发了一句:“怎么回事?”等了十来分钟没有等着他的回音。打开微信群,看到杨腾霄老师也发了一首哭悼张老师的诗,接着还发了几张关于张老师生前的照片,我开始意识到张老师估计是出事了。但潜意识里我多么希望这则消息不是真的,我还想确认一下,便又打开了其他微信群,没有发现蛛丝网迹。我又回过头来看张焰铎老师和杨腾霄老师的微信,都说得那么言之凿凿。还在疑惑不安中,5分钟后,关于张老师的各种消息和悼念诗文就在群里炸开了。
张乃光老师的突然去世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一
我和张乃光老师结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张乃光,1949年出生于云南大理,和我一样是地道的白族人。据了解,张乃光老师的祖辈是白族典型的耕读之家,他的母亲是民国时期大理女师的学生,成家后非常重视对4个子女的教育,把张乃光老师的两个姐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这位知性的白族母亲对张乃光兄弟两人的学习也从没放松过,1964年中学期末考试,张乃光的学习成绩平均分为99.2分,为全年级第一名。1969年,张乃光老师到农村插队务农,1971年起在大理州委宣传部工作,并于同年参加了《苍山红梅》创作组的编剧工作。此后,张乃光老师先后在大理日报社、大理州文联工作,曾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州作协主席,《大理文化》常务副主编、副编审,云南省文联委员,省作协常务理事。2006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说到张乃光先生的文学人生,《大理文化》是绕不开的一个环节。我曾在张旭之子张友先生所撰写的《张旭传略》一文中读到:1979年元月,张旭如愿从成都调回到大理州,出任州革委会副主任(后改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9年5月,在他的建议和督促下,大理州文教局文化科领头创办主编的《大理文化》第一期问世了,构建了大理与外界联络,走出苍山洱海,走向金马碧鸡,走向五湖四海的窗口。张友在《张旭传略》一文中介绍了《大理文化》创办的发起、初衷与基本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张旭老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他希望《大理文化》要以其深厚的乡土民情、浓重的民族气息、厚重的历史文化,依托苍山洱海的魅力、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众多的读者,要寓思想与政治于知识性、艺术性、资料性之中,把《大理文化》办成云南省内文学性、史学性、民族性、民俗性融为一体的通俗刊物。该文还介绍,20世纪80年代,由于《大理文化》坚持了把“民族性和地方性寓于文化性、艺术性、文学性之中”的办刊宗旨,曾被中宣部评为全国二十种优秀期刊之一。
同样,我从张乃光老师所写《我与〈大理文化〉》一文中得知:20世纪70年代末,张老师在《大理简讯》编辑室任编辑。1982年,《大理简讯》改为《大理报》,之后又改刊为《大理日报》。其间,张乃光主要从事《大理日报》文学副刊“洱海”栏目的编辑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大理文化》杂志创刊后,由于编辑《大理日报》副刊的业务关系,亦由于对文学创作的爱好和在作协任职的因缘,张乃光老师有事没事都喜欢往《大理文化》编辑部跑,除了尹明举先生,还认识了施立卓先生等其他编辑,并与《大理文化》几任主编李一夫、杨崇斌、赵怀瑾都经常往来,与《大理文化》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1982年1月公开发表在《大理文化》上“编辑的话”说:“《大理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艺术综合性杂志,它力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主要反映本地区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新道德;介绍大理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学、风光名勝、风俗民情、古今人物等,寓思想性、知识性于趣味性之中,并以学术资料见长。”1984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宣传简讯》第22期,分别发表了《充满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大理文化〉致力于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和发展》和《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大理文化〉》两篇文章,对《大理文化》的创刊经验作了介绍,肯定了创刊“突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着重介绍了刊物“坚持题材、作者、读者均以本地州为主,以培养和扶持文化新人作为己任”的方针。云南省作家协会的《创作通讯》上也发表了题为《“三个为主”不动摇,办刊一年步步高》的评论。从此,“三个为主”的办刊方针,一直以来成为了《大理文化》的宗旨。1984年8月5日,《云南日报》发表该报资深记者林之和汉宗采访《大理文化》的一篇通讯,标题为《这也是清泉》,记者在通讯中说:“在访问中,我们才发现人们对杂志的编辑方针有议论,特别看不起从头到尾的‘土里土气,尽是些地方的东西。但是,我们倒真佩服编辑们的清醒,眼光高明,他们知道越是地方的‘土东西,越具有世界的魅力。可以说,这几年来,《大理文化》从省内飞向省外,从国内飞向国外,‘土里土气便是它坚强的翅膀。”通讯还说:“我们仿佛觉得这里也是一眼清泉,流淌着大理文化的玉液琼浆!”
到了1995年,《大理文化》因编辑人手缺乏,在施立卓老师的推荐和促成下,张乃光老师被聘请为《大理文化》诗歌栏目的特邀编辑。1996年,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举办的“金誉杯”云南省优秀社科期刊奖评比活动中,《大理文化》被省里评为“云南省一级社科期刊”。1997年,中共州委决定由张乃光老师担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接到州委任命通知之后,张乃光老师于1997年3月到大理州文联报到,1997年3月至1999年2月,任《大理文化》副主编;1999年3月至2002年12月,任编辑部主任;2003年之后又任常务副主编。在此期间,张乃光老师对《大理文化》的认识与感情也逐渐加深。
张乃光老师调任州文联副主席,专心从事《大理文化》的编辑工作后,十分重视《大理文化》的定位问题。在未从事《大理文化》编辑工作前,受到一些文学界朋友的影响,他也支持《大理文化》应改名为《大理文艺》,以发表文学艺术作品为主。到大理州文联工作后,他才发现这种认识不一定符合《大理文化》的办刊实际。大理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是办好这份杂志的资源优势,不充分依靠这种资源,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办出自身特色,难以在刊物之林立足。
基于以上的一些认识,在张乃光老师等《大理文化》编辑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从1998年开始,编辑部对《大理文化》的栏目作了一些规范和调整,设置了小说栏目“彩云南现”、散文栏目“雪泥鸿爪”、诗歌栏目“七色琴弦”、散文栏目“四季风铃”、学生作文栏目“校园踏青”、杂文栏目“露天茶坊”、历史文化栏目“古雪神云”。其中,张乃光老师承担了散文、诗歌的责任编辑,并尝试在散文栏目的每篇文章前配上阅读笔记,对作品进行随感、随笔式的点评。刊物出版之后,读者、作者反映很好,并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的“大理作家”群和“大理学者”群,活跃在这个作家群里的本土作家有:张长、原因、张焰铎、杨腾霄、张乃光、菡芳、王彦军、彭镇远、彭怀仁、刘绍良、杨圭臬、陆家瑞、魏向阳、李洪文、袁冬苇、高为华、铁栗、苏金鸿、杨保中等,年轻一点的还有纳张元、李智红、杨泽文、杨义龙、杨学文、赵敏、杨建宇等;“大理学者”群则有张旭、杨永新、张文勋、李缵绪、杨延福、李公、尹明举、施立卓、廖德广、张锡禄、段鼎周、吴棠、杨锐明、施珍华、杨恒灿、张福孙、杨晓东、郭开云、何金龙、赵守值、段伶、杜乙简、赵寅松、杨政业、张文渤、田怀清、宋炳龙、张笑等。那个时候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不仅是滇西八地州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更是文化中心,名家荟萃,人才辈出,而在“滇西文化中心”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大理文化》的平台作用。2001年3月,“滇西八地州笔会”在怒江召开,那次因州文联没有人参加,指派我为大理州作家代表团领队,大理州作家代表在那次会议中备受欢迎与尊重,我们自己也因此倍感自豪和感动。
1998年4月10日,金庸先生应大理州政府邀请,到大理州开展学术交流相关活动,州文联受州政府委托举办了“金庸学术研讨会”。会后,《大理文化》刊发了专题报告,还选用了著名专家、学者、作家评“金庸与大理”的文章,其中诸如曾庆瑞的《不要失落“通俗”的家园》、汤世杰的《试论〈天龙八部〉的地域文化描写》、张长的《开卷的悬念》等一批论文在《大理文化》发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一些本地作者和外地作者在研讨会交谈中言辞恳切地说,《大理文化》坚持“三个为主”的办刊原则是对的,但不能“画地为牢”,拒绝外地的稿子,办成封闭性的刊物,外地好的稿子也应该引进来,增强开放性才能扩大影响力。这件事给张乃光老师的触动和启示是:坚持题材、作者、读者以本地州为主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把三个为“主”变成三个唯“一”。大理要走向世界,必须要让世界走向自己。就像施立卓先生和张乃光先生谈到《大理文化》如何面向世界时,不无风趣地说:“办刊方针也不能一成不变,要与时俱进,常变常新。”两位从风雨几十年走过来的办刊人深信:“金庸笔会”之所以在大理召开,正是因为金庸作品中有大理;研究金庸的人之所以研究大理,也是因为金庸的作品中有大理;《大理文化》如果不立足于大理,就不再是“大理文化”。他们深知:变是常理,变是常态,变是常规。但无论怎么变化,都变不到不用本地本民族作家文章和反映本地区本民族作品的那一天。他们感恩:这是走在前面的有识之士给大理州文坛争取到的一份基业,耕耘下的一块园地,播种下的一片希望的种子,是培养州内文艺新人,结识和交流州外文艺名流的一种平台。他们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越是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性。如果哪一天《大理文化》“常变常新”到没有“大理”这个文化元素了,《大理文化》也就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张乃光老师和他的同仁是这样想的,他们在办好《大理文化》杂志上的所有努力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仰的。他们为此苦心耕耘着《大理文化》,并付出了汗水,付出了心血,付出了努力,他们也在艰辛的付出和对信念的执守中得到了作者的认可,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得到了所有关心《大理文化》社会各界的认可,也收获了快乐和喜悦,收获了《大理文化》结出的累累硕果。
二
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张乃光老师的起步应该从1971年参与大理州白剧团的《苍山红梅》歌舞剧的编剧创作开始算起。《苍山红梅》写的是碧溪大队合作医疗站在发展过程中,围绕着“服务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开展的一场激烈斗争。赤脚医生阿梅面对复杂的斗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群众,紧紧依靠党组织,粉碎了阶级敌人王汉卿企图篡夺医疗站大权的阴谋,抵制了组长段凌云所推行的错误卫生路线,使合作医疗站沿着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胜利前进。该剧认真学习和吸取了革命现代京剧的经验,弘扬和创新了传统的白剧音乐,较好地塑造了医疗卫生战线上的英雄战士阿梅的形象。该剧的创作和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创作一样,多属于集体创作。而在该剧的文字编剧创作过程中,具有较好文学功底和能力的张乃光起了重要作用。该作品由于剧情的曲折起伏,人物形象塑造真实成功,不仅在州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久以后剧本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苍山红梅》的成功创作和日常工作表现出色,张乃光被安排到州委宣传部工作。张乃光老师的文学梦也从那时候起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乃光老师于1980年以“激光”的筆名,开始在《大理文化》1980年第5期发表组诗《致华而不实的诗人》;接着,又在《大理文化》1980年第6期与作家杨圭臬合作发表了散文《打雕场上》。之后陆陆续续发表了散文《高黎贡山的歌声》、小说《弯弯曲曲的小路》《编辑部里的故事》等作品,这些作品以真实、纯朴、自然、流畅、优美的风格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给大理州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作为大理散文创作的领军人物,张乃光老师数十年厚积薄发、笔耕不辍,先后出版散文集《秋天的湖》《走进视野》《蓝洱海·白月亮》《爱的流泉》,诗集《蓝手帕》等多部优秀作品。大量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民族文学》《新观察》《中华散文》《华夏散文》《广西文学》《边疆文学》《山花》《雪莲》《滇池》《延安文学》《野草》等全国百余家报刊;2005年至2008年,张乃光的散文作品连续四年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精短美文”年度选本和《中国当代散文(西南卷)》《2005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等。散文集《秋天的湖》荣获“云南省第三届优秀文学艺术创作奖”,散文作品《蓝洱海·白月亮》入选“云南作家精品文库”,并荣获第九届云南日报文学奖。许多学者写过专题研究他的理论文章,他的创作引起了《文学自由谈》等多家评论刊物的关注,该刊物于1998年第一期以《张乃光的散文世界》为题发表评论说:“乃光是一个真正热爱写作,而且用心研究写作的人,他的散文在取材布局、叙述方式、语言色彩、美学取向等方面,极尽变化,引人入胜。”张乃光先生的作品还引起北京文学界的广泛兴趣,专门组织过张乃光老师散文创作的文学研讨会,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对张乃光老师文学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评论文章中,云南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邓家鲜女士的《以真爱守住故土,用真情抒写生活——白族著名作家张乃光散文审美追求》一文,基本概括了张乃光老师在散文创作审美追求方面的主要特征。邓家鲜以张乃光的散文集《秋天的湖》和《走进视野》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用真爱守故土”“用真爱抒写生活”“质朴无华真情的表述”三个方面对张乃光先生的散文创作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诠释,认为张乃光的散文是用真情浇灌出来的散文,看似平铺直叙,类似白描,实则朴素中见深刻,平淡中见真情,是一种饱含情恋而融入理性的抒发,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这种明畅自然的艺术境界的构建,对建设本色散文语言,创作纯正散文,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和影响。
我所看到的关于张乃光诗文的评论文章还不少,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张永权先生的《走进读者视野的真文字》一文。该文通过对张乃光老师《走进视野》一书的具体分析,指出:大理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走进乃光创作视野的,却少有诗情画意,而多了些现实生活的厚重,多了些风雨的沧桑,因此走进作者视野的白族大地自然就会从表面的看风景,走向可看、可读、可品、可思的真文字的境界,这也正是乃光《走进视野》为我们创造出的散文天地。
而在我看来,张乃光老师笔下的诗文,可以概括为寄情苍洱山水、关注现实生活、怀揣人间冷暖、叩问世道人心四个方面。大理的山水风光赋予了他灵魂、灵性和灵感,使他笔下的大自然充满了泥土气息和花草树木的芬芳;艰难厚重而又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赋予了他爱恨情仇,使他笔下的人物总是饱含了深情厚谊;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赋予了他悲悯与仁爱,使他笔下的悲欢离合总是那么温暖和煦、生动感人;鲜活生动的世道人心,赋予了他充满智慧的感悟的哲思,使他笔下的星空总是那么安详宁静而又高远深邃。张乃光老师的目光是犀利的也是包容的,张乃光老师的性格是温柔的也是倔强的,张乃光老师的内心是细腻的也是执着的,张乃光老师的意志是果敢的也是坚韧的。张乃光老师把这一切涵化于他的笔端,就形成了他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读张乃光老师的文学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不论是《秋天的湖》《蓝洱海·白月亮》还是《走进视野》给予我最大的感觉和震撼是“真”,是真知,是真情,是真实,是真率。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真知,是真知识,真感悟,真知灼见,所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你读不到不着边界的话,读不到没有把握的话。不讲原则的话不说,不讲天理良心的话不说,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是錾刀雕刻出来的,线条分明,轮廓明显,往往力透纸背,发出微光。他的真情主要體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充满了人情、人性、人味和人道,个性突出,爱憎分明,七情六欲没有一点掺假,喜怒哀乐全都跃然纸上。他的真实,源于他的生活,源于他的内心,源于他与大自然的物我同化,源于他对周围环境的体贴入微的观察,源于他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源于他对命运的深刻感悟。他活着,他思考,他感悟,他创作,他存在,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生活,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诗意,更是充满了真情实感。他的真率,体现在他文字中的率直、率真和率性,体现在他文字中的爱恨情仇都是那样的真实自然,嬉笑怒骂都是那样的纯真和质朴,以至使他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苦辣酸甜,充满着对人生命运的一种深深的思考、悲悯、关怀和博爱。为了表现作品的真知、真情、真实、真率,张乃光老师特别注重作品中的细节表达,往往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使作品情节一波三折,悬念迭出,摇曳生姿,呼之欲出,每一个标点符号和字句都充满了理趣、意趣和情趣,回味无穷。
我在撰写《大理龙尾关艺文志》中,收录的张乃光老师的散文作品《残垣上的风景》《小巷深处有眼井》《守井老人》,都是写大理下关龙尾古城司空见惯的人和事,都从小处着笔,通过小景物(残垣)、小人物(护井老人)、小事件(护井、摩挲“松鼠尾巴”),道尽了龙尾关的古今沧桑和世态人心。而他的《苍山第二十峰》本是一则传说故事,文章色彩本应是奇幻的和浪漫的,作者却把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通过对那么悲惨、苦难、可怜和不幸的主人公被欺骗、被挤压、被算计、被伤害、被摧残,最后被逼搬出苍山的“铁云峰”的不公命运描写,赋予了作品超乎寻常的人情味、烟火味和人生况味,读之怆然,忍不住要落下泪来,同情之心、悲悯之心油然而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文坛上,数百年来影响了几代作家的“多余人”形象,在白州乃至于全国的文学创作中无人问津,而张乃光老师用他的一则传说故事弥补了这个空白。
正是因为张乃光的文学作品的这一特点,阅读他的作品,往往使州内读者倍感亲切,越读越有味道,使州外读者倍感新鲜,越读越感兴趣。从文学作品的数量而言,张乃光先生在大理州内并不突出,但从质量和艺术价值来说,“望其项背”这四个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胡廷武把他列入“云南知名作家”的评价是确切而公正的。这就注定了他的作品,他作品中的明泽、生动、优美、隽永和诗意,不仅过去的人、今天的人喜欢,还将永远被人喜欢下去。
三
张乃光老师先后在大理州委宣传部、大理日报社、大理州文联工作,在担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期间,始终没有脱离《大理文化》的编辑工作,退休后被大理州白族学会聘为《白族》杂志编辑,数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甘为人梯,扶持培养了大量文学新人,同时不遗余力为许多文学新秀写序作评,推荐文章发表。他的创作大多以家乡大理为题材,用精美的文学作品宣传推介大理,引领大理作家群形成了别具地域特色的风格流派,为大理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乃光老师对编辑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在培养大理州文学新人方面付出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用稿的时候,只认稿件不认人,只要是好的稿件,不论是谁写的,有没有名气,是初学者还是道上同行,他都会用,认稿不认人是他编辑工作中始终坚守的。那些年,从大理州文坛走过来的作家,几乎都有幸受过他的教诲和关爱。兼收并蓄、百花齐放、不搞门派是张乃光老师在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的另一个原则。不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素材;不论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不论是传统的,现代的,只要是好文章,他都能慧眼识宝,他都喜欢,他都会用。在这方面,没有人不为张乃光老师的眼光和格局所折服,所感动,所钦佩。不论对哪个作者或哪篇稿件,只要经他的手,他都报以极大的热忱,认真负责,总是想方设法跟作者取得联系,像兄长,像朋友,像亲人,像同道,文稿中的每一个细小问题他都要与作者认识探讨,共同讨论,共同商量,没有全部理解、弄清真相前,绝不会随意“处置”一篇文章,乃至于文章发表后作者是否已收到样书和稿费,他都要过问。
张乃光先生德艺双馨,人品文品,高山仰止,有口皆碑。他的辞世,是大理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文学领军人物,失去了一位呕心沥血的好老师,同时也失去了一位最可信赖的好朋友。我从雪片一样哀悼张乃光老师的各种微信中确认了张乃光老师鹤驾的消息后,看着人们对张老师生前事迹的各种缅怀,我一边流泪,一边打开手机的文字输入键盘,这些文字全都是像自己跳出来似的,便有了下面的这首诗——
才高乃低调,仗义常执言。
名师驾鹤去,高山不曾眠。
所幸身作则,后继有新贤。
华京起新浪,浪浪涌潮前。
我本褛骚客,相交已忘年。
知事曾指导,西门共流连。
金庸曾晤面,古镇惜状元。
循循颇善诱,谆谆蒙教诲。
为我背黑锅,相见一婉然。
率性肝胆照,携提不避贤。
自古同气求,知性相连理。
文章千古事,知己一世缘。
孤舟从此逝,破浪无帆舷!
以上这首诗中的“知事”指的是本人小说《知事李慎修》,“西门”指本人纪实散文《西门街扫描》,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曾被张老师采用于《大理文化》。而詩中说到的“金庸”之事,指的是1998年4月在大理州博物馆举办了金庸笔会,邀请了金庸先生参加,并授予先生“大理荣誉市民”的金钥匙。我有幸参加了此次笔会,并提交了学术交流报告《旧瓶装新酒的金庸小说》。与会者几乎都是全国一流的研究金庸先生的名家,在研讨会所形成的《金庸与大理》一书的《前言》中,张老师作为本书的主编和《前言》的撰写人,不因我是文学新人,人微言轻就被忽略了,而是把我文章中的看法作为一种观点直接写入前言:“大理州作者杨学文则指出,如果没有传统武侠小说的这个‘旧瓶和现代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这个‘新酒的完美结合,二者缺一也就形不成金庸现象。”以上的介绍,使我受宠若惊,终身难忘。诗中说到的“古镇惜状元”,指的是本人的一篇写沙溪古镇的文章中,引用了杨升庵题兴教寺海棠的诗作。为了确保引文的准确无误,张老师曾先后两次给我打电话认真核实。诗中还说到他为我“背黑锅”,这件事情有点私密,说的是我的一个文友被我家中无端打破了醋坛子的爱人张冠李戴错当成张老师亲人,打电话给张老师臭骂了他一通。张老师不仅把误会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任其臭骂,不久我和他见面时,他也只是定定地看着我哈哈大笑,没有丝毫责备之意。张老师如此豁达、大胆和幽默,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心中有块磊、有沟壑、有涵养、有气量的人,他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让我一辈子都感激不尽。
我再次打开文友们的微信,一边流泪一边品读着他们对张乃光老师的哀悼诗文。张焰铎老师的《哭乃光》诗云:“噩耗天降/无泪无语/你叹孤云独醒/我哀光逝人寰/文思邈远/友情难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诗的背后,有11个合十和10个痛哭,悲痛之情跃然纸上。
大理作家杨腾霄老师不仅与张乃光老师是文学同道,还与张乃光老师“游友”,相处非一朝一夕,自然对张乃光老师和他的家人很熟悉,可谓一往情深。他的《乃光其人》一诗是这样写的:
昨晚,他走了/此刻他的尸体还静静排队/等候火化/大理文坛再也不会有/最慈祥忠厚的散文大家/乃光其人,我半世纪的好友文友身影/是他亲率州文联王仲宽等到大理古城/我九十高龄的母亲灵堂首叩,花圈,凭吊//我让我的速写让他/永恒亘古我心//蓝洱海,白月亮/老大理,老下关/高原淡水叙述/不紧不慢有如/浪拍岸//有时,也漩窝/但,淡 /可以水滴/石穿。乃光/你的文笔没有沉入湖底/洱海永远扑刷扑刷作响/你耳朵听到了吗/你天生长了一双形如人耳的洱海啊。
年过古稀的杨腾霄老师去灵堂和张乃光老师告别,约的是茶山青老师。茶老师后来告诉我,杨腾霄老师一路都是泪眼汪汪,除了叹息,便是摇头。可见,张乃光老师的去世,在他心目中留下的伤痛有多深!
让我落泪不止的,还有镜泷和郁东两人的诗。镜泷的诗叫《相逢已无“来年”,再期只在“梦中”——悼张乃光老师》,诗云:
微信里,你还在,头像是你的半身照/你深情凝目,鬓角虽然有白发掩映/但无法掩饰你高鼻深目的俊美面容/想起你,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消息传来,许多人不敢相信/然而,事实俱在,无数人垂泪悲悼/苍洱有情,应与下关风一起念叨你的名字/文坛知遇,省内外唁电飞传;/人们不会忘记你的美文,更不会忘记/你亲切如家人的循循善诱和关怀备至//你生命的指针停留于2023年1月10日凌晨/你微信的动静停留于2022年12月19日/行走于龙尾关,你留下了最日常的场景/你自己经营的公众号“湖光心影”停更于/2022年10月14日上午9:33的《词八首》/你最后一首《鹧鸪天》里写到:/“举杯思友人何在,岂敢悲秋一己怜?”/而今,众亲友举杯,你和蔼的音容何在……//你在公众号连载《绕着洱海说故事》/然而,这故事停更于2022年7月11日的/第五十二个篇章:苍山仙乐撩人心/你留下的文字,如何不是“苍山仙乐”/如今,又将撩动多少苍洱子民的心扉//还记得,《细嗅蔷薇》分享会上/你匆匆赶来,作了精彩的发言/没留下一起餐饮,骑上摩托你潇洒而去/这一去,就没能再次亲聆你的慈言/只是偶尔在微信里问讯一声,然而/山高水长,正如你在另一首词中所说:/“举杯却怕来年约,雨巷槐花在梦中”/相逢已无“来年”,再期只在“梦中”//你留下的最大财富,除了文字/更有你的为人:宽厚如苍洱/你对文友的鼓励:润物细无声/苍洱大地有你这样的赤子是有幸的/能认识你这样的长者,我们是有幸的!//文字若有灵,你那用心浇灌的文字/当继续滋养苍洱大地,佑我苍生/苍山披雪兮,魂兮归来!/洱海托月兮,魄兮归来!/疾病能三番两次夺走人的生命/但夺不走人的魂魄,何况是你/你的魂魄光照千古,你的人格巍巍屹立/文坛有失,苍洱永思,念你如常!
镜泷这首诗前面还有一个题记说:“惊闻张乃光老师因脑梗走了,他首先是个好人,然后才是一个好作家。他斯文、儒雅、勤奋、良善、和蔼,思想深邃却平易近人。《细嗅蔷薇》分享会上,他骑着摩托车亲自赶来,结束后匆匆离去。”这是对作家的怎样的一种认可、关爱的激励呀。上文中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理作为滇西文化中心,团结在州文联和《大理文化》周围形成的作家群和学者群,如果没有张乃光老师及其同行的吸引力、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就不会形成当时那样的气候和氛围。
郁东的诗叫《光,在内心深处璀璨——致著名作家张乃光》。诗的前面还有个“引”:“大理州文坛领军人物、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乃光先生于2023年1月10日1时2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大理去世,享年74岁。”“今年元旦,他微祝我二十字‘盼春早来,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吉庆有余,福享新年!我对张乃光老师的评价是:‘人文俱佳,德艺双馨,情怀胸襟,苍洱铭镌。‘惊闻噩耗,我面对书房很久无语,谨片拾往事以悼之。”郁东的诗和镜泷的诗一样写得很长,但同样也是催人泪下,字字见真情:
你是一束光,照亮文字/前行的路上/你一直温暖着我/大理文坛的领军人/人品和文品是两面旗帜/让多少人敬佩学习/在海心亭在永仁方山/在天华山在凤凰古城/从《大理报》的“洱海”副刊/到《大理文化》的“七色琴弦”/你把我青春的文字/一行又一行斧正重拾//新年的祝福还温暖着/2022年的风寒和余疾/却盯紧了你/光的璀璨卷起/内心的风暴/朋友圈的消息/让我面对书架/默默无语//三十年前拜访你/你猜出了我青春的年纪/你用心编织洱海新人/报刊版面上多了个郁东的名字//2023年新年祝福/在微信上还彼此温暖着/那年你工整的字迹/又一行行映入眼里/“内有照片,请勿折叠”/这是你给我寄来的/湖南采风照/你的亲切与平易近人/与张家界的摘星台/金鞭溪,凤凰古城/湖南韶山冲的荷塘/留在记忆里//那年滇西笔会/在龙山背对洱海/你为我们留下一帧年轻之照/直到现在还清晰着记忆/你们青春年华,努力吧/写作没有终点/照片上一边是纳张元杨义龙/一边是杨泽文陈洪金和我/就是这句话,这幅照/多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你是一束光,照亮文字/前行的路上/你一直鼓励着我/盼春吧,春会早来/你的祝福词/与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举世之祝福/是心有大爱者/留给人间的祝词/吉庆有余福享新年/我的文字怎么承载/你在新年赋予的意义//你是一束光,照亮文字/前行的路上/你永远温暖着我/你走,坚定地走/这多年沿着滇西峡谷走/前方在前/天空高悬着头顶/共和国的同龄人/在文字的纯净里/找到自由的灵魂/那是一面湖水的静美/那是内心之光的明证。
一个编辑不论在岗不在岗、退休不退休,却始终能和作者打成一片,始终维护着文学上的沟通和交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没有文学使命和文学担当的编辑,没有真情和作家相守相伴相处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悼念张乃光老师的雪片一样还有好多,无法在此全部抄录。我所知道的是张乃光老师退休后,有一段时间联系少了,但心里却一直没有把他忘怀。有时候几个文友凑在一起,不约而同就会说起张乃光老师来,有的说他平易近人,有的说他和蔼可亲,有的说他认真负责,有的说他人情味浓,有的说他博大精深,有的说他慧眼识宝,大家除了说他的好,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从他的身上挑出点毛病来……我知道他们都是在想张老师了。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们通过网络,通过各种形式对张乃光老师自发哀悼,就充分说明了对张乃光老师人品、文品的充分肯定,以及张老师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州文联和《大理文化》杂志社的相关领导对张乃光老师的病逝相当重视,专门打电话给我,约我给他们写一篇缅怀张乃光老师的文章,殷殷嘱托了他们对张老师的一片手足之情、师友之情、同事之情和战友之情,表达了他们对张乃光老师的深切缅怀。
前两年经常在微信中经常看到张老师和我的另一个恩师在北京帮小孩看娃娃,恰好我家小孩也混迹北京。微信闲聊中曾告诉小孩过一两年退休也在北京了,唯一的心愿就是请二位恩师见个面吃顿饭什么的。心愿未了,恩师已去——呜呜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