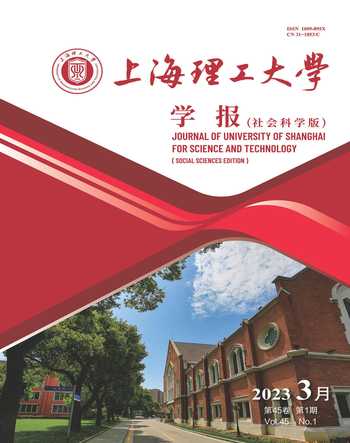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
滕梅 杨绮瑞
摘要: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认知;隐喻;诗歌意象;翻译;花意象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3)01?0015?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3.01.003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oetic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Based on Translation of Flower Image
TENG Mei,YANG Qirui
( Collegeof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As imag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poetry, its transl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in translating poems. To our delight,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poetic image transl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poetic image is essentially a conceptual metaphor mapped from the source domain “ image” to the target domain “ idea”.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oetic image depend on corresponding mapping relationships in two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we studied the translation of flower image which is popular in classical poetry, and summed up fiv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oetic image , namely, literal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plus interpretation, changing image to express meaning, expressing meaning without image and transliteration plus interpretat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oetic imag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cognition;metaphor;poetic image;translation;flower image
詩歌作为中华文明不容忽视的珍宝,其翻译历来受到重视。与其他体裁不同的是,诗歌语言凝练隽永,但传达的意义却极其丰富,这使得诗歌翻译困难重重。诗歌意象是诗歌结构的基本单位,由客观世界中的物象与诗人主观情感互相交融而成,具有“表述功能、建构功能和美感功能”[1],所以,意象翻译在诗歌翻译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意象翻译研究成果颇丰,例如李气纠等采取了文化翻译观视角[2],文旭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了意象的翻译[3]。认知语言学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取得了很大进展,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局限,使得翻译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思维层面的问题。认知语言学视角下:顾建敏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意象翻译[4];李占喜进行了关联视阈下文化意象的翻译研究[5];权循莲等采取了概念隐喻视角研究汉语古诗意象的英译[6];杨俊峰从意象图式理论角度探讨了意象翻译[7]。另外还有研究涉及概念整合理论、语言的象似性理论等。
在认知语言学中,意象的本质与隐喻具有高度吻合性,因此,把意象视为隐喻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意象翻译方法的新思路。本研究将意象作为一种认知隐喻,并以花意象为例,从认知角度探讨对意象的理解及翻译。
一、认知视角下的隐喻
自古希腊起,关于隐喻的系统研究就已经展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定义了隐喻,将隐喻视作一种修辞,同时提出隐喻的替代论。他认为,隐喻是以事物之间的共性为基础进行的替代或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后来的隐喻研究奠定了基础,很长一段时间里,隐喻都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但这种研究方式“局限于传统的修辞学框架,很难从根本上解释隐喻产生的内在机制”[3]。
作为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代表人物,Lakoff 和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提出了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理论,即概念隐喻论,象征着隐喻研究迈入了崭新的时代。认知语言学中,隐喻被视为一种人类认知事物的方式,而并非语言的表面现象。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隐喻是“通过一类事体来理解另一类事体”[8]。概念隐喻论中,隐喻被分为两个层次,即概念隐喻和语言隐喻,其中概念隐喻指的是“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而语言隐喻则是这种映射在语言上的表达形式。概念隐喻包括四要素,即始发域、目标域、身体经验和映射[3]。这四个要素构成了概念隐喻的基本结构,即基于身体经验,由始发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理解目标域是基于理解始发域之上的,通过认知推理将始发域的一个或多个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从而使目标域获得始发域的相关特征。例如,在“生命是一段旅程”这个隐喻中,始发域是相对清晰的“旅程”,人们借助对旅程的体验,将旅程有始有终等特征映射到“生命”这一目标域上,得到对于生命的理解。始发域与目标域,或者说喻体和本体之间一定是存在某种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是二者本来就具有的,也可能是新创造出来的。为了正确地理解隐喻,发掘始发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说找出连结喻体和本体的喻底,至关重要。
二、認知隐喻与诗歌意象
诗歌以凝练的语言传达丰富的意义,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诗歌意象。屈光认为“由于作家的主观情志即‘意与客观对象即‘象互感, 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即字面意义和隐意的艺术形象称为意象”[9]。其中“象”指的是一切具有物理形态的客观存在物, 而“意”指的是诗人的主观意识活动。所谓“意象”,不是“意”与“象”的简单叠加,而是诗人经过思维加工,将感情寄寓在客观物象上,以“象”蕴“意”,因而意象一般都具有双重意义。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诗歌意象被视为一种隐喻。上文提到,概念隐喻就是借助身体经验由始发域向目标域的映射,借助始发域理解目标域。在诗歌意象中,意象中的“象”是始发域,而“意”则是目标域。诗人借助自身的体验,将客观物象的特征映射到自己的主观情志中,形成隐喻。例如,古诗中常常使用“竹”这一意象来象征高风亮节,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这样的说法,诗人凭借关于竹子的经验,将竹子虚心、有节、根固、质坚和挺拔的概念特征映射到人的品质中。
把意象作为隐喻能够为译者进行意象翻译提供指导。译者得以从认知的角度理解分析意象,利用隐喻理论解释意象的产生,从而更好地把握原文意象想要表达的“意”,并且在译文中重构意象。
三、基于认知隐喻理论的诗歌意象翻译?以花意象为例
认知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也就是体验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观决定了认知视角下的翻译方法。文旭等在《认知翻译学》一书中提到,体验主义哲学有以下三个主要观点[3]。第一,思维或认知是具身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源自身体经验,也就是说,经验决定了人们的认知。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能只考虑语言层面的转换,同时也要关注经验结构,寻求经验结构的再现。译者应当利用源语的经验结构来理解原文,然后结合译文读者的经验结构来重现原作的意义与精神。其次,思维是富有想象力的。除了来源于直接经验的概念,人们也能够通过隐喻和转喻等方式间接地认知事物,这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研究作者的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等问题。最后,思维具有完型特征。人类的概念结构具有整体性,所以译者在翻译时应当从整体上把握原文的结构和意义。
译者在翻译时会构建两个心理空间:即原文空间和译者空间[3]。对于认知隐喻来说,始发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同时存在于原文空间和译者空间。翻译隐喻的过程中,译者首先通过源语经验来理解原文空间中始发域和目标域的联系,再将这一联系移植到译者空间。可以说,隐喻翻译的实质是翻译映射关系。基于人类的共有体验和隐喻思维模式,有一些隐喻同时存在于英汉文化中,例如“时光飞逝”(time flies)这种隐喻可以被直接移植到译文中。但同时隐喻与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认知语言学认为对客观世界的体验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来源。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存在差异,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民族则必然拥有不同的体验,因而有些隐喻只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当中,无法被直接移植到译文中,这时就需要采用其他的隐喻翻译方法。文旭等提出了四种隐喻翻译方法,分别是隐喻概念域的对等映射、转换喻体、喻体加喻义以及舍喻体译喻义[3]。
上文提到,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意象是一种隐喻,所以译者在翻译意象时可以把意象当作隐喻来处理,借鉴隐喻的翻译方法。认知隐喻与诗歌意象的关系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关系。意象的始发域以具体物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意象的目标域是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意志等,不能被直接表现出来。译者可以把隐喻的翻译方法应用到意象翻译中,但是要根据意象的特殊性将这些方法具体化。
花是古今中外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其文化内涵和情感精神十分丰富。英汉文化中都存在着大量花意象,出于人类的共有经验,英汉文化对于一部分花意象有着共同的理解,而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花朵种类不同以及文化因素造成的花朵内涵不同,英汉文化对于另一部分花意象的理解则存在差别。下文将以花意象为例,根据隐喻的翻译方法,提出意象翻译的五种方法。
(一)直译
隐喻概念域的对等映射对应意象翻译中的直译。有些隐喻源自于人们对世界普遍的经验,这些隐喻在源语和目的语中具有相同的内容形式与文化内涵,因此可以采用直译的方式。例如,“时间就是金钱”( Time is money )这一隐喻,中英文中都借助金钱这一具体的概念来认知时间这一较为抽象的概念,把金钱“宝贵”这一特征映射到时间上,像这样的隐喻就可以采取直译的方法,既不改变本体和喻体,也能完整地传达始发域和目标域的联系。翻译意象时,如果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采用相同的物象来表达相同的情感或思想,可以使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中的物象。
例1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
译文 Her jade-white face crisscrossed with tears in lonely world,
Like a spray of pear blossoms in sprain rain im- pearled [10].(許渊冲)
英汉文化把花与美人或者女性容貌联系起来,例如中英文里都用牡丹来喻指美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牡丹常比喻容貌美丽、地位尊崇的女性。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用牡丹来形容女子的表达,例如《德伯家的苔丝》中就有“peonymouth”这样的用法,用牡丹来形容女孩的嘴唇[11]。中英文化都将花“美丽”的特征映射到女子上,两种文化对“花-
美人”这一组映射有着共同的认识,因此诗中映射美人的花意象可以直译。例1诗句写杨贵妃哭泣时宛如梨花带雨,梨花这一意象实际上指的是美人,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可以被译文读者接受。
例2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
译文 At dusk the flowers fall in the eastern wind just,
Like Green Pearl tumbling down and birds mournfully sing [12].(许渊冲)
中国人常借用落花来表达身世飘零之感,英语中也有用花朵暗指人物命运的用法,例如“push up daisies ”指的是人死去后被埋葬。所以,花与人物命运的映射关系同时存在于两种文化当中,这类花意象可以采取直译方法。例2此诗属咏史怀古诗,唐代诗人杜牧途经石崇的金谷园遗址时有感而发。
落花这个意象通常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因为从隐喻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在中文语境下还是在英文语境下,人们都把花开花落的过程映射到生命上,将落花与生命的消亡联系在一起。“落花-死亡”的映射关系同时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中,采取直译的方法,能够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二)变象达意
第二种隐喻翻译方法是转换喻体,在意象翻译中即变象达意。不同的文化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喻体来表达同一本体,即始发域不同但目标域相同,这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传达喻义,译者将原文中的喻体替换成目的语读者熟知的喻体,在译者空间重构始发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举例来说,同样是表达“新生事物大量涌现”这一概念,中文用“雨后春笋”来表达,英语里则用“like mushrooms ”表达,因此译者在翻译“雨后春笋”时,需要把春笋这一喻体替换为英语读者熟悉的“mushrooms ”。在意象翻译中,不同的文化可能会用不同的物象表达相似的情感内涵,这时为了让译文读者能够重构这样的映射关系,译者需要把原文的物象转换为译文读者所熟悉的物象,以达到传递作者情感与思想的目的,即变象达意。
例3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
译文 Peach and plum blossoms in the town fear wind and showers,
But spring dwells by the creekside where blos- som wildflowers [13].(许渊冲、许明)
这首词末尾两句看似是对比城中的桃李和田园的荠菜花,实则是表达词人对城市繁华生活的厌弃,以及对田园质朴生活的赞美。中国读者很容易将荠菜花“清新质朴”的特点映射到田园生活上。而对于译文读者来说,荠菜花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物象,译者没有选择直译,而是将其转化为“wild flowers ”,点明了此花生长在乡野之间,使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花-田园生活”这一组映射关系。
例4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晏殊《蝶恋花》)
译文 Orchids shed tears with doleful asters in mist grey.
How can they stand the cold silk curtains can t allay?
A pair of swallows flies away[13].(许渊冲、许明)
例句中,词人借菊花、兰花、燕子这三个意象抒发了苦闷的相思之情。这里的菊花意象映射的是词人的心情,译文将其译为“aster ”而没有直译为“chrysanthemums ”。aster 与chrysanthemums 虽然同样属菊科,但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属。也就是说, aster 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菊花意象,但是 aster (即紫菀属植物)分布于温带地区,尤其是北美地区,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是一种更加熟悉的物象。此外,这里的菊花意象并没有与“重阳节”或是“隐逸高洁品质”等特殊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而是象征词人情感,读者可以借助语境将花与词人的相思苦闷之情联系在一起。
(三)直译加解释
第三种方法是隐喻和喻底相结合,即意象翻译中的直译加解释。隐喻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的思维能力,也取决于读者的思维能力”[14]。如上文提到的,源语和目的语可以通过转换喻体来传递相似的映射关系,然而源语里有些映射关系无法通过这样的方式移植到目的语中,这类空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源语概念隐喻是以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将源语喻体直译出来,然后另加解释。例如,在“Pandoras box ”这一表达中,英文利用潘多拉魔盒来比喻万恶之源,而中文里并没有类似隐喻表达这一概念,缺乏相应的映射关系,并且由于经验的缺乏,直译会使中文读者难以理解其真正含义,因此可以使用直译加注的方法。随着中西文化间交流日益密切,直译加注这一方法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传播,“Pandoras box ”如今被直译为“潘多拉魔盒”也可以被中文读者所理解。这样的隐喻翻译方法对应到意象翻译当中,即某个物象与某种情感或思想的映射关系在目的语文化中处于缺失的状态,译者在翻译时除了将物象直译出来之外,还要加以额外的解释,把始发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解释出来,来帮助译文读者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映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情感思想。
例5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饮酒(其五)》)
译文(a) I pluck chrysanthemums under the eastern hedge,
And gaze afar towards the southern mountains[15].(William Ackerman )
譯文(b) 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pleasure,
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 [15].(汪榕培)
译文(c) I pick fence-side chrysanthemumsat will,
And leisurely l see the southern hill [15].(许渊冲)
诗歌中也常使用花朵来映射人物品格。例如菊花淡雅、耐寒、不与百花争艳,常被田园诗人用来隐喻人物的高洁品格。例5中诗人借菊花的品格来喻指自己的志向,译者只有翻译时将菊花所代表的隐逸高洁之感传达给译文读者,才能使他们理解菊花和诗人品格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读者基于文化历史知识可以将菊花“淡雅耐寒”的特点映射到个人品格上,而译文读者则由于缺乏背景知识而不能在头脑中构成这一映射关系。译文(a)采取直译的方式,并未解释菊花这一意象,读者读来并不能理解诗人选择菊花这个意象的深层含义。译文 (b)和(c)则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了“with pleasure ”和“at will ”来表现诗人的闲适安逸和避世情怀,更贴合原文。此外,笔者认为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式也未尝不可,这样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构建“菊花-高洁品格”的映射关系。
例6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译文(a) When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comes round,
I will come for chrysanthemums again[16].(许渊冲)
译文(b) When Double Ninth Festival comes round,
Ill come again to enjoy chrysanthemums be found [16].(蓝庭)
译文(c) Looking forward to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we are,
To again gather here and chrysanthemums admire [16].(曾培慈)
英汉文化中都存在与特定社会习俗相关联的花意象,但由于英汉文化历史的差异,这种映射关系在另一种文化中一般都是缺失的。菊花与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相关联,古时人们惯有在重阳节簪菊花的习俗,诗人常以菊花来喻指这一特殊时节。这种映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不存在,所以针对这样的意象,使用直译加解释的方法更为恰当。例6三种译文对菊花这个意象都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但由于译文读者缺乏相关的文化经验,难以将菊花和重阳节联系在一起,所以三位译者都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上了“for ”“enjoy ”或“admire ”来解释重阳节赏菊的风俗[16],帮助译文读者重构“菊花-重阳节”的映射关系。
(四)舍象取意
第四种隐喻翻译方法是舍喻体译喻义,即意象翻译中的舍象取意法。上面提到,由于文化的差异,原文的映射关系无法通过转换喻体移植到译文中,可以采取直译加解释的方法。然而,有时原文的喻体在目的语文化中可能有着与源语文化截然相反的意义,直译和直译加解释的方式都有可能会造成目的语读者的误解,这就需要译者舍弃喻体,直接译出喻义。例如,在“red tape ”这个隐喻里,英汉文化中喻体“红色”的内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文化中红色的概念隐喻多是正面的,象征着吉祥、喜庆和社会主义等,而英语文化中红色的概念隐喻则大多带有消极意味,象征着危险、恐怖和残暴等。因此,这种情况下只能译出其喻义“繁文缛节”。在意象翻译当中,当某一物象在英汉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截然相反又没有其他的物象可以替代时,译者可以将原文具体物象略去不译,而只译出其映射的情感与思想,但这无疑于译文的“形美”有损。
例7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柳永《鹤冲天》)
译文 In the singsong houses and brothels,
I keep a rendezvous behind painted screens [17].(杨宪益、戴乃迭)
花在中国文化中还被用来喻指出卖色相的女子,因而有“寻花问柳”“花街柳巷”这样的说法,而西方文化中,花多与正面、积极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译者在翻译这样的花意象时,一来找不到合适的物象来替代花,二来由于意义上存在矛盾,直译会给读者造成理解困难,因而选择舍象取意的方法最为合适。例7中的烟花并非指的是烟火,而是指出卖色相的女子,烟花巷陌则指的是寻欢作乐的场所。译文没有把花这个具体的物象译出来,而是选择译出烟花的喻义。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没能将映射关系移植到译文当中,但是传递了原作情感,不会造成读者误解。
例8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李清照《采桑子》)
译文 The wind and the rain came suddenly in the evening.
They washed up the heat of Summerss rays.
Having played the sheng-huang for a while,
I did a little make-up before the mirror[18].(茅于美)
中国文化中,菱花原指菱属植物的花,因古代以铜为镜,日光照射下则发光影似菱花,后也有镜子直接仿照菱花形状而制,故人们将镜子称为菱花。菱这一意象在中文语境中多是积极含义,田园诗词常描写泛舟采菱场景,以表现田园生活的质朴自然,用菱花来喻指铜镜也是为了突出其精美。而在英语文化中,菱角较少被食用,而且常常泛滥成灾,因而带有消极含义。也就是说,英汉文化中关于“菱花-铜镜”不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且菱花在两种文化中的含义是矛盾的。因此,这首词里的菱花意象不宜直译为“water chestnut flower ”,而是应当舍弃物象直接译出其喻义。
(五)音译加解释
当原文喻体在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中意义差异较大且没有合适喻体替换时,除了可以不译喻体只译喻义之外,还可以采用音译原文喻体的方式,即在目的语中另创一个喻体。比如龙这个中华文化中的传统形象代表着尊贵、至高无上,中华儿女被称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所谓的“龙”,也就是“dragon ”则代表着邪恶。这样看来,把龙译为“dragon ”显然是不合适的,即便加注解释,也容易造成目的语读者的误解,因而“将中国龙音译为loong更为恰当”[19]。在意象翻译中,译者可以音译原文的物象,即在目的语文化中新创一个物象,然后另作解释,将这个新物象与原文想要传达的情感思想联系到一起。翻译时使用恰当音译,“不仅可以解决文化上的翻译困难,而且有助于文化传播”[20]。
以花意象为例,前文提到,牡丹因其色泽艳丽、花朵饱满历来受到追捧,常象征着典雅、高贵、吉祥等,因而是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牡丹一般来说都被译作“peony”, 然而特定品种的牡丹如“洛阳红”则不宜直译。而由于英汉文化中红色的内涵不同,如果将诗歌中的“洛阳红”直译作“Luoyang Red”,则可能会给英文读者带来“危险、暴力、血腥”等负面联想,因而此处将其音译为“Luo- yang Hong Peony”,然后再另作解释似更为恰当。
四、结束语
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意象可以看作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将意象视为隐喻使得人们可以利用隐喻的结构及其产生机制来理解意象,為分析意象和翻译意象提供了新视角。由于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的身体经验不同,意象隐喻的映射关系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也可能不同。据此,提出意象翻译的五种方法:直译、变象达意、直译加解释、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以花意象为例进行探讨,花意象在两种文化中的映射关系为不同意象翻译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 曹苇舫 , 吴晓.诗歌意象功能论[J].文学评论 ,2002(6): 118?125.
[2] 李气纠,李世琴.文化翻译观下中国古典诗歌中“玉”意象的英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9):58?61.
[3] 文旭, 肖开容.认知翻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4] 顾建敏.关联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意象互文性及其翻译[J].外语教学, 2011,32(5): 110?113.
[5] 李占喜, 何自然.从关联域视角分析文化意象翻译中的文化亏损[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2):40?43.
[6] 权循莲, 田德蓓.概念隐喻视角下汉语古诗意象的英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0(1): 127?132.
[7] 杨俊峰.从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看意象图式理论的阐释空间[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4):66?70.
[8]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9] 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02(3):162?171.
[10] 许渊冲.唐诗三百首新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11] 陈静, 许先文.英汉“花”的隐喻认知对比与翻译[J].阅江学刊, 2016(5): 103?110.
[12] 许渊冲.唐诗三百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3] 谢真元.一生必读宋词三百首鉴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14] 曹灵美, 柳超健.“草”隐喻的英译认知研究[J].中国翻译, 2018(6):94?99.
[15] 汪榕培.陶诗英译百花开?陶渊明《饮酒》(其五)英译比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4):41?45.
[16] 王金玲 , 庄贺.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意象传达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189?194.
[17] 聂鑫森今译,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古诗苑汉英译丛宋词:汉英对照[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1.
[18] 茅于美.漱玉撷英?李清照词英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19] 黄佶.关于“龙”的英译名修改问题[J].社会科学,2006(11): 161?169.
[20] 项东 , 王蒙.中国传统文化文本英译的音译规范刍议[J].中国翻译, 2013(4): 104?109.
(编辑:朱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