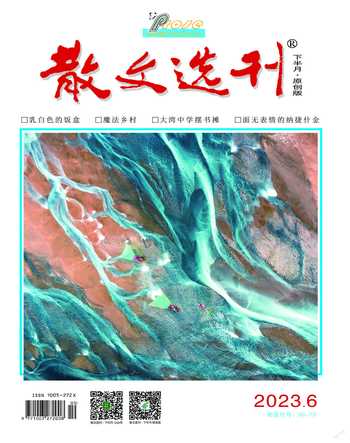墙头上的那株草
李唯峰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墙头上钻出了一株不知名的草。
草籽是怎么到墙頭上去的呢?是被四处游荡的风儿吹上去的,还是被调皮的小鼠衔上去的,抑或是被在墙头上玩耍或在空中飞过的鸟儿屙上去的?不管怎样,这粒草籽的顽强萌发,又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又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抹生命的绿色。
这株小草立足于由混凝土和红砖黏合而成的坚硬砖墙之上,扎根在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砖缝之中,却萌出了芽,拔出了茎,抽出了叶,站在高高的墙头上向世界昭示着生命的绿色与蓬勃,这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一天下午,突然怪云四合,雷电交加。暴风像疯了一般扫荡着一切,院中那棵粗壮稳重的老枣树在风中狂舞,有的屋瓦竟然像纸片一样被狂风吹起。
一会儿,风小了,鸽卵一样大小的冰雹像一枚枚炸弹从天而降,击打着大地上的一切,一会儿的工夫就盖严了地面。冰雹累了,停了,紧接着暴雨又降临,并且越下越起劲,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样子。
大雨几乎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走到院子里。院子里一片狼藉,积水还能没过脚踝。我走近墙头看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草竟然还在,但已经被摧残得不像样子了:它的身躯歪在一边,只靠几丝根须和墙头相连,大部分的茎节已经断折,叶子残缺不全。
过了几天,那株小草又站起来了!虽然站得有些吃力,甚至站得有些狼狈,但毕竟站起来了!
天上的雨好像都在那天下完了,此后许久没有下雨。太阳悬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不知疲倦地炙烤着大地,大地几乎都冒烟了。土地已经龟裂,庄稼的叶子已经耷拉下来并开始卷曲,宣告着它们的奄奄一息。墙头就像一面烧红的鏊子,热得不敢往上放手。小草蔫头耷脑,忍受着烈日和鏊子的暴晒熬煎。
小草的叶子在日渐变黄蜷缩,到后来纤细的茎也在慢慢变黄,看来生命正在慢慢逃离它的躯壳。不久,小草的茎叶完全变黄了,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
终于下雨了,我又心有不甘地看了看那株草,它依旧黄黄的,一丝一毫的生机也没有,看来它真的死了,再也活转不过来了。
又过了几天,我发现小草的根部好像透出了一点儿绿色。我走近几步,揉了揉眼睛仔细观看,不错,那确实是彰显生命色彩的绿,尽管只是那么一点点,尽管是那样的让人不易察觉。此后这点绿逐渐蔓延,终于在根部又萌出了新芽,继而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
到了秋天它开花了,花是那么小,那么不鲜艳,甚至让人怀疑那是否是花。但它不在乎别人对它的看法,也不在乎有没有欣赏者,照样开得轰轰烈烈。
如今我已搬离了那个小院,远离了那个墙头和墙头上的那株草,但那株草还常常走进我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