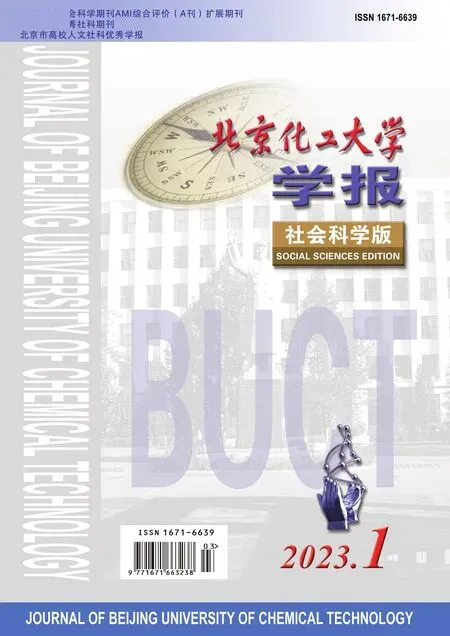幽冥法文化视野下的明清民间法律意识
——以游冥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张婉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有学者指出,“中国民间法存在于家族制度、神权观念、民间性组织制定的规范、风俗习惯等多种渊源之中”[1],“神权观念主要表现在神明裁判、神庙祭典、求神问卜等仪式活动上,如神明裁判便是运用神灵意志大量介入人类行为的是非辨别与纠纷处理”[2]。可见,以地狱审判为重要内容的幽冥法文化也可以视为民间法的一部分。不同于现实中法文化包含物质(法律机构、设施、文本等)和意识(对法的认识、思考、研究等)两个层面,幽冥法文化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层面的隐性法文化,虽然它缺少现实的制度性存在,但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指引和规范着现实信众的言行[3]。幽冥法文化借助因果报应和冥府审判,以一种看不见的正义弥补了现实正义的缺憾,从另一角度树立了人们对正义的信心,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在中国,幽冥法文化口口相传,同时大量见之于宗教典籍、小说、戏曲和以宝卷为代表的各种说唱文学作品中。“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4]。游冥宝卷立足于宝卷中的游冥故事,是指以人物的“(因得道/死亡/入梦)入冥—游冥—还阳/投胎”为典型故事情节,通过对地狱情状的种种描写,以达到宣传轮回果报之说、劝人修善弃恶作用的说唱文学作品。作为俗文学,宝卷的民间视角非常突出,其对民间社会百姓大众的日常生活描述也非常丰富,构成了百姓大众的一个知识源泉。游冥宝卷从阴间律法、冥府审判、地狱刑罚等方面集中全面地展现了幽冥法文化,折射出诸多明清时期民间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心态。
一、寄意幽冥的正义幻想
在社会秩序的实现中,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障,二者的相互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互补作用。然而,人世间的社会秩序永远不可能圆满无缺,现实司法的不公与疏漏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面对这种困惑与缺憾,民众希望以神灵的完美无私来达到赏善罚恶、消灾祈福的目的。于是,宗教成为法律的辅助者,所谓“明有王法,暗有神灵”[5],法律的惩恶扬善导引功能很大一部分转化到了鬼神那里。瞿同祖先生就此认为:“法律对于鬼神的借助和依赖,以及宗教制裁与法律制裁的联系,可谓备至。……可以说法律制裁是主体,宗教制裁则居于辅助的地位。”[6]当然,在乡民心目中,世俗王法自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诚如俗谚所云“四季春为首,万事法当先”,“人随王法,草随风”[7],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们简单朴素的法律意识。然而,统治者历来压制诉讼,清朝康熙皇帝曾公开宣称:“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则讼事必剧增。若讼者得利,争端则倍加。届时,即以民之半数为官为吏,也无以断余半之讼案也。故朕意以为对好讼者宜严,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见官则不寒而栗。”[8]不仅统治者压制诉讼,封建官员们基于道德主义的法律观念也持一种以和为贵、息争厌讼的司法态度,如清人刘礼淞所言:“夫听讼而使民咸惕然内讼(自省)以几于无讼,此守土者(即地方长吏)之责也。”[9]加之司法资源的短缺,司法过程的黑暗腐败,老百姓极易产生“惧讼”心理(1)《目连宝卷全集》有一段话非常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惧讼”心理:“乃官司一事,更加大怕。千思万想,费尽心计,跑来跑去,挖尽路头,吞饥受饿,用尽铜钱,反被差房辱骂,皂吏敲打。官司输起,遍身排打一顿,如鸡落粪缸回来,你道羞也不羞。讼事破财最伤心,成冤结仇为此因。劝人和事莫经官,彼此两家也安宁。”参见:目连宝卷全集[Z].光绪三年杭州西湖慧空经房刻本:12-13.,在权利主张难以通过官方诉讼途径来实现之时,他们往往转而求助于自己所信仰的阴司审判体系,帮助他们解决现世未了的怨愤与不平,从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三说得好:“何缘世上多神鬼?只为人心有不平。若使光明如白日,纵然有鬼也无灵。”[10]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已经形成了成熟完善的冥界官僚和司法体系,如宝卷所言,“阳有阳律,阴有阴条。凡人在阳间造下无边罪过,阴司治下无限地狱”[11]。游冥宝卷在吸收佛道教地狱信仰,继承以往游冥故事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塑造了丰富完善的冥界人物系统。宝卷中从阎君到小鬼,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如《轮回宝传》所言,“阳间官府活阎君,差役犹如恶鬼使,书吏犹如判官们,阴比阳同一定理”[12],神鬼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监察、审判、惩罚机制,其核心为赏善罚恶。
宝卷中冥府的监察机制严密而有序,以灶王、土地、城隍、日游神、夜游神等为代表的地方神灵是冥府的主要监察人员。他们将每个阳世之人的善恶言行记录在案,纤悉无遗。《目连宝卷全集》写刘氏在傅员外升天之际,发下若开斋破戒便不得好死、地狱受苦的重誓,而“刘氏罚咒随口出,谁知公曹写分明”。同卷还提到“东厨司命每日见刘氏青提,十分作恶,……今已恶贯将满,不免驾升祥云,达奏天庭”[13]。《游冥宝传》言:“土府灶神最灵验,将他罪孽记阴间。”[14]《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言:“阳间做事神难骗,灶司启奏上天庭。”[15]《轮回宝传》中二殿大王听刘京假诉、一片虚言,高声大骂道:“刘京真乃是个万恶之鬼。每日有日游神、夜游神、司命、灶君,将你善恶奏上天堂地府,簿记分明,丝毫不差。”[16]同卷还提到三殿大王传家先与门神来核对刘京善恶状况,可见二者也有监察之职。完成察录后,“监察官”们由下而上,层层上达,“灶王报与土地,土地报与城隍,城隍报与天齐,天齐申与幽冥地府地藏菩萨,这菩萨批与十王”[17]。由此完成对人间善恶的有效鉴察。
强大的监察能力让冥府完全掌握了每个人的生平记录,故而在进入冥府审判环节时,其审问多为程序性的。但这种程序性的审判却必不可少,因为它赋予了人们对命运之因果律的信心。宝卷中冥府审判的提起一般为当事人寿命终结之后,根据其所造诸业,亡灵被押送到冥府接受审判或者是作为被害人在冥府告状。宝卷中经常提到冥府衙门放告(2)所谓放告,是指官府每月只有在特定日期才受理百姓所告案件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放告的日期,明清律典中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是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相应日期。,准予鬼魂告状。如《秦雪梅三元记宝卷》中秦雪梅撞死后入冥,“走了一程衙门见,门口男女闹音音。忽听堂鼓打三下,衙门放告挂端正。男女分班传进去,一批一批放出门”[18]。《玉英宝卷》写玉英魂魄随金童玉女来到阴司,那日“五殿阎罗正当放告日期,吩咐鬼卒开门放告”[19]。《鸡鸣宝卷》中出场判官自报家门:“俺乃森罗殿下总判官是也,玉帝命我执掌阴曹枉死城中一切屈死总案。今日乃逢放告之期,有恐冤魂发下,即当带上堂来,为此升堂查察。”[20]
在游冥宝卷中,冥府审判如何弄清犯罪事实,如何让当事人承认犯罪事实,也是刻画和表现的重点,因为这关系到冥府审判是否是彻底的准确和公正。冥府审判中的事实确认主要依赖冥簿、业秤、业镜以及证人作证。冥簿之说可能来自于道教(3)道教的中心理论之一即为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并予以相应的报应。如《太平经》卷一一瘙懟所云:“不知天遣神往记之,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记录世人善恶的是司命、司录二神,司命录善,司录记恶。道教这种观念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观不谋而合,冥簿可能因此才被吸收进民间的地狱信仰中并成为冥府审判的重要依据。参见: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4.,是对命定思想形象化解释的产物。冥簿作为阴司法律文书,忠实无谬地记录了世间所有人的生死、善恶、命运祸福,如影随形,无法摆脱,因此成为冥府审判中确认事实的最重要依据。游冥宝卷中的冥簿有不同类别,如生死簿、善恶簿等,分别由不同的判官掌握。《雪梅宝卷》说:“世间万般善恶事,注定生死簿中查。”[21]《轮回宝传》说:“(阎王)吩咐判事官将刘京善恶簿从头一一指与刘京细看,当堂对质分明。”[22]冥府以秤来称量罪福从而判定死者善恶的方式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入冥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4)《冥祥记》“宋沙门僧规见称罪福事”一文写沙门僧规“轻犯小戒,多游俗家”,一日无病暴卒,被绳索缚入一城:有一人,衣帻并赤,语(僧)规曰:“汝生世时,有何罪福?依实说之,勿妄言也。”……有顷,吏至长木下,提一匮(柜)土,县(悬)铁梁上称之.如觉低昂。吏谓规曰:“此称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应先受罚。”参见:鲁迅.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313.。游冥宝卷中也多次出现业秤,如《王大娘游十殿宝卷》写“王大娘五殿罪名受过,来到第六殿卞成大王审问,叫夜叉将王大娘上秤称了,然后定罪”[23]。《王氏女三世卷》言:“来到平等大王殿,一杆大秤挂前庭。新死亡人来到此,都要将来上秤称。无罪之人重八两,有罪之人重千斤。”[24]冥簿和业秤,无赖者可以诬之不准确,而业镜的出现则让其罪业无所遁形。业镜,也称孽镜,最早出现于佛教经书[25]。其强大的再现功能可以对亡灵产生绝对震慑使之百口莫辩,低头认罪。游冥宝卷中的业镜一般出现在第五殿,如《梁皇宝卷》载:“来到五殿阎王案,孽镜台前照得真。孽镜照出有对证,灵魂件件见分明。一一从头来招罪,小鬼敲打剥衣襟。”[26]《金锁宝卷》也说:“第五殿,阎罗王,镜台地狱。这些人,来一照,善恶分明。”[27]《轮回宝传》中五殿阎罗天子问刘京:“你在本院台前观看,镜内照出十恶不善之罪,对质明白,丝毫不差,不得屈你,该无强辩。”[28]当然也有别的说法,如河阳宝卷《十王卷》中业镜位于一殿秦广大王处,“东面高台一座,有大镜子一面。上写‘孽镜台前无好人’七个字。台高丈二,镜大十围。一生作善作恶,镜中照出丝毫。罪犯不得隐瞒,判断容情,休想动念”[29]。《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中孽镜台也归秦广王管理,公主入冥后,“行之不远,来至孽镜台前,只见一个红发鬼兵,青面獠牙,拿着一人跪在台前,上有一镜,那鬼兵指手指脚。旁有一官人,手拿簿笔,点头书写。公主问曰:‘此是何故?’判官曰:‘此人在生所作罪过,不肯承认,在此照他生前之罪,判官旁书记挂,以便发于二殿受罪’”[30]。与业镜相关,明清衙门普遍悬挂的“明镜高悬”匾额,从信仰的层面来说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神判传统的变形或遗迹从而具有了神圣品格,产生了“神道设教”的司法功能。这块匾额不仅象征着神灵对司法官员明察秋毫、公正无私的祈盼和约束,也对跪于公案之下的原被两造造成心灵的震慑和制约,蕴含着传统中国司法的理想。除此之外,阴司审判还有证人作证,不过这里的证人不一定是人,而是其他有情生命。《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言:“(阎王)便叫受杀众生事,个个前来对分明。只见猪羊鸡鹅鸭,齐来跪伏乱纷纷。扭扯王文来讨命,一命今朝殄一命。”[31]《轮回宝传》载:“一殿秦广大王骂道:‘吩咐左右,与我将六畜牲命带进,对证分明。’……牛马六畜齐带进,个个殿前把冤伸。阳间畜物不会说,阴司各各会诉情。”[32]
阳间官府可能迫于证据不足或证据灭失等问题,产生种种疑难案件,甚至造成冤假错案,而冥府则由于冥簿、业秤、业镜的存在得以永远掌握真相,真正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不论男女、老幼、尊卑、贵贱,即使能够侥幸避开阳间社会的法律制裁,也最终难逃阴间律法的追究惩罚。从这层意义上看,冥府的审判寄予了人们对终极正义的期盼和想象性满足。另一方面,冥簿、业秤、业镜作为具象的审判工具把审判过程形象化,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隐含着对审判者获取证据时权力运作技术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反映了阳间司法中对于事实认定的艰难,暴露出人的认识能力和重构以往能力的有限,实际上触及到了人类永恒的能力局限和悲剧境遇,因此,不能仅仅简单被理解为鬼神迷信。生活在缺乏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人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超自然的鬼神赏罚,这是一种绝望的希望。
总之,宝卷集中展示了底层大众敬神畏鬼心理下的鬼神化法律意识,他们对灶王、土地、城隍为代表的地狱监察机制和以十殿阎君为中心的审判—惩罚机制深信不疑,容易令其因畏惧报应而不为恶行,从而养成自主的守法意识,有助于世俗法律的有效施行。事实上,冥府诉讼不仅是小说家言,现实中也有以此作为伸冤途径的践行者:即阳世含冤之人通过世间诉讼无法申雪冤情时而向冥府提起诉讼,以获得另一个新的司法体系的庇护。如2006年在吐鲁番编号为2006SYM4号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份缘禾二年(432)写给冥府的冥讼文书[33],兹抄录如下:
(前缺)
1. ]□[ ]□[ ]□[
2. 缘禾二年十月廿七日,高昌郡高宁县
4. 立身不越王法,今横为叔琳见状
6. 察;盐罗大王,平等之主,愿加威
7. 神,召琳夫妻及男女子孙检校。冀蒙列理,辞具。
8. 货母子白大公、己父,明为了理,
9. 莫爰(缓)岁月。
(余白)
文书中原告赵货是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的百姓,时年三十岁,为人安分守法,却被叔叔赵琳告到官府,最终枉死,满怀怨恨的他因此向阎罗王提起诉讼,请求拘勾赵琳全家来冥府对质[34]。可见,五世纪初期的高昌百姓已普遍相信阴司也有司法系统,幽魂在阴间也能够申诉冤屈。直至民国时期,徽州歙县漳潭仍有告冥状现象[35]。不仅是平民百姓,连封建官吏们都对阴司审判寄予一定的期望,明代府、州、县官关于鬼神的祭文中写道:“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极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杖决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36]祭文以城隍神的明察秋毫威慑犯罪者,以补救现实法网的疏漏之处。此外,由于城隍爷能断狱决案,审理案件的法官便利用某些民众敬神畏鬼的心理,故意做作,将一些疑难案件放在城隍庙里审理,以城隍神的所谓英明来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如清蓝鼎元所著《鹿洲公案》虽有修饰润色之痕,但所记均为真实案件的判决,其中的《幽魂对质》一案,叙江、罗两姓霸占吊杆汲水灌田,与杨姓族人发生殴击,将杨仙友当场打死。蓝鼎元再三审讯,无人招供承认。蓝鼎元遂在天色昏暗、阴风惨惨之时将案犯带到城隍庙中审理。城隍神是记录、奖惩一城之人善恶功过的阴间官员,在城隍庙里审讯罪犯,本身已含有以城隍神威慑罪犯的意义,而法官蓝鼎元又假唤被害人的幽魂来与罪犯对质,就更容易摧垮罪犯的精神防线。正如蓝鼎元所言:“疑狱难决之处,不得不用权术。试思此案若非冤魂对质,何能使凶手伏辜?即将数十人尽加刑夹,愈夹愈不得情,如何定谳?妙在晦夕凄风,乃冤鬼出来之时,城隍摄鬼,又是众人所信;许多排场森森凛凛,令人毛发悚竖;而神机妙用,全在举头一观。盖罪人心虚,自然与众不同也。此窍既得,便可迎刃而解。”[37]蓝鼎元正是利用了民众对城隍摄鬼说的虔信和敬畏,设置了好似阴间审案的阴森排场,才得以“乘虚而入”,查明真凶。《聊斋志异》里的“胭脂”一案、《学治臆说》中的“刘开扬”一案、《新齐谐》中的“火烧盐船”一案,都是在城隍庙审理案件的典型代表。
二、法德含混的法制观念
游冥宝卷所体现出的冥律规范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或轻或重的过错行为。这些冥律规范大多十分具体而缺乏概括性,指引性非常强。比如《观音济度本愿真经》载“凡神会演戏,不点忠孝节义之事鼓励风俗,偏点那风流邪淫之文,使男女动情,以假作真,节义难全”[38]者死后入抽肠剖腹地狱受罪,这种行为或许是当时比较常见的“有伤风化”的行为,但却难以概括出其他污染社会风气的文化娱乐行为。不过毕竟因其简单具体,故而具备了较强的指引作用。但也有一些冥律规范的表述缺乏具体性,而概括性太强,如《龙图宝卷》说,“此等人在阳间多做恶事”[39],因而在风雷地狱被高高吊起;河阳宝卷《十王卷》认为,“穷不安分守纪,富不敬老怜贫”[40],死后会堕入镬汤炉炭地狱受刑;《唐太宗游地狱》介绍第五层土雷狱所犯罪业为“在世上,逞英雄,耍显威风。欺良善,压孤寡,使了奸心”[41]等。
宝卷中特别能体现庶民法律意识和契约观念的例子是关于欠债还钱的认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中国古人遵奉的伦理准则。古人之间一旦发生“钱债田土”纠纷,往往会寻求调解甚至诉诸衙门以得到救济。但如果遇到负债者抵赖、出逃或者始终没有能力还清债务时,又该如何处置?在古人心目中,若有人活着时欠人财物未能偿还,那么即使死后到了阴间,也一样要受到惩罚,来生转为畜类以偿还债务。《修真宝传》说:“若欠他人钱和米,变化牛马还他人。”[42]《观音游殿宝卷》中“在阳间借人财物,不肯还人,被人讨急,即便搬场移处”[43]者入阴司铁床地狱受罪。《地藏王菩萨执掌幽冥宝卷》中戴文投胎变牛,因他“该富贵家银两、粮食,脱生与他家投胎,还债一遭,腿上写‘戴文’二字,脱生阳间,以传后世”[44]。《轮回宝传》中野狗、野牛自言道:“只因前少你的债,欠米三斗未还清。死后发我来变狗,你家还债七年春”,“前世少你钱十串,贫穷未曾还得明。不想死入幽冥地,发在你家变牛身”[45]。毫无疑问,这些说法是中国传统报应观念在契约故事中的反映,体现出民间对欠债赖账败德行为的强烈谴责。它们讲述的虽然不是现实社会中的事实,但折射出一种明显的契约意识或者说是关于契约的信仰。这种获得了宗教信仰支撑的“欠债还钱”的观念,恰恰证明了明清时期庶民百姓强烈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
除此之外,游冥宝卷中的冥律规范道德化、宗教化色彩十分明显,体现出民间法与德含混交融的法制观念。这里的德既包括世俗道德,也包括宗教道德。不少冥律规范在现在看来仅仅是违反了一些世俗道德。如说谎骗人、搬弄是非:
罪人口中吐鲜血,咽喉闭塞不通风。王氏便问作何孽,仙童便答哄骗人。在生行人来问路,问南指北误行人[46]。(《王氏女三世卷》)
此等人在阳间好说闲话,搬弄是非,将好说瞎,吹涨捏塌,入阴曹就受割舌头的苦[47]。(《黄氏女宝卷》)
如不爱惜五谷、衣服,不敬惜字纸:
不惜绫罗救寒苦,寒冰地狱冷难禁。……作贱物类轻米谷,罚你碓捣碎纷纷[48]。(《目连宝卷全集》)
饿鬼地狱瘦得很,生前五谷大看轻。粪池地狱臭得很,不敬字纸秽神明[49]。(《韩祖成仙宝传》)
如为富不仁:
把鬼犯用法绳一一捆绑,用铜汁灌口中疼痛难当。问此鬼犯何罪受这苦况,……苛索财逼押人房屋佃当,肥己身不管人一家死亡[50]。(《目连救母幽冥宝传》)
此名滑油山。凡人在阳间,有钱不肯修桥补路,施舍路旁灯油,行路不让老人以及残疾,死后罚上此山受苦[51]。(《目连三世宝卷》)
而且,这些世俗道德很难说属于正统的儒家思想,它所宣传的不过是不要说是道非、要讲诚信、要爱惜粮食衣物、要乐善好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尽管都与儒家道德相兼容,却未必仅仅属于儒家。
另外亦有不少规范是对违反了宗教道德的概括,如杀生:
此山名为刀山狱,尖刀密密好惊人。在生宰杀猪羊卖,杀生害命伤众生。……只见牛头将刀砍,滚汤泼煎罪人身。此是阳间屠牛汉,杀牛宰犬戮生灵[52]。(《三世修道黄氏宝卷》)
在世为人做厨子,专杀猪羊鹅鸭身。细切皮来粗切肉,罚他地狱受难辛[53]。(《王氏女三世卷》)
如破人斋戒:
只见夜叉将锯解,满身解得血淋淋。此人在世行恶汉,破人斋戒不良心[54]。(《三世修道黄氏宝卷》)
毁佛谤圣是你造,不该扯碎大乘经。狗肉馒首去斋僧,将你重责不非轻[55]。(《梁皇宝卷》)
如侮慢神佛:
釜盆地狱皮脱尽,身体不洁厌灶君[56]。(《韩祖成仙宝传》)
刘氏五辛秽佛神。葱韭齑蒜并胡荽,油菜名即芸薹荤。秽污之手经乱翻,酒肉荤日喷经文。今朝罚你粪池狱,一日三餐吃粪清[57]。(《目连宝卷全集》)
从以上诸例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进入到游冥宝卷的冥律规范中。这些世俗道德都是那一时代社会道德和习俗的反映,面对司法无权、无力管辖的道德堕落危机,游冥宝卷的地狱中出现了大量专门针对伦理道德方面过失的刑罚,希望借此来警醒世人、遏制恶行。至于宗教道德在冥律中的出现,则与佛教的发展传播和宝卷本身的宗教性有关。尽管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有善恶报应的观念,但是地狱思想及冥律规范却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一步充实发展起来的,因此冥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而渊源于佛教俗讲的宝卷,在题材内容和说唱形式上都深受佛教影响,其间渗透着佛教的价值观念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尽管游冥宝卷列举了种种招致地狱报应的恶行,但它毕竟是对具体行为的文字描述,不可能涵盖无遗,而且同一种行为失范,往往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地狱刑罚,冥律规范在内容及其运用上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灵活性和模糊性。这一方面体现出底层俗文学的流动性和变异性,另一方面,这种设计或许正是古时“礼”与“法”界限模糊、互相混同的艺术化表现。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多重规范之下,既包括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又包括在社会中生长起来的各种社会规范——习惯的、道德的、宗教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古时往往浑然一体,虽然性质、形式不同,但同具社会约束力,因为在古人心目中,一切规范都有法的意义,即所谓“情理难容者,国法难容”。而且对于底层大众来说,他们的认知水平也没有达到能够明确区分法律和道德的程度。传统社会儒家重视礼教,提出“以礼入法”“出礼入刑”的主张,使法律为传统道德服务。如《孔子家语》“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58],《大戴礼记·盛德》“礼度,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59],《唐律疏议》“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60],《清通志·刑法略》“德礼之所不格,则刑以治之”[61],均系此义。自汉代以后,法家衰而儒家盛,礼治、德治与法治的思想趋于折衷调和,礼刑合而为一,法律与道德显示出同质异态之体相。明儒叶良佩云:“夫刑法者,礼之辅也。礼者晅润而法者震曜,礼者身躯而法者手足,礼者主君而法者弼佐,彼此相须以为道,盖阙一不可焉者也。”[62]这已是古代社会末期成熟的法律观,它强调礼法统一,表现出对法律道德化的强烈认可,法律作为礼教道德的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游冥宝卷直接宣传道德化色彩浓重的冥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一个黑白分明、善恶对峙的道德世界,成为构建传统社会道德化的司法正义观的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说游冥宝卷中的冥律规范所折射出的明清时期平民大众法制观的相对含混,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做判断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法德含混的法制观念,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另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并且是传统社会行政、司法官僚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制度,一个在功能上互补的制度”[63]。传统的道德话语不仅规约着大众的行为,而且尽可能地将这种道德内化为他们的一种自我约束,就其功能来说,它其实是一种政治学,一种治理学,一种法学。在这个意义上,在传统社会中,所谓的“德”也是一种“法”,一种在社会大众中获得普遍认可却不成文的观念上的“法”。表现在游冥宝卷中,底层的创作者们将纷繁细致的世俗道德、宗教道德吸纳融合进阴间律法中,以行为的善与恶而不是罪与非罪作为阴司审判的唯一标准,以超越法律界限的社会公德与伦理公德触及灵魂的拷问,在功能上弥补了阳世法律和道德的不足及缺憾之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下层的绝对主导,提出了民间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与道德行为规范,建立了民间自己的“法庭”,这里面隐含着民间向司法权力发言的一种精神需要。
三、刑罚制度的女性规训
理论上,地狱的受刑者应是一切不善有罪之人,但是在游冥宝卷中,男性和女性出现的比例还是稍有差别的。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妇女受地狱之刑的可能性似乎比男性要大得多;而在古代现实社会中,女性由于活动范围等的限制,其犯罪数量和犯罪种类相对于男性来说是极少的。游冥宝卷所述的地狱之刑,大致针对两种罪行:一种是普适性的罪行,即不分男女均可能触犯;另一种是专指性的罪行,尤其指向于女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血湖(或称血河、血盆、血池)地狱(5)道教的血湖观念来源于佛教“血盆地狱”观念,佛教有《佛说大藏正教血盆经》,道教有《太一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元始天尊说灵宝升玄济度血湖真经》等,都是以血湖地狱为中心展开。佛教血盆地狱的罪魂是一切妇女,而道教血湖地狱中罪魂的身份性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次出现了“不分男女”“产死妇女”和“一切妇女”三种观念。这样的发展过程,体现出女性原罪色彩的从无到有和道教女性观从较为平等到歧视女性的演变。参见:武清旸.道教“血湖地狱”罪魂身份的演变论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6(6):128-134.。此类记述可摭拾数例:
五殿阎罗管血河,血河便是女人多。万丈流波千尺泪,过头没脑浸其身。披头撇发嚎啕哭,叉入河中受苦辛。此等女人前生月性往来、临盆生产,一切秽衣溪河洗濯,污秽水浆,触河神祇,取水煎茶供佛,触犯诸佛菩萨,还有不贤之妇,临盆淹死儿女,还有一等羞辱妇女,私受胎孕,用药打下,连累自死,此等女人更加孽罪沉重[64]。(《吕祖宝卷》)
男子罪孽由自可,女子罪孽似山坡。生男育女多代过,死在阴司坐血河。儿女阳间争名类,娘在阴司莫奈何。男学目连莫几个,母亲何必苦奔波。……世世男子为何因,前世积德斋戒人[65]。(《重刻修真宝传》)
当然,也有个别宝卷认为血湖池并非仅为女性设立,如《观音游地狱》提到“活在阳间妇女生产身亡,因为生男育女故到血河池,还有男人夏天乘凉弗得知日月三光赤身露体,故到阴司受此报也”[66],但女性因月经、生产或堕胎导致血水污秽神灵而堕入血湖池仍然是最主流的认知。明清时期,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日臻完善,游冥宝卷中的血湖地狱涵盖了佛教的地狱说、儒佛的伦理观以及道教的修行方法,是三教合一的产物。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状况,“污染罪”成为她们无法逃脱的罪孽。这种宣扬女性天生有罪的刑罚,裹挟着宗教禁忌与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压抑女性,降低女性的自我认同,使其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自轻自贱的心理,从而使男女两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等差和两性之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化、凝固化。要想脱离血湖地狱,儿女的救赎必不可少,孝顺男女需要“持斋三年,专诵《血盆经》一藏,可免此罪,即得往生佛地也”[67]。儿女的救赎有效地阻止了女性注定的苦难和痛苦,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命运和业力的必然,说明了一个通过外部实体(子女、神佛菩萨等)富有同情心的行为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地狱刑罚在命运、业力和救赎、报恩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可惜,为了突出报娘恩的孝道精神,女性最终沦为被救赎的弱者和罪人。
除了血湖地狱,另有一些地狱的罪过也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如石磨石压地狱,是毁骂公婆者接受刑罚的地方,《蜜蜂记宝卷》载:“安心就把桥上过,又见磨子磨人身。家中常把公婆骂,死有阴司不容情。”[68]《三世修道黄氏宝卷》载:“头发挽在高梁上,一块压石重千斤。此是毁骂公婆妇,落在此狱不翻身。”[69]《秀女宝卷》亦载:“骂公婆,怨丈夫,压磨地狱。”[70]又如铁床地狱,是通奸害夫者受刑之处,《三世修道黄氏宝卷》写道:“罪人押在铁床上,原来俱是女人身。此人在世贪淫妇,暗欺毁骂丈夫身。”[71]《唐王游地狱》也写道:“十三层来铁床狱,轮奸通奸害夫君。自己丈夫她不爱,跟上贼汉胡乱行。”[72]再如滑油山,涂脂抹粉者死后难过此山。《目连宝卷全集》说:“目连又到滑油山,罪人叫苦实伤心。只为阳间油搽发,胭脂花粉引愚人。”[73]靖江宝卷《庚申宝卷》也说:“阳日三间搽脂抹粉妆美貌,阴司难过滑油山。”[74]还有一些地狱的罪过,女性的犯罪可能性也高于男性,比如剜眼地狱是调唆是非者所处的地狱,如《黄氏女宝卷》记述黄氏女游冥来到剜眼地狱,只见“两个鬼使把一个女人绑在树上,用刀把那妇人的两眼挖了,又把奶头割了,那妇人只疼得嚎啕大哭。这宗人,模样好,心肠不好。她每日,只爱得,梳洗打扮。公婆们,说几句,就把眼瞪。姊妹们,稍不对,使气动身。邻居间,为小事,大吵大嚷。一件事,她总爱,鼓舌摇唇。母老虎,女夜叉,乡里憎恨。冥王府,勾她来,受些苦刑”[75]。《唐王游地狱》亦载:“十四层来磨眼狱,都是调唆是非人。姑嫂不和两头掇,调唆丈夫出家门。”[76]宝卷借地狱刑罚强调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孝亲”“贞顺贤良”“节俭朴素”等要求,成为男权社会用来束缚女性的又一道枷锁。
每一种刑罚制度都根源于其母体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宗教性文学,宝卷中种种针对女性的地狱刑罚,暴露出佛教和儒家对女性的歧视态度。一方面,宝卷渊源于佛教俗讲,它劝导信众“持斋念佛”,其中也渗透着佛教的女性观。儒家固然贬低女性,佛教则对女性更为歧视。相比于儒家对女性行止的要求,佛教对女性信众有着更多约束,其对世俗女性“八十四态”(6)《大爱道比丘尼经》提出的“女人八十四态”充满着性别歧视。该经声称天下男子很难不为女人所惑,并将这种被迷惑的起因归结到女性的种种欲态,即“女人态”。这些外在的“女人八十四态”可以分为虚荣好饰、故作姿态、思念男子、自骄慢他、嫉妒破坏、悭贪追悔、含毒骂詈、憍恼亲里、谄诡害他、诅咒伤慈、窃人隐私、调戏语人、贪积不厌等类别。(八十四种不正确的姿态和心态)的批评和限制,得出了“女人甚可畏也”的结论,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游冥宝卷中地狱刑罚的设置,多少受到了佛教这种女性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法律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制定的。男性是法律的主体,女性作为从属者只能成为法律的客体,她们的法律地位比较低,其言行既受到法律的制约,又备受儒家“三从四德”伦理规范的束缚。而地狱权力机构既是宗教的想象,更是对人间的摹写,游冥宝卷中从阎君、判官到牛头、马面,都是作为男性来描述刻画的,它所建构的幽冥世界也是一个男权统治者主宰的社会。因此,幽冥世界的冥律规范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男性的眼光,折射出明清时期民间对于刑罚与性别的一种保守陈腐认知。
不难发现,上文所举诸种针对女性的地狱刑罚,特别侧重于女性伦理道德方面的罪过,这和现实社会中王法对女性涉及道德伦常方面特别是违反宗族、夫妇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犯罪惩罚也十分严重是一致的。如夫、妻侵犯对方尊长时严惩其妻,对夫的惩罚却轻得多,《大明律·刑律三·斗殴》的“殴祖父母、父母”条曰:“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77]而“妻妾殴夫”条曰:“若(婿)殴妻之父母者,杖一百;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罪一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78]《大明律·刑律四·骂詈》的“骂祖父母、父母”条曰:“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绞。”[79]而“妻妾骂夫期亲尊长”条曰:“若(婿)骂妻之父母者,杖六十。”[80]再如历代法律对于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均从重处刑,《大明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81]清朝沿袭明朝的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82]。从律文看,有夫之妇比无夫之妇的通奸罪处罚更重。可是有妇之夫通奸,法律上并没有比照无妇之夫与人通奸加重处罚。居丧奸中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犯奸者,各加凡奸罪二等”[83]。此处律文表明在丈夫丧期内,妻子犯奸要重罚,但并未见到规定在妻子丧期内,丈夫犯奸要受到怎样的处罚。这种同罪异罚现象体现了夫妻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和夫权对女性的严重束缚和奴役。
社会性别(gender)不同于生理性别(sex),它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男权社会通过意识形态(宗法礼教)的强化,将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差异进行夸大,从而以男权文化的性别标准对性别不断进行界定与评判[84]。我国古代社会的性别制度,以“阴阳刚柔”观念作为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论根基,制造出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标准。随着这种性别标准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法律之中,并投影到冥律规范。可能由于宝卷的受众中女性占比非常高,游冥宝卷主动突出和强调了那些专门针对女性的地狱刑罚,和阳世法律对女性的规训与惩罚相互配合,以此收到更好的教化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冥律规范对建构、强化社会性别角色也有重要作用,它和阳世法律合谋造就了社会性别,以看似彻底的公正掩盖了性别歧视,欺骗了女性却又获得女性的认可,成为塑造“理想”女性、巩固和强化父权制的工具之一。
四、结语
恩格斯曾说:“即使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85]幽冥法文化作为阳世法律、道德标准、价值判断的投影,反映了人们无力改变现实的种种无奈,寄托着时人对公平正义的理想期待。
对于长久生活在较为封闭乡村的庶民百姓来说,王法似乎太过遥远,也太过抽象与繁琐,接受度相当有限。诚如明代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九云:“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86]清人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亦云:“盖庸人妇稚,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87]教化乡愚妇孺,通俗化、宗教化的善恶报应故事可能比王法与道德的教条规训来得更有效。因为意识形态的教化并不仅仅是庙堂之内儒家知识分子的主动承当,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念也难免意识形态的渗透,包括宝卷在内的各类通俗文艺对富有平民化色彩的冥律的积极宣扬,在一定程度上就履行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甚至发挥着王法所不及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社会控制作用的大众文学也是一种“法律”。透过冥律的宣扬和幽冥世界正义观的感召,对于善恶报应故事中那些罪名的认知,构成了底层庶民社会的法律常识,也成为维持国家法秩序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游冥宝卷,作为幽冥法文化的重要载体保留着丰富的冥律材料,并融入了俗世律令精神,在这里小民百姓用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表达了对于法律的思考与感情。在游冥宝卷的宣讲中,听卷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道德教化和“普法”宣传,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犯罪的效果,对庶民的法律观念产生深刻影响。时至今日,游冥宝卷依然是我们从“小传统”的角度窥探古人法律意识和法律心态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