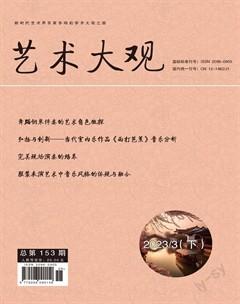浅论陈洪绶的艺术特征及影响
胡波


摘 要:本文关注明代晚期艺术家陈洪绶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之间的对比,勾勒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局限于從时间脉络上去观察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从形式表现、情感表达等方面去观察。同时探讨陈洪绶的艺术思想对清代扬州八怪的影响,从扬州八怪之“怪”和批判意识等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陈洪绶;绘画;比较;影响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3)09-00-03
一、陈洪绶的比较研究
从关于陈洪绶和西方艺术大师的比较研究来看,如《陈洪绶与伦勃朗艺术人格心理探究与比较》《陈洪绶与伦勃朗的艺术人格比较》《在陈洪绶与委拉斯贵支的画作之后——关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中国与西班牙人物绘画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和时代》《伦勃朗和陈洪绶——中西版画比较的一个视点》《中西传统木版画比较研究导论——以丢勒和陈洪绶个案研究为例》等文章,出现了将陈洪绶的绘画和西方艺术进行比较的倾向。
将这些研究进行规律性的发掘和归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流于讲述陈洪绶和相对应大师的生平、艺术成就、创作类型(如版画)、个性、社会环境等。我们跳出这些研究思路的时候就会发现,以上学者选取的西方艺术家要么在时间维度上有着某些重叠或者说时间的间隔不是很大,且艺术创作的类型类似,或者在讲述两者之间的创作背景。比如,陈洪绶生活的年代是1598年到1652年之间,荷兰画派伦勃朗生活的年代是1606年到1669年。这里并不是想批评这种思路,但这篇文章将提供另外一种思路来看待陈洪绶的艺术特色。
二、陈洪绶和蒙克等的对比
在笔者《陈洪绶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相似之处》一文的第三部分,讲述了陈洪绶绘画的表现形式和思想主张,那部分的内容只是介绍了陈洪绶绘画中的情感意识、变形和批判意识,并将陈洪绶和西方某些现代大师进行了简单的比较说明。这里笔者将提出陈洪绶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中蒙克等创作相似之处。
我们以陈洪绶和蒙克的绘画为例进行比较分析。陈洪绶的《自画像》(见图1)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衣带宽松,眉宇间透着一股苦闷、不如意、焦虑,身旁一个坛子,唯一可以确定其文人身份的是其用来枕胳膊的装饰精美的书。这里的陈洪绶无疑将自己生活中郁闷、痛苦的一面清晰地展示了出来,同时,让我们对比一下蒙克的《呐喊》中人物的焦虑、痛苦、迷茫。
蒙克创作《呐喊》这幅作品的时间是198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的欧洲各国因为军备竞赛,导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不平衡和倾斜。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精神麻木、恐惧,加之蒙克早年父母双亡和自身疾病缠身的经历,《呐喊》就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出来了。在笔者《陈洪绶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相似之处》一文的第一部分提到过陈洪绶的生平经历,他和蒙克的曲折经历对他俩的画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我们同时看到这两幅作品的时候的,一定可以明晰地看到,这种对人的潜意识的形象的描绘。只不过陈洪绶的作品看上去更多的是苦闷,不像蒙克更多表现的是恐惧意识。艺术家的思想是其所创作作品的灵魂所在,他在人物画和版画上的情感表达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而陈洪绶的这种反传统的绘画思想表现形式(已经区别于前代表现隐逸、生活纪实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想是何其相似,画面人物的茫然、木讷、无意识、内心的涌动、悲哀、恐惧都跃然画上。这好像很好地展示了西方表现美学中克罗齐、伯格森、科林伍德的思想,如直觉即表现、心理时间、情感通过艺术的语言形式得以清晰的表达。而陈洪绶的《自画像》等作品恰好体现了这些美学思想,即张扬情感的表达。
也许这里会有人说这种比较还没有那种有一条时间线索的牵引来得清晰和明确。从画面的颜色来看,就完全不在一个比较层面上,且不说高更曾指导保罗·塞吕西耶和蒙克等表现主义艺术家的色彩,就单论以色彩闻名的野兽派已和陈洪绶淡雅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技法上,蒙克等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创作大多是平涂,或许这个和油画刷颜料有关。但明显与陈洪绶这种以毛笔勾勒线条和轮廓的创作有着明显区别。这似乎完全对应了沃尔夫林《艺术史的基本原理》中“线描与图绘”这样一种对立的原理。那还有什么可比性,因为要有比较就必然要有联系,不然毫无意义。
这种思路岂不是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吗?其实不然,这三个例子和陈洪绶的绘画有着内在的联系:即他们都注重对人物内心的表现。西方后印象派开始的艺术就一直处在对简单模仿自然、再现表达和传统艺术表现的对立面,强调对自身内在表达,注重自我情绪。精英、小众、反传统、打破形式边界、思想意识、内心世界、注重揭示意识的深层体验是西方现代艺术的几个关键词。陈洪绶这种知识文人阶层,在明末社会还属于道德精英行列;画面上怪诞的变形是反传统的证明,不拘一格的绘画形式在不停地打破自宋以来对自然的模仿,即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世界”的创造。陈洪绶将丧妻、仕途曲折和对政治腐败的无奈,以及自己内心的痛苦都挥洒在画面上了。
也许又会有人反驳,陈洪绶的文人身份和个人情绪的表达,在中国早期绘画就有了。毕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位创作者内心的世界肯定是不同的。詹景凤和董其昌就曾论述过,文人画早在唐代王维时期就已经出现,士大夫阶层出现在更早的魏晋时代。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陈洪绶作为分析这种现代性的标准?为什么不把这种选择提前到魏晋、唐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这里就不得说到明末市民阶层对职业画家的影响(陈洪绶为打着文人身份标签的职业画家)。市民阶层和商品经济的萌芽,让这些职业画家有着自己的市场去表现本我的东西,故情绪的表达就有了微妙的变化。至于与前代艺术家的不同在陈洪绶的情感意识部分已有论述。
三、陈洪绶对“扬州八怪”的影响
艺术流派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些思想倾向、创作技法、艺术主张、创作风格等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艺术家,进而形成的艺术家群体。笔者的这种提法可能会打破人们常规对艺术流派在时间上的界定和划分,但之所以会这样看待扬州八怪和陈洪绶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市民阶层和赞助人的影响
时间推移到扬州八怪時期正好是清代中期乾隆年间,此时的商品交易以广州十三行和扬州盐商为代表。当时虽有地方性的战争和灾害发生,但扬州一直保持着繁华。经济的繁荣,促使市民阶层的滋生和发展,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他们就成了扬州职业画家作品的主要购买者,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职业画家就是依托这样的环境进行创作的。此时扬州八怪的创作题材明显趋于平民化。
扬州商人这种士人和商人相结合的身份,让他们将绘画本身看成是文化身份的追求。“像‘四君子(梅、兰、竹、菊)这样的经典文化主题成为创作的题材。与此同时,这些主题的象征意义开始被冲淡或是曲解。金农创作的一幅梅枝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农的商人朋友江春新娶了一名小妾,金农遂作此图以示祝贺。”[1]扬州商人和市民一方面接受士人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创作持开放态度。扬州职业画家此时的创作不再以自我的修养为标准,而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的表现,不需要与古代绘画大师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也就给了他们自我表达的空间。以扬州八怪为例,他们的身份还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多年科考,仕途不顺;二是厌恶官场,以绘画为生;三是纯粹的职业画家。在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像金农送给江春的梅枝图和罗聘这样的《鬼趣图》(见图3)来表达自我情感和关注点。
(二)“扬州八怪”之“怪”的分析
有些学者在书写扬州八怪的绘画风格时,将影响扬州八怪的主要人物列为:徐渭、高其佩、石涛;也有学者在评价扬州八怪的艺术成就时归纳为师法自然和具有创新精神。这两者并不冲突,石涛的“师我法,用我法”等主张都是强调在学习古人的同时,不要拘泥于前人的条条框框,要有自己的创新。这里可以用张躁的“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来解释,就是在模仿外界事物,客观描绘的同时要有自己的加工。扬州八怪的创作需要结合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一方面,统治阶级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如此时心学盛行,却引起统治者的“关注”;另一方面,当时主流艺术的保守,以清初四王为代表的主流艺术一直影响颇大,导致人们寻求个性解放,将自我态度表现在画面上。以罗聘的《鬼趣图》为例,人物刻画极度调侃,两只青蛙一样的手掌,造型扭曲怪异。李方膺的钟馗和小鬼这一部分更是讽刺意味强烈,小鬼们“谄媚”地对待钟馗。“从他画中描绘的那些脑满肠肥的胖鬼、戴红樱帽衣不蔽体的穷鬼、近女色的富鬼等形象,可知系画家借虚幻之鬼以讽喻社会现实”[2]。罗聘没有被“盛世太平”的表象所迷惑,清醒地看到了“太平”背后的种种黑暗,画面中变形的人物是作者内心形象的表现刻画。
(三)批判意识
郑板桥画竹题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直接表露了艺术家的心声。由于市民阶层和赞助人的影响,扬州八怪的创作不需要对艺术本身的传统负责,不再以文人的自娱自乐和自我修养为创作的宗旨,更多的用手中的画笔表现对生活的看法;更多地体现了对平民百姓的关注,揭露社会的丑恶。
他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下层,描绘百姓的疾苦和生活。如黄慎的《渔翁父图》,衣衫褴褛的老人,被生活压弯了身躯,表现了对渔民凄苦的同情。“骊山在画幅上公开写‘与隶凶如马踢人等,所有这些均表现画家对于黑暗社会种种不公平现象的不满情绪。”[3]这些材料均表明扬州八怪在绘画创作中对社会的批判和自我立场的表达。
而扬州八怪的这些特色陈洪绶身上也有,这也是为什么说扬州八怪是陈洪绶的现代精神的延续。而出于这样一种内在“结构”性的延续,故选择陈洪绶这个“点”作为比较的起点。
参考文献:
[1]李铸晋,石莉,译.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2]薄松年,陈少丰,张同霞,林通雁,编著.中国美术史教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3]王健.浅论“扬州八怪”的艺术特点[D].中央美术学院,2012.
——陈洪绶书画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