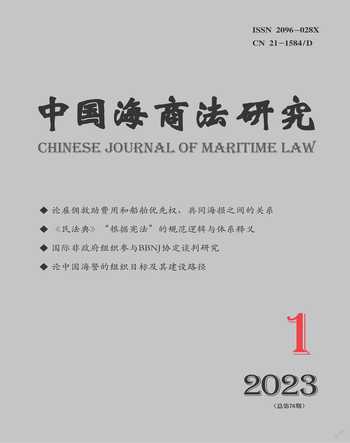《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界定与适用
摘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将其未予规定的事项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一般国际法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各国也较少直接将其作为海洋确权的法律依据,导致中国以此构建海洋权利主张存在难度。对一般国际法的界定可将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将其归纳为包含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与国内法普遍適用的规则,以及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强行法,在国际条约、法院规约、司法实践及海洋领域广泛运用。一般国际法实质有效且有法律约束力,对于规则与权利的确认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可运用一般国际法构建海洋权利主张,从诚实信用、有约必守、禁止反言等一般法律原则角度构建南海历史性权利,以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满足国家海洋维权的现实需求,促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与海洋法新发展。
关键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般国际法;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强行法;历史性权利;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3)01-0058-11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reamb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ZHANG Qiyue
(Institut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As is provided in the preamb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 that “matters not regulated by this Convention continue to be governed by the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e concept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s rarely discussed during the years of application of UNCLOS and is rarely used as the legal basis for determining maritime rights by countries, which result in difficulty for China to claim maritime rights.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categorie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discussion in the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summarize it a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general regulation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nd appli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and jus cogens with higher legal effect.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s universally applied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tatutes of Courts and judicial practices, and is highly recognized in the law of the sea regime.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has practical effect with legally binding force and has significant value in the confirmation of rules and rights. China has the right to reasonably utilize the concept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for maritime claims, build historic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such as good faith, pacta sunt servanda and estoppel, and provide legal basis for the regime of continental states outlying archipelagos with emerg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so as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ountries to safeguard their maritime rights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UNCLOS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the sea.
Key words:UNCLOS;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jus cogens; historic rights; the regime of continental states outlying archipelag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通过以来,在海洋领域系统地建立了规则与秩序,推动了海洋法规则的整合与法典化发展,也促进了海洋的和平使用和对海洋资源公平有效地利用,实现了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和资源保护,为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约》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在后续适用中逐渐解决。《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应当如何界定与适用,直接关系到中国海洋权利的维护。尽管序言中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当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从字面上对《公约》未涉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但无论是条文本身还是评注,都未能对一般国际法的含义和范畴作出明确解释,甚至有个别国家曲解这一规则,以此作为批驳中国海洋权利主张的依据,影响海洋法规则的发展与国际舆论的走向;国际社会也存在将《公约》条文视为全部海洋法规则,忽视一般国际法作为海洋领域适用的重要依据的倾向,限缩了一般国际法的适用空间,更无益于海洋法规则在解释与适用中的动态化发展。为一般国际法正本清源,明确其在国际实践特别是海洋领域的运用,将为海洋法规则正确的解释适用与中国海洋权利的维护发挥出更多积极作用。
一、一般国际法的范畴具有综合性与发展性
对于一般国际法的界定可以在国际法渊源范畴内讨论。尽管一般国际法并未在《国际法院规约》(简称《规约》)第38条第1款中被作为特定一类的法律渊源,但一般国际法作为经常被使用却很少被明确定义的概念,可以视为包含多重渊源的综合性概念,不仅因其包含多种法律渊源而具有综合性,其本身也有发展性和流动性。
(一)一般国际法的范畴具有综合性
国际法学界对于一般国际法的界定是发展变化的。20世纪主流观点认为,一般国际法主要或仅指习惯国际法,【Grigory Tunkin, Is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Customary Law Onl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534, p.535(1993).】原因在于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相似,具有广泛性、一般性等特征,通过法律拟制和默示同意达到普遍适用的效果,二者均属于具有普遍效力的规则。【参见禾木:《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兼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的区别》,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68页。】但这一观点无法回避二者的区别,即习惯国际法仅能通过对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判断将“持续的反对者”排除适用,而对一般国际法的反对意见却很难获取和收集。由此,将一般国际法等同于习惯国际法具有片面性,二者差距较大,应当分别探讨。国际法委员会从未将“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作为同义词使用。
与之并行的另一观点是,一般国际法被视为《规约》第38条第1款(c)项中的“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原因在于一般法律原则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成为所有国家能适用的法律基础,【Charles Kotuby,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International Due Process, and the Modern Rol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23:411, p.417(2013).】具有相当的广泛性、高度认可性和一致性。【M. Cherif Bassiouni,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768, p.780(1990).】尽管一般法律原则不包含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但能体现出各国共同认可与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与一般国际法原则存在相似性。
笔者更倾向于选取国际法委员会就国际法碎片化提出的报告中关于一般国际法界定的规范。报告认为,一般国际法明确指习惯国际法、被文明国家所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用来填补特别法体系的空缺,并为相关法律的适用提供解释。一般国际法与特殊国际法相对应,而后者往往指协定国际法即成文法,通常包含国际条约、双多边协定。一般国际法可以理解为国际公约、条约、协定形式之外的国际法规则,范畴较为广泛。
这一观点也得到国际法院主席罗莎琳·希金斯(Rosalyn Higgins)的证实,即一般国际法是指通过国家实践证明的习惯国际法,也包括被普遍接受的一般性原则。普热梅斯瓦夫·萨加内克(Przemysaw Saganek)教授也注意到,有观点认为一般国际法在主要渊源即习惯国际法的基础上也包括一般法律原则,且部分一般国际法不具有习惯法的性质。【Przemyslaw Saganek, The Sources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Recent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9:37, p.38, 47(2019).】德雷·特拉迪(Dire Tladi)教授在关于强行法的识别问题的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中提出,某项规则要成为强行法,必须要成为一般国际法,【Dire Tladi, First Report on Jus Cogens, United Nations Digital Library (Mar. 7, 2016),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30720?ln=en.】由此确认强行法与一般国际法存在重叠。甚至是少数联大决议、未生效的国际公约草案、其他不明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文件、国际会议报告、政策声明,以及国内法规则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属于一般国际法范畴。【Rüdiger Wolfrum,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s, Rules and Standards),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Dec. 30, 2010), https://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mpeipro/e3544.013.3544/law-mpeipro-e3544.】綜上,一般国际法作为与协定国际法相对应的概念,明确包含习惯国际法这一最主要的要素,也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参见赵海乐:《一般国际法在“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中的作用探析》,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21年第2期,第99页。】及一般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立法和实践中衍生出的原则以及处于法律形成进程中的原则。【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gainst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United Nations (Jul. 18, 2006), https://legal.un.org/ilc/documentation/english/a_cn4_l702.pdf.】由此,笔者更倾向于将一般国际法作为包含多重渊源的复合型概念的表达。
(二)一般国际法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一般国际法的范畴并非闭合,而是具有开放性与发展性。首先,一般国际法包含了《规约》第38条第1款中的多重国际法渊源,具有综合性;再加上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变化,一般国际法能够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跟进发展。
其次,多种国际法渊源也有路径和可能性转化为一般国际法。不同法律渊源的规则能够反映出普遍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从中提炼出的共性有可能成为一般国际法规则或原则。这一过程通常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及司法机构的判断来实现。例如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就明确条约规则在符合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可以转化为一般国际法规则,【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eb. 20, 1999),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51/051-19690220-JUD-01-00-EN.pdf.】反映出不同法律渊源之间具有开放性与发展性的特征。司法机构对一般国际法的判断,也能起到法律解释的作用。
相反,一般国际法也有路径转化为其他法律渊源,如更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一般国际法作为反映多国共识的概括性规范,可以体现在国际公约和条约中,既可以将其作为兜底性条款,起到补充适用的作用,也可以在国际条约的文本表述中纳入一般国际法,作为制衡性力量,通过要求成文法规则不得与之相违背,从而起到对成文法的制约作用。
最后,一般国际法与其他类别的法律渊源本身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国家对于规则是明示还是拟制的同意。这种理解实际上突破了《规约》第38条不同法律渊源之间的界限与条条框框,打破了多重渊源之间分离与割裂的壁垒。【Michael Wood, First Report on Formation and Evidenc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United Nations
(May 17, 2013), https://legal.un.org/ilc/documentation/english/a_cn4_663.pdf.】从整体角度理解国际法渊源,在相互交织与重合的渊源之间提炼出共性,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一般国际法,用发展和流动的视角看待不同渊源之间的转化,打破了不同主体之间基于不同利益、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文化背景而固有的鸿沟,形成并强化了具有共识性质的、国际社会整体认可的规范和意识。甚至有学者认为,《规约》第38条并不意在穷尽国际法院所能适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类型,其主要立法目的在于为法庭审理案件提供指导性参考。【Gerald G. Fitzmaurice, Som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Form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Routledge, 1958, p.77.】
(三)一般国际法的概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般国际法在普遍意义上包含规则和原则两种形式,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明确性,后者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第一,一般国际法规则作为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则,能为各主体创设权利和义务,实际有效且具有法律约束力。判断一般国际法规则的约束力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方面着手。在形式方面,部分一般国际法规则能够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明确且具体的條约规则。这一转化路径已经被国际法院所认可。【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Concerning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70/070-19841126-JUD-01-00-EN.pdf.】各国以签署条约的方式表示同意,达成的规则对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有约必守”“禁止反言”的原则,各主体应当自觉遵守规则。在实质方面,如果因违反规则而招致法律后果,违反者应当承担责任。
第二,一般国际法原则尚未以成文法形式体现出来,但包含着从各类法律渊源中提炼出的共性,能反映出各国的共识,体现出各主体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共同的意愿,经由国际社会合意达成,具有“拟制的同意”的法律效果,相当于“国际社会的认可”,【参见刘晨虹:《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之“国际习惯法”说新解》,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9期,第3页。】兼具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约束力。主权国家不能以违背国家同意为由拒绝遵守一般国际法原则。甚至也有学者认为,一般国际法原则将成为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尽管这一论断可能具有夸张的成分,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三,一般国际法也包括部分强制性规则即强行法。【Cestmir Cepelka,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 Outer Space, Journal of Air Law and Commerce, Vol.36:30, p.46(1970).】强行法指不得被国家通过协议有所减损或排除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具有不容违反、不能减损、不能更改的特点,【United Na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1961), United Nations,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9_1_1961.pdf.】相比于习惯法与条约法有优先性,【Elihu Lauterpa,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ep. 13, 1993),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91/091-19930913-ORD-01-05-EN.pdf.】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位阶。与强行法冲突的条约或习惯法规则均属无效。有观点认为,强行法体现出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意,属于一般国际法的一种,反映出一般国际法与强行法存在重叠,各国不能违背强行法义务。【Dominic N. Dagbanja, The Conflict of Legal Norms and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owards the Constitutional-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mperatives Theory, Transnational Legal Theory, Vol.6:518, p.534, 537(2015).】
第四,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能起到法律解释的作用,促进规则实现既定的目标和宗旨,具有独特的功能性价值。一般国际法在推动相关规则解释的过程中,可以增强法律适用的能力,实现既定的法律目标和宗旨,对既有的成文法和其他类别的法律渊源予以补充。综上,无论一般国际法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存在都具有现实价值,都能产生事实上的法律约束力和法律效果。这也成为一般国际法能在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各领域广泛运用的原因。
二、一般国际法在多个领域有广泛的运用
(一)一般国际法对条约起到补充或制衡作用
探讨一般国际法的范畴不仅是国际法基本理论的问题,也能促进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在条约法领域,1964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第3款使用了一般国际法概念,用以论证“使馆馆舍不得充作与本公约或一般国际法之其他规则、或派遣国与接受国间有效之特别协定所规定之使馆职务不相符合之用途”,将一般国际法与该公约并行适用、补充论证。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United Na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 United Nations, https://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将一般国际法作为与条约相互制衡的力量。在这两份公约中,一般国际法成为检验公约规则是否符合更普遍的国际法规范的手段,也作为对公约未尽事项的兜底性规定。【参见张乃根:《中国对南海诸岛屿领土主权的一般国际法依据》,载《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23页。】由此,一般国际法在条约中普遍适用,但其用途和思路存在不同。
(二)一般国际法成为司法机构判决的法律依據
20世纪初,当一般国际法的概念尚未完全形成时,类似的表述就普遍在各类法院规约中广泛运用,作为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1907年《关于建立中美洲法院公约》第21条规定,在裁决各类事实时,中美洲法院应当以自由意志为据进行管理,依照国际法原则,考虑到法律要点。【Conven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American Court of Justice (1907), Dipublico.org International Law (Sep. 26, 2010), https://english.dipublico.org/182/convention-for-the-establishment-of-a-central-american-court-of-justice-1907.】1907年《关于建立国际捕获法院公约》第7条第1款和第2款也将公平和衡平的一般性规则作为法律依据。【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Prize Court, Springer,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2F978-94-015-7601-7_17.】其中“国际法原则”与“公平和衡平的一般性规则”均作为一般国际法的雏形。
此后,一般国际法的各类表现形式,如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与规则纷纷在法院规约中得到体现,既包括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将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作为重要的国际法渊源,【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en/statute.】也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1条第1款第3项表明,可适用法涵盖“从通常对该犯罪行使管辖权的国家的国内法中得出的一般法律原则,但这些原则不得违反本规约、国际法和国际承认的规范和标准”。【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Jul. 17, 1998), https://www.icc-cpi.int/sites/default/files/RS-Eng.pdf.】除此之外,2004年《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关于建立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议定书》第61条将“被非洲国家普遍认同的一般法律规则”作为可适用法,将一般法律规则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广泛运用习惯国际法与一般法律原则,作为规则解释的路径。【James Cameron & Kevin R. Gray,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50:248, p.249(2001).】
综上,国际司法机构通过法院规约、组织的内部议事规则,将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一般国际法规则等概念纳入法律适用范围,【Mathias Forteau,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rocedural Law,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Jan. 30, 2018), https://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mpeipro/e3544.013.3544/law-mpeipro-e3544.】赋予其开放性解释,充分体现出各国已达成共识的一般法律规则和原则在司法机构中的广泛适用。
(三)一般国际法作为规则解释与适用的工具
一般国际法作为在国际法院、区域法院、国内法院中普遍适用的工具,既能为司法机构的法律适用与解释提供依据,也能在司法实践中推动规则的渐进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法律适用价值。
早在1924年“希腊诉英国马弗罗玛提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中,国际法院就适用一般国际法确定义务,认为这种对义务确认的方式不能被排除在外。【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The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A/A_02/06_Mavrommatis_en_Palestine_Arret.pdf.】在1949年“科孚海峽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某些一般性和被广泛认可的原则,即对人道和人性的初步思考,在和平时期甚至比在战争时期更加严格,【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Corfu Channel Cas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001-19490409-JUD-01-00-EN.pdf.】表明了一般国际法原则已得到国际法院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类似的观点在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中再次得以确认。国际法院认为,美国政府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确保遵守《日内瓦公约》第1条规则。这一义务不仅源自于公约本身,也源自于人道法的一般性原则。对有关国家使用武力的情形不仅在多边条约中予以规定,也在一般国际法中有所体现。美国不仅应遵守公约义务,也应遵守人道法的一般性原则。【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Concerning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70/070-19841126-JUD-01-00-EN.pdf.】
一般国际法也被用来解释特定的术语和规范。在1997年“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工程案”中,国际法院将一般国际法作为理解“国家必要性”和为不法行为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依据。【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Concerning the Gabikovo-Nagymaros Project(Hungary/Slovaki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ep. 25, 1997),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92/092-19970925-JUD-01-00-EN.pdf.】
在1999年“‘塞加号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几内亚主张“国家必要性”的诉求也同样运用一般国际法证成并解释其行为的合法性。【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he M/V “Saiga” (No. 2) Case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Jul.1, 1999),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published/C2-J-1_Jul_99.pdf.】在2003年“石油平台案”中,国际法院法官库伊曼斯(Judge Kooijmans)的个人意见认为,一般国际法是用以解释具体条约规则不可或缺的标准。为判断特定行为是否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则和自卫权的习惯法,确定是否应当采取特定行动保护必要的安全利益,界定“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必要性”“自卫权”的概念,将不可避免地诉诸一般国际法。【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Concerning Oil Platform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ov. 6, 2003),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90/090-20031106-JUD-01-00-EN.pdf.】
综上,一般国际法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价值。首先,当确定某个问题是否属于司法机构管辖时,法院或法庭能依据一般国际法作出判断。其次,某项行为或义务可能同时受条约和一般国际法调整。国际法院在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则时,通常也将一般国际法作为前提。二者相互印证、共同适用、密不可分。再次,当条约与成文法规则难以覆盖所有情形时,一般国际法能补充适用。最后,一般国际法能对规则的适用予以解释。一般国际法在司法实践中被反复运用和强调,权威性极高。在司法实践中援引一般国际法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一般国际法的运用也反映出司法机构对规则解释和适用的能力。
(四)一般国际法成为海洋领域重要的法律依据
一般国际法时常被用于海洋法案件审理中,作为判决和裁决的重要法律依据。在1951年“英国诉挪威渔业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挪威的海洋划界体系适用一般国际法;认可挪威海岸线适用直线基线,将其作为“一般国际法在特定案件中的适用”。【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5/005-19511218-JUD-01-00-EN.pdf.】在“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中,国际法院确认,该案涉及的关于大陆架的实践,包括不得阻碍铺设或维护海底电缆和管道,不得干涉航行自由和捕鱼自由等,均属于习惯国际法范畴,也是一般海洋法的原则和规则,很大程度上在1958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简称《大陆架公约》)前形成。这些权利与该公约中规定的大陆架权利具有同等的效力。尽管这些权利后续也在《大陆架公约》中有所体现,但《大陆架公约》的制定并不意在宣布或确认权利的存在。已经存在的大陆架权利也不会因公约的适用而受到减损。这一案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确认了海洋领域的一般国际法切实有效,也明确了后续制定的成文法规则不能阻碍先行规则和义务的适用,为中国行使《公约》制定前已经确认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1999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塞加号案”中,法庭认为几内亚应当履行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义务,其中不仅包括《公约》规定的义务,也包括一般国际法赋予的义务。在论证“用尽当地救济”的概念时,法庭参考并适用了一般国际法,也援引了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2条,认为圣文森特的主张并不满足“用尽当地救济”的前提条件。
在2004年“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划界案”中,附件七仲裁庭将“磋商的义务”理解为在一般国际法下建立的义务,这项义务并不要求各方持续进行毫无成果的磋商。在讨论“单边提起仲裁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时,法庭首先判断单边提起仲裁是否违反《公约》第300条关于“诚意和滥用权利”的规定与是否构成对一般国际法的滥用。仲裁庭强调,既要考虑与双方有关的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中的规则,也要考虑一般国际法原则,以及国际法庭和仲裁庭判決或裁决的贡献,也包括公法学家对这些法律规则的理解。【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pr. 11, 2006),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116.】
一般国际法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海洋法案件中,也被国际海洋法法庭赋予更重要的地位,增强国际社会对一般国际法的理解,也丰富了海洋法的内涵。【Michael Wood,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2:351, p.351(2007).】国际法院主席罗莎琳·希金斯(Rosalyn Higgins)在2006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成立十周年的讲话中称,法庭处理海洋领域的法律问题,但其自身也处于一般国际法范畴内,在专门的条约机制中应当遵守一般国际法。【Rosalyn Higgins, Statement of Judge Rosalyn Higgin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Tribunal,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Sep. 29, 2006),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lendar_of_events/10_anniversary/Statement_10_anniversary_Higgins.pdf.】法庭主席沃尔弗鲁姆(Rüdiger Wolfrum)法官也回顾了法庭对一般国际法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一般国际法与航行自由、船舶和船员的迅速释放、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核设施的调试和放射性物质的移动、岛礁建设活动、渔业和执法活动中使用武力、紧追权的行使、船舶和船旗国的关系等方面。【Rüdiger Wolfrum, Statement of Judge Rüdiger Wolfrum,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remony to Commemorate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Tribunal,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Sep. 29, 2006),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statements_of_president/wolfrum/tenth_anniversary_290906_eng.pdf.pdf.】此外,一般国际法也体现在《公约》条文中。法庭在“‘塞加号案”中也明确,《公约》第91条关于“船舶的国籍”的规定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一般国际法法典化,直接表明《公约》与一般国际法间存在重叠。综上,在海洋法司法实践与法庭发展中,一般国际法的广泛适用,为推动国际法和海洋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国际法与一般法律原则成为论证包括传统捕鱼权在内的历史性权利的重要法律依据。在202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侵犯加勒比海的主权和海洋空间案”中,薛捍勤法官在论及哥伦比亚是否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传统捕鱼权的个人声明中表示,当公约规则并未明确表达包含传统捕鱼权时,一般国际法将持续适用,作为管理这些事务的依据。【XUE Hanqin, Declaration of Judge Xu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pr. 21, 2022),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55/155-20220421-JUD-01-06-EN.pdf.】类似地,在2009年“苏丹与南苏丹阿卜耶伊地区划界案”中,裁决认为,根据一般法律原则,当缺乏明确相反的协议时,传统权利通常被认为不受任何领土划界的影响。【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Matter of an Arbitration Before a Tribunal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and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on Delimiting Abyei Area,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Jul. 22, 2009),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8820.】由此,一般国际法与一般法律原则成为证明历史性权利与传统捕鱼权的法律依据,在海洋领域广泛运用。
三、《公约》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与《公约》规则平等适用
(一)一般国际法的法律效力不低于《公约》规则
第一,一般国际法包含《规约》第38条第1款中的多重法律渊源,其法律效力不低于作为条约法的《公约》。如前所述,一般国际法作为包括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强行法规范、国际和国内普遍认可的法律规则和原則,以及反映部分国际条约规则的综合性概念,几乎包括《规约》第38条第1款中各类别的法律渊源。除强制性规范具有更高的效力位阶外,第(a)(b)(c)项中的国际公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具有相同的效力位阶,均作为《规约》第38条中的主要法律渊源。由此,一般国际法的效力至少不低于《公约》规则。
第二,《公约》虽然以条约形式存在,但条文也包括多重法律渊源,这些渊源的效力与条约处于同等位阶。首先,《公约》作为习惯国际法的法典化,其主体由习惯国际法构成。即使确有少量国家并非《公约》缔约国,但只要这些国家不以“持续的反对者”姿态出现,《公约》就对这些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根据法庭对“‘塞加号案”的论述,《公约》条文与一般国际法存在部分重叠。再加上《公约》序言将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表明尽管二者分属不同领域,但未存在冲突对立、相互割裂,反而补充适用、密不可分。
最后,一般国际法作为《公约》的补充,尽管存在“特殊法优先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顺序,但这一表述并不是判断法律渊源之间位阶高低与效力大小的依据,各国应当同时遵守《公约》与一般国际法,况且二者并不存在冲突与对立,更不存在一般国际法影响、阻碍、减损《公约》实施的情形。对于一般国际法与特殊国际法的区分本来就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分标准。综上,一般国际法的效力和地位并不低于《公约》规则。
(二)《公约》规则难以解决海洋领域所有问题
第一,《公约》不能将所有海洋法问题纳入条文的调整范围内。尽管《公约》系统地对海洋法规则作出解释,被誉为“海洋法宪章”,但并不意味着《公约》能解决与海洋有关的一切问题。即使存在未被《公约》条文确认的权利与未被《公约》纳入调整范围的事项,也不意味着该权利主张不具有合法性。此外,《公约》不能减损在其之前就已形成的权利并否认长期形成的实践。
第二,《公约》的磋商方式决定了其自身有局限性。《公约》在磋商中面临显著的政治和法律困难。各国以利益集团的方式开展磋商,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从而形成“一揽子协定”,导致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不得不在磋商中作出妥协。例如群岛国家为促进群岛制度尽快通过,放弃与拥有远洋群岛的大陆国家的合作,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后期仅将群岛基线和水域制度应用于群岛国,成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未被纳入《公约》范畴的原因。这一磋商方式导致《公约》自始存在局限性。
第三,尽管各国在磋商中试图对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予以调整,但随着国家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海洋领域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原有的《公约》体系难以涵盖其适用期间及未来海洋领域存在的新问题,难以反映和应对海洋法领域的新变化。海洋规则的法典化和渐进式发展也伴随着碎片化和不成体系等问题,这也是当今国际法各领域存在的普遍趋势和共同特点。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国际法碎片化的报告中也指出,没有任何体系能够自给自足。无论是《公约》本身还是整个海洋法律体系,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应当通过不断发展来实现海洋法体系不断完善的需求。
(三)一般国际法成为《公约》规则的补充适用
第一,当《公约》规则缺失时,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能补充提供法律依据。一般国际法的种类和范围丰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在法律适用中能起到兜底的作用。更为常见的是,某项行为或义务可能同时从《公约》和一般国际法中获得法律依据,受到二者共同的约束。
第二,一般国际法能为海洋领域的渐进式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海洋事务是不断演进的。无论是《公约》的调整与修改,还是新规则的磋商与制定,抑或是习惯国际法的演进,都需要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也都存在一定难度。再加上法律本身存在滞后性的特点,法律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与国际实践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导致规则与实践之间存在永恒的“时间差”。对此,一般国际法有能力为各国在未来解决海洋法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一般国际法作为《公约》规则的解释手段与法律解释的工具,通過对条文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使《公约》成为一项“活的文件”,满足自身不断成长的需要,适应国际实践的发展趋势。《公约》中的概念如适当顾及、诚实与善意,需要诉诸一般国际法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此外,也不能排除《公约》规则与一般国际法之间存在“沟壑”是立法者故意为之。这一立法技巧使海洋法规则的解释适用空间增大,以此满足实践发展变化的需要。
(四)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实质有效
第一,《公约》的通过与缔结是成员国对《公约》整体的确认,自然也包括对序言部分达成的合意。序言作为理解条约规则、领悟条约精神、实现《公约》目标和宗旨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法律效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强调,“条约的解释应当结合上下文并连同其序言和附件在内”。条约的通过与缔结是“国家同意”的体现,表明国家自愿受到《公约》规则的约束。根据“有约必守”“禁止反言”【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45/045-19620615-JUD-01-00-EN.pdf.】以及“诚实与善意”【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uclear Test Case (Australia v. Franc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58/058-19741220-JUD-01-00-EN.pdf.】等原则,各国有义务主动遵守序言规则,实现其目的和宗旨。
第二,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为各国明确创设了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违反一般国际法的主体应当承担责任。例如,《公约》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各国应当以互相谅解与合作的精神解决争端,由此对各国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此类争端。因此,《公约》的序言具有法律效力与约束力。
第三,《公约》尊重和保障他国依据其他国际法渊源所获得的权利。《公约》第311条在处理“同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中明确:“本公约应不改变各缔约国根据与本公约相符合的其他条约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但以不影响其他缔约国根据本公约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为限。”《公约》对于其他国际法渊源持尊重、开放、包容的态度,不影响、阻碍、减损其他条约的适用。由此,《公约》的内在逻辑是保持不同法律渊源之间的平等与协调,使其各自能够发挥预期作用。
四、运用一般国际法论证中国海洋权利主张的途径
(一)中国部分海洋权利主张并未在《公约》条文中明确体现
一方面,《公约》赋予沿海国的管辖范围未能涵盖中国在南海主张历史性权利的海域。中国需要从《公约》以外的法律渊源中寻找法律原则,可以考虑将一般国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和习惯国际法作为切入点。另一方面,《公约》并未包含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致使中国需要诉诸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论证权利。【参见雷筱璐:《历史性权利对〈海洋法公约〉相关制度和规则的促进作用》,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4页。】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际法,都将尊重国家的主权与自由意志作为核心价值。早在1927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在“‘荷花号案”中就确立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而非“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该案判决明确,在国际法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国家享有主权和自由,【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The Case of the S.S. “Lotu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permanent-court-of-international-justice/serie_A/A_10/30_Lotus_Arret.pdf.】更不能将《公约》外的权利视作非法。在不违反《公约》的前提下,国家实践应当得到认可。况且海洋法是在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的基础上建立的,由国际习惯不断推动海洋法的创新与发展。
(二)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可以诉诸一般法律原则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不应当被界定为与《公约》规则存在冲突,而是作为在《公约》制定前就已经形成并广泛适用的海洋权利,应归结为海洋新旧秩序的差异。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可以从一般国际法中尊重国家主权、禁止反言、诚实信用等一般法律原则的角度予以论证。历史性权利并不构成对《公约》的减损和例外,而是对一般国际法的适用。权利论证可以从如下思路展开。
第一,一般国际法将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置于重要地位。国际社会应当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确认各国的领土主张。“先占”作为领土取得的重要途径,构成一国在领土上的“主权行为”,成为判断领土主权归属的重要要件。他国的默认也是确认“主权行为”的前提。中国从历史性证据出发,论证对南海岛礁主权的占有和对历史性权利水域的利用符合国际法上“先占”的法律要件,具有可行性。况且尊重国家主权早已成为处理现代国际法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属于一般国际法且具有强行法效力。由此,从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般国际法出发,中国能够构建对南海岛礁的主权与对海域的历史性权利。
第二,尊重既成事实、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已经成为各国认可与遵守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历史性权利作为沿海国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权利,在以《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条约法对其确认之前就早已存在。【参见李永、张丽娜:《论历史性权利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第191页。】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是一国和平、长期、有效地行使权利的实践,也是一般国际法中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要求。尊重在海洋法规则确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得到国际法院认可。在“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中,国际法院认定,部分关于大陆架的实践属于习惯国际法范畴,例如不得阻碍铺设或维护海底电缆和管道、不得干涉航行和捕鱼自由等。这些规则属于一般海洋法的规则和原则,在《大陆架公约》之前就已形成,是具有同等效力的大陆架权利。上述权利在《大陆架公约》中有所体现,而该公约并不意在宣布或确认其存在,却仅为了确认既存的大陆架权利并不能因该公约的实施而受到减损。该案成为中国证明在《公约》之前确立的权利主张不应当得到减损的有力的判例法依据。
第三,默示同意与禁止反言成为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确权的重要依据。在长期实践中,对一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利的承认很少有机会经由他国的明示同意得以确认,他国也无义务对此表达认可。因此,搜集明示同意的证据并不现实。相反,不提出反对意见的默示同意也能产生相当于正面承认的法律效果。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已经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同,而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可往往通过默示同意与禁止反言的方式体现。【参见刘晨虹:《中国南海断续线在国际习惯法中的定位探索》,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38页。】基于已经形成的默示同意,各国理应遵守禁止反言的法律义务,包括国家的沉默将产生禁止反言的法律效力。禁止反言原则已经在“隆端寺案”“东格陵兰案”“利比亚和乍得领土争端案”“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白礁岛主权争端案”中被广泛适用,成为判断他国明确知晓并同意国家权利主张的重要法律依据。
况且,中国已经掌握他国明示承认中国南海领土主权与海域管辖的依据。1956年6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在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时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进一步具体介绍了越南方面的材料,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属于中国了。”【外交部:《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载中国南海网2016年6月24日,http://subsites.chinadaily.com.cn/SouthChinaSea/2016-06/24/c_52626.htm。】基于禁止反言原则,越南当前主张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岛礁领土主权与海洋权利于法无据。
(三)中国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的权利主张是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
尽管《公约》并未将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纳入《公约》明文规定的范畴,但一系列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反映出这一规则在习惯国际法体系下不断形成与演进,【参见丁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处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一般国际法关系问题探析》,载《南海法学》2017年第4期,第105页。】本质上属于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发展趋向。【参见王勇:《中国在南海地区构建远洋群岛法律制度析论》,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102页。】据统计,在20个拥有远洋群岛的大陆国家中,有17个国家将远洋群岛视为整体,并划设直线基线。尽管美国国务院与中国国际法学会关于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的统计方法存在区别,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美国强调个别国家在部分群岛外围划设直线基线,而并未将全部群岛圈在基线内的做法不符合群岛基线的划设方法。但美国不能以此否认的是,无论是将群岛作为整体,还是在多个岛礁边缘划设直线基线主张群岛内水域权利的操作,都反映出在数个岛礁外围划设直线基线有逐渐形成国家实践与国际习惯的趋势。也有国家,例如厄瓜多尔,基于历史、地理的实际考虑,将数个岛屿作为整体。由此,这项制度能反映不少国家的实际需要,属于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也有资深学者主张,如果国际社会经过不断研讨,积极整理已有的实践经验,将“非群岛国家的群岛水域”实践塑造成国际“共识”,将其运用在相关国际问题中,甚至进一步将“共识”推展成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国际立法草案”,逐渐形成未来的成文法,将减少国际争端,推动海洋法的发展。【参见傅崐成:《全球海洋法治面对的挑战与对策》,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90页。】
“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意味着新规则仍在构建过程中。尽管国际社会可能对此存在争议,但其已有获得国际司法机构承认的趋势。在202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实体判决中,法院在探讨毗连区内水下文物立法时,运用“正在增长的国家数量”的表述证明国家实践的普遍性与广泛性,以此反映国际社会认同的趋势,而无意于确认国家数量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国家实践。【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lleged Violations of Sovereignty Rights and Maritime Spaces in the Caribbean Sea (Nicaragua v. Columbi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pr. 21, 2022), https://www.icj-cij.org/public/files/case-related/155/155-20220421-JUD-01-00-EN.pdf.】基于這一思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在全部或部分岛礁外部划设直线基线,这一方式正在获得更加广泛的国家实践,被中国及其他具有类似地理、历史原因而需要划设整体基线的国家所适用,未来将在国际社会中形成更广泛的法律确信,并成为习惯国际法。
尽管美国多次反对一些大陆国家设立远洋群岛法律制度,将其视为过度的海洋权利主张,但其结果只能导致美国作为“持续的反对者”,这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对美国无效。但单凭美国的做法无法阻止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美国本身不是《公约》缔约国,却又以《公约》为依据,指责中国行为违反《公约》规则,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条约与第三国的关系,即“条约对第三国既无损,也无益的原则”。美国通过官方声明、公开指责、发布《海洋界限》报告的方式,反对中国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的权利主张,并不必然阻碍这一趋势的形成。
五、中国倡导《公约》中一般国际法有效适用的路径
(一)引导国际社会从整体角度解释与适用海洋法规则
国际法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不同的法律渊源之间相互交织、存在重叠。虽然《公约》本身是条约法,但与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国际法存在重叠。为对海洋法规则作全面准确的理解,中国应当倡导国际社会从整体角度对海洋法规则予以解释和适用,将文本之外的一般国际法、习惯国际法、强行法纳入海洋法规则整体的解释范围,实现海洋法规则的整体性适用。正如2022年4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纪念《公约》通过四十周年高级别会议上书面声明所述,《公约》是现代海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参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呼吁准确完整地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新华网2022年4月30日,http://m.news.cn/2022-04/30/c_1128610605.htm。】对于《公约》的解释不能一味地诉诸文义解释、体系解释,而应当兼顾目的解释,即以维护海洋秩序的和平稳定作为宗旨,从这一初衷出发,引导国际社会从整体角度对规则进行解释与适用,实现维护海洋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
(二)倡导对海洋法的发展应当满足国家的现实需求
《公约》规则和国际实践之间存在着“沟壑”。面对国际实践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公约》的解释与适用是使《公约》具有成长性与发展性的关键所在,能使《公约》成为“活的法律”;另一方面,在海洋法体系下,确立新的规则也是满足实践需求的重要路径。
首先,在规则解释方面,未来中国应当倡导理论界与实务界给予国家实践和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以更高的重视与认可,这是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与新的海洋法规则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应当倡导国际社会尊重历史,认识到在《公约》缔结前中国周边海域已经形成的长期、稳定、和平的区域秩序,基于既成事实,维护既有的稳定秩序,相较于拘泥于具体规则的适用更加重要。
其次,继《公约》实施后,围绕《公约》与海洋法体系的新规则层出不穷。例如1994年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决议通过《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为“区域”及其资源确立了制度。【United Nations,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 XI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United Nations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Nov. 16, 1994),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agreement_part_xi/agreement_part_xi.htm.】《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United Nations (Jan. 14, 2023),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fish_stocks_agreement_states_parties.htm.】BBNJ协定和《国际海底区域开发规章草案》成为《公约》生效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其制定和实施势必将对现有的国际海洋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三)争取规则制定与解释的话语权以实现国家利益
在《公约》磋商过程中,中国曾经一度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基于77国集团和中国的利益集团集体发声。例如在《公约》磋商中,中国将专属经济区制度笼统地理解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的法律制度,将倡导这一制度的实施作为反对西方国家霸权的重要途径,而并未认识到国家海岸线长度直接决定了其所能依据这一制度获取的海洋利益,也并未深度思考该制度在未来漫长的时间维度内对中国是否有利。虽然站在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立场参与《公约》谈判磋商在彼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但如今中国更需要且应基于本国立场表达自身诉求。【参见张琪悦:《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海洋法律外交实践与能力提升》,载《理论月刊》2019年第10期,第17页。】
随着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海洋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当从先前学习和掌握《公约》规则逐渐转变为参与海洋立法与规则的解释与适用,进一步增强相关能力。只有争取与自身能力和责任相匹配的话语权,才更有机会推动国际法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使中国从国际法律规则中获取正当的利益。如果一味作为规则的接受者与遵循者,就很有可能使中国在寻求《公约》外的法律渊源构建海洋权利、主张海洋利益时处于不利地位,对后续海洋维权与执法造成阻碍。
在未来更长的时间维度内,中国应当在《公约》规则制定与完善的过程中勇于表明自身观点,敢于坚持表明自身立场,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在国际法和海洋法规则制定中争取到话语权,【参见何志鹏、王艺曌:《对历史性权利与海洋航行自由的国际法反思》,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3页。】并在此过程中增强议题设置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积极推动《公约》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促进海洋法治与国际法治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六、结语
《公约》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如何理解与处理《公约》之外的海洋法权利,协调《公约》与其他类别的海洋法渊源之间的关系,有待在后续实践中得到解决。推动《公约》序言中确立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的解释与适用,不仅为调整《公约》之外的海洋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中国构建海洋权利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一般国际法具有综合性与开放性,其含义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一般国际法不仅包括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规则和部分强行法内容,也包括国际法与国内法中普遍适用的原则,成为法律拟制的同意,能够与其他类别的法律渊源互相转化,在海洋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尽管一般国际法仅体现在《公约》序言中,但作为包含多重法律渊源的综合性概念,其法律效力与地位与《公约》处于同一位阶。《公约》不能影响、阻碍、减损一般国际法的实施。序言中的一般国际法为各方明确创设了權利义务,实质有效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中国部分海洋权利主张,特别是历史性权利和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并未纳入《公约》规则体系,而对于一般国际法的论证将成为构建中国海洋权利主张的关键。中国主张历史性权利可诉诸尊重国家主权、禁止反言、默示同意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一般法律原则。中国对南海岛礁享有领土主权已经得到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同意。中国主张的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是正在形成的习惯国际法,将在数个岛屿之外划设直线基线的方式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已经得到不少国家认可与适用。国家实践数量的增长反映出国际社会呈现出逐渐认可的趋势,反映出新规则的形成。
《公约》制定与实施期间,中国正逐渐从被动的接纳者与学习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与海洋制度的引领者。在未来中国应当继续引领《公约》的发展方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公约》并非海洋法规则的全部,从整体角度适用海洋法规则,有助于推动海洋法与国际法规则的体系化发展,满足国际社会与国家实践的发展需求;同时,应争取规则解释与适用的话语权与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推动海洋法向着对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改变中国长期所处的不利地位,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强国与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作用,积极推动海洋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