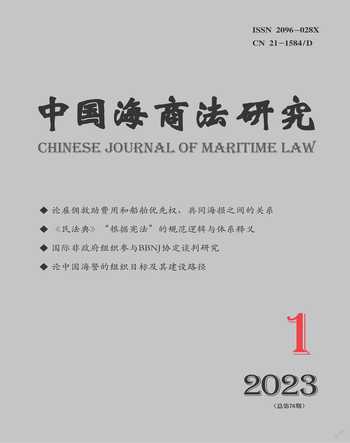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桑远棵
摘要:国家反诉是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程序性机制,但在实际适用当中面临重大的制度性困境。绝大多数国家反诉被仲裁庭以缺乏管辖权或可受理性为由驳回,胜诉的案件屈指可数。研究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可受理性与诉因要件缺乏全面、具体的规制。从当前来看,化解国家反诉适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如下:一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直接规定国家具有反诉权;二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须存在事实联系;三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设定具体的投资者义务。长远来看,构建体系化的国家反诉规则,不仅能够实现司法经济与司法协调之双重功能,还有助于推动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国家反诉;管辖权;可受理性;诉因
中图分类号:D99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3)01-0102-11
Application Dilemma and Its Approach on the State Counterclai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ANG Yuanke
(School of Law,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State counterclaim is an important procedural mechanis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whereas its application has confronted with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dilemma in practice. Most of the State counterclaims have been dismissed by arbitral tribunals for the reasons of lack of jurisdiction or admissibility and the case involving State counterclaim has been rarely supported. By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the occurrence of such phenomenon are that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fail to, in a comprehensive and concrete manner, regulate the jurisdiction, admissibility and cause of action issues of State counterclaim. Seeing for the time being,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dilemma of State counterclaim are as following: Firstly, to directly grant the State the right of counterclai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Secondly, to explicitly require the existence of factual connectedness between State counterclaim and investors primary clai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Thirdly, to incorporate specific obligation of investo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In the long run, 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rules of State counterclaim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dual functions of judicial economy and judicial coordination, and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balance of investor and State.
Key word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tate counterclaim; jurisdiction; admissibility; cause of action
一、問题的提出
国家反诉是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程序性机制,近年来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17年的Burlington v. Ecuador案(简称Burlington案)和2019年的Perenco v. Ecuador案(简称Perenco案)具有标志性意义,东道国厄瓜多尔提出的两份环境反诉都获得了仲裁庭的支持,美国与法国投资者需分别承担39 199 373美元
①
和54 439 517美元②的损害赔偿金。这两起成功的国家反诉案件不仅开辟了对外国投资者破坏东道国环境等不法行为进行追责的救济路径,还进一步突显了国家反诉的制度性价值。
第十一版《布莱克法律词典》就“反诉”给出的定义是,在提起原始诉求或本诉之后针对反对方主张的救济性诉求,或是反对或抵消原告诉求的被告诉求。【Bryan A. Garnar 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11th ed., Thomson West, 2019, p.402.】国家反诉则是指国家或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提出的旨在否定或抵消投资者原始诉求或本诉的诉求,亦称之为东道国反请求。从制度性价值方面而言,国家反诉可以改变东道国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始终处于被动抗辩的不利处境,避免其成为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永远的”被申请人,【Ina C. Popova & Fiona Poon, From Perpetual Respondent to Aspiring Counterclaimant? State Counterclaims in the New Wav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B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view, Vol.2:223, p.223-224(2015).】从根本上改变投资者与国家在程序性权利上的不对等性,还能间接地防止投资者滥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行为,【Shahrizal M. Zin, Reappraising Access to Justice in ISDS: A Critical Review on State Recourse to Counterclaim, in Alan M. Anderson & Ben Beaumont eds.,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Reform, Replace or Status Quo?,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20, p.228.】促使投资者进行负责任的投资活动。然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获得仲裁庭支持的国家反诉案件非常少,而且实际进入到实体事项审理阶段的也仅有6起案件,【六个案件分别是Perenco案;Burlington案;2016年的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a Republic案
(简称Urbaser案);2012年的Antoine Goetz v. Burndi案(简称Goetz案);2014年的Hesham TM Al-Warraq v. Republic of Indonesia案(UNCITRAL Case, Award, 15 December 2014);2017年的Tethyan Copper Company Pty Limited v.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案(ICSID Case No.ARB/12/1,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Liability, 10 November 2017)。】大多数仲裁庭要么以不存在国家反诉同意为由认定不具有管辖权,要么以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之间缺乏联系为由认定不存在可受理性,进而在管辖权阶段便驳回了国家反诉。
对于上述现象,有学者直言国家反诉经历了三十年的失败史。【Ana Vohryzek-Griest, State Counterclaim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 A History of 30 Years of Failure, International Law: Revista Colombi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Vol.15:83, p.83(2009).】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异乎寻常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可受理性和诉因要件缺乏全面、具体的规制,致使实践中不同案件的仲裁庭就此作出了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对国家反诉的实践发展而言构成了重大的制度性障碍。202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UNCITRAL)第三工作组在第39次会议上着重指出了国家反诉面临的投资者义务规范缺失与可受理性问题,并正在考虑设计一个国家反诉的框架,希望借此降低不确定性、促进公平与法治以及最终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ultiple Proceedings and Counterclaims,United Nations(Jan. 22, 2020),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20/006/03/PDF/V2000603.pdf?OpenElement.】摩洛哥和南非在提交给UNCITRAL第三工作组的投资者与国家争议解决的可能改革文件中也提到国家反诉的构建问题。【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orocco,United Nations(Mar. 4, 2019),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12/95/PDF/V1901295.pdf?OpenElement;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United Nations (Jul. 17, 2019),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72/51/PDF/V1907251.pdf?OpenElement.】筆者立足于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剖析国家反诉的三大核心要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体系化国家反诉规则的具体路径。
二、国家反诉的管辖权要件:同意
同意是国际司法机构获得管辖权的根本依据。对于国际投资仲裁而言,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仲裁庭的管辖权来源于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同意,管辖范围则取决于同意的范围,否则仲裁庭无权受理和裁断相关投资争议。如果仲裁庭对当事人未予同意或同意之外的事项作出裁决,可能导致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等不利后果。对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简称ICSID)裁决而言,当事人可以依据《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第52条第1款第2项“仲裁庭明显越权”请求临时委员会撤销裁决;对于非ICSID裁决,当事人则有权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3项“裁决构成超裁”请求执行地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部分或全部裁决。因此,国家反诉的同意对于仲裁庭的管辖权以及裁决的可执行性而言都至为重要。
在性质方面,国家反诉是一项有别于投资者本诉的全新诉求,具有独立性或自治性,不同于针对投资者的本诉所提出的抗辩或否定。【Maxi Scherer, Stuart Bruce & Juliane Reschke, Environmental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CSID Review, Vol.36:413, p.414(2021).】这就意味着国家反诉也应满足同意这一核心要件,即投资者与东道国应当就国家反诉达成仲裁合意。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商事主体或者国际投资合同中的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缔结的仲裁协议不同,对于依据国际投资条约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投资者和国家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有其特殊的同意形式,国家通常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发出永久性、单方面的仲裁要约,外国投资者提起仲裁请求,则被视为接受了仲裁要约,如此一来便拟制为双方形成了仲裁合意或达成了仲裁协议。这种特殊形式的仲裁协议被称之为“无共同利益关系的仲裁”。【Jan Paulsson, 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 ICSID Review, Vol.10:232, p.232-233(1995).】实践表明,同意是阻碍国家反诉获得仲裁庭支持并广泛适用的核心障碍,目前对于是否存在国家反诉同意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径与表现形式。
(一)国家反诉同意的解释路径与表现形式
1.国家反诉同意应根据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予以确定
实践当中,根据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来确定是否存在国家反诉同意的解释方法为大多数仲裁庭所接受。因为从一定程度上看,争议解决条款本身间接地反映了条约缔约国对于可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的界定,尤其是其限制性或宽泛性表述对于国家是否具有提起反诉的权利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一,如果争议解决条款对投资争议类型设定了特定限制,则排除存在国家反诉同意的可能性。在Spyridon Roussalis v. Romania案(简称Roussalis案)中,多数仲裁员认为对于是否存在国家反诉同意,必须首先根据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予以确定。本案中《希腊与罗马尼亚双边投资条约》第9条第1款规定:“一个缔约国的投资者和另一缔约国之间关于后者在本条约下的义务的争议,如果可能的话,应由争议当事人友好解决。”【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ellenic Ae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of Romania on the Promotion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Investment Policy Hub(May 23, 1997),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6544/download.】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毫无疑问,这一条款将管辖权限于投资者就东道国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提起的诉求,“争议”本身是指东道国未遵守投资条约而已。【Spyridon Roussalis v. Romania, ICSID Case No.ARB/06/1, Award, 7 December 2011, paras.865-869.】因此,仲裁庭判定本案不存在国家反诉同意。
同样,在2016年的Rusoro v. Venezuela案中,尽管仲裁庭承认《ICSID附加便利规则》第47条允许国家提出反诉,【《ICSID附加便利规则》第47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附随的或附加的或反诉,只要这些附随的诉求属于当事人仲裁协议的范围。”】但又认为国家反诉必须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之内,依据是《加拿大与委内瑞拉双边投资条约》第12条:该条第1款将可仲裁的投资争议限缩于投资者提出的东道国违反本条约的诉求;第2款规定如果投资者认为东道国违反了双边投资条约,
允许投资者确定此项诉求,告知东道国且决定未来仲裁的范围;第3款和第4款都规定提起仲裁程序的主体仅仅是投资者。【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Venezuela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Investment Policy Hub(Jul. 1, 199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644/download.】这就表明,双边投资条约仅仅赋予投资者提起仲裁的程序性权利,仲裁庭的权限仅仅是裁断投资者提出的东道国违反投资条约的诉求。【Rusoro Mining Limited v.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ARB(AF)/12/5, Award, 22 August 2016, paras.621-627.】仲裁庭由此认定本案不存在国家反诉同意。
第二,如果争议解决条款未限制投资争议类型与投资仲裁程序的启动主体,则存在国家反诉同意的可能性。在2012年的Inmaris v. Ukraine案(简称Inmaris案)中,仲裁庭判定自身具有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德国与乌克兰双边投资条约》第11条规定:“任何一个缔约方和另一缔约方国民或公司之间涉及投资的争议都应尽可能由争议当事人友好解决。”【Vertrag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Ukraine über die Frderung und den gegenseitigen Schutz von Kapitalanlagen, Investment Policy Hub(Feb 15, 1993),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1442/download.】仲裁庭认为其对任何一个缔约方和另一缔约方国民或公司之间涉及投资的争议都具有管辖权,被申请人提出的反诉是一项产生于其与申请人之间涉及投资的争议,这项争议是申请人同意提交仲裁的更大范围的争议的组成部分,因此被申请人的反诉属于仲裁庭的管辖权范围。【Inmaris Perestroika Sailing Maritime Services GmbH and Others v. Ukraine, ICSID Case No.ARB/08/8, Award, 1 March 2012, para.432.】无独有偶,2016年Urbaser案的仲裁庭也是基于《西班牙与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第10条认定存在国家反诉同意。【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a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7/26, Award, 8 December 2016, paras.1143-1148.】第10條第1款规定,一个缔约国和其他缔约国的投资者之间涉及投资的争议应尽可能由当事人友好解决;第2款规定,如果未达成和解,依据任何一个当事人的请求,投资争议应当提交至东道国的主管法庭;第3款规定,依据任何一个争议当事人的请求,在特定情形下争议可以提交至国际仲裁庭。【Acuerdo para la Prohocion y la Proteccion Reciproca de Inversiones Entre el Reino de Espaaa y la Republica Argentina, Investment Policy Hub(Oct. 3, 1991),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119/download.】仲裁庭认为上述三款规定对于谁是申请人谁是被申请人完全持中立立场,也就表明任何一个争议当事人都有权提起仲裁程序。此外,申请人还承认双边投资条约没有对谁可以提出诉求设定属人限制,而且其作出的承诺也没有排除被申请人的反诉。【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a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7/26, Award, 8 December 2016, paras.1143-1146.】
2.当事人同意适用ICSID仲裁则视为构成国家反诉的同意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既然争议当事人已经同意适用ICSID仲裁,在投资者提交给ICSID仲裁诉求时就应当被默认为或者附带性地同意了国家反诉,因为《华盛顿公约》第46条【《华盛顿公约》第46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法庭应当依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决定任何直接产生于争议标的物的附随的或附加的诉求或反诉,只要它们属于当事人的同意范围以及属于中心的管辖范围。”】和《ICSID仲裁规则》第40条【《ICSID仲裁规则》第40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提交一份直接产生于争议标的物的附随的或附加的诉求或反诉,只要这些附随的诉求属于当事人的同意范围以及属于中心的管辖范围。”】都明确允许国家提起反诉。从本质上看,这种理论是从当事人选择适用ICSID仲裁的这一行为来推定存在国家反诉同意,而不论国际投资条约中的争议解决条款等其他规定。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已经有少数的仲裁庭或仲裁员认可并适用这种推定同意或默示同意理论。2011年Roussalis案的仲裁员迈克尔·瑞斯曼(Michael Reisman)教授在其异议意见中便坚定支持这种立场,他认为当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国附带地同意ICSID管辖,《华盛顿公约》第46条的“同意”就已经在事实上被引入到投资者所选择的ICSID仲裁程序。【Spyridon Roussalis v. Romania, ICSID Case No.ARB/06/1, Award, Dissenting Opinion by W. Michael Reisman, 28 December 2011.】随后,2012年Goetz案仲裁庭的观点几乎与迈克尔·瑞斯曼教授的一样,他们认为布隆迪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这一特别行为就表明其已经接受了任何可交由ICSID仲裁的争议将受到《华盛顿公约》项下规则的支配。尤其是,布隆迪接受了在投资仲裁程序中提起的反诉将由仲裁庭依据《华盛顿公约》第46条及《ICSID仲裁规则》第40条进行裁断。而且,投资者接受了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仲裁要约,就应等同于接受了反诉,这种双重同意赋予了仲裁庭审理反诉的管辖权。正因为如此,双边投资条约中没有规定仲裁庭的反诉管辖权条款,是无关紧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还直接援引了迈克尔·瑞斯曼教授的上述观点来强化其裁判说理。【Antoine Goetz v. Burundi, ICSID No.ARB/01/2, Award, 21 June 2012, paras.278-279.】
3.国际投资条约明确排除了特定类型的反诉,反向推定允许其他类型的反诉
在Aven v. Costa Rica案(简称Aven案)中,被申请人哥斯达黎加提出了环境反诉,所依据的理由是《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DR-CAFTA)已经为国家反诉预留了可能性。【The 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Aug. 5, 2004),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cafta-dr-dominican-republic-central-america-fta/final-text.】具体而言:一是DR-CAFTA既没有排除、也没有禁止仲裁庭对反诉行使管辖权,这些条款对投资争议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身份完全持中立态度;二是只有DR-CAFTA第10.20条第7款提及反诉,即被申请人不得主张抗辩、反诉抵消权或者以其他任何理由主张申请人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依据保险与担保合同就其全部或部分损害的补偿金或赔偿金。换言之,既然DR-CAFTA已经明确排除了被申请人在保险和担保合同项下的反诉权利,也就间接表明其他任何类型的反诉都是被允许的。【David Aven et al. v.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 Case No.UNCT/15/3, Final Award, 18 September 2018, paras.690-694.】
4.投资者与东道国达成单独的国家反诉管辖权协议
在Burlington案中,申请人Burlington在厄瓜多尔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投资活动。厄瓜多尔提出的环境反诉是申请人的投资活动对第7号与第21号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根据厄瓜多尔的法律,申请人应对环境损害承担严格责任,即申请人应支付给厄瓜多尔赔偿金总额是2 797 007 091美元。本案中,申请人和厄瓜多尔就国家反诉的管辖权问题单独签订了一份协议。【Burlington Resources Inc.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ARB/08/5, Decision on Counterclaims, 7 February 2017, para.6.】
5.投资者未及时对仲裁庭的反诉管辖权提出异议,视为构成国家反诉同意
在Perenco案中,厄瓜多尔提出的环境反诉是要求申请人Perenco承担第7号与第21号区域环境损害的恢复费用。该案中,申请人从事的石油开采业具有内生的环境风险,尤其是在环境非常脆弱的亚马逊森林。由于申请人在以上两个区域的开采活动中明知其投资活动的重大环境影响,也没有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故应承担环境损害的恢复费用。应当指出,申请人是在提起仲裁的5年后以及仲裁庭已经就环境反诉作出临时决定之后才对环境反诉的可受理性提出异议,此前从未对
东道国环境反诉的管辖权或可受理性提出过任何异议,【Perenco Ecuador Limited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ARB/08/6, Decision on Perencos Application for Dismissal of Ecuadors Counterclaims, 18 August 2017, paras.35, 44.】因此仲裁庭將投资者此种不作为或参与国家反诉实体事项审理的行为推定为构成国家反诉同意。
(二)对国家反诉同意解释路径与表现形式的评价
一是根据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来确定存在国家反诉同意的解释路径。从当前来看,多数意见认为国家反诉的同意必须来源于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因为它直接划定了可仲裁的投资争议范围。一旦投资者接受了仲裁要约,当事人便对投资争议的范围形成了合意。而且,投资者只能接受仲裁要约的全部事项,不得进行任何挑选,更不得任意排除东道国的反诉权利。【参见肖军、康雪飘:《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仲裁同意问题》,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5期,第87-91页。】在此情形下,国际投资条约中那些宽泛的或不设限制的争议解决条款具有包含国家反诉的充分空间。相反,争议解决条款的狭隘性或限制性表述则很可能将国家反诉排除出可仲裁的投资争议范围。历史上,《华盛顿公约》的缔约材料就曾经明确提到第9节(现第46条)根本无意扩大仲裁庭的管辖权,其中一个代表团提到反诉管辖权必须经过当事人明确授予,而不是要求当事人明确排除。【ICSID:History of the ICSID Convention(Vol.II-1), ICSID Publication, 2009, p.573.】因此,对于是否存在国家反诉同意,可以根据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所设定的可仲裁的投资争议范围予以确定。
二是从当事人同意适用ICSID仲裁的行为本身来推定存在国家反诉同意的解释路径。从价值层面来看,这种解释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这种解释方法可以避免出现投资争议结果的不一致性,提高投资争议解决效率,以实现司法协调与司法经济之双重目标。实际上,《华盛顿公约》具有鼓励、支持国家反诉的倾向性立场,这种立场不仅体现在公约第46条明确允许国家提起反诉,还体现在《华盛顿公约》的名称以及第36条也都直接表明它并未将ICSID仲裁程序的启动权限缩于投资者。【《华盛顿公约》的缔约材料也同样申明允许投资者和东道国提起仲裁程序,因为公约在条款的设计上致力于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上维持微妙的平衡。See Thomas Kendra, State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New Lease of Life?,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29:575, p.577(2013).】《华盛顿公约》的缔约材料也进一步表明,引入第46条是为了避免在其他单独的程序如东道国的法院提出关联性诉求,ICSID仲裁庭与东道国的法院可能就具有牵连关系的投资争议作出完全不一致的决定,这不仅使得投资争议解决趋于复杂化,也会降低程序性效率与不当增加当事人的争议解决成本,更有违《华盛顿公约》的文本与精神。在2015年的Marco v. Romania案中,仲裁员卢比诺(Rubino)在其异议意见中更是认为,被申请人的反诉是其自身抗辩的自然延伸,很难接受投资条约的缔约国有意在不同的法院和仲裁庭产生平行诉讼程序。【Marco Gavazzi & Stefano Gavazzi v. Romania, ICSID Case No.ARB/12/2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dmissibility and Liability, 21 April 2015, Dissenting Opinion of Arbitrator Mauro Rubino Sammartano, para.42.】
另一方面,这种解释方法可以防止再次出现投资争议。投资条约缔约国在同意ICSID仲裁时,必然期待与其密切关联的投资争议全部交由单一程序解决,将此类争议交由不同的法庭可能再次引发其他的投资争议。正如迈克爾·瑞斯曼教授所言,如果东道国法院作出了不利判决,先前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被申请人可能再次成为申请人并据此提起另一个投资仲裁诉求,【Spyridon Roussalis v. Romania, ICSID Case No.ARB/06/1, Award, Dissenting Opinion by W. Michael Reisman, 28 December 2011.】当事人可能陷入到循环往复的争议解决过程之中,并不符合《华盛顿公约》促进投资争议通过国际司法机制予以解决的根本目标。从文义的角度视之,《华盛顿公约》第46条要求排除反诉必须是当事人以明示形式表示,否则就应视为仲裁庭有权裁断与投资者本诉相关联的反诉。换言之,如果争议当事人没有明确表示排除反诉,反诉理应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从《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历史来看,所涉及的缔约材料也都没有表明国家有意限制或排除反诉。如果不存在此类情形,便可以推定投资者同意反诉一并交由仲裁庭解决,这应当是一项默认规则。【M.N. Bravin & A.B. Kaplan, Arbitrating Closely Related Counterclaims at ICSID in the Wake of Spyridon Roussalis v. Romania,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Vol.9:1, p.7(2012).】
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当事人同意适用ICSID仲裁以及《华盛顿公约》第46条、《ICSID仲裁规则》第40条便直接认定存在国家反诉同意,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争议。产生此种争议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适用《华盛顿公约》第46条的前提条件是反诉必须属于当事人的同意范围,投资者提起诉求这一行为本身不足以推定为构成国家反诉同意;二是不考虑国际投资条约的相关争议解决条款,尤其是国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设定的仲裁要约范围,很可能会不当地扩大ICSID仲裁的范围,这不仅有可能违反条约缔约国的真实意图,还将进一步加剧当事人之间程序性权利的不平等性。基于此,有学者对迈克尔·瑞斯曼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强烈驳斥,并认为默示推定同意理论构成对所适用的国际投资条约和法律文件的非法修改。【Dafina Atanasova, Adrian Martinez Benoit & Josef Ostransky,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31:357, p.359(2014).】
三是通过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排除特定类型的反诉反过来推定允许其他类型的反诉的解释路径。这种解释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实践中,这类条款经常出现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如198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投资协定》第12条第5款、1998年《中国与巴巴多斯双边投资协定》第9条第8款、2009年《科威特与新加坡双边投资条约》第9条第6款、2018年《阿根廷与日本双边投资条约》第25条第14款。不过,这类条款能否成为构成国家反诉同意的法律基础,并未获得仲裁庭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尤其是,如果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限制了可仲裁的投资争议类型或者仲裁程序的启动主体,那么这类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应具有优先性。
四是通过投资者与东道国单独达成一份反诉的管辖权协议以及因投资者未及时对反诉管辖权提出异议来推定存在国家反诉同意这两种表现形式。就前者而言,当事人缔结单独的国家反诉管辖权协议是形成国家反诉同意的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不过投资者大多为避免承担责任,不仅不会与东道国缔结此种反诉管辖权协议,还会极力否定仲裁庭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因而这种国家反诉的同意形式并不常见。至于后者,国家反诉的默示同意形式亦不常见,因为投资者一般都会在庭审的开始阶段便极力抗辩仲裁庭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因而默示同意几乎很少发生。
三、国家反诉的可受理性要件:联系
国家反诉的可受理性要件,是指国家反诉必须与投资者本诉存在必要的联系或牵连关系,仲裁庭才具有一并裁断的权限。从价值层面而言,这项要件是为了促使仲裁庭更为全面地审查当事人的诉求、作出一致性裁决以及实现司法程序的经济性。从文本上看,《华盛顿公约》第46条几乎完全照搬了国际法院《法院规则》第80条,【《法院规则》第80条第1款规定:“反诉可以提出,但以与当事国另一方的诉讼请求的标的直接有关并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之内为限。”】二者都要求反诉必须直接产生于争议标的物。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联系”的法律性质为可受理性而非管辖权事项。【Andrea Marco Steingruber, Antoine Goetz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Burundi—Consent and Arbitral Tribunal Competence to Hear Counterclaims in Treaty-based ICSID Arbitrations, ICSID Review, Vol.28:291, p.300(2013); Dafina Atanasova, Adrian Martinez Benoit & Josef Ostransky,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31:357, p.380(2014); Arnaud de Nanteuil,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Old Questions, New Answers, Law &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Vol.17:374, p.385(2018).】例如,Goetz案和Metal-Tech v. Uzbekistan案的仲裁庭都將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必须具备的“联系”定性为可受理性。【Antoine Goetz v. Burndi,ICSID No.ARB/01/2,Award, 21 June 2012, para.283; Metal-Tech Ltd v. Republic of Uzbekistan, ICSID ARB/10/3, Award, 4 October 2013, para.407.】当前存在的最大争议问题是国家反诉必须与投资者本诉存在何种程度上的联系,是必须同时存在法律联系与事实联系?还是仅须存在事实联系?实践之中,不同的仲裁庭就此“联系”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案。
(一)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之间“联系”的解释分歧
1.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须同时存在法律联系与事实联系
现有实践表明,东道国提出的反诉大多是依据其国内法,即投资者的行为违反了东道国的某个法律,而不同于投资者本诉所依据的国际法——国际投资条约。由于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缺少相同的法律依据或不存在法律联系,多个案件的仲裁庭认定国家反诉不具有可受理性,继而判定不具有国家反诉的管辖权。例如,在2011年的Paushok v. Mongolia案(简称Paushok案)中,仲裁庭认为国家反诉必须与投资者本诉来源于同一个法律基础——国际投资条约,国家反诉来源于投资者违反东道国法律不符合联系要件。仲裁庭并未支持被申请人提出的7项反诉,如申请人拖欠税收与费用、违反了环境保护义务,而是认为反诉来源于蒙古国公法且仅仅产生不遵守蒙古国公法如蒙古国税法之类的事项,这些事项完全属于蒙古国法院的专属管辖范围,不能够认为它们与基于国际投资条约和国际法的申请人本诉构成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在申请人的诉求与反诉之间创设了一种合理联系。【Sergei Paushok, CJSC Golden East Company, CJSC Vostokneftegaz Company v.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Liability, 28 April 2011, paras.694-695.】
与此相类似的是2004年的Saluka v. Czech案(简称Saluka案)和1988年的Amco v. Indonesia案(简称Amco案)。在Saluka案中,被申请人捷克提出的第D项至第K项反诉都涉及申请人未遵守捷克的法律,例如,捷克的银行法律与条例、商业法典、民法典、经济竞争保护法。仲裁庭认为这些反诉无法被认定为与本诉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或者与本诉有相同的起源、来源和运行整体。被申请人的反诉来源于捷克法,原则上这些争议应通过捷克法上的适当程序予以解决,而不是通过国际投资条约项下的投资仲裁程序。【Saluka Investments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ver the Czech Republics Counterclaim, 7 May 2004, paras.78-79.】在Amco案中,被申请人印度尼西亚以申请人实施了税收欺诈为由提出反诉。仲裁庭认为,应正确区分一般法律意义上在东道国范围内适用于法人或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与适用于投资者的国际投资条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涉及后者的法律争议属于《华盛顿公约》第25条第1款的范围,原则上涉及前者的法律争议应交由相关国家的适当程序予以解决,除非一般性法律产生了《华盛顿公约》项下的投资争议。很明显,禁止参与税收欺诈的义务属于印度尼西亚法律上的一般性义务,其并未被投资条约予以特别规定,也并未直接产生于投资活动。【Amco v. Republic of Indonesia, Resubmitted Case: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0 May 1988, paras.125-126.】
2.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仅须存在事实联系
实践中,也有部分仲裁庭仅仅要求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存在事实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考虑法律联系,径直认定国家反诉符合可受理性要件。一般情形下,事实联系大多比较容易满足,只须国家反诉与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存在必要的关联性即可。
在Goetz案中,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非法撤销了银行运营证书的行为构成对投资条约的违反,被申请人布隆迪提出的反诉则是基于申请人未能遵守同一个银行运营证书规定的义务,仲裁庭认为主要争议是终止这项证书的合法性以及因为违反该项义务所造成的银行倒闭问题,反诉是布隆迪因为那些违反义务的行为所遭受的偏见,与争议标的物具有直接关联性,因而符合可受理要件。【Antoine Goetz v. Burundi, ICSID No.ARB/01/2, Award, 21 June 2012, para.285.】同样,Inmaris案的仲裁庭裁定被申请人的反诉与本诉之间符合联系要件,因为被申请人的反诉是一项与投资相关联的争议,这项争议是申请人同意提交仲裁的更大争议范围的组成部分。【Inmaris Perestroika Sailing Maritime Services GmbH and Others v. Ukraine, ICSID Case No.ARB/08/8, Award, 1 March 2012, para.432.】事實上,这两个案件的仲裁庭都没有考虑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之间的法律联系,而只是概括地认定国家反诉只要涉及投资争议便符合可受理性要件。
(二)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之间“联系”的应然解释
不难看出,阻碍仲裁庭对国家反诉行使管辖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多数仲裁庭要求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必须存在法律联系。但也要看到,一方面,如果绝对地要求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存在相同的国际法基础,即来源于同一个国际投资条约,是基于不合理的和限制性的解释方法,因为它忽视了国际投资条约很少规定具体投资者义务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Paushok案与Saluka案等案件的仲裁庭过多地依赖最早的基于投资合同引起的ICSID仲裁案件——Klckner v. Cameroon案(简称Klckner案),该案仲裁庭判定反诉必须与本诉存在相同的法律来源,而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Klckner Industrie-Anlagen GmbH et al. v. Republic of Cameroon & Société Camerounaise des Engrais S.A., ICSID Case No.ARB/81/2, Award, 21 October 1983. See 1994, 2 ICSID Rep. 9, 17.】Klckner案确立的联系标准被随后的ICSID仲裁庭作为先例援用,所造成的结果是东道国基于投资者违反本国法律尤其是本国公法提起的反诉被相继驳回,因为这些来源于东道国法律的反诉被认定为缺乏相同的法律来源。无疑,ICSID仲裁庭没有考虑到这一联系标准的适用应仅限于投资合同仲裁。对于投资条约仲裁而言,投资者与东道国一般不存在类似的投资合同,也就没有理由再继续要求反诉与本诉存在相同的法律来源,否则国家反诉的可适用性将永远停留在规则层面。
历史上,第一版《ICSID仲裁规则》的官方注释提到一点:为了使反诉具有可受理性,反诉必须直接产生于争议的标的物,满足这项条件的标准是本诉与反诉之间的事实联系是如此紧密而要求一并裁断后者。【ICSID, Regulations and Rules(In Effect on January 1, 1968), ICSID Publication, 1975, p.105.】2015年,法国政府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立场性文件中阐明,应当预想到仲裁庭裁定被申请人提交的反诉的可能性,只要反诉与主要争议所涉及的事实具有充分联系。【Towards a New Way to Settle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Investors, France Diplomacy(May 30, 2015),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20150530_isds_papier_eng_vf_cle09912d.pdf.】皮埃尔·拉里夫(Pierre Lalive)和劳拉·哈荣(Laura Halonen)两位学者亦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国家反诉与本诉必须存在法律联系,如果《华盛顿公约》有此意向,则应予以明示规定,否则反诉与本诉只须存在事实联系便足矣。【Pierre Lalive & Laura Halonen,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ounterclaim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zec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141, p.144(2011).】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修订的《UNCITRAL仲裁规则》第21条第3款直接删去了1976年版《UNCITRAL仲裁规则》第19条第3款【1976年版《UNCITRAL仲裁规则》第19条第3款规定:“被诉人可在其答辩书中,或如仲裁庭决定根据情况有理由延迟时,则可在仲裁程序的稍后阶段中,提出由同一合同所引起的反诉,或提出由同一合同所引起的索赔,已达到抵消的目的。”】关于反诉的联系要件——同一合同。UNCITRAL作此番修改的意图是认识到,如果要求本诉与反诉之间存在法律联系,实际上已经无法适应国家作为投资争议当事人以及投资条约仲裁的特殊情形,废除联系则使其足以包含更加广泛的情形。
因此,如果绝对地要求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必须同时存在法律与事实联系,不仅过于苛刻和不合理,还将极大地压缩国家反诉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的适用空间,以及加剧投资者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在此情形下,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之间的联系应当指向的是事实联系,即反诉与投资争议所涉及的事实具有密切联系,否则《华盛顿公约》第46条与《ICSID仲裁规则》第40条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僵尸条款,而这并不符合《华盛顿公约》的内在目标。
四、国家反诉的诉因要件:投资者义务
从性质上看,国家反诉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都属于程序性要件,一旦这两项要件获得满足,国家则必须证明国家反诉存在诉因,即国际投资条约中存在规制投资者相应行为的实体性义务。否则,国家反诉将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也无法获得仲裁庭的支持。实践中,不同的仲裁庭在此方面所持立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一)投资者义务法律来源的立场分歧
1.国际投资条约上的投资者义务
实践之中,多数仲裁庭认为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必须存在规制投资者行为的具体义务,否则国家反诉将因缺乏诉因而无法获得支持。在Urbaser案中,仲裁庭在实体审理阶段以投资者缺乏国际法上的义务为由,最终没有支持国家反诉。具言之,东道国没有说明投资者在提供水资源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人权义务是来源于国际法,东道国认为投资者明显违反了适用于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但这个主张并没有援引任何特定的国际法义务,而仅仅是依赖基于特许经营权协议下的投资者义务。此外,东道国也承认反诉缺乏国际法上的诉因。【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The Argentina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7/26, Award, 8 December 2016, paras.1206-1207.】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Aven案中,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活动对拉斯奥拉斯地区造成巨大的环境损害,如森林植被层的消失、土壤的沉降、湿地的破坏,所提出的反诉是申请人应对环境损害承担责任以及必须恢复该地的生态系统。仲裁庭则认为,尽管DR-CAFTA第10条包含了一些投资者在东道国环境法方面的义务。例如,要求任何投资者不得忽视或违反东道国采取的保护动植物和人类的措施。不过,这些条款意在确保国家在其领域内对环境措施具有重大裁量权,而并没有为投资者施加任何肯定性义务,也没有规定任何违反国家制定的环境条例的行为将构成对条约的违反,而这恰恰可能是反诉的法律基础。【David Aven et al. v.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 Case No.UNCT/15/3, Final Award, 18 September 2018, paras.734, 743.】因此,仲裁庭以投资者缺乏国际投资条约上的实体性义务为由而未支持国家反诉。
2.东道国国内法上的投资者义务
事实上,也有少数仲裁庭支持东道国基于投资者违反本国法律所提出的反诉。在Burlington案中,厄瓜多尔根据本国法提出了环境反诉,要求投资者对第7号和第21号区域的环境损害承担严格责任。环境损害主要表现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仲裁庭认定应根据厄瓜多尔的国内法来裁断实体性投资争议。【Burlington Resources Inc.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ARB/08/5, Decision on Counterclaims, 7 February 2017, para.159.】同样,在Perenco案中厄瓜多尔请求仲裁庭判定投资者承担恢复第7号和第21号区域的环境损害费用。仲裁庭最终支持厄瓜多尔提出的环境反诉,并认为厄瓜多尔法律提供了评估第7号和第21号区域的环境条件标准,对于发生于2008年7月至2009年7月的超过规制标准的污染,根据厄瓜多尔《宪法》中环境损害的严格责任机制,投资者应当承担严格责任。【Perenco Ecuador Limited v. The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ARB/08/6, Interim Decis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Counterclaim, 11 August 2015, paras.36, 65-70, 611.】
(二)規制投资者义务的应然路径
至今为止,两个成功的国家反诉案件——Burlington案与Perenco案都是依据东道国的国内法,或者说仲裁庭认定东道国的国内法构成国家反诉的诉因要件。尽管这种立场得到了少数学者的支持,其认为环境反诉的法律基础必然来源于国内法,要求反诉依据国际法不仅不切合实际,也无助于事。【SHAO Xuan,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Rights Counterclaim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t the Crossroad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24:157, p.157(2021).】但实践中,这种观点并没有获得绝大多数仲裁庭的接受。绝大多数仲裁庭要求国家反诉必须存在国际法上的诉因,即国际投资条约的实体性规则中应包含具体的投资者义务。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东道国依据其国内法提起反诉,投资者将因此承担过多的且不可预见的责任,而这并不符合投资者与资本输出国的核心利益。
历史上,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具有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天然倾向,所有的实体性条款几乎全部是关于东道国保护与促进投资的义务,而缺少专门规定投资者义务的实体性条款。在这方面,UNCITRAL第三工作组特别指出国家反诉所涉及到的根本问题便是国际投资条约几乎没有为投资者设定义务,极大地限制了国家提起反诉的可能性。【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ultiple Proceedings and Counterclaims,
United Nations (Jan. 20, 2020),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20/006/03/PDF/V2000603.pdf?OpenElement.】202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还专门就2 575个国际投资条约进行了统计分析,只有40个正文规定有企业社会责任条款,112个含有劳工标准,317个包括环境和健康条款。【联合国:《符合人权的国际投资条约》,载联合国数字图书馆2021年7月21日,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936777/files/A_76_238-ZH.pdf。】这些条款对投资者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但在实质意义上无法作为国家反诉的实体性依据,【参见刘瑛、张威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9页。】进而导致东道国不得不以其国内法作为提起反诉的法律依据。但就大多数情形而言,仅仅违反国内法义务不足以使仲裁庭的管辖权延伸至国家反诉。【Yaraslau Kryvoi, Counterclaim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MyGov,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1:216, p.239(2012).】因此,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设定具体的投资者义务规则应成为国际投资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规则的完善路径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适用困境主要根源于现有国际投资条约对管辖权、可受理性和诉因要件缺乏全面、具体的规制。从上述三个方面完善现有的国家反诉规则,是化解国家反诉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适用困境的根本出路。
(一)管辖权要件的完善路径
国家反诉的管辖权要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投资者和东道国是否就反诉形成了仲裁合意,这是仲裁庭受理国家反诉的基础条件。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大多没有明确规定东道国具有提起反诉的权利,导致仲裁庭就国家反诉的同意产生了重大分歧。解决国家反诉同意的不确定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种规范路径。
第一种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允许国家提出反诉或者赋予国家反诉权。例如,2015年《印度双边投资条约范本草案》单独设立了国家反诉条款,第14.11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当事国有权就投资者违反第三章第9条至第12条的义务提起反诉……”【Model Text for the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MyGov (Mar. 24, 2015), https://www.mygov.in/sites/default/files/master_image/Model%20Text%20for%20the%20Indian%20Bilateral%20Investment%20Treaty.pdf.】2007年《东南非共同市场投资协定》(简称COMESA)第28条第9款也规定:“成员国可以COMESA投资者未能履行本协定下的义务为由提出反诉,包括遵守所有可适用的国内措施的义务或未能采取所有可减轻潜在损害的合理措施的义务。”【Investment Agreement for the COMESA Common Investment Area, Investment Policy Hub (May 23, 2007),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3092/download.】第二种是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当投资者接受了东道国的仲裁要约,视为同意东道国的反诉权。【Ted Gleason, Examining Host-State Counterclaims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from Human Rights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21:427, p.440(2021).】第三種体现于《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投资条约示范草案》的评论,即投资者可以提交诉求至仲裁庭解决,表现为投资者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同意反诉仲裁文件,并由此确认其同意受制于投资者的义务以及同意在争议当事人提交直接产生于争议标的物的反诉时交由同一个仲裁庭予以解决。【Jose Antonio Rivas, ICSID Treaty Counterclaims: Case Law and Treaty Evolution, in Jean E. Kalicki & Anna Joubin-Bret eds., Reshap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ey for the 21st Century, Brill Nijhoff, 2015, p.820.】第四种是在国际投资条约的争议解决条款中,对可仲裁的投资争议类型不设任何限制,也不限定仲裁程序启动主体的身份。例如,2003年《中国与德国双边投资条约》第9条规定:“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就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可能由争议双方当事人友好解决。”
比较而言,前三种路径都是为了在国际投资条约中以明示方式确立国家反诉的同意问题,因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不会引发争议。尤其是第一种与第二种路径,因其较为直接与明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条约或国际投资条约范本所采用。【2018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9.19条第2款、2018年《阿根廷与阿联酋双边投资条约》第28条第4款、2016年《斯洛伐克与伊朗双边投资条约》第14条第3款。】相较而言,第四种路径是当前仲裁庭确定是否存在国家反诉同意的主要方法,尽管它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具有反诉权,但它为国家反诉预留了充分的制度性空间。不过,这种路径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在具体的解释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分歧。因此,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对于是否存在国家反诉同意所引发的争议,更适当的做法是采用第一种或者第二种规范路径。
(二)可受理性要件的完善路径
可受理性要件是仲裁庭受理并裁断国家反诉的重要条件。如果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不存在必要的联系或牵连关系,仲裁庭对国家反诉的裁断可能构成越权裁判,所作出的裁决则可能得不到承认与执行。尽管实践中对“联系”的解释存在不同方案,但结合国际投资法的特殊性质与国际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之间的联系应当指向的是事实联系,而不是法律联系。
从当前来看,解决国家反诉可受理性问题存在两大路径:一方面,可以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规定国家反诉应与投资者本诉存在事实联系,即国家反诉产生于投资活动或者与投资活动具有事实上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规定东道国有权依据本国法提起反诉。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消除“联系”在解释上的不一致性,还能扩大国家反诉的适用范围。例如,2016年《斯洛伐克与伊朗双边投资条约》第14条第3款便规定:“被申请人有权以申请人未能履行其在本条约定项下遵守东道国法律的义务或者未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来减轻潜在损害为由提出反诉。”【Agreement Between the Slovak Republic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or the Promotion and Reciprocal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Investment Policy Hub(Jan. 19, 201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3601/download.】比较而言,如果采用第二种规范路径允许东道国依据其本国法提起反诉,很可能会不当地扩大投资者的义务范围,而且要求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承担过多的东道国法上的义务势必遭到其强烈抵制。因此,更为适当的做法是采用第一种规范路径,这种路径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仲裁庭对“联系”作出限制性解释所产生的适用困境,从而保证国家反诉这一程序性救济机制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有效运行。
(三)诉因要件的完善路径
一直以來,国际投资条约的主要目的便是促进投资和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这就造成投资条约的全部条款几乎完全围绕东道国的义务而展开,直接规定投资者承担特定义务的实体性规则极为少见。尽管当前也有少数国际投资条约的前言规定,承认投资者有义务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法律,例如,2001年《中国和尼日利亚双边投资条约》、2002年《中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双边投资条约》,但这类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并没有为投资者设定具体的义务,因而无法作为国家反诉的实体性依据。
因此,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引入具体的投资者义务,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反诉的诉因缺失问题,还是保障国家反诉发挥其制度性功能的关键条件。从当前来看,规制投资者义务主要存在三种途径:第一,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直接规定投资者在环境、人权等方面的具体义务。例如,2016年《摩洛哥与尼日利亚的双边投资条约》首次在条约正文明确规定投资者人权义务,第18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应当维护东道国的人权,第18条第4款还要求投资者在管理或运营投资活动中不得规避当事国在国际环境、劳工和人权领域的义务。【Reciprocal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Morocco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Investment Policy Hub(Dec. 3, 2016),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y-files/5409/download.】第二,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直接援引涉及投资者义务的国际公约作为投资争议的准据法,也就是从国际投资条约外部间接地引入具体的投资者义务。第三,可以在国家投资条约中明确规定投资者违反东道国法律的特定行为构成对条约的违反,东道国有权依此提起反诉。例如,《英联邦国际投资协定指引》阐明,东道国可以就投资者未能遵守本国法上的义务提起反诉。【Jose Antonio Rivas, ICSID Treaty Counterclaims: Case Law and Treaty Evolution, in Jean E. Kalicki & Anna Joubin-Bret eds., Reshap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ey for the 21st Century, Brill Nijhoff, 2015, p.819.】归纳而言,第二种规范路径是一种引入投资者义务的间接路径,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可,第三种规范路径则不当地扩大了投资者的责任范围,势必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支持。因此,最为适当的做法是采用第一种规范路径,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规定投资者应当承担的具体义务,为国家反诉的有效运行提供最为直接的实体性依据,同时也可以防止不当地扩大投资者承担义务的范围。
六、结语
总而言之,国家反诉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制度性价值不容忽视,是未来国际投资法的重要发展方向。从表面上看,它不仅能够提高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效率,降低当事人使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费用,以此实现司法经济功能,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避免产生平行诉讼程序和矛盾裁判决定的现象,进而实现司法协调功能。更加重要的是,国家反诉裁决能够通过《华盛顿公约》与《纽约公约》在全球范围获得自由流通,故其可执行性亦将获得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从本质上看,构建体系化的国家反诉规则不仅有利于改变投资者与东道国在程序性权利上的非对等性,推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均衡化,缓解当前国际投资仲裁所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还能够间接地推动投资者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与进行负责任的国际投资活动,最终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从管辖权、可受理性与诉因三个方面构建体系化的国家反诉规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反诉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面临的适用困境。具言之:第一,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直接规定国家具有反诉权;第二,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明确国家反诉与投资者本诉须存在事实联系;第三,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设定具体的投资者义务。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在构建国家反诉规则上具有明显的、强烈的制度性需求。一方面是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处于高位,而且呈现不断增长之趋势;另一方面是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期,势必对外资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使外国投资者得不到充分补偿,进而引发投资争议。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很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诉诸国际仲裁庭。然而,中国现有的一百多份投资条约大多没有设定全面的国家反诉规则,尤其是在管辖权方面将可以提交仲裁的争议限缩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关于征收或国有化措施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因要件方面也仅仅原则性要求投资者遵守东道国的法律,这就使得中国政府无法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提起国家反诉,因而长期处于被动防守之态势。未来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的修订与升级过程中,中国应致力于构建体系化的国家反诉规则,从而更加全面地维护本国的规制权与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