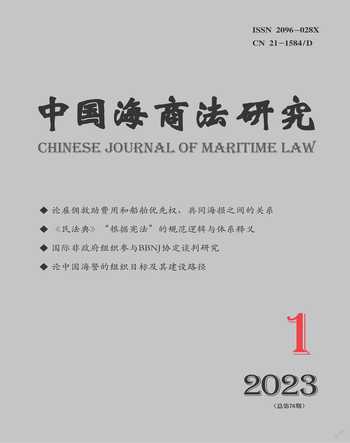《民法典》“根据宪法”的规范逻辑与体系释义
摘要:在《民法典》編纂过程中,关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表述始终存有争议,并集中表现为民法独立说、民宪平行说与宪法至上说这三种观点。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论以及理论基础,现有学说并未形成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融贯性的规范理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本身具备来自规范层面、国家权力关系层面以及基本权利“客观法”层面的正当性基础。从宪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可以系统探寻“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意涵,并将这一抽象的原则转为在规范层面和技术层面可供操作的规则。一方面,在积极意义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要求《民法典》积极落实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性保障功能以及国家保护义务功能;另一方面,在消极意义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要求《民法典》应始终恪守宪法框架秩序这一基本边界,在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严格遵循合宪性解释方法以及合宪性审查标准,以切实发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指示作用。
关键词:“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民法典》;规范意涵;制度性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3;D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3)01-0025-11
Normative Logic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Civil Code
WANG Zh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Civil Code,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dispute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which focuses on three views,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theory of civil law”,“the parallel theory of civil law and constitution” and “the supremacy of constitution”. Due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basis, the existing theories have not yet formed a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istency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has a legitimate basis from the normative level, the state power relationship level and the basic rights “objective law”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doctrine,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can be explored, and this abstract principl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operational rules at the normative and technical levels. On the one hand, in a positive sense,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e Civil Code to actively implement the functions of systematic guarante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national protection oblig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n a negative sense,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the Civil Code always abide by its basic boundaries, that is, the order of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strictly follow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criteria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reby effectively playing the normative role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Key words:“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the Civil Code; normative meaning; systematic guarantee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也是一国法律体系的法源和权源所在。因此,立法者在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典的过程中,理应积极从宪法中找寻合法性与正当性,即必须将宪法作为根本依据,以彰显部门法的宪法渊源。【“法的渊源”包括四种含义:一是法的实质渊源,即法是根源于客观物质条件还是主观意志;二是法的形式渊源,即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三是法的效力渊源,即法由何种国家机关制定;四是法的材料渊源,即形成法的材料来源成文法还是来源政策、习惯、宗教、礼仪、道德、典章或理论、学说等。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立法的权力渊源和内容渊源分别是在第三层和第四层意义上使用。】然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宪法学与部门法学缺乏深入互动和交流,各方关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表述常常陷入争论之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到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关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争论就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在原《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有关民法作为基本法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讨论更是始终牵动人心。此后,随着原《物权法》正式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纳入第1条,相关争论也并未偃旗息鼓,依旧不时擦出火花。理论上的徘徊不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立法者时常陷入踌躇,据学者统计,截至2021年10月份,现行288件法律中,仅有97件明確吸收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参见张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蕴涵与立法表达》,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3期,第109页。】这就表明这一理论仍有厘清的必要。从事实角度来看,“根据宪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制定期间又一次引发了争论,学界关于是否有必要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纳入《民法典》,仍然是见仁见智。2020年5月份颁布的《民法典》在第1条明确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民法典》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本款看似有着“定分止争”的效果,但宪法和民法究竟是何种关系?当前争论的焦点为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否具备正当性基础?更重要的是,“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仅仅起到价值宣誓作用,还是具备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上的规范指向?显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建构起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动态关系,推动部门宪法教义学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植:《民法典》“根据宪法”的规范逻辑与体系释义
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理论争议
在《民法典》的编撰过程中,关于民法和宪法的关系始终备受关注。民法学者与宪法学者延续2006年原《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界分的讨论,围绕民法和宪法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并集中表现为民法独立说、民宪平行说与宪法至上说三种观点。
(一)民法独立说
所谓民法独立说,是指部分民法学者主张基于私法自治的需要,民法本身浑然一体,独立于宪法之外,并呈现出一套泾渭分明的逻辑体系。
一方面,就历史积淀而言,民法的历史积淀要远超过宪法。民法本身来源于市民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经历了习惯法、成文法、制定法、判例法等多种形式,不遗余力地调整着市民社会的关系演变,早在1804年就产生了著名的《法国民法典》,反观宪法更多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产生,直至1787年才形成了第一部明确的成文宪法,且1787年《美国宪法》,无论是篇幅、结构还是影响力都远不如《法国民法典》那样深远。此时,如果强行将民法置于宪法之下,不仅会扰乱民法的逻辑体系,同时也会是宪法无法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就调整范围而言,民法和宪法分别对应私法和公法这两个维度。民法和宪法虽然都是一国重要的法律构成,但却分别面向不同的法律关系抑或调整范围,即民法更多是市民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反观宪法则更多是政治国家逐渐成熟的法律外观。申言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本身就是一套二元结构,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期间,国家就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这进一步表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二元结构,因此,理应通过不同的法律加以调整,即民法调整市民社会领域的私权,宪法则调整政治国家领域的公权,基于“守夜人”的政治属性,私权始终构成公权力的行为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法和宪法本应互不干扰,二者分别扮演着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基本法角色。【参见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17-120页。】
如此,如果秉承上述观点,“根据宪法,制定民法”的逻辑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正如郭道晖、梁慧星指出,公法优位主义并不可取,适度承认和确立私法优位主义,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具创见性。【参见郭道晖、梁慧星、
摘要》,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第2-3页。】
(二)民宪平行说
所谓民宪平行说,是指民法和宪法分别对应不同的领域范围和价值指涉,并无优劣和高低之说,而是表现为平行的法律关系。当然这种平行并不意味着法律效力的一致,而是指调整内容、规范方式以及目的价值的平行。在此意义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只能体现宪法在法律效力上优于民法,但却并不意味着宪法在内容上相对于民法的优势地位,更不能简单以“母法”和“子法”的称谓来回应宪法和民法之间的关系,相反,与其将二者的关系定位为“母子”,倒不如直接描述为相辅相成的平行样态。毕竟,立足于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性,宪法作为根本法无疑处于法律效力上的最顶端,法律在效力上当然要以宪法为依据,民法也不能例外,但这种效力上的优位更多指向形式意义,并不意味在内容设定上要将宪法定位为母法,民法只能将宪法予以具体化。【参见王利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4-75页。】事实上,宪法和民法在最初的设定上就呈现出迥异差别,前者更多对应“限制公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因此内容上自然以国家组织法和基本权利保障法为主,公权内部关系、公权与公民基本权利关系是重中之重。民法在设定上则更多是为了调适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私权自由,甚至民法的条款都以微观的技术性规则呈现出来,与宏观层面的“公权—私权”关系相去甚远。【参见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22-123页。】例如,民法的很多规则如无权代理、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都是民法所特有的,并不涉及宏观层面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此时,如果强行将宪法付诸民法领域的技术性规则,不仅会降低民法规则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动辄宪法化的思维还会稀释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存在“用大炮打小鸟”的嫌疑。一言以蔽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特指法律效力抑或立法权来源,在内容设定上并不成立。有鉴于此,龙卫球等学者主张为避免宪法对民法的全面辐射,应该调整“根据宪法”的法律表述,以更明确的话语指出,从而全面彰显宪法和民法的平行对等关系。【参见龙卫球:《民法典编纂要警惕“宪法依据”陷阱》,载财新网2015年4月22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4-22/100802509.html。】
值得注意的是,平行说和独立说虽然在论证结论表述和具体论证方式上存在着不同,但在诸多方面的观点都具有相同之处。具体来说,平行说和独立说都以“民法相对于宪法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的,都表达了对以宪法来统摄民法观点的实质性抗拒,都强调民法与宪法在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功能层次上的不同,只不过平行说相对于独立说而言承认宪法对民法具有形式上的效力优位地位。
(三)宪法至上说
上述民法独立说以及民宪平行说更多以民法学者为代表。宪法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同样有所回应,并大多主张宪法作为根本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地位超然,因此,《民法典》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纳入第1条并无不妥之处,理由如下。
首先,就民法和宪法的历史积淀而言,仅仅从诞生的历史长短来界定民法和宪法的关系未免过于武断,如果理由正当,后来者居上也没有任何不妥。当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愈发成熟,部门法法典化的呼声愈发高涨,但晚近以来,民法典时代仅仅是法律化时代的一个侧面,随着现代宪法兴起,后者业已逐步取代了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根本法、基本法、框架秩序等多元形式呈现出来。【参见林来梵、龙卫球、王涌等:《对话一:民法典编纂的宪法问题》,载《交大法学》2016年第4期,第5-32页。】在一定程度上,现有民法学说业已脱离了中国现有法秩序,将私法自治提升到自然法原则的高度,因此并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其次,就民法与宪法的调整对象而言,在当前语境下,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并非二元对立,彼此之间也并非绝对分离,而是呈现出相互交融之势,此时,宪法并非仅仅调适政治国家,作为一种框架秩序,其业已成为整个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础,奠定了整个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秩序。【参见韩大元、林来梵、白斌等:《行宪以法,驭法以宪:再谈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7页。】照此意义,宪法理应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础”,【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1年第11期,第8页。】仅仅将宪法认定为公法规范,未免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此外,现代宪法本身是一部权利保障法,无论其在内容上如何设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都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其中,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一个系统功能,不仅需要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平等私主体之间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同样至关重要。
最后,就民法和宪法的价值关系而言,相较于民法独立说和民宪平行说,赋予宪法以优位地位更能够在价值层面上树立法制统一和权利保障的理念。通过在《民法典》中规定“根据宪法”,则不仅可以阐明民事部门法间立法权的逻辑关系,同时可以明确规范效力的来源,【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6页。】无疑更加符合现代宪法理念。
由此可知,当前无论是民法学界抑或是宪法学界,对于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界定似乎都存在一定主观性和片面性,即更多是从本学科视角出发,带有很强的学科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不仅是视角上缺乏一致,对于这对关系的解释也缺乏方法上的统一。在笔者看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本非一个系统问题,必须采取客观、综合且全面的态度来理性看待。
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正当性基础
(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基础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规范层面上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备充分的形式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能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以及宪法性法律层面得到充分回应。
一方面,就宪法层面而言,《宪法》第5条“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条款对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予以了明确界定,【《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其中,享有立法权的主体的数量、权限以及行使立法权的方式等,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在此,根据凯尔森的“规范等级理论”,国家法律并非位于同一位面之上,而是具有一定的阶梯性质,并集中表现为“低级规范—高级规范—基础规范”,其中,后者直接决定了前者的创设方式和创设内容,并最终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和体系性的法律组合。【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3-194页。】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中国的基础规范,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所有法规范,都必须在《宪法》的指引下在法秩序体系内实现融贯,以此来捍卫法制体系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民法典》的立法依据和立法权限条款并非是独存的,中国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都明确在第1条吸收了本款内容。其一,就组织法层面而言,包括《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简称《监察法》)等都在一开始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部分在一开始未予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法,如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也将本款纳入了正式规定。其二,在部门法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簡称《刑法》)、《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等都在第1条明确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即便是在制定期间充满争议的原《物权法》,最后也吸收了这一条款。作为部门法,民法独立说、民宪平行说的观点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刑法》和《监察法》,但这两部法律最后选择了妥协。正如叶海波所言,在法律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是立法者依宪立法的自我确证和事实陈述,也是立法权法定(包括权源法定和法源法定)原则的规范要求。【参见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20页。】因此,通过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整体观察,《民法典》虽然同其他法律在规范领域和法律性质上存在不同,但是仍必须要在国家的统一法秩序中寻找到作为立法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的立法依据。
(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国家权力关系基础
探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能离开国家权力的配置关系。在中国,任何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受到宪法的约束和限制,立法权亦不例外。
一方面,从制宪权理论角度,可以认识限制立法权的必要性。制宪权是指制定宪法的权力,又被西耶斯称为原始的创造性权力,【参见[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国内在宪法学研究早期,对于制宪权下了诸多定义,如许崇德认为,制宪权是指制定和修改国家根本法,即宪法的根本性权力。【参见许崇德:《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朱福惠认为应该从内容、主体和程序这三个维度来界定制宪权,即制宪权是指规定国家基本制度、调整国家基本关系的根本性权力,是特定主体通过特定程序和方式行使的,区别于普通立法性权力的始源性权力。【参见朱福惠:《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徐秀义和韩大元认为,制宪权是一个综合体系,既涵盖制宪活动的事实,也包括宪法至上的政治权威。【参见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均强调制宪权的主权性、至上性和根本性。事实上,制宪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立法活动和立法权具有紧密的联系。换言之,虽然在制宪权概念出现之前,立法活动就已经在事实上存在了,但是制宪权概念得到承认之后,便呈现为主权性权力,立法权则成为制宪权所衍生、委托的下阶权力,自始至终接受宪法的监督和约束。此时,尽管国家呈现出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效力位阶上却等级分明,其中,宪法作为根本法,统领国家一切法律事项,调整国家法律关系,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法律则负责将抽象的宪法原则具体化为可供操作的法律规则。在立法的过程中,必须有效约束和限制立法权来保障以宪法为核心的法秩序体系的融贯性和规范效力。“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有利于在民事立法中,依据宪法规范和限制国家立法权,保障民事立法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从对议会民主的理论反思角度,也可以认识限制立法权的必要性。当今时代下,仅仅依靠多数主义的议会民主原则并不足以防范立法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毕竟议会行使立法权只能保障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却并不能保障立法内容的合宪性。同理,将《民法典》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诉诸代议制民主看似合理,但受制于种种因素,代议制民主也并非始终具有可靠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民主链条极有可能因为代表自身素质不够、代表存在独立利益、议会会期短暂、立法任务紧张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出现断裂,并最终制定出不正义的法律。除此之外,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国家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人民通过契约所缔结的结果,其中,人民作为主权者,享有国家最高的权力,行使包括制宪权在内的主权性权力。立法权则是制宪权所派生的下阶权力,即人民通过在宪法中设定立法权,委托特定机关从事国家立法活动。立法权是依据宪法而产生的权力,受宪法的约束,唯有国民拥有制宪权。【参见[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64页。】毕竟,法律很难完全反映每一个人的意志,而只能寻求其中的最大公约数。法治普遍性和权威性等品质在带来积极价值的同时,本身也导致一定的消极代价,即人民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对不正义的法律予以适当容忍。申言之,这种以“多数决”为特征的民主程序更多在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并不能够保障全体选民利益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极有可能忽视甚至是牺牲少数选民的利益,此外,即便选民民意得以有效传输,也不能证明所立之法一定是良法。
因此,通过在《民法典》中引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以有效监督议会立法权的行使,防止《民法典》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侵犯。
(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客观法”基础
在《民法典》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具备形式正当性,而且还具备实质正当性,且这种正当性更多来源于基本权利保障。众所周知,《宪法》第33条第3款的“尊重”和“保障”与主观法和客觀法相互呼应,【《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辅之以《宪法》第二章所规定的具体基本权利,共同从根本法层面构筑了中国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形成了一套基本权利的框架秩序。
事实上,在魏玛宪法时期,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并无太大威慑力,对于国家机关而言,其更多被视为一种价值裁量空间,只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目标导向作用。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更不能以此为依据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能被动地等待立法予以形成。但在二战之后,这种空洞的基本权利条款逐渐开始演变为直接约束国家机关的“客观规范”或者“客观法”。所谓客观法,是指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本身作为国家的框架秩序,包括立法者在内的国家机关必须积极遵从,即一切国家公权力都必须时刻接受这一“框架秩序”的约束,并尽一切可能去推动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5-26页。】照此意义,立法者所有的立法行为都被赋予了这一使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更是有义务去将宪法中的权利规范加以具体化。因此,在《民法典》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就可以被解释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始终将基本权利条款作为立法的考量因素,以推动基本权利的全面实现。立足于这一点,相对于宪法全方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民法则仅仅是基本权利保障的一个侧面,即是以保障财产权为核心的基本法。【参见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23-125页。】申言之,面对宪法这一权利保障的框架秩序,民法仅仅面向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保障,也仅仅是宪法民事权利的具体化,因此,在《民法典》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能够弥补宪法私法化的不足,还能为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奠定基础,使民事权利得到更为充分的诉讼法保障。【参见秦前红:《民法典编纂中的宪法学难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1-26页。】
此外,客观法秩序还意味着国家面对基本权利,不仅需要消极不作为,同时还需要积极作为,在平等私主体之间承担起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即保护公民免受平等“第三人”的侵害。毕竟,国家垄断了公民私力救济的权力,因此,当公民遭受平等第三方的侵害时,立法者当然负有义务来改善这一现状。申言之,随着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国家早已不是侵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唯一主体,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有可能遭受来自国家以外的第三人的侵害,【参见王进文:《基本权国家保护义务的疏释与展开——理论溯源、规范实践与本土化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107页。】来自企业、行业等由私主体造成的威胁和灾难较公权力更为严重地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权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基本权利保障难题。【参见龚向和、刘耀辉:《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59页。】期间,以科技变革为主的社会变化对传统权利格局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科技等现代技术的影响下,相关私主体之间的利益侵害现象也愈发频繁。【参见侯学宾、郑智航:《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提升与未来关注》,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第97-98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显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页。】截至目前,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都已经意识到了国家保护义务的重要性。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德国诞生于1974年德国联邦法院
“第一次堕胎案”判决,此后,经历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施莱尔绑架案”“航空噪声污染案”“第二次堕胎案”以及“航空安全法案”而不断丰富,【参见王进文:《基本权国家保护义务的疏释与展开——理论溯源、规范实践与本土化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107-109页。】业已形成了一套与基本权利防御权相并列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相关学者也纷纷发文对国家保护义务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阐释。如陈征主要介紹了国家保护义务的基本框架,并初步预测了国家保护义务功能在中国的制度化;王锴围绕《宪法》第49条,系统论述了国家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义务;龚向和则主要阐明了国家保护义务的层次以及国家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的关系。【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3-60页;龚向和、刘耀辉:《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62-65页;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8-9页。】不同于防御权功能的双方关系架构,在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之下,则往往需要将视角置于国家、私人受害者、私人侵害者三方关系架构之下进行考量。此时,国家需要从基本权之敌转变为基本权的保护者,对基本权主体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进行调和:一方面,国家与受害者之间形成保护义务链条。国家通过完善立法,为受害者提供完善的权利保障框架,以此形成公法上的权利给付体系。另一方面,国家和加害者之间形成防御权链条。国家在对加害者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同时,还需要恪守防御权的保障框架,以此避免形成对加害者自由权的不当限制。此时,基于上述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民法典》作为私权领域的基本法,当然有必要在宪法指示下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进而改善不对等的私权结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积极规范意涵
民法和宪法纵然存在一定区别,但二者都蕴含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指向,此时,面对宪法私法化的制度障碍,如何让部门法承担一定宪法功能,【参见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宪法功能——超越宪法施行法与民法帝国主义》,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40-47页。】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抽象的原则转为在规范层面和技术层面可供操作的规则,就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建构民法与宪法的动态关系,还能够突破宪法和民法各自的局限性,通过协同配合,最大程度上推动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毕竟,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分殊仅是表面现象,但在价值层面却是殊途同归,即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此时,“根据宪法,制定民法”本身具有一定的积极指向,要求《民法典》积极落实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性保障功能以及国家保护义务功能。
(一)《民法典》积极落实制度性保障功能
基本权利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定基本权利能否实现,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往往都需要依赖一定的制度。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功能要求各个权力机关理应积极建构各项制度,从而为基本权利奠定制度依托。期间,立法者作为制度形成的前端,往往负有重要使命,这意味着立法者面对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必须积极通过立法建构各项基本权利制度,从而促使基本权利的内涵得以全面实现。在这一意义上,“根据宪法”首先意味着立法者积极完善立法,建构各项基本权利的保障制度。考虑到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这些制度至少包括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财产权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个人信息保障制度等。在此,为了系统论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制度性保障功能,不妨以婚姻制度、财产权制度以及个人信息保障制度为例加以阐释。
首先,就婚姻制度而言,《宪法》第49条的“婚姻家庭”条款与《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存在密切关联,【《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后者通过在《民法典》中对宪法条款加以制度化,能够和《宪法》形成完美呼应。此时,包括结婚自由制度、离婚自由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制度等,就构成了整个婚姻家庭条款的制度性保障。正如在施密特看来,制度性保障有着天然被国家立法限制的属性,这些制度仅仅是在国家之内存在,是一种受到法律承认的制度,而非原则上不受限制的自由权。【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页。】照此意义上,婚姻自由当然构成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部分,因此其并非可以主张之主观权利,而是国家应予以保障的制度安排。“没有法律,婚姻自由将无从谈起。”【参见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2-13页。】显然,《民法典》通过将宪法条款加以制度化,有效保障了婚姻制度的核心内容。
其次,就财产权保障制度而言,现行《宪法》明确将财产权纳入“总纲”,并在第13条就财产权进行了系统规定,【《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表明私有财产权保障业已成为一个宪法议题。但宪法财产权条款毕竟属于宪法统领性规范,《民法典》有关其规范结构、保障范围以及判断标准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了关于财产权的定性与保障。毕竟,立足于《宪法》第13条第1款“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只要公民财产符合“合法性”要件,就自然属于宪法财产权的范畴,并受到宪法的积极保障。但“合法”一詞的外延极其广泛,如果缺乏良好民法物权制度的“制度性保障”,宪法财产权规定就很容易陷入空中楼阁般的尴尬境地。基于此,《民法典》对财产权保障制度进行了系统规定,将抽象的宪法财产权条款通过代理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继承制度、产权制度、物权法制度等进行多个角度的细化,不仅如此,还紧紧追寻大数据时代的特质,在《民法典》第127条中设定了有关数据财产和虚拟财产的保障制度。【《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尤其是将虚拟财产纳入财产权的范围之中,不仅增加了物的种类,促使财产权形态由有体化过渡为无体化,而且这种物质形态上的拓展,能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社会变迁对现有财产权制度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承认虚拟财产的价值,还可以为今后财产客体的变迁提供思路,即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是网络虚拟财产,诸如其他形式的财产,如果具备宪法价值,同样应该被纳入宪法财产权的范畴之中。
最后,就个人信息保障制度而言,《宪法》在第38条和第40条分别就人格尊严和通信自由进行了规定。【《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但权利的外延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发展导致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在既有权利无法满足利益诉求时,便自然产生了新的权利需求和权利主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数字经济的高度繁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据资源在国家生产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以科技变革为主的社会变化对公民个人信息保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科技等现代技术的影响下,数据权需求随之产生,【参见侯学宾、郑智航:《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提升与未来关注》,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第91页。】相关私主体之间的利益侵害现象也愈发频繁,这些个人信息保障需求势必会反映到立法层面中去。普通个人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红利之时,也时常伴随着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公开与权利的让渡。而互联网企业作为数据资源的集散地,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在数据处理和使用方面往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囿于上述宪法条款的抽象,如果缺乏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那么公民的人格尊严和通信自由将始终无法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民法典》单独设定一章“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并就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分析乃至交易进行系统规定,通过对信息交易制度、处理制度、责任制度的建构,较好地厘清了数据所有者与数据使用者的关系,使公民的个人信息保障具备了制度性依托,这也是制度性保障功能的鲜明体现。
总之,宪法和民法在基本权利保障领域殊途同归,在宪法确立基本权利保障的事项和目标之后,基本权利的客观法秩序要求立法者设定专门的基本权利保障制度,从而为特定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制度依托。【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页。】
(二)《民法典》积极落实组织保障功能
除了制度性保障之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时意味着《民法典》必须为相关基本权利提供相应的组织与程序保障,这也是客观法秩序下的另一重要功能。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既然基本权利约束包括立法者在内的国家公权力,那么积极的组织和程序保障就构成了基本权利客观法功能下课予立法者积极形成制度的义务,同样是为追求基本权利本身的达成。【有关积极/消极的制度性保障这一说法在中国主要是由欧爱民引入,此外,许育典也认为制度性保障存在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制度性保障基本就是上文中施密特所说的制度核心不得侵犯,而积极的制度性保障是课予立法者积极形成制度的义务。参见欧爱民:《德国宪法制度性保障的二元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17-124页;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16-119页。】
就组织性保障而言,在《民法典》提供制度性保障之后,还必须依赖特定的主体用以执行或者监督,如此才能让制度性保障功能充分落地。事实上,现有《民法典》的很多规定都体现了组织性保障的功能。例如,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保障而言,《民法典》考虑到这部分人智识不够成熟,特别规定包括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门等在内的组织,保障其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民法典》第24条规定:“……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
状况,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条规定的有关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此时,如果缺乏这些组织的帮助,在必要情况下就很难实现自身的权益保障。此外,为了保障业主的权利,《民法典》还专门设置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这些组织,用以制定特定组织章程、选定物业服务机构、管理小区维修资金等事项,不仅如此,为了强化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权威,还赋予了其决定对于业主的法律约束力。再比如,为了保障特定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民法典》规定,进行临床试验理应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同意,从而有效改善公民与医疗机构的不对等地位。【《民法典》第1008条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书面同意。”】
(三)《民法典》积极落实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
诚如上文所言,不同于传统视阈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简单划分,在大数据时代下,市民社会并非始终以对等私主体的形式呈现,其内部固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已然发生变化,一些以企业和行业为代表的准权力机构开始愈发庞大起来,这些准权力机构的生成逻辑虽然不同于国家机关,但却能产生出类似于国家机关的权力统治模式,时刻影响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此时,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下的一种具体功能,不同于广义上的组织性保障、制度性保障。国家保护义务由于仅仅面向来自私主体的侵害,因此保护义务首要约束立法机关,在内容的设定上也更多以立法保护为主,行政和司法保护为辅。毕竟,健全的立法体系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前提所在,立法者在前端审慎平衡不同权利主体的基本权利冲突,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设定一个权利保障的基本框架,可以有效约束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此前,学界中张翔列举了两种典型的国家立法保护义务,即刑法上的保护和警察法上的保护,前者用以针对不法私主体的犯罪行为,后者则主要针对不法私主体的紧迫侵害行为,【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8页。】但随着自由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过渡,当前仅仅通过刑法和警察法的立法保护已经远远不够,唯有在宪法的指引下,建立起以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法以及基本权利专门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才能更好地保护基本权利主体免受私主体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立法者的立法保护义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动态且持续的过程,申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法律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立法者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必要时甚至要制定新的规范,否则同样违反了保护义务。【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5頁。】
此外,《民法典》“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是一种价值上的宣誓,本身还意味着立法者在履行保护义务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一套明晰的、类似于比例原则的标准用于自我评估。国内外学术界虽然意识到了国家保护义务的重要性,但对于评估立法者履行保护义务是否达到宪法要求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基于此,“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主张立法者履行保护义务需要遵循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探寻该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并系统建构该原则的适用标准,以期为立法者更好地履行保护义务提供宪法指引。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是指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判断国家机关是否积极作为,是否达到了宪法所要求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根据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无论基于社会现实需求还是中国宪法给立法者提出的要求,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都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适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来判断立法保护是否达到了宪法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推动合宪性审查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在适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时,既应当强调宪法对立法的指引,又应当认同宪法秩序要通过立法形成。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作为宪法给立法者提出的最低保护要求,限于对被保护人期待可能性的审查,既能够确保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发挥应有作用,又能充分尊重民主立法。
四、“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消极规范意涵
事实证明,法治蕴含的形式主义价值虽然有助于立法权的合法性,但却并不能够保障《民法典》本身合乎宪法秩序。与之相应,法律至上并不等同于《民法典》的合宪性,而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秩序的重要手段,实质法治主张《民法典》要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宪法框架秩序。基于此,“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是合乎法律以及对法律的机械适用,立法者以及《民法典》本身也必须合乎宪法。毕竟,前述立法权的统一和法律体系的内部统一只是法制统一的理想状态,一旦出现抵触和违反,相应的纠偏机制就必须随时出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要求《民法典》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应严格恪守宪法框架秩序的消极边界,始终遵循合宪性解释方法以及合宪性审查标准。
(一)《民法典》应严格遵循合宪性解释方法
虽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立法层面的规范要求,但是“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意义不仅限于立法过程之中。由于立法者理性的局限性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漏洞,需要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法官的个案裁判来及时填补法律漏洞。这一过程不仅是法律适用的过程,更是立法过程的延续。
在《民法典》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以为法律漏洞填补中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提供法律依据。【参见王利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4-75页。】宪法对于民法的解释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在采取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法官甚至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来进行案件的审理,但就中国而言,则可以通过合宪性解释来强化宪法在《民法典》中的适用。【中国司法实践也已经逐步采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在其“裁判依据”部分,尽管依然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也明确规定:“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被看作是对《民法典》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认可。】合宪性解释本就脱胎于基本权利的审查,健全的解释规则得以确保《民法典》规范更加符合宪法,避免因为动辄出现违宪嫌疑而降低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本身是法律解释而非宪法解释,解释对象也是法律而并非宪法。根据不同的适用目的,可被区分为解释规则、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三个层次。【其中,在解释规则层面,合宪性解释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的影响;在冲突规则层面,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在保全规则层面,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性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84页;转引自李海平:《合宪性解释的功能》,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44页。】由于在不同层次适用合宪性解释意在实现的目的有所差异,评价法律解释是否具有合宪性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事实上,《民法典》的法律解释结论是否符合宪法的判断标准与宪法所保护的价值息息相关,中国宪法的平等权条款、财产权保障条款、人格尊严条款等都可以折射到《民法典》的适用过程中,促使对《民法典》的理解和适用最符合宪法的精神指向。毕竟,对于权利规范而言,基本权利是宪法所期待实现的具体价值,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结论被具体化为符合基本权利的解释结论,换言之,合宪性解释就是合基本权利的解释。
当解释者适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法律解释结论后,合宪性解释要求解释者在多个解释结论中筛选出符合宪法的解释结论,解释者通常需要采取选择或排除的方式确定《民法典》中法律文本的具体含义。【“这就是说,如果某个《民法典》解释结论符合宪法,就应当选择其作为解释结论;如果所作的法律解释违反了宪法,就应当予以排除。”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7页。】申言之,解释者需要对各法律解释结论的合宪性逐一作出判断,才能最终筛选出符合宪法的解释结论,冲突规则层面的合宪性解释有一定的合宪性审查意味。【参见李海平:《合宪性解释的功能》,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51页。】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宪性解释并不是对《民法典》是否符合宪法的判断,而是对《民法典》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判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解释者根据传统法律解释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出的各法律解释结论。解释者对《民法典》权利规范的合宪性解释涉及对公民法律层面权利限制程度的合宪性审查,故在对权利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中向下融入整套法规范体系的价值秩序是宪法层面所设定的基本权利。与之相应,合宪性解释意在规范解释者的审查行为,避免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违宪法律解释结论的侵犯。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合宪性解释并非完全杜绝了《民法典》的解释和适用空间,尤其是对于立法者而言,宪法作为一种框架秩序而存在,立法者在这一框架内享有较大活动空间以及自主裁量权,合宪性审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对其价值选择和判断予以充分的尊重。【参见陈征:《论比例原则对立法权的约束及其界限》,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151-152页。】这就意味着当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秩序被立法者合宪地具体化为法律秩序时,合宪性解释主体应当遵守这一秩序,尊重《民法典》的规范基础和价值意涵,进而选择不超出立法者意志的解释结论。
(二)《民法典》应严格恪守合宪性审查标准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本身具备授权与限权的双重属性,其在宣誓《民法典》合法性与正当性,赋予其法律效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民法典》必须恪守宪法的边界。毕竟,从宪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宪法作为一种框架秩序,在框架秩序之内,立法者享有自主的活动空间,但在框架秩序之外,则是立法者的禁足之地,否则就是对宪法权威和尊严的亵渎。申言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虽然设定了《民法典》的形成空间,但也从侧面划定了其《民法典》规定事项的界限,一旦跨越这一界限,这就意味着其违反了宪法的不抵触原则,侵蚀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那么,《民法典》中“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要配套何种标准来进行合宪性审查呢?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主体合宪性标准、内容合宪性标准、方式合宪性标准以及价值合宪性标准。
首先,就主体合宪性标准而言,“基本法律”是《宪法》与《立法法》界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民事立法权限的重要标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共同作为立法权主体,但其民事立法权限却存在迥然区别,根据《宪法》第62条第3项以及第67条第2项、第3项,【《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发现“基本法律”是界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民事立法权限的重要标准,不仅如此,这一法律术语背后还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事立法权是存在边界的。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将立法权局限于代议机关与政府之间进行讨论,但代议机关不仅仅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其内部往往有着不同的机构和职能划分,在中国则总体上分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但二者并非同一立法权主体,这集中表现为二者在立法代表性、立法权内容和立法程序上的重大差别,并由此决定二者民事立法权具有不同的宪法效果。对此,有必要转换视角,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置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进行理解,即其不仅要求民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加以规定,还要求事关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民法基本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就非基本构成要素制定民事非基本法律,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民事基本法律的部分修改权。
其次,就内容合宪性标准而言,立法权作为制宪权的延伸,其在内容上必须依照宪法设定的框架行使。事实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本身内含着对立法权的监督和防范。正如在孟德斯鳩看来,基于民主的立法权实际上更具扩张性,很容易僭越其他两权的内容。【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1页。】
制宪者们尤为重视对国家立法权的防范,例如麦迪逊指出,在代议制的共和体制下,对行政长官的权力范围和任期都有仔细的限制,反观立法者则更有机会接近人民的钱袋,并通过其掌握的财政权迫使其他部门就范。有鉴于此,只有给予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主管人员以一定的手段来抵制立法部门的侵犯,才能更好地防范立法权。【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294页。】总体而言,分权制衡理论是消极权力观的产物,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更多带有防范和抵触情绪。民事立法权作为立法权的基本形态,防止议会多数主义对少数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无疑至关重要。由此,“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意味着《民法典》在内容设定上需要遵循重要性法律保留理论,即以对基本权利的影响为标准,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之实现有重要影响的立法事项,如国家任务之演变、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等都属于宪法保留的范畴,理应由宪法进行调适,而不能放任《民法典》自由裁量。
再次,就方式合宪性标准而言,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督促立法者积极履行立法义务,立法者的民主政治空间理应受到宪法的约束,即特定事项不仅在范围上属于立法者的保留空间,在方式上也必须由立法者制定法律,而不能随意通过授权的形式制定行政法规。此前我们将法律保留理论完全视作立法者的民主政治空间,这并不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建构完善的国家民主法秩序,因为其忽视了法律保留理论对于立法者自身的约束,一旦立法者怠于立法,习惯性以授权的方式行使立法权,难免会架空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法律保留制度本身也就徒有虚表了。
最后,就价值合宪性标准而言,国家借助《民法典》实现“定分止争”非是盲目状态下的全方位回应,而必须跳出消耗与成果的比率关系,综合考量立法权的功能边界。这尤其适用于国家调控,即当国家试图通过特定立法功能来完成国家任务时,必须综合考量这一任务是否有必要,如果非完成不可,是否必须通过民事立法权这一形式,交由市场或者私人能否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显然,鉴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之时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故借助民事立法权仅仅是补充性和辅助性手段,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竞争机制始终是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工具,它能使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社会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率。因此,为了不影响这种市场均衡,“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要求国家行使民事立法权时必须审慎考量,严格遵循立法中立性原则,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任务,以此避免因立法调控不当而改变有效率的经济活动,进而对社会主义市场运行产生不良影响。
总之,通过在《民法典》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以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直接有效的规范依据,即根据制宪权理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會本身也要在宪法秩序内行使立法权,而不能以《民法典》形式外观的合法性来豁免实质内容合宪性的要求,一旦其立法权行使偏离宪法设定的轨道,就必须适时启动合宪性审查机制进行纠偏,【参见苗连营:《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77页。】以此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宪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五、结语
在《民法典》编撰过程中,“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表述始终存有争议,并集中表现为民法独立说、民宪平行说与宪法至上说三种观点,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统一,这些认知或多或少存有不足。事实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规范层面上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备充分的形式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不仅能够从《宪法》《立法法》以及宪法性法律层面得到法制统一的证成,同时还能从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层面得到积极回应。同时,相比于民法至上和宪法至上的地位之争,笔者更倾向于立足于宪法教义学,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抽象的原则转为在规范层面和技术层面可供操作的规则。毕竟,民法和宪法纵然存在一定区别,但二者都蕴含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指向,此时,面对宪法私法化的制度障碍,让部门法承担一定宪法功能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建构民法与宪法的动态关系,还能够突破宪法和民法各自的局限性,通过协同配合,最大程度上推动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毕竟,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分殊仅是表面现象,但在价值层面上却是殊途同归,即都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理应切实发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效力,即一方面,在积极意义上,“根据宪法,制定民法”要求《民法典》积极落实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性保障功能以及国家保护义务功能;另一方面,在消极意义上,“根据宪法,制定民法”要求《民法典》应始终恪守宪法框架秩序这一基本边界,在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严格遵循合宪性解释方法以及合宪性审查标准。总之,通过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行宪法教义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同时还能切实发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指示作用,
今后理应拓宽研究样本,继续强化部门法宪法教义学的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完善提供规范导向与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