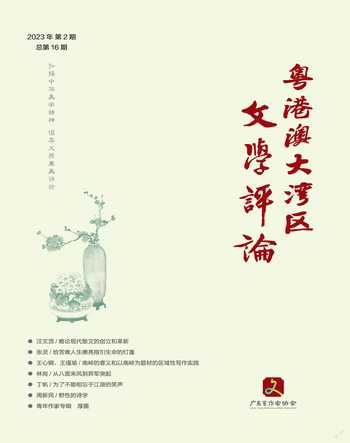文化的拼图
厚圃
一、童年的“缺失”
我的故乡在潮汕平原,老屋紧挨着樟林古港,樟林是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潮汕商帮、“红头船”的历史和各种传奇故事萦绕着它,也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娱乐,白天,我和小伙伴们大都奔跑于荒山野地,捕鱼捞虾打泥仗,身上糊成与土地一样的黑褐色,到了傍晚,我们三两下扒光饭碗,好悄悄紧跟某个乡里的大人混进附近一家露天剧场,坐在花岗岩做成的条凳上看电影,听潮剧,时不时还有艺人说书。更多时候,我们聚集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听乡亲们讲“古”,那些奇闻逸事牢牢地吸引着我,尤其是英雄传奇,年少的我常常臆想着自己是个游侠,可以在“江湖”上纵横驰骋。
我一度以为,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和潮汕平原大同小异,直到去北方念大学时才发现,自己的“潮汕普通话”别人居然听不懂,需靠“纸笔”问路。在北方四年,我切身体会到中国之大,南北差异之悬殊,然而这些巨大差异并未给我和老乡们带来太多不适,相反还引诱着我们欢畅地融入其中,好像大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于是静下心来思考“民族”啊“地域”啊这些概念,哪怕是族群不同、语言不通、习俗迥异,但总有什么是相同相通的,那应该就是我们整个民族血液里亘古不变的东西。
伴随着成长我渐渐明白,现代人所谓的“江湖”,并不是我小时候所幻想的行侠仗义快意恩仇,而是生活对你的零敲碎打,直到把你逼进夹缝犄角不得不向现实俯首听命,而那个少年们都曾有过的江湖侠客梦注定要陨落!没有人能逃脱物质世界近乎残酷的碾压,至于那不管不顾的青春早就悄然逝去,眼看着时光如沙从指缝间漏走,我开始竭力想要留住点什么。虽然已是21世纪,我的潮汕乡亲依然说着最接近于古语的潮汕话,喝着烫嘴的工夫茶,看着传承下来的“老戏”,经年累月地“拜老爷”,不管到了哪里,只要喊一声“家己人”,就有乡亲出手相帮……这些原本在我眼里习以为常的东西慢慢地变得不再轻淡了,我开始珍视故乡的与众不同,珍惜故乡依然保留着的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我甚至相信这些传统中饱含着中华民族最精彩最璀璨的文化。
“故乡”这个词,对于今天生活在深圳的我来说是具有多层指向的,既有地理学、生命学意义上的具体指归,又包含着历史、精神、艺术等精神指涉和情感认同,它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界定,颇能引发共情和诗意的想象。故乡对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应该也必然具备多重的象征意义,可能象征着童年的美好,或者对某个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记忆;也可能象征着自我的理想化人格,或者精神的故园。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故乡”不同的语义,就我自己,“故乡”既是回忆的存在,也是真实的存在,既是理想和现实的交融,也是希望之所在,甚至可以说它是世间一切美好和希冀的代名词,也是我“信仰”中的一个精神图腾。我离开得越久,走得越远,那种想要叙述它的愿望就好比银器,因不断的擦拭而愈加光亮。
出门在外多年,值得庆幸的是,那个乡下少年的江湖英雄梦还没有碎,纵然现实空间不允许我自如腾挪,在精神世界里我起码还能无拘无束,策马奔腾。
有人说,在每个人成年之后的潜意识里,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解释为在试图弥补童年的缺失。作为现实世界的造梦者,我陆续创作了一些与“故乡”相关的散文和小说,比如长篇小说《结发》《我们走在大路上》,中篇小说《喜娇》,短篇小说《永生》《成人礼》等,它们不光是我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对故乡文化历史的梳理和怀恋,更是助我找到人生中缺失的那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故乡完整了我的文学,而文学完整了我的人生。
二、创作的“私心”
在我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陆续出版过几本书,得到过同道与读者珍贵的反馈,这些都汇成了激发我的力量,我更加埋首于潮汕地方文献和与潮汕相关的研究论文上,因为我知道,我的“百宝箱”一直还没真正打开,这个箱子里装着潮汕文化的精髓,也装着我窥探世界的第三只眼。这期间,我读了不少东西方大师的作品,他们对文化的归纳总结更新了我的认知,让我更加明晰地认识到在中华文化多层面多意义多种表现形式当中,似乎还差了一块关于潮汕文化的拼图。这冥冥中的召唤催生了我的灵感,而家乡的红头船便是我冒险“出海”的不二之选,樟林古港就是我的舞台,我要在這里为故乡唱一台真正的激情“大戏”。这是故乡给我独有的馈赠,而我也应该且必须有所回馈。
深圳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也在这出大戏中起到关键作用。应该感谢深圳,正是由于它足够现代,没有悠久而沉重的历史包袱,才让我有勇气站在这个“新世界”的入口,去反观故乡的近代历史,重构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那颗埋进思想里的种子经过了漫长的浇水施肥,终于拱出了土壤迎来了阳光雨露。“樟树埠”在我脑海中渐渐成形并述诸笔端,它跟清代的樟林一样,是由本地人外来人共同组成的一个港口,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和地方文化在此交织碰撞,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沿海城市的真实写照。“樟树埠”跟深圳也十分近似,商业发达,南来北往,多元文化在此交融激荡,包容开放,崇尚自由与创新,支持梦想与传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樟树埠”就是那个时代的“深圳”!
《拖神》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对我来说算是一次探险。约瑟夫·坎贝尔说:“突破个人局限的巨痛乃是精神成长的巨痛。艺术、文学、神话与礼拜、哲学及苦修的磨练,都是帮助个人突破局限的视域,进入不断扩大理解领域的工具。”写长达60万字的作品,要说没有纠结和挣扎,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大决心和大格局,也是难以企及的。当然知识储备也很重要,若是“供养”不足,很可能就会“烂尾”。所以大到历史事件,小至一街一景,甚至微缩到一个点心,一种药草,都得尊重历史恢复原貌。这个知识储备的过程是漫长而细致的,之中得到过不少师友的支持,像我的师弟、中山大学胡锐颖博士就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而我的父亲,见到旧书摊就赶忙凑过去,生怕错过任何有用的,在家乡为我搜罗了数百册与乡俗风情相关的书籍。有了足够多的资料史料还不够,因为我不是写说明文或者百度词条,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除了还原时代的场景外,更需要灵魂的加入,否则就会变得枯索无趣。我一直觉得,中国古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一个“化”字,只有嚼烂了手头的材料吞进肚子里,才能将它“化”为自己的血肉,让史料和资料“活”起来,“站”起来,直到行动自如。
《拖神》的创作过程,也是我在写作方法上的全新探索和重构。之前我的作品虽然也引起过一些反响,但写法还是比较传统的,这次,必须拿出更加新颖的构思。我的设想是,小说的内容尽量涵盖潮汕文化的方方面面,力求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那种类型。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能脱离小说的本质,必须以故事情节人物的发展为基础,所以创作时又要格外警惕主次不分,喧宾夺主。也就是说,小说的脉络要清晰,结构要稳固,不管是单线还是多线,三维还是多维,都应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杂而不乱,多而不散,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却又必须围绕着想要表达的精神主旨。同时,因为这部小说篇幅较大,对我的耐心和思维逻辑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经过多番思考反复推敲,我决定采用多维的结构来搭建这部小说的框架,以人鬼神三重视角展示天地间“人”的伟力。全书共十三章,分奇数章和偶数章两部分,奇数章为神鬼视角,偶数章为凡人视角。奇数章是神鬼独白,是“诗”,偶数章则是历史背景下潮汕商帮的命运与传奇,是“史”。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的奇数章和偶数章形成了多个“声部”,我很喜欢这种归纳,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正是有意设计这样的回环,形成一种“复调”式的咏叹,既喧嚣又和谐,而人便在这喧嚣的复调中成长,立于天地间且最终超越神鬼。
如果从时间序列来说,小说既是写过去,也是写现在,更是写未来。说它写过去,是指它写的大多是已然发生的事;说它写现在,哪怕是历史小说也是为了借古鉴今,反思当下;说它写未来,是希望能够警醒世人和读者,未来的人生该如何度过。《拖神》也是如此,同时它还夹带了我的一点“私心”。我在书中对潮汕文化的挖掘和追问,其实也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的追问,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否离得开传统的影响?而在由地域文化所组成的整个民族文化版图中,潮汕文化不仅不该缺席,还应当放射出它独特的光彩。我的这部作品或者说一家之言,设若能够为弘扬潮汕文化起到一点作用,引发外界对它的关注,最终能在文化的版图上拼上这么小小的一块,那么我的这个“自私”的愿望也就达成了。
三、隐藏的“神性”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意识流作品,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在创作《拖神》时,我并不想一味地模仿马尔克斯,我写的是中国的乡土,写的是我的故乡,我当然要寻觅具有华人文化特征的东西,我想创作出中国化的“魔幻主义”,也可以叫它“民族魔幻主义”。放眼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地缘特色,中国的乡村则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皈依之所,即便是像我这样的“深圳人”,又或者是在深圳出生长大的“00后”,身上也都携带着这种“乡土”的记忆和痕迹,这是融入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哪怕有一天“鄉土中国”在形式上土崩瓦解,但作为一个民族的魂魄是永远抹不去的,而我想要追寻的就是这个“魂魄”,我想把它从历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只有看清自己的来处,才能知道自己的去处!
潮汕平原的“近代发展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高度浓缩,我选择从我熟悉的地方出发来回溯整个民族的过去,希望通过我的解构和重铸唤醒民族的古老之魂,让它走出阴影,和现代世界发生冲突碰撞。所以说,这部小说不只是披着魔幻的外衣,它所呈现的是当下世界的真正“魔幻”之处,是自然和超自然的以及人类的本质、意识和组成世界序列的“超魔幻”,如果读者能够真正读出这个民族的“超魔幻”,那对我无疑是最好的鞭策。
鲁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有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在《拖神》创作中,与其说我在写潮汕文化,写潮汕族群,不如说我在写一个大写的“人”字。我不厌其烦地在人神鬼的关系中“神话”人,召唤着人类蓬勃的生命力,以唤醒每个人心中隐藏的“神性”。我在小说中所虚构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既是困顿中的众生,更是挣扎于欲望和诱惑之中的众生,这其中,最让我醉心的是以陈鹤寿为代表的平民英雄谱系,他们在多灾多难的大时代中不屈不挠地抗争,最终挣脱了命运的羁缚。哪个时代都有个体的挣扎和无奈,然而只要有陈鹤寿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便可稳稳立于时代洪流之中,不被裹挟,也不被诱惑,活出宇宙间这个大写的“我”来。
从有人类历史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是潮汕平原还是中国的其他地方,世界的本质似乎从未变过,人的本质也从未“现代”过,在这个语义之下,《拖神》不再是某个地域的作品,潮汕平原只不过是它的一只“眼”,通过这只眼,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够看清生活的本质,更多地思考信仰和时间这类永恒的话题,通过关注自身的命运和个体存在的价值,唤醒心中的“神性”,从而在泥沙俱下的时代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在现实与梦想间找到自己的支点,不惘然一生。
作者单位:深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