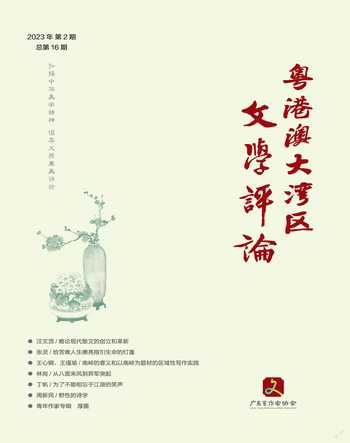为了不能相忘于江湖的笑声
主持人语:吴周文教授是著名的散文研究学者,同时与广东文坛和出版界多有交集,建立了深厚情谊。2022年4月,吴先生遽然逝世,乃散文研究界的一大损失,令人痛惜。值吴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特约丁帆、王兆胜、陈剑晖三位学者撰写怀念和研究文章,以示对吴周文先生的深切缅怀。(陈剑晖)
小引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作为一个江湖中人,我最不屑庄子的这种故作高深的玄学,因为他轻轻地抹去了人生中最柔软,也是最坚硬的那个人性的驻留。
这些年,我的师辈、我的同辈,甚至我的晚辈同仁与友人都一个个逐渐离我而去,在悲痛与思念之余,总想写下一点文字,以寄托我的哀思,可是最想写的东西却不能写出来,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最遗憾的是,我最熟悉的老师董建先生去世时,许多报纸、杂志约请我写一篇纪念文字,我提出了两个条件:字数在一万字以上;内容不能做伤筋动骨的删除。前者连南方的一个著名报纸都没有答应,后者是许多刊物都万万不能答应的。其实,我想写出一个经历了两个大动荡时代学人灵魂深处的真情实感来,写出那个活生生的、没有脱离“低级趣味”、内心既充满着自信,却又天真幼稚的真人。我甚至征求了董晓的意见,我文中会写到董先生的私生活,董晓毫不犹豫爽快地说:照写不误!然而,几年过去了,我的腹稿打了一遍又一遍,却无从下笔,倘若我违心地写一篇肤浅的纪念文字,那是对逝者的不敬,也是对历史的亵渎,因为我并不想以相忘于江湖的绝情了断我与逝者永远的精神依偎。
这次,那个叫我“小老弟”的吴周文先生去世了,北京和广东的散文研究大家王兆胜与陈剑晖先生约我写一遍纪念吴周文先生的文字,作为一个曾经在扬州师院读书时的晚辈学生,同时也是与我在学术生涯中过从甚密的性情中人,更是对我的所谓散文随笔创作进行细读研耕的评论老将,吴周文也是我无法相忘于江湖的先生。
他的病故是突然的,那一天,张王飞先生电话中告诉我,吴周文先生住院了,我们商量抽空去一趟扬州探望;过了几天,得知他已安然无恙出院了,心中不免庆幸;又过了几天,突然传来他瞬间离世的噩耗,莫名惊诧之余,不免黯然神伤起来。
与吴周文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了,那是我在扬州师院上学时就久闻大名的杨朔散文研究专家,虽然他并没有直接任过我的课,但也是学生时代的仰慕的老师。当然,后来我对杨朔散文在文学史地位上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后来与吴先生友情的进一步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日上午,在寂静无声的图书馆里,我这个逃现代汉语课的顽主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虽然讨厌作家花了冗长的篇幅去描写地主奥勃洛摩夫在床上迟迟不起的细节,但是,他让我突然想起了阿Q,地主和农民不是一个阶级,然而,两个不同国别的作家揭示的国民性和民族劣根性难道不是相同的吗?一个奇怪的念头让我想起了一个伟人说过的那句并不引人注意的话来:地主阶级思想就是代表整个农民阶级的思想。于是,这种危险的思考让我徘徊彷徨于难解的困惑之中。
此时,一个精神矍铄的中年人轻声走到我的对面,打断了我的思考,他拿着一本书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读起来,我却不自然起来了,你想,一个陌生的老师坐在你的对面,那是一种无法对话的尴尬,我欲逃之夭夭,则又不敢冒昧,显出不敬。这时,他打破了尴尬的寂静:同学,你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我如实告知后,他说:我叫吴周文,是写作教研室的老师,我立马起身,表示敬意。他挥挥手,让我坐下,又补了一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于是,我开始如坐针毡,佯装看书,却一个字都无法入脑。
好不容易挨到了图书馆下班的铃声响起,我恭恭敬敬向刚刚认识的吴周文老师道别,飞也似的逃离了图书馆阅览室。从此以后,偶然在图书馆里碰上吴周文先生,我也绕道而行,并不敢直视先生的目光。他与图书馆里的几个男男女女管理员都很熟,经常站在高高的借书柜台边与那个面容像卡西莫多似的长者聊天,恰恰那个姓金的老头也是我所尊敬的长者,因为我十分惊讶地发现,每借一本书,他都能介绍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真是神了。后来我也将这个右派分子写进了《先生素描》之中,再后来,吴周文先生专门在一篇文章中纠正了我对他身世的误传,可见吴先生对他更加了解和佩服。扬州师院图书馆成为我与吴先生相识的起锚地,虽然有点尴尬与别扭,却也难忘。
70年代的扬州城并不大,出门便可遇见熟人,比如在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新华书店门前购买新印刷的《唐诗三百首》的长长队伍里,一眼就瞟见了吴先生精神抖擞的面容,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便有了一种读书人的亲近。在曾华鹏先生的客厅里也曾遇到过吴先生在那里高谈阔论的笑声,便又有了一种同道者的愉悦。
他虽然不是那种浓眉大眼的帅哥,但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却让人过目不忘,眼睛不大,但一到激情时,便瞪得圆大,放出咄咄逼人的光来。也许正是他特别的眼神和他滔滔不绝的精彩演讲,招来了许多听他课的学生,记得前一届毕业生中的一个南通籍系花就是他的粉丝,在我们这届学生中广为流传。
1983年结婚后,我住在师院筒子楼的一号楼里,每天中午到教工食堂去打饭,便会经常碰见吴周文老师,在排队间隙,我们常常聊学术选题问题,引得众人侧目相看。1979年我在《文学评论》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论文后,恰好,吴周文先生在1980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朱自清散文的评论文章,因此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聊天话题。
吴老师在他的随笔《品读三位老弟》中直接称呼我是小老弟,他大我近一轮,十一岁的年龄差,是一个称呼尴尬的辈分,在我心目中,我是将他看作老师的,所以我对他的称谓一直是“吳老师”,如今他已驾鹤仙去,也是我“先生素描”里的人物了,所以我改称他为“先生”,以示景仰。
我算是那个年代运气好的年轻学人,但在师长面前从未有过一丝僭越和骄傲的行为,因为是这个学校滋养了我,是这些老师孜孜以求的学术追求精神,感染鞭策着我不断前行,吴周文先生虽未直接任过我的课,但是他的刻苦精神也是激励我不敢懈怠的动力,作为长者前辈,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他近期的散文研究的学术规划,让我佩服之至,触发了我不得不思考自己对未来学术研究的整体规划。
20世纪的1984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叶子铭先生参加《茅盾全集》的编纂工作,整天埋头在朝内大街166号那栋楼房的书桌上做校勘工作。一日,吴周文先生来京拜访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恰好住在那个十分简陋寒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里,他乡遇故知,分外亲切,他是平生第一次进京,于是,我陪着他去天安门、去逛王府井大街、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观看内部电影。离京前,我俩相约去拜望《文学评论》的陈骏涛先生,因为陳先生是我俩共同的责编。
那是一个燠热的夏日,陈骏涛先生在距他家不远的一个小酒馆里请我们用餐,每人一大杯一升装的冰镇扎啤,我们边饮边聊,吴周文先生时而向陈骏涛先生请教选题的事宜,恭敬谦和有加;时而滔滔不绝陈述着自己论题的写作计划。啤酒加灌肠,很是尽兴,那是我在那个年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次畅饮畅叙,虽然是首都的路边小酒馆,微醺让我这个冷眼旁观聊天的晚辈,心也不禁热了起来。时间过去了三十八年,那一顿畅饮的扎啤味道还久久地在我的舌尖味蕾上萦绕。
1988年底,我终于走完了客居扬州十四年的历史,回到了家乡南京。“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小杜式感慨,则让许多人世人忘却了下一句的含义,我道是,此一句是我人生驿站面对时间年轮的难忘江湖。而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意境却是更能解释我离扬而去的心情,开始我以为“无赖”是“无奈”的误植,后来才知道此词乃有通假之意,便释然了,不过,繁华的大唐时代,文人骚客在扬州留下的多为男女情缘的眷恋,“萧娘”“桃叶”便是徐诗中的主题,而我留下的扬州眷恋却是江湖师友不相忘的义气情缘。
本以为我与吴周文先生的交往会在我离开扬州后慢慢淡化,孰料,他的77届几个写散文和搞散文评论的铁杆门生,却将我与吴先生的关系纽带越系越紧了,其中张王飞和林道立先生为最,他俩是吴周文先生散文研究的长期合作者,历时40多年之久,师生之谊情深意笃,恰恰他俩又是我四十年的故交同事。
每每回到扬州,有时他们就把吴周文先生请来一起吃早茶,共进午餐或晚餐,于是,便又开始聆听到了吴先生的高谈阔论和爽朗笑声,这让我想起了钱钟书在《说笑》中的两段话:“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用这两段话来形容吴周文先生的笑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熟悉他的朋友只要一听到他的笑声,就可以看到他在电光闪烁下的面孔,而那道电光就来自于他那双有点夸张的炯炯有神的眼神。用钱钟书引用“天为之笑”典故,总结成“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的“闪电”,是对吴周文先生讲课聊天时神情的绝佳描写,这是在许许多多学术讨论会上得以验证的真谛。在扬州、在南京、在北京、在广州……吴周文的笑声撒落在了全国各地的山川大海和江河湖泊中,但并不是我在少年时代看到的那本从《地下的笑声》中发出的幼稚拙劣的笑声,因为吴先生是真诚爽朗、发自肺腑的地上的笑声。然而,用“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来形容吴先生间或开启的口腔,显然就不合适了,因为长期抽烟的缘故,唇吻间闪出的是并无光泽且稀松的黄黑色牙齿。
吴周文先生倒是喜欢在席间随性喝上几盅的,虽然不胜酒力,但喝个一二两助兴,却是非常高兴的。啜饮之后,他的笑声更爽,谈性更浓,烟瘾更大,此时此刻,他喜欢谈文坛的花絮与掌故,听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微醺之时,便更喜欢将三字名字的晚辈去掉一个姓字,让学生们感到亲近和亲切,而像我这样姓名只有二字者,他也就从同志改为先生了,我一再强调我是晚辈学生,你直呼其名更为亲切。
未曾想到的是,这四年来,他竟然专门研读我的散文随笔起来了,这让我诚惶诚恐,甚至不敢阅读,一是因为他是我的师长,作序可以,写评论却折煞我也;二是我写散文随笔皆是出于好玩,用另一种形式抒发性情而已,尤其是纾解胸中之块垒,做曲笔的游戏,一旦被人揭开画皮,终究有些尴尬;三是自认为写就的散文随笔资质品味有限,均为博朋友同道一哂之文,孰料吴先生如此认真研读,真让我无地自容。2019年初,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先生“风骨”的敬仰与褒扬——评论丁帆的〈先生素描〉》一文,我不敢同意他对我文字的褒扬,因为我不配,但他最后一段的鞭策却切中我意:“他将‘先生们的生平事迹缩小在‘素描的叙述框架里,以求‘传略或‘小史的艺术概括;将对先生们的学理认知作为品鉴的放大镜,以求人格品藻理性穿透力的深刻;用智慧的修辞和感念的诗情,自由、洒脱地进行梦呓般的‘随笔,以求自我形式创造的高度自由。在丁帆,信手码字,手由心来,什么范式、什么陈规、什么戒律都约束不了他。极度的随意与太多的自由,便成为其‘素描文体最显著的特征。”去除其中的溢美之词,我以为吴老师对我写作初衷所要表达的内容和形式概括是十分准确的,虽然我还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但我深深地铭记了先生的期待,斯人已逝,笑声尚在,作为座右铭,这段话我谨记了。
同年,他又发表了《品味三位老弟》的随笔,紧接着,在2021年的《当代文坛》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学者散文与“中国问题”言说的先锋姿态——以丁帆、王尧为讨论中心》,其实,吴先生是以此为论述的切口,充分表达了一个前辈知识分子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再次呼唤。同年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的长文《丁帆“学者随笔”论》,也是如此这般地强调启蒙精神,使我感动不已。其中对我随笔写作的概括,呈现出的是一个师者敏锐的洞察力,二次启蒙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休克的点位抓得十分准确,让我不得不佩服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守护,知音和同道让我欣慰不已,尤其是最后一段,在他离去之后,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一句成为“一个直立行走的大写的人”让我们醍醐灌顶。
2020年5月23日是吴先生80 岁寿辰,那正是我刚刚在5天前走完68个岁月的生日纪念,张王飞先生约我一起去扬州给吴先生祝寿,可当时正值一个博士答辩会议走不开,错过了此次聚会的机缘,不过我让王飞捎去了一副祝寿对联:文移北斗成天象,月捧南山作寿杯。那天晚上,除了张王飞外,还有王慧骐、林道立、蒋亚林诸兄,他们举着我写的对联放了视频给我看,那时,我多么想去敬吴先生一杯寿酒啊,可惜不能将至。散文家王慧骐兄特地写了一篇散文,以作纪念,谁知此文竟然成为我们聚首的永诀之文。
斯人驾鹤西去,他留在我们心间爽朗的笑声,却在阴阳两隔的空间里久久回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