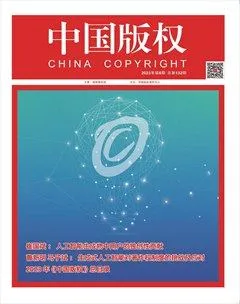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及其启示
熊超成
关键词:法律史视角;清末通商续约;涉外版权;级差效应;有限保护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版权已成为一个无论如何既回避不了也绕不开的问题。”如何处理涉外版权问题,特别是对外国版权是否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又是其中关键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双边互惠到多边条约的国际保护道路,这是以其国内版权保护制度为基础的。与之相比,我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初次面临涉外版权问题时,国内相关产业培育不足,版权制度并未建立,往往是被动面对这一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在涉外版权问题的政策选择上,发达国家可能无法提供理想的借鉴模型,我国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的应对之道。
为此,本文不再向比较法寻找模板,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考察清末对涉外版权保护问题的处理。这种考察法律史的视角并非法教义学层面的历史解释。由于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法统,《大清著作权律》等文本已不是现行法直接相关的立法史料,无法在历史解释层面提供帮助。不过,这并不妨碍法律史视角以史为鉴的功能:前人对类似法律问题处理的经验或教训,可以为今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重要的智识借鉴。基于这一视角,我国清末首度面临外国作品的保护问题时的中西失衡背景,恰恰与现今后发国家面临该问题的不平衡处境更为类似。因此,本文以清末涉外版权问题的处理——包括对外谈判与国内司法为样本,考察其得失,以期为我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处理涉外版权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一、清末涉外版权问题的出现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律制度始于清末,且被有的学者称为“枪口下的法律”。这用来描述涉外版权更为准确,因为清王朝当时面临最紧迫的是对外国版权的保护问题。
涉外版权问题起初并不起眼。19世纪末,随着中西经贸关系进一步拓展,涉外知识产权问题开始增加:最初在商标领域,随着洋货在中国流行,国内未经许可使用外国商号和商标的情形日益增多,外国商人希望他们的商标能够在中国受到保护,并认为这种利益将是巨大的,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四万万消费者”的预期市场。与此类似,列强在版权贸易上也存在着这样的想象,因为清末我国已经成为外国书籍的一个巨大销售市场。同时,列强这种跨国保护的愿望并非空想,当时西方进入知识产权的世界主义时期,特别是随着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1886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成功签订。不过,这种国际保护以地域性为基础,西方列强在签订这些条约前建立了国内版权保护制度。这也意味着如果版权在一国受到侵犯,自然应该首先寻求该国的救济。
问题在于,清朝自身并无现成的版权保护制度。清朝时期仍基本延续着宋、元以来的办法,采取诉诸官府、张贴榜文等发布告示的方式来防范和警戒盗版行为。各国列强不再指望在中国法律制度内寻求救济,开始求助于本国在清朝的外国领事馆。不过这些措施也不奏效,因为商标、作品由于具有非物质性,难以直接实现物理控制,高度依赖法律的强制保护,因而在租界或条约开放口岸以外的广大地区缺乏有效执行力。
因此,尽管列强在鸦片战争后赢得一系列外交让步,甚至通过会审公廨获得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基本实现对华通商自由,但版权贸易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是全新的市场,也需要全新的制度保障。在这种贸易中,版权发展水平较高的一国想要实现对另一国的经济收益,依靠的是级差效应,这需要二者的版权制度水平接近。列强要扩展贸易市场实现收益,必然要向清政府提出保护版权的要求,这是此前中外条约谈判中并未涉及的议题。
二、清末涉外版权谈判的博弈
20世纪初,列强正式把版权条款摆上了谈判桌,清政府由此陷入不平等状态下的博弈困境。
(一)治外法权与级差效应
清末涉外版权谈判最早展开于中英之间。英国人承诺,如果清政府能真正实现他们的要求,可以让清朝海关建立新的关税税率、禁止鸦片,甚至“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随后美、日两国也以与中方续修商约为契机加入版权保护条款,并也有类似承诺。面对这一极具诱惑的许诺,清政府很难不动心,事实上,后来包括《大清著作权律》在内的清末修律,就肇端于清政府想要废除领事裁判权。清政府主要有两个考虑:一则出于外交压力,《辛丑条约》相关条款为列强敦促清政府建立版权制度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二则东邻日本的成功使清廷受到鼓舞,日本明治维新后颁布《著作权法》——其中包含保护涉外版权条款等一系列举措,最后成功废除了外国领事裁判权。正是在意识到版权问题与治外法权的这种关联之后,清政府开始认真对待涉外版权问题的谈判。
但是,列强之所以甘愿以放弃治外法权为诱饵,是因为保护版权能给他们带来另一个好处,而这却将对清政府构成不利:清政府保护外国版权将使级差效应成为现实,导致版权贸易逆差。通常国家间进行版权条约谈判,假定了两国从中所获取的利益将大致平等。这意味着条约最终完成之前,必须确保著作在这两个国家所能得到的保护是实质性相同的,不仅具有某种形式类似的义务。举例说明,甲乙两国版权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甲国是乙国作品的净进口国,那么甲国是否对来自乙国的作品给予版权保护呢?简单的回答是不保护。因为保护将导致乙国作品在甲国价格上涨,甲国国民必须支付更多费用;即使甲国作品也会在乙国得到保护而获益,但由于版权产业水平的差距,甲国支出大于收益,这就造成甲国的贸易逆差,而乙国则从中获利,这就是版权保护的级差效应。清政府面临的正是甲国处境,一旦满足列强版权保护要求,就会出现前述级差效应。
这样,清政府在对外谈判中陷入两难:保护外国版权是收回治外法权的条件,但这会导致级差效应,加剧贸易逆差。
(二)国内两种代表性主张
涉外版权谈判一时成为中国朝野的敏感问题。清朝大臣、学界以及书商等社会各界对美、日两国提出的续约要求反应强烈,大致出现了反对与赞成两派主张。
1.不保护外国版权的主张
清朝教育部管学大臣张百熙反对保护外国版权,竭力反对中国与日、美建立版权保护双边同盟,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经济成本考虑,由于语言障碍,中国卖书人很难靠翻译西方书籍“射利”,这样就不至于过于侵害他国利益;二是出于文化传播考虑,保护版权阻碍西文书籍流通,不利于中国讲求西学、变法维新,而如果读西书的人多,那么国人对西方事务了解就有利于中西商务,对西方也有利。他还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办理商约大臣盛宣怀,力陈保护版权带来的弊害,同时强调“现在中国振兴教育,研究学问,势必广译东西书,方足以开民智……不立版权,其益更大。”可见,官方内部反对保护的主要理由是助力国内讲求西学,国民完成近代化转型。教育界人士对保护外国版权的看法与此类似。北洋大学堂的学生因担心加入版权同盟后会抬高书价而买不起书,集体抗议。蔡元培也反对中日版权盟约,他通过陈述中日双方的共同利益,认为中日更应站在同一阵线,应对西方的版权主张。
在民间,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认为版权同盟条约适用于发达国家,在我国民智尚稚时大不可,且“一有退让,遗祸无穷”,明确反对商约谈判中加入版权保护的条款。即使1905年到外务部任职,他仍起草了《对(版权律)、(出版条律)草稿意见书》一文,并再次强调中国科学未兴,亟待从外国输入,若授予外国所有书籍以版权,则是“我以实际之权利,易彼虚名之保护。”张元济显然看到了这种保护将导致的级差效应及其后果。
总体而言,由于当时我国正值追求西学热潮,保护外国版权影响翻译书籍出版与销售,短期内会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影响。反对者正是站在了这一角度,但却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比如,蔡元培反对保护外国版权却不反对国内实施版权制度,张元济也对内尊重和倡导版权保护,切实推动版权保护。这“令人产生一种内外有别的印象。对内尊重版权,尽量协商解决;对外据理力争,毫不妥协”。
2.有限保护外国版权的主张
洋务派官员对保护外国版权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虽然刘坤一、张之洞在收到张百熙电文后随即致电吕海寰、盛宣怀,转达反对商约中加入版权条款的意见,但是他们也都知道完全拒绝该条款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张之洞并未坚决反对版权条款,他对译书、版权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曲循“无志气图小利”文人的意愿,主张“断不能全驳,且亦不宜全驳”,因为它正“可借以鼓舞东儒多出新书,有益我之学堂”。尤其是张之洞作为清朝实权派官员,更在意的是美、日提出以治外法权换重订商约这个事关全局的许诺,他的看法也基本代表朝廷最终意见——“墨守旧章,授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收长驾远驭之效”。深谙为政之道的张之洞整体把握清朝外交方针,综合考虑国内实际,提出了版权谈判的三条原则:1.版权保护的时间要有限制;2.版权保护的地域要有限制;3.版权保护的内容要有所区分,不能一概保护。事实上,后来的谈判也基本按照有限保护的这个方向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开始从正当基础与鼓励创造的功能来看待版权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长远效果,已经超越了保护主义,这是难能可贵的。相反,部分保守派官僚没有真正尊重版权,为维护统治特权呈现出另一种“内外有别”:一方面愿意保护外国版权以换取治外法权;另一面却对国内各民间书局保护版权的诉求熟视无睹。可见,即使同样是支持保护外国版权,官方内部态度也不一致。
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积极赞成保护包括外国在内的版权。严复认为“著述译纂之业最难,敝精劳神矣”,版权乃是对著译者精神劳动的补偿,且有助于兴盛著译风气,振兴教育,他力主应当通过国家立法对中外作品给予平等的保护。梁启超站在著者“私见”的立场,把版权与繁荣译书事业联系起来,希望尽快在中国通都大邑严行版权制度。他们已注意到版权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影响,其义利观在版权实践与西方观念的影响下,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来,初步认识到了版权的私权本质有助于国内相关经济产业的培育,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社会文明进步。
上述争论反映了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与博弈,涉外版权谈判已经不再是仅关于贸易互惠本身,而更关乎内外利益博弈的政治策略。
三、清末涉外版权的有限保护方案
清政府在涉外版权谈判中沿着张之洞的三条原则据理力争,以减少不利影响,而美、日等列强也没有真正想要放弃治外法权,双方最后达成有限保护条款。
(一)有限保护条款的达成
其中,《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23日在华盛顿互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于同年11月24日在北京互换。其中版权条款分别位于《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1款与《中日通商行船续约》第5款。这两个版权保护条款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其一,将对美/日的版权保护范围限定为“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或“特为中国人备用”,而且只禁止翻印不禁止翻译,这可最大化促进中方讲求西学、开启民智有益的译本传播;其二,版权保护必须向当局登记,但没有说明登记机关,只是援照或适用商标保护办法;其三,在保护期限上,美国最初提出14年,张之洞力主5年,最后采纳了当时《伯尔尼公约》赋予翻译版权的10年保护期;而中日条款中的印书之权并没有规定保护期限,明显比中美条款更为含糊。中美条款内容详细,美方考虑的是届时可直接根据条约的内容请求保护;日方则认为将版权问题浓缩在一个条款中难免挂一漏万,要求中国政府制定一个专门保护版权的章程,因而在本次谈判中只是达成了基本共识。
上述有限保护的涉外版权条款,是清末中国少见的取得一定成功的外交谈判成果,特别是依照中美续约第11款与中日续约第5款第2项,仅限于“专备中国人民所用”,它将在华洋诉讼中彰显威力,成为中方胜诉的关键条款,下文各作一例示。
(二)有限保护条款的适用
1909年日商斋藤秀三郎诉至诚书局翻印一案(正则英语教科书案),上海会审公廨紧扣中日条约规定的“特为中国人备用”,认为“按照条约,斋藤秀三郎亦无控告之权”,因为“日本臣民为中国人备用起见,以中国语文著作书籍,中国一律保护云云。可见,非用中国语文,及非为中国人备用者,即不在保护之列。”类似的,1911年美商经恩公司诉商务印书馆翻印案中,会审公廨也在判决要旨中指出:“美约第11款所许之版权,系以专为中国人民之用,已无疑义……非以华文著作者,概难保护。”最终,美商经恩公司与商务印书馆协议合作,解决历来翻印纠纷。这两起纠纷中,“特为中国人备用”“专备为中国人民之用”的法定条款,为巧妙化解涉外版权纠纷提供了依据。
四、结语:级差效应与政策选择
只要有文化交流与技术转移的需求,国家间的版权保护问题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考察清末涉外版权谈判历史并非纯粹的知识考古,而是可以为我国应对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提供启示。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应对级差效应的政策选择上。
在版权制度水平上,对外政策应避免造成过度的级差效应。比如,面对美国以贸易制裁进行的单边施压,我国与之进行版权双边谈判时应丢掉幻想,一方面鉴于我国市场规模对美国的重要性,坚持以市场换时间、以时间换发展空间的思路;另一方面要坚定多边主义立场,善于运用多边主义的产物——国际条约而据理力争,在具体条款上通过细化不同事项,限制一些措施的适用范围。如此,在我国制度水平已达到国际条约的保护水准后,应避免版权制度水平过快拉升,阻却级差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我国发展利益。
当然,我国已然是版权大国,面对一些后发国家时享有级差效应的优势,在对外维护自身利益时,也要看到清末推行移植西方版权制度的失败——“列强们似乎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努力向中国政府表明,为什么知识产权法有利于中国”。因此,我国推动主要贸易国家的版权制度水平时,要充分考虑互惠性,允许他国根据自身水平作出一定调整,让合作国家切实感受到版权保护的好处。
最后,我们应冷静客观地看待版权的私权本质。涉外版权政策无法与国内版权发展水平分开。由于版权是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在没有超越这个阶段之前,关键要加强自身的版权建设,提升版权发展水平,才能最终为对外版权谈判争取最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