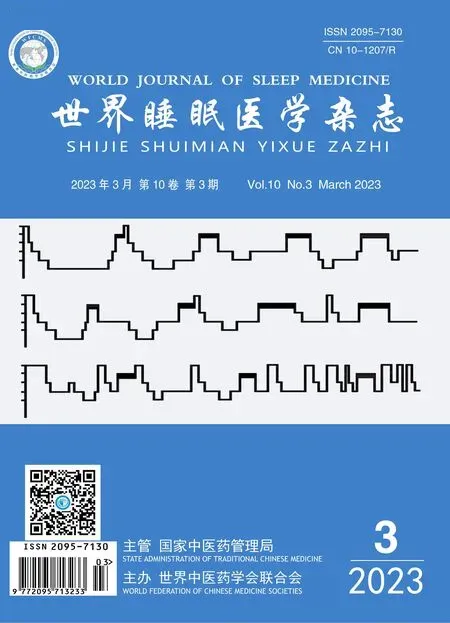基于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不同人格特质的女性失眠障碍患者疗效研究
冯 霞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州省精神卫生中心,贵阳,550001)
失眠症是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睡眠障碍疾病[1]。相关研究表明器质性疾病或心理疾病如抑郁、焦虑等都可以引发失眠。近年来随着生活压力的提升、生活作息不规律等,人群中失眠症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其中女性患者约为男性患者的1.5倍,与女性患高血压、抑郁症等相关,对女性群体有极大危害[2]。目前临床主要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及物理治疗等[3],失眠的认知行为(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CBT-I)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失眠障碍的首选治疗方式,但由于女性个体差异性往往疗效不理想,本研究通过从不同人格特征角度出发,探究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对女性失眠治疗的疗效差异。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8月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失眠障碍女性患者45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调查的3个维度因子的T分>61.5分将患者分为神经质组、外向性组、精神质组,每组15例。EPQ问卷是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系和精神病研究所艾森克教授由人格理论编制[4]。本研究采用龚耀先修订的成人式问卷,共88个条目。它由3个人格维度和1个掩饰量表组成编制,P、E、N因子T分>61.5分别表示精神质、外向、神经质。神经质组平均年龄(37.73±9.80)岁,汉族12例,其他民族3例,婚姻状况:未婚5例,已婚8例,离婚或丧偶2例。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5例,高中或中专1例,大学或大专8例,研究生及以上1例。职业:事业单位0例,职员9例,个体4例,退休2例。有躯体疾病2例,无躯体疾病13例,有既往史3例,无既往史12例,平均病程(4.32±1.33)年。外向性组平均年龄(36.00±9.40)岁,汉族12例,其他民族3例,婚姻状况:未婚2例,已婚11例,离婚或丧偶2例。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例,高中或中专1例,大学或大专10例,研究生及以上3例。职业:事业单位4例,职员8例,个体1例,退休2例。有躯体疾病2例,无躯体疾病13例,有既往史1例,无既往史14例,平均病程(4.35±1.74)年。
精神质组平均年龄(36.53±9.15)岁,汉族14例,其他民族1例,婚姻状况:未婚2例,已婚11例,离婚或丧偶2例。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4例,高中或中专0例,大学或大专9例,研究生及以上2例。职业:事业单位4例,职员7例,个体3例,退休1例。有躯体疾病2例,无躯体疾病13例,有既往史1例,无既往史14例,平均病程(4.30±1.62)年。3组患者年龄、民族、婚姻状况、职业、躯体疾病、既往史与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纳入标准 1)年龄24~60岁,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2)符合DSM-5失眠障碍诊断标准;3)入院前2周内未服用镇静类催眠药物;4)患者积极配合,有较好的依从性;5)SAS分<59分、SDS<62分,EPQ的各因子分(神经质N、精神质P、内外质E)其中任一个因子>61.5分;6)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1)严重躯体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2)导致失眠其他疾病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快速眼动睡眠障碍等;3)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等其他精神疾病;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5)目前服用抗精神病药、催眠镇静药等精神类药品。
1.4 研究方法 科室建立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小组,由经过专业失眠认知行为培训的睡眠专科医护人员负责执行,根据每周患者的反馈情况调整治疗内容,共治疗8周,包括:1)睡眠限制疗法,对患者每晚的卧床时间进行严格的控制,保证每天同一段时间睡眠;2)刺激控制疗法,以恢复卧床为信号对睡眠进行诱导,引发患者认知中床与睡眠的关联;3)放松疗法,给予放松治疗,减轻患者的焦虑紧张情绪;4)认知疗法从根本上改变患者对失眠不合理认知,密切与患者沟通,建立情感与行为的桥梁。
1.5 观察指标 1)观察治疗前后3组患者SAS、SDS、PSQI分值的变化。2)治疗前后3组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PSG)入睡潜伏期(Sleep Latency,SL)、总睡眠时间(Total Sleep Time,TST)、入睡觉醒次数(Sleep Wake Times,WASO)、睡眠效率(Sleep Efficiency,SE)指标。

2 结果
2.1 3组治疗前后PSQI、SAS、SDS评分比较 经过8周CBT-I干预后,3组PSQI、SAS、SDS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P<0.05)。与神经质组比较,外向性组、精神质组的PSQI、SAS、SDS评分显著降低(P<0.05),与外向性组比较,治疗后精神质组的PSQI与SAS评分比较差异无明显意义(P>0.05),SDS评分显著降低(P<0.05)。见表1。

表1 3组患者PSQI、SAS、SDS评分比较分)
2.2 3组患者治疗前后PSG参数比较 治疗后各组患者睡眠效率(SE)均较治疗前提高(P<0.05),神经质组治疗前后SL、WASO、TST变化不明显(P>0.05),外向性组、精神质组治疗后SL、WASO显著降低,TST显著升高(P<0.05)。且与神经质组比较,外向性组SL、WASO较低、TST、SE较高,精神质组SL较低、SE较高(均P<0.05)。见表2。

表2 3组治疗前后PSG参数比较
3 讨论
睡眠可使身体疲劳得到恢复、机体功能归于正常,而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尤其是当前新冠疫情时期失业、隔离引起的长期焦虑环境下,失眠障碍问题日渐突出[5]。失眠障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失眠障碍患病率更高,且随着年龄增长失眠风险也更大[6-7]。研究表明女性大脑区域中存在与雌激素相关的受体,当同时发生情绪障碍、疼痛、肥胖等困扰时,一系列反馈调节通路会被激活使失眠障碍问题更加恶化[8-9]。目前关于女性失眠障碍多围绕围绝经期激素水平的机制研究[10],既往报道显示人格特征对于失眠的诱发因素及持续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11],而对于不同人格特征失眠障碍女性的疗效差异相关报道较少。目前失眠障碍非药物治疗方法主要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CBT-I)[12],其疗效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也十分紧密[13]。PSQI评分是反映睡眠质量的主要的量表指标之一,其分值越低表明睡眠质量越高[14],SAS、SDS评分分别反映焦虑与抑郁2种主要负性情绪,二者分值越高表明情绪越严重[15]。本研究中3组女性患者经过8周的CBT-I干预后,PSQI、SAS、SDS评分均显著降低,睡眠质量、抑郁与焦虑不良情绪均有改善,相较于神经质组,外向性组、精神质组的睡眠质量改善更明显。目前研究表明CBT-I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重建正确认知[16],与本研究改善女性失眠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情绪结果类似。同时本研究中CBT-I同样可帮助女性患者重建理性、积极的睡眠信念,睡眠限制疗法主要通过减少清醒状态的卧床时间来提高患者睡眠效率,而放松疗法主要通过深呼吸、冥想等方式放松使觉醒次数减少,刺激控制疗法通过控制患者固定上床、起床时间等重建条件反射式的入睡意识[17]。神经质型女性患者CBT-I的治疗效果低于其他人格特质,可能是因为神经质型女性大多表现为敏感多疑、性格内向等特点,易受外界刺激加重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且难以自控、反复波动导致治疗效果不佳。
多导睡眠监测(PSG)可以客观地了解失眠患者睡眠的情况,可以排除部分假性失眠或其他类型的睡眠障碍,提高失眠的诊断准确性[18]。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治疗后3组患者SE均有提高,神经质组患者治疗前后SL、WASO、TST变化不明显,与神经质组比较,外向性组SL、WASO较低、TST、SE较高,精神质组SL较低、SE较高,可见CBT-I客观上对神经质型女性患者失眠障碍改善的效果差于其他人格的患者。女性的激素水平呈现周期性波动特点会加深其抑郁和焦虑,且比男性更容易进入反刍的思维模式,对创伤性事件的态度更消极,使得女性发生失眠的风险提高[19]。而神经质型女性诱发心理异常的阈值更低,可能会对很小的刺激作出神经质的反应[20],对于焦虑等情绪波动更加难以控制,因此相对精神质和外向型人格,CBT-I可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神经质型女性看待负性事件的思维模式和态度,其负性情绪反复发作难以平复和稳定,使得失眠障碍的治疗效果不佳。此外,神经质人格对于抑郁症的发生有一定预测作用,高度神经质与抑郁症状的发生及夜间睡眠障碍存在相关性[21]。本研究中CBT-I对神经质型女性患者治疗后抑郁评分仍显著高于其他人格,客观睡眠质量治疗后没有改善,和以往对抑郁与睡眠质量相关性研究的结果类似。
综上所述,CBT-I可以有效提高女性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焦虑及抑郁情绪,并有效提高精神质型及外向型女性失眠患者的客观睡眠质量,为女性失眠障碍患者针对性和差异性治疗提供了参考。但本文仍有一些不足,如样本量较小,不足以代表整个年龄层次的女性失眠群体,治疗后缺乏进一步随访评估,未来希望开展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以深入探究患者人格特质与失眠治疗疗效的相关性。
利益冲突声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