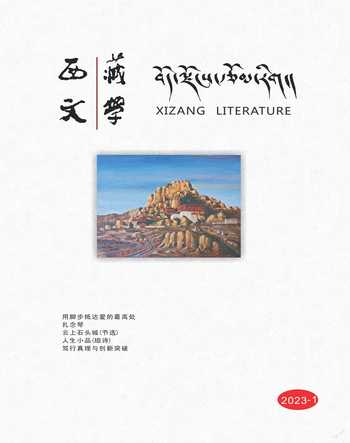我的爷爷
左中右
我的爷爷左保运,生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卒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按照我们当地的计算方法,享年九十三岁。这一天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一日,黄历上讲宜结婚、求子、出行、搬家、开业、祈福、安葬等。因为风俗及疫情的原因,爷爷安葬时间定在十二月六日。
当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村中道路时,站在街头巷口的那些女人们都在不由自主地慨叹:“这个老头可是个有福的人啊!”我知道她们的羡慕有道理,因为爷爷的确子孙满堂,而且都极其孝顺,可爷爷一生所经受的苦难,又怎可与外人说道?
爷爷那一辈共兄妹六人,他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时候家里穷,爷爷就跟着他的大哥到山西洪洞县地主家里做长工。爷爷个头没有他的大哥高,但干活却毫不逊色,推独轮小车更是一把好手。好多时候,别人干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而我的爷爷总能用他瘦弱的身板顶上去,仿佛清汤寡水的饮食没有影响他的力气。农活忙完了,爷爷还要去放羊,羊在草地里轻松咀嚼,而我的爷爷却在更深的草地里割草。爷爷本不用那么忙碌,可他总担心有些羊会夜里挨饿。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么瘦弱的爷爷为什么那样拼死拼活地干。后来,爷爷在我家里住,我们对饮小酌,我不经意地问他:“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留在山西,给我们找一个地主家的千金奶奶?”爷爷总是笑而不语,明亮的双眸一直注视着那浅浅的酒杯。我很想知道,透过那泛着泡沫的酒杯,爷爷是否会看到一个“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婷婷佳丽,还是会回想起“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的牧羊少女?但不知道为何,抗日战争结束后,我爷爷的大哥还是匆匆带着他那依依不舍的三弟坚决地回了老家。
回到老家的爷爷少言寡语,像他在山西那样,挣扎着推稳他生活的独轮车。二十多年的时间,先是结婚,后又有了我的爸爸、我的二叔、三叔,但他的生活没有多少改观,仍然借住在堂兄家的牲口屋里。尽管我一直都不太清楚我爷爷那几个兄妹的名字,但“左保运”三个字戴在我爷爷的头上,足见我的曾祖父對我爷爷的厚望以及命运对他的垂青。保运保运,保佑好运,保有好运。不知道是我那福泽不深的奶奶见识太浅,还是爷爷的运气积累不够,最后奶奶还是在生我姑姑时撒手而去。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带着四个孩子,尤其是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还会奢望什么好运?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爷爷相信一个人不可能一直走背运,也没有人会去悲失路之人,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改变家庭的重任,最终还是落在我父亲这个长子身上。也许那个年代叫“建林”的男人都有几分吸引力吧,我的父亲左建林竟然被邻村一个家境殷实的红卫兵女小将看上了。这个红卫兵小将,就是我的母亲。虽然她大字不识几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但《毛主席语录》她却能倒背如流。自从我母亲来到左家后,我爷爷脸上笑容明显多了。白天,我的母亲把我那姑姑捆扎在她的背上,带着他们父子四人一起挣工分,晚上又搂着小姑酣然入梦。母亲隔一段时间,总会悄悄地从我外婆和她的大姐、二姐、三姐家里带回些白面、红薯、萝卜甚至腊肉给我的爷爷及他的孩子们解馋。更主要的是,在我母亲不断把她娘家东西搬往婆家后,竟然还带着我爷爷他们父子四人盖起了家里的第一座房子,虽然只是简陋的三间土坯房,却已让我爷爷干涩的眼睛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母亲性格耿直、恩怨分明,她不喜欢拐弯抹角,也不允许是非不分。因此,她常常对我的二叔、三叔、姑姑甚至是邻居们批评指责甚至破口大骂。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还有我的爷爷总会一声不吭站在旁边。母亲累了,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喘着气,父亲则回屋子里做饭,而我的爷爷却总是郑重其事对周围人说:“大媳妇脾气不好,但心善,是不会和你们记仇的。”
等我上小学后,父母亲就带着我大哥到很远的徐州去做些小买卖了,我姐姐和二哥又去了我们乡里读书,家里只剩下爷爷跟我。我喜欢静静地坐在屋前左边的门台上,看着院子里楝树上的小鸟不停啄着球形的果实,却又不断从嘴边掉落在地面上的样子,然后自己傻傻地偷笑。小鸟怎么那么笨啊,楝子又圆又大,小鸟的嘴怎么都无法吞下,可为什么每每又不愿意放弃呢?还有爷爷的炊烟,也是倔强得很,总是在低矮的屋里窜来窜去,实在没地方躲藏了,才从屋顶的缝隙里挤出来一些。我不喜欢在烟雾弥漫的屋里吃饭,而爷爷却异常享受那种烟雾缭绕的感觉。爷爷也做不了什么美味珍馐,一般都是清水煮面,然后再炒一个辣椒或者熟个瓜豆,有点咸味能够下饭即可。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给了我极大影响,以至于后来我到西部援藏后仍保留着简简单单、清汤寡水的饮食方式,哪怕是朋友们到我那里做客,迎接他们的永远都是炒鸡蛋、炒辣椒或者清水煮豆腐这些简简单单、一清二白的饭食。朋友们有时候也会针对饭菜给我提意见,提醒我应该讲求色香味俱全,而我则会极力反驳:“你们来我这里不就是吃个饭、喝个酒,追求个酒足饭饱吗?”朋友又会说:“在保障酒足饭饱的基础上讲究色香味俱全,是不是会更让人赏心悦目、经久难忘?我们重视内容,但也不能忽视形式,只有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白天面对他们,我不屑于多加反驳,他们不知晓我跟爷爷的感情,又怎么能够体会爷爷对我的影响呢?又岂能因为他们的三言两语而改变我对爷爷生活方式的传承呢?可晚上我躺在床上,又总觉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明明自己可以把形式和内容做到完美统一,可为什么抱着固化的思想不愿意改变呢?难道那特殊的贫困年代形成的生活方式真的值得我一直铭记和传承吗?看着窗外摇曳的月光,我知道自己抱残守缺的执念不是对过往生活的尊重,而是自己内心对惰性思想的放纵和袒护,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沉溺和纵容。拿远离故土、简单饮食的现状来腐蚀、抵消不远万里的雄心壮志又何尝不是对初心的一种背叛呢?而我的爷爷啊,不管别人说他有福也好,自己过得困苦也罢,早已在那炊烟缭绕的小屋里,达到了他人生的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吧!
过去最开心的时候是曾祖母到来的日子,爷爷总会炒上两个鸡蛋或者在街头买些豌豆馅儿,让我贫乏的味蕾充满空前的幸福。或者,等到周末,爷爷总会带着我赶会儿集,有时候我们会喝上一碗豆腐脑儿,吃上两根油条或者五六个肉包;有时候也会喝上一碗丸子汤,然后再吃上一个烧饼,至于羊肉汤,那是后来我上班了,才有机会跟爷爷一起去品尝到的美食。爷爷的口袋里从来都是用小毛巾包裹着的一打零钱,可能有两三块,也可能有四五块。我不知道爷爷怎么每次都那么有钱。
后来我到乡里读书,破旧的小屋平常就只有爷爷一个人。六十多岁的老人守着一个孤零零的屋子,爷爷突然有了找个老伴的冲动。我爸妈在外面也能干,多少挣了些钱,对于单身了三十多年的爷爷很是理解,在帮着找老伴的这件事上也十分积极。那时候,家里的收音机播出最多的就是征婚广告。一遇到有五六十岁的单身女性,父亲总会让我记录下来,有时候当时没听清,便会要求我在夜里重复收听,直到记录清楚为止。父亲做事情有恒心、有毅力,在到过新乡市获嘉县、原阳县、延津县、封丘县、长垣县和濮阳市濮阳县、清丰县、南乐县、范县、台前县等地方后,终于带回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奶奶”。她人很周正,而且干活还勤快,屋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我爷爷觉得他的高光时刻就要到来了,可还没等高兴几天,我那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奶奶”连同家里的一千多块钱一块儿不见了。爷爷找了好久,也难过了好久,最终还是在众人对骗子的诅咒声讨中再也不提找“奶奶”的事情了。爷爷有个妹妹,以前还不怎么来往,可自从那个“奶奶”不见后,爷爷就愿意到十多里地外的妹妹家说说话。那时候的爷爷,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辆自行车,那样再去自己的妹妹家里就方便多了。我的父亲依旧不言不语,只是没多久就骑回了一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花了六百多块钱。爷爷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了两天就感觉索然无味,最终还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骑着“永久”自行车去了他的妹妹家里。那天的午饭丰盛与否从没听爷爷提起過,但那确是爷爷唯一一次在他妹妹家里喝的一顿酒。飘飘然的爷爷推着“永久”,走过熙攘的街道、走向乡间小路。两个精壮的小伙儿从后面尾随而来,爷爷竟然没有发现,直到一个抱着爷爷不松手,另一个骑着那辆“永久”自行车扬长而去,爷爷才突然警觉。爷爷看着两个人一前一后朝两个方向逃去,竟是茫然无措地坐在坚硬的土路当中。在不远处的路口,爷爷似乎看到了他唯一的外甥正朝着自己的方向哈哈大笑。
那一晚,爷爷摸着黑回到自己床上,竟然一连躺了两天没有喝一口水。等我的曾祖母晃动着她那三寸金莲走到床前,我爷爷只是喊了一声:“娘。”便下床给他的母亲打了两个荷包蛋。母子二人沐浴在缓缓流淌的炊烟中,盯着在夕阳中升腾的袅袅尘埃,谁都没有开口。爷爷从此不爱出家门了,而且还同他唯一的妹妹断绝了联系。没过两年,爷爷的大哥去世了,他们共同的妹妹来吊唁,而我的爷爷一直待在他的母亲身边,没有落泪,也没有同他的妹妹说一句话。爷爷的二哥、四弟、五弟相继离开,哪怕送别的唢呐再响亮,他的妹妹哭得再伤心,爷爷仍旧没有同他的妹妹说上一句话。直到我那活了一百零三岁的曾祖母去世,爷爷才带领着他那唯一的妹妹一起将我的曾祖母跟我那早已过世的曾祖父合葬在一起。后来,我的二叔因为肺癌也去世了,而我的爷爷始终坐在那有着靠背的小马扎上,孤零零地看着我们这些忙碌的孙子孙女给他的二儿子叩首、跪拜、送终。当喧嚣的响器伴着送行的队伍渐行渐远,我那孤单的爷爷会不会在转身的瞬间,泪流满面?我的爷爷那么倔强地活着,是为了什么,又在等待着什么?
我大学毕业时,去了我们市里的一高当老师。爷爷为了支持我在城里站稳脚跟,就把他攒了一生的五千元积蓄交给了我,让我尽快买房、结婚、生孩子。我的爱人也很感动,自结婚后就一直让爷爷住在家里。爷爷不愿意只是待在家里等着孙子孙媳伺候,于是就承担起给家里买早餐的任务。爷爷每天起得早,就一个个大街小巷地摸索、询问,直到在祥和四街的胡同里找见一家跟他差不多年纪仍然在炸油条的早餐摊主时,才算固定下来。爷爷总会带回来两根油条、七八个包子和一碗豆腐脑儿,然后很自豪地对我跟爱人说:“这家油条好吃,而且一块钱两根,包子也多给了 两个。”
没多久,我跟爱人有了儿子,儿子渐渐步入幼儿园,我也因工作需要调入市政办公室搞文字工作,爱人又每日早出晚归,家里便开始忙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爷爷主动承担起接送我儿子上学的任务。早上八点,爷爷左手提着书包,右手牵着我那淘气的儿子,晃晃悠悠走向学校。下午不到四点,爷爷就带着他那有靠背的马扎坐在学校大门口了。等人渐渐地多起来,爷爷就收起马扎站在大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只要放学的铃声一响,不管有没有孩子冲出来,他总会举起马扎不停地晃动。有时候,因为儿子调皮,老师也会把他留在后面出教室,可等走出校园,总能看到空荡荡的大门口,仍有一位老人在不停舞动着一个小马扎。儿子兴冲冲地跑过去,爷爷总会先接过他的书包然后连同爷爷自己的马扎抓在一起,再牵着儿子胖嘟嘟的小手,走向回家的路。
没多久,爷爷脚底长了鸡眼。尽管疼痛,他仍然每天坚持着接送我儿子,只是速度缓慢多了。我爱人看不过去,就每天晚上给爷爷泡脚,切除引起疼痛的角质。那一段时间,我的爷爷像个孩子,逢人就说他的孙媳妇给他洗脚修脚,可贤惠啦。别人多不为意,现在的年轻人自己洗个脚都不平常,何况是给隔辈的老人了。爷爷不管这些,只要有观众在,总会滔滔不绝地沉醉其中。我的爱人也总想带着爷爷去买些新的换季衣服,可他怎么都不答应,只是在我爱人整理和淘汰我那些陈旧的衣服时表现得很坚决:“这衣服好,穿着暖和,可不能扔了。”然后就匆忙抱回自己的小屋。那些年,除了我姐姐和姑姑能逢年过节买些新衣服外,爷爷基本上都是捡拾我穿旧的衣服,并且甘之如饴。这算不算做孙子的一种遗憾呢?如果我跟爱人强拉着爷爷去买件新衣服,至少买一件上档次的,爷爷会不会更舒心,会不会大摇大摆穿着衣服昂首出门去?
爷爷跟我们住在一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过生日。刚开始,我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带着爷爷回老家,然后我们兄妹四家带些烟酒、糕点,而我的叔叔、姑姑则拿些鸡蛋,一大家子坐在家里,吃团圆饭,其乐融融。随着我父母渐老,便把寿宴的地点放在了酒店,我们兄妹四人带着全家仍然积极相聚,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可我的叔叔、姑姑却以种种借口不再参加了。后来,我大哥家有了孙子孙女,我二哥在生了两个女儿后也添了儿子,而我又来到遥远的边疆援藏,我父母便不再张罗我们兄妹四人给我们的爷爷祝寿了。我能理解,父母终归心疼,不愿意我们奔波辛苦。可没有回家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泡在材料堆里,让眼睛昏黄,使胳膊麻木冰凉;我的大哥忙生意业务,陪着喝酒打麻将、下澡堂;还有我的二哥一直在基层,庸庸碌碌、茫然无方。而爷爷跟我的父亲单独喝酒时,会不会诉说前些年的生日和那些年的风光?人为什么要过生日呢?世间又为什么要有节日呢?是为了历史的铭记,还是为了现实的团圆?经历过风风雨雨、聚合悲欢,人生真的需要仪式感。生日不过了,兄弟们一年也难以团圆,还拿什么诉说血肉相连?一根弹簧拉伸久了,很难再伸缩回去,而人呢?如果没有节日调节,没有仪式感推动,我们长期超负荷、一成不变的运动,是不是更容易出现问题呢?文化是什么?是为了让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人之外的其他东西。机器虽然重要,但始终少了温情,而仪式感,恰恰弥补了我们的空虚缺憾,让我们懂得珍重自我,不负离殇。
我儿子上初中后,爷爷便选择回老家跟我父母一起住。爷爷想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到周边的村子去看看唱戏;也想在自己的村子里到处转转,同每一个熟人打打招呼;还想搬着他那有靠背的小马扎坐在门口,等着我从遥远的地方回来看他。爷爷想出去看戏方便,我父亲便买来了三轮电动车,只是骑了没几次,便静静地停在院子里了。爷爷还是喜欢拉出他的小马扎,坐在门口看人来人往,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只要微笑致意,他们都会停首报以招呼。有时候,爷爷也会接上熟人的一根烟,抽上几口,遇到特别亲近的人,也会留人在家里喝两杯。我父亲从不多说,只要爷爷能吸烟、喝酒仿佛就依然老当益壮,要不然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爷爷将走的那些日子,我刚好在家。我跟他说话时一直很正常,还不时拉我的手大声说话,那开心的笑容像孩子。爷爷临走的前一天,我订好了机票去厦门参加招商推介会,可航空公司却打来电话取消了航班。晚上,几个朋友又抽空喊着小聚,只是当我喝下第一小杯酒时就开始呕吐不止,即便喝了酸奶仍是吃不下一口菜。我当即告罪离席,匆匆往家返。路上,接到母亲电话,说爷爷吃不下饭,要求我明天回老家看看,我恍然大悟。第二天,爷爷的小屋里挤满了人,我父母、我三叔、我姑姑,还有我哥哥嫂子。他们看见我,都打着招呼并且让开了一条道。我走到床前,爷爷一直“啊”“嗨”地嚷着,谁都不让靠近。我先是叫了一声“爷”,接着又大声喊道:“小三回来看你了。”爷爷似乎听到了声音,停止了叫喊,又向外轻轻扭了扭头。我急忙抓住爷爷的手摇了摇,爷爷的手刚开始想挣脱,后又紧紧地握着,好一会儿才无力松开。晚上,爷爷竟然吃了蛋糕、鸡蛋羹和奶粉,虽然吐了不少,但还是让众人松了口气。只是当众人转过身,信心十足讨论着爷爷至少还能撑过十天半月时,爷爷却悄悄地闭上了眼睛。晚上七点四十五分,我的爷爷再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他默默相对一生的世界。
十二月六日上午九点零六,我们给逝去的爷爷起坟,旭日穿过厚厚云层,当空普照。下午四点零六分,爷爷入土为安,夕阳又染红西天云朵。送殡的队伍静静散去,我在黄昏中蹒跚归来,空空荡荡的家门口,只有呼呼的风声在空空哀嚎,像爷爷“啊”“嗨”的叫喊。
恍惚间,我不知道,当我下次回来时,还会不会看到家门口那个拉着有靠背的小马扎,使劲朝着我的车窗摆手的爷爷。
责任编辑:康松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