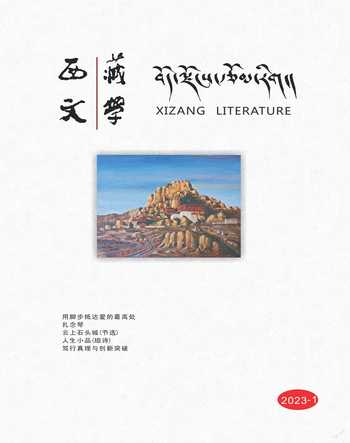二十八年为一见
冶生福
1
真没想到,不过短短几天,我们还是和马忠元老人离别了。
我们曾和马忠元老人一同采访过化隆群科,探望过苦芦湾九十多岁的老奶奶。那天忠元老人坐在老奶奶家的土炕上情绪激动,我们采访化隆县群科镇这一支苦芦湾回族支系从大河家逃到群科的历史,忠元老人一直在擦着眼泪,当时我不忍看忠元老人。
在手机微信、抖音、快手的碎片化信息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也碎片化了,甚至碎成一地鸡毛。真情变成了卖点,生活变成了表演,崇高变成了笑点,善良变成了做作。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不能理解老一辈人的纯朴感情,不能理解他们这一辈人眼泪的 价值。
忠元老人还陪我们去了民和的很多地方采访,在长途跋涉中,辛苦自知、劳累自尝,但忠元老人仍是一路谈笑风生。他年轻时曾在果洛州达日县工作过,后来又到西藏做过生意,他与许多藏族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这个走流量蹭热点的时代,我觉得用情谊这个词比友谊更贴切。
再一次见到忠元老人时,竟然是在他的葬礼上。
葬礼肃穆凝重,忠元老人表情安详,我们熟悉的那个红脸庞变成了黄白色;我们沉浸在那次群科之行的回忆中,忠元老人的眼泪和他擦拭眼泪的动作历历在目。
亲戚都来见忠元老人最后一面,安静的脚步、低低的言语、克制的抽泣笼罩着我们。
窗外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一位老人和一位中年人闯了进来,老人略显疲态,脸色红中带黑,手上缠着红色的佛珠;中年人穿着半长藏服,头发卷曲,右手食指上戴绿松石戒指。
忠元老人的一位小孙女钻出人群扑向中年人,喊了一声:“藏族达达(伯伯)!”中年藏族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他抱紧了小女孩。
藏族老人踉踉跄跄走了上去揭开忠元老人脸上的毛巾,双眼通红,久久望着忠元老人的脸。他的嘴颤抖着、念叨着、哽咽着:“阿窝(哥哥)你走了,阿窝(哥哥)你走了!”
那位中年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去把忠元老人的头抱在怀中,放声痛哭。
一位年轻人想上去劝中年人,却被旁边的回族老人轻轻拉住了。
等他哭够了,一位老人走上前说:“我们给他洗洗,等他洗完最后一个大净(沐浴),就让他走吧!”
中年男人这才立起身子。
老人们依次提来了温水,灌满了所有的弯柄汤瓶,安静地给忠元老人洗最后一次 大净。
忠元老人家里一阵沉静,只隐约听得见水流声。
我想起了采访忠元老人时的情景,老人的白胡子、红脸庞和利索的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人最不愿意窝在家里饿肚子,他一生奔波在外,到过果洛州,到过西藏,躲着“投机倒把”的罪名做小生意,他还给我讲了几个奔波中的小故事:
“我原来在果洛州达日县做过几年生意,后来因种种原因我没能回去。1984年我承包了我们公社的五五式大拖拉机到西藏去修路,我自己不会开拖拉机,就雇了一个司机,司机只会开车,不会修车。我们从格尔木拉了十桶油往唐古拉走,晚上十二点时,突然发现拖拉机不走了。下去一看,原来轮胎爆了,我和司机便换上了备用胎。
“唐古拉的路非常危险,司机胆子小,他说啥也不开了。深更半夜司机不开怎么行,我说:‘我来开!之前我可从来没开过拖拉机,这会儿只能硬着头皮开。我让司机替我挂了三挡,调好油门,我便一直握着方向盘,因为不会换挡,上山是三挡,下山也是三挡。后来到了沱沱河,车胎又爆了。幸好那边有个平安县的拖拉机手,我跟他们买轮胎,聊天当中得知他们到这里搞运输被人骗了。我手上刚好有四份修路合同,我给了他们一份,然后他们连夜帮忙补好了我的车胎。
“我们在西藏那曲修了几天的路,可是司机又不想干了。我说:‘你把我拉到这儿,我又不会开车,我怎么办?可是司机还是走了。我只好把公社的拖拉机卖掉,这样回去对公社也有个交代。
“在一个民和司机的推荐下,我把拖拉机卖给了羊八井那儿认识的一个村书记,我只身一人坐在拖拉机上走了三天,我不知道我的结局会怎样。后来到了堆龙德庆县,在村书记班玛旦增家吃了三天干炒面,班玛旦增终于贷到了款,拖拉机卖了一万三千四。
“藏族同胞真是好,那时社会治安不太好,班玛旦增书记专门给我派了个人,临走时叮嘱那人说:‘你把老马安全地送到拉萨,老马干啥,你干啥,老马吃饭你吃饭,老马上厕所你守着,等老马安全回去后你再回来。这个藏族人心诚,一直陪我回去。
“当时卖车的钱还不是百元的,全是二元五元的,带在身上很不方便。我在拉萨找到了一家河州回族饭馆,我只是说想换钱,没想到老板痛快地答应了,问我一共多少钱?我说是六千,他数都没数,直接拿走了。后来我不放心,回去要又不好意思,只好听天由命。后来有一天那老板说:‘你的钱我换好了,你来取。我去取时,一分不少,整六千!”
2
忠元老人葬礼上的人越来越多,忠元老人的儿子接待着亲戚朋友们,忠元老人沐浴后的水从屋里陆续地提了出来,人们让出了一条路。
风在枝头呜呜作响。
再過一些时间,就要给忠元老人穿上三尺白布送到清真寺了。
八年多的采访中,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些苦芦湾老人们。他们经历了民国时期、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也经历了生活物质紧张的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面对艰难困苦,他们几乎都不愿窝在家里,他们宁愿出门在外忍饥挨饿,宁愿在外面担风受险也不愿意在家里混吃等死,他们能在黄河里只身抱着羊皮筏子渡河做小生意,他们能在煤洞子里弯腰拉着煤皮袋挣个养命钱。
忠元老人不紧不慢、略带沙哑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
“那时拉萨有一家藏回开的鞋厂,后来改成了旅社,对外承包。当时承包费是一年三万三,我签了三年合同,我一个人在拉萨开旅店生意。当时我付清公社拖拉机的款项后,身上只剩了四百块钱。我买了几个大茶壶,又买了几个汽油炉子,老板是我,服务员也是我。
“后来我雇了一个人,我回老家把家里人接到了拉萨。1989年我完成了朝觐,把旅店承包给了别人,那个人经营得不好,老板打电话让我回去继续承包,我又回到了拉萨开旅店。我的两个儿子在那里从幼儿园上到了初中。
“旅店这生意我干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我也做点其他生意,比如羊绒、柏木、虫草、麝香等物品的买卖,同时还有藏族地区的酥油等。因为多年在藏族地区做生意,我会说一些藏语,也赢得了藏族同胞的心。做生意就讲个诚信,玉树的几个藏族同胞每年都把十几斤虫草放到我这儿,说放我这儿他们放心,每次到年终才来结账。”
忠元老人的埋体(遗体)快洗好了,阿訇们裁开白棉布作开凡(裹尸布),回族亡人的穿戴很简单,洗完后用大白布扯成三大块,第一片布穿过头,盖到膝盖上,第二片布从膝盖盖到脚,第三片布从头裹到脚。
门口传来了压抑的争吵声,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那个藏族中年人,他涨红了脸,正把一沓钱往管葬礼的人怀里塞,而那人不收他的钱。藏族中年人渐渐地有了点怒意:“你为什么不收我们的钱?”那个藏族老人拉了拉他的袖子。
忠元老人的儿子赶紧走上去解释了半天,藏族中年人还是怏怏不乐。我问了下,原来那两个藏族同胞是忠元老人的朋友,中年人是老人的儿子,叫索南达杰。
这下我想起来了,我和忠元老人采访时,老人提到过这两位达日县的藏族朋友,他曾经在果洛州达日县工作过,在那里,忠元老人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多年前我在果洛达日县工作时,曾与果洛的藏族朋友班玛洛赛来往,后来我离开果洛后,回到老家,又跑西藏,天南海北到处走。他一直在找我,一直打听我的消息。
“那一年我在青岛,他让他儿子索南达杰来西宁找我,没找到,后来从卖虫草的商人那儿打听到我的手机号,他一打电话,开口就说:‘我父亲找你找了二十八年。
“后来他们一家人来西宁看望我,给我带了酥油、蕨麻、曲拉,我每年喝的酥油茶里的酥油就是他捎下来的。索南达杰常说我是他的异族叔叔。”
我不禁朝那个红脸庞的藏族汉子多望了几眼,他委屈地缩在人群里,身子不停地抽 搐着。
几个人用担架抬着忠元老人的埋体去往清真寺。周围传来了低低的哭泣声,索南达杰怯怯地挤到担架前,想抬忠元老人的担架,一位年轻人看了看他,给他让出最前面的位置,索南达杰把担架的一头稳稳地放在肩上,朝门口走去。
忠元老人走了,但我一直对忠元老人与藏族朋友之间的情谊印象深刻,超越他们之间友谊的那种东西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可我就是握不住它。
它究竟是什么呢?
时隔多年,又经历了鼠年之新冠疫情,人们似乎失去了什么,又似乎得到了什么,其心情、其生活都无法细说。
我终于约到了索南达杰,他还是那样,红脸庞,宽阔的胸膛留着草原的影子。
我们要了杯茶,茶杯里的菊花渐次盛开。
说起忠元老人,索南达杰眼睛红了,他说起了与忠元老人的点点滴滴:
“马叔叔和我父亲是故交,他们曾一块工作过,马叔叔的藏语说得很流利,他们在一起时,很开心。
“在我十六七岁时,马叔叔经常到我们果洛州达日县来做小生意,他也承包些乡下小工程。那段时间我母亲病了,父亲要送母亲到玉树去看病,可是又不放心我,马叔叔说可以由他来照顾我。
“母亲去玉树治病期间,马叔叔就像父亲一样照顾我,他边做生意,边伺候我上学。放学早一点,我等他,他早一点,他等我。马叔叔做饭手艺好,他包的饺子,一个个饱满好吃,他还能拉一手细如发丝的拉面呢!
“我最喜欢吃马叔叔的拉面,我吃饱了就不再想父母,安心地学习。马叔叔为了我,还托人从西宁买来复习资料和小人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我常用‘桃园三结义来形容父亲和马叔叔的关系。在我心中,马叔叔就是我的长辈,我甚至把自己当作马叔叔的儿子。”
索南达杰喝了一口茶,盯着杯里的菊花,胸口一起一伏:
“母亲在玉树没治好病,父亲又打算送到西宁治。这时母亲已无法下床,生活又不能自理,从玉树到西宁有几百公里,那会儿全是山路、沙土路,路途长又不平坦,母亲是撑不到西宁的。
县里为父亲提供了一辆破解放车。可是怎样让母亲即不受罪又能安全地送到西宁呢?我父亲为难了好多天。
“马叔叔带我到了玉树,马叔叔看了看我母亲的情况,又围着解放车看了看,没说 什么。
“等到中午时,马叔叔右肩扛了一个钢丝床,左手拿了一堆牛皮绳,他让父亲跳上解放车车厢,他俩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马叔叔在车上朝我招手,让我上去。
“车厢中间的钢丝床用牛皮绳从四周绑得紧紧的,钢丝床悬空在车里,有点像今天的蹦蹦床。马叔叔让我躺上去试试,我躺上去觉得很舒服。马叔叔的这一招确实高,汽车颠簸的力量全被牛皮绳和钢丝床化解掉了,不用再担心母亲撑不到西宁,汽车司机直朝马叔叔竖大拇指。
“母亲被安全地放在钢丝床上,車顶上又盖了篷布,父亲和马叔叔在车厢里照顾母亲,我坐在驾驶室里。
“在玉树,天气变幻莫测,一会儿雨,一会儿雪,尤其到了秋季,雪说下就下。这一路因为下雪而泥泞难行,我们走了两天才到麻多,在麻多住了一晚。在车上,我从后窗不停地朝车厢望,觉得马叔叔和我们如同一家人,如果马叔叔有难事,我父亲也会这样帮他。
“我们终于到了西宁,住进了医院,马叔叔又回民和老家,从民和老家给我们带来吃的喝的用的,甚至还给母亲带来一双布鞋。过了一个月,母亲的病仍不见好转,父亲继续在西宁照顾母亲,我回了达日县,马叔叔陪我回达日。他在达日县一边继续做他的小本生意,一边给我做饭照顾我上学。
“两个月后,母亲去世了。在母亲的葬礼上,马叔叔也来了,他用回族人的方式安慰着我父亲,用回族人的方式为我母亲祈祷,我当时抱着马叔叔哭。
“马叔叔陪了我们三个月,父亲和马叔叔像过去一样经商,马叔叔也像过去一样照 顾我。
“三个月后,马叔叔回了民和老家,这一别就是二十八年。
“我给马叔叔写过四五封信,我记得我这样写道:‘敬爱的马叔叔,我很想念你。接下来,我就写我父亲的情况和我的学习情况,最后在信的落款处,我郑重地写上:‘你的干儿子索南达杰。
“马叔叔也给我回信,让我孝敬父亲,提高学习成绩,还说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大概过了半年后,就再也收不到信了。”
茶室的灯光柔柔地照在索南达杰棱角分明的脸上,隔壁房间传来麻将的喧嚣声,我俩面前放着两杯菊花茶、一沓纸、一支笔。
“我父亲一直到退休,都没收到过马叔叔的信,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后来我们达日县的几个人去西藏拉萨,他们回来后说,有一个回族白胡子老人在打听我们,我们知道他一定就是马叔叔。
“后来,我们去西藏拉萨了,我们到处打听马叔叔的消息,但没能再联系上马叔叔,后来才知道,他回了民和老家。
“这一隔就是二十八年。”
3
我往索南達杰的杯子里添了点水,杯中的菊花绽放得旺盛无比,一条条花优雅地舒展开来。
窗外是城市的灯光,梦幻、迷离,隔壁的麻将声正急,服务员在吧台上着急地划动着抖音和快手,碎片化的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突然让我对相隔一杯茶、一张桌子的索南达杰感到恍惚。
索南达杰似乎也被服务员的短视频音影响了,他说:“老人们常说,过去修行高的人会看见千里之外的人,如今通过手机不但可以见人,还能付钱。可是你再也要不到隔壁的一个热馍馍,你再也要不到隔壁的一口热奶茶。我多么向往闻到隔壁馍馍的香味,我多么向往喝到隔壁的奶茶啊!”
我苦涩地笑了笑,在这碎片化的城市里,只有外卖员小哥能闻到,不对,他也闻不到,饭菜都被打包了。我说:“你还是说说二十八年里怎样寻找忠元老人的吧。”
索南达杰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我想念过去马叔叔在我家的时候,他每次来我家时,父亲就会从柜子深处拿出一套马叔叔专用的锅碗瓢盆,马叔叔简单洗一洗,然后和面,熟练地给我们拉拉面,真忘不了马叔叔的那碗拉面。
“马叔叔到来时,父亲总是很高兴,他和马叔叔用藏语聊天,语速快得像泉水,他俩轮流说到了什么地方,骑了什么马,遇了个什么人,说着说着两人都哈哈大笑。
“马叔叔一到我家,父亲第一件事情就是领马叔叔到羊圈里挑羊,父亲总是挑最好的,马叔叔自己却总是挑只瘦弱的,很快我们家就会有羊肉香味。
“清晨,马叔叔早早起来洗小净,做礼拜。而父亲早早起来念佛经,转佛塔。然后两人就开始喝酥油茶,拌糌粑面。
“他们常说善是所有人、所有事的基础。
“还是说说我和父亲找马叔叔的事吧,隔了二十八年,我们仍是没有马叔叔的消息。
“有一天我到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那天正是个星期五,好多老人都聚集到寺里。突然我心里一动,一种强烈的冲动压倒了我,我走进寺里,向一个白胡子老人打听马叔叔,我说是个白胡子的民和人,叫马忠元。
“这个老人想了想,说好像有这么个人。看着我着急的样子,他问我:‘他欠了你的钱吗?我说:‘没欠,他是我的恩人,我的叔叔!老人笑了,他说他打听下。
“老人在问了好几个人后,满脸笑容地迎过来。他说:‘娃娃,你运气好,我给你要上了他的手机号。
“我那时的激动你想象不到,找了二十八年,竟然在这里找到了。
“我赶紧打电话,一听马叔叔熟悉的声音,我都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说我是索南达杰呀,马叔叔问了我父亲怎样,说了好多话。马叔叔说他在青岛,听到我在西宁,他说明天就回来。
“果然第二天他就坐着飞机赶回了西宁。
“我找到了马叔叔家,留下了联系方式,还带着父亲探望了马叔叔,从此每年我都会从果洛给马叔叔带新鲜的酥油,后来我和马叔叔的儿子们也成为了如亲兄弟一般。马叔叔常说:‘你们要像我们一样好,我们都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顺便也说说另外一件事,我父亲带母亲治病时,塔尔寺旁边也有个父亲的世交,叫尔不都,那时他每天都叫他的子女们给我父母送吃的,送喝的。他们家养着一头黄牛,黄牛的奶质不好,他怕母亲喝不习惯,每天挤完奶就和对门邻居的牦牛奶兑换。起初对门的不答应,后来听说是送给生病的藏族同胞,他就答应了。从尔不都家到医院有一段泥土路,一下雨,路面上全是泥,可是母亲治病那些时间,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照顾着我们。
“马叔叔和尔不都都是好人,可是如今马叔叔不在了。”
望着窗外渐浓的夜色,我突然问起忠元老人葬礼上的事。
索南达杰激动起来:
“那天我也打听了回族葬礼上的习惯,人一去世都有随礼的习惯。我和父亲准备了薄礼,可是他们不收。当时我也比较着急,一着急我心里就不高兴,我想马叔叔刚去世,他们是不是嫌我们了,是不是对我们有看法呀?现在想想自己都有点后悔,葬礼上其实所有人都没收礼。马叔叔走时说了,他一生不欠别人的钱,在他去世后不收别人一分钱。马叔叔就是马叔叔!”
我说:“我那天在忠元老人的葬礼上看见了你,你给忠元老人抬了担架。”
索南达杰神色凝重起来:“对,我应该给马叔叔抬一程的。”
索南达杰大口地喝着茶,看着窗外渐浓的天色,我俩渐渐融进西宁灯光灿烂的深夜。
责任编辑:康松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