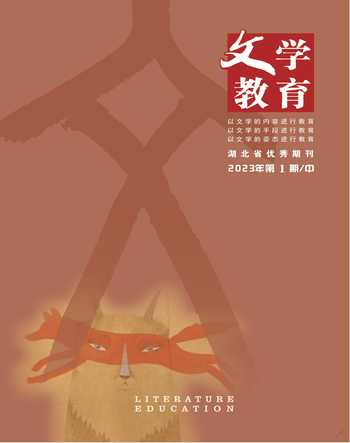细读《雷霆的话》看人神之约
张恒
内容摘要:《荒原》向来备受关注,这首长诗描述了一战后西方社会传统信仰逐渐崩塌,新的秩序无从建立的“荒原”局面。本文重点解读《雷霆的话》一节,探讨艾略特借助“春雷”警醒人类,重建人神之约,上演现代版“出埃及记”。
关键词:《荒原》 《雷霆的话》 人神之约 《我与你》
《荒原》的前四章诗歌讲述了“荒原人”的可悲境遇,第五章明确人神关系的重建不仅可以拯救人类,还能获得超越现实物质的能量源泉,达到心灵的无限平安。艾略特下笔从容,一气呵成的《雷霆的话》[1]包含了诗人“求助宗教拯救现代荒原的堕落,及其希望和绝望并存的痛苦心理”[2],因此更能突显重缔人神之约的目的。本文根据译本默认《雷霆的话》为八个小节,借文本寻找人神离散又重建的蛛丝马迹。
一.人与神的离散——人类文明没落史
艾略特用三行诗描述《圣经》中的三个重要场面。首句讲逮捕耶稣的场景,即“火把把流汗的面庞照得通红以后”。福音书中描述耶稣说自己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接着开始三次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之前一样。(太26:42)另一部福音书描述更为具体,耶稣在祷告后,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22:44)耶稣的恐惧与“流汗的面庞”相呼应。第二句即“花园里是那寒霜般的沉寂以后”指耶稣被带走后的场景。声称要追随一生的门徒作鸟兽散,客西马尼园只留下寂静,何其悲凉。镜头一转来到第三个场景,“经过了岩石地带的悲痛以后”是指耶稣受难后。荒山之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演奏复活的序曲。三个场景“蒙太奇”式地展现神之子的遭遇后,终于轮到主角“春雷”登场。“监狱宫殿和春雷的/回响在远山那边震荡”,此处“回响”有几层含义:一指耶稣的呼号。耶稣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二是指磐石崩裂的回响。耶稣断气后“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太27:51);三是指春雷的回响。耶稣完成替众生赎罪的使命,这片被诅咒的荒原终于有了重生的希望,即雷响之后,雨要来了。
“他当时是活着的现在是死了/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稍带一点耐心”此处要联系耶稣对受难和复活的预言,“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5)救世主在春雷中为众人舍命,虽死犹生,而人类遗忘使命,人神离散的结局正在上演。艾略特此处借耶稣之死大声呼号:“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惊雷,是极含蓄的无声呐喊。
下一节反复与“水”相关,因为“水”是信仰与重生的代名词。首先看《创世纪》,第一日出现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1:2)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创1:6-1:7)第五日,神说:“水要多多滋养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创1:21-1:22)水作为世界的界线隔开了上下,神主张在水中滋养出生命,这里的“水”是生命之源。其次,《出埃及记》中“摩西”出生也与“水”有关。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时发现了蒲草篮子里的男婴,取名“摩西”,“希伯来语意为‘从水里拉出来,而‘从水而出的古希腊文为‘sunistem为‘立定之意,如‘万有也靠他而立”[3],即“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西1:17)这一寓意将水赋予了深刻的再生意义,同理耶稣和信徒们的受洗皆是“再生”。而在艾略特笔下,荒原处于没有生气、濒临死亡的境地,“这里的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也不能坐”,人没有行动、话语和思想,只剩一副躯干,“各种世界像在空地里拾柴火的/老妇人那样运转着”[4]。被春雷击打的山间形成一种让人窒息的、虚无的、真空的状态。
第三小节更能展现艾略特对“水”的用意,分别从内容、声音和诗歌形态上强调“水”的消逝,人神离散的事实。首先引用“磐石出水”的典故。百姓因在旅途中没有水喝发怨言,摩西求耶和华,耶和华便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出17:6)这是艾略特从内容上暗示“水”作为生命源泉的意义。其次,他还从声音上强调“没有水”。“滴水歌”是艾略特的得意之作,是“全诗最佳的一段”[5],是将诗歌形式和艺术内涵紧密结合的典范。蜂雀画眉声调清亮、音韵甜美,其歌唱不仅悦耳,还如甘泉一般流淌心间,这是艾略特在声音上借用鸟雀的歌声强调“水”,暗示人类重缔人神之约的希望。另外,艾略特还在诗歌形态上强调“水”。我们可以将这一小段诗歌的最后一个字连接起来,就会出现一条类似“S”的曲线,似乎是一条蜿蜒的溪流。此种手法并不新奇,比如肯明斯的《太阳下山》。
诗歌形式古怪,只有破折号一处标点。“全诗除最后一字‘S系大写外,全部小写,可能暗示不愿破坏钟声回荡的旋律;大写的‘S可能象征梦幻之多,之大”[6],诗人显然在描写夕阳西下,远近敎堂钟声齐鸣时的感觉,但诗中未提及一字。“风”将大海“卷进梦中”,诗歌似乎要将风的形态展现出来,表达波动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测艾略特也是用诗歌形态暗示“水”对于荒原的重要意義。
在第四五节中,紫色的暮色、倒塌的城楼、文化名城的衰落,都在暗指战争厮杀,这与耶和华的叮嘱背道而驰。假如上一节我们还在猜测“谁是那个总是走在你身旁的第三人”,这一节(“这是什么声音在高高的天上”)就告诉我们,是炮火淹没了耶和华悲伤的呢喃。“慈母”般的呢喃诉说着人神之约断裂之后神对“孩子”离经叛道的绝望,直至所有的文明“忽喇喇似大厦倾”,一切化为虚无(Unreal[7])。
第六节中,战乱的人类生活在无水的荒原上,“有声音在空的水池、干的井里歌唱”联系《耶利米书》和《箴言》来理解。“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又有“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箴5:15)。艾略特暗示人类背弃上帝,就连“教堂”都成为圣杯传说中“凶险的教堂”,即一个荒芜残破,空无一物的空间,暗示神圣之地已被人抛弃。因此,人类精神上的信仰和形式上的信仰都已经彻底忘却,诗人影射了人类文明没落的结局。从第一节艾略特呼喊着“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到第三节荒原世界没有一滴“水”,从第五节文化名城皆为虚无到凶险教堂只剩“枯骨”,艾略特尽全力书写人神的离散的悲惨结局,即文明的没落和人类精神的荒芜。
二.人与神的相遇——现代版“出埃及记”
“荒原”是一个整合性与直喻性兼具的意象,它整合了全诗冗杂又沉重的内容,直喻了现代西方社会丧失信仰的境况。有学者认为《荒原》有两层属性,第一位是“荒”,第二位是“救”[8]。《雷霆的话》第一小节讲述福音书里耶稣受难的过程,包括被捕前、被捕时、受难后三个画面。经过此番考验,耶稣毅然决然献出自己,神之子已经“死去”,众人活着却“快要死去”。再回首耶稣受难,艾略特正在提醒人类,荒瘠的困境正是因为当下没有奔赴受难的勇气。这是艾略特对“荒原人”给出的第一声“惊雷”,是一种启示,一种预警,是对人类必须悔悟的警告。
在二、三节中,艾略特从诗歌内容、声音和布局上强调“水”,暗示“水”是人类重生的源泉,是人神缔约的媒介,“雷霆的话”自然是拯救荒原的关键。接着“谁是那个总是走在你身旁的第三人”,“第三人”是有深意的。耶和华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在荒原中时隐时现“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第三人”悄悄随人行进,这和耶和华指引摩西带领民众离开埃及十分相似。人类已到绝境,最终只能像《出埃及记》一样跋山涉水,流血牺牲才能达到流着奶与蜜之地。联系“磐石出水”的典故暗示当下人类的经历就是现代版的“出埃及记”。这种猜测的依据有二,一是全诗的荒原意象都在反映“水”的干涸,同时磐石涌泉又出自《出埃及记》;二是《出埃及记》中的重新立约。“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事。”(出34:10)立约呼应了结尾的雷霆之语。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这些细节不是偶然,是艾略特向人类发出的警告,人类想要得到生命之水必须重拾人类信仰,归根结底还是要缔结人神之约。这一节通过“没有水”指出人神之约断裂后的人的悲惨处境,即“人不能停止或思想”,这是诗人为警醒人类送出的第二声“惊雷”,比上一次更加迫切。“只有一只公鸡站在屋脊上/咯咯喔喔咯咯喔喔”,鸡鸣是吉兆,公鸡一声破晓驱散鬼魅,同样与耶稣受难有关。艾略特再次暗示人类得救的希望,紧接着闪电到来,湿风到来,“雨”终将到来。第七节出现了“恒河”和“喜马望山”,在圣河圣山的背景下,依然诉说了人类重拾精神信仰的愿望。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前七节的内容,诗人先讲“人神之约的断裂”,接着表明“神为子民走向歧途的悲伤”,最后来到第八节“神宽容慈悲的给予人类启示”,雷霆的话是神最仁慈的告诫:即“舍己为人。同情。克制。”这是重缔人神之约的唯一方法。首先是“舍己为人”,如耶稣一般,精神荒芜的现代人能否追寻心灵的安宁要看舍不舍得“给予”;“同情”是“打开牢笼,停止孤立,破除自我与外界相通”[9],也是抛弃冷漠,打开感知接受世界,与他人相连,拒绝绝对的对立和对抗;三是“克制”,像耶稣一样不惧生死的考验,像约伯一样领悟信仰的真谛,在情欲之海中学会自持。因此,艾略特用“荒原”象征现实人类空虚的精神世界甚至异化后的自暴自弃,一声声惊雷都是艾略特对现代人的警醒,是重新缔约的方法,这三句教导终将指引人类重新上演现代版的“出埃及记”,完成战后的深刻反思。
三.相遇之后的出路——构建“我——你”关系世界
特雷·伊格尔顿认为《荒原》是一首向人们“暗示生殖崇拜就包含着西方得救之线索的诗”[10],他认为艾略特利用一种极右的权威主义否定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借助“充满暗示性的扑朔迷离的意象”恢复“一个在血液与内脏之中的普遍认同感”[11]。艾略特在战后借助如此隐晦的语言实际上是看到推倒一切,重新来过的契机,正如伊格尔顿在《T.S.艾略特的〈标准〉》中所说:“如果文明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么也就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并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说,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面向未来前进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根植于传统的过去之中……通过它,人们回归到现代之前的资源里,以期向后运动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12]工业革命后,人类走上现代化之路,随后“现代化”无限膨胀,最终在一战中爆发出毁灭一切的力量。战争,促使人类思考未来走向。结合《荒原》全诗,西方世界处于精神凋零的边缘,人类的世界皆没落在“紫色的暮色”中,战争就是典型的“我——它”世界的结果,所以艾略特借《雷霆的话》重新上演“出埃及记”,提醒人类与上帝重新立约,人类应构建“我——你”世界。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讨论了“相遇哲学”。他点明世界的二重性和人生的二重性,“我——你”世界与“我——它”世界的对立。“我——它”世界即人类将万物看作与“我”相分离、相对立的对象,“它”世界变成为我所用、满足欲求的工具,即“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当做使用对象”[13]。如今,技术的发展无限拓展了人类的欲望,人根据目的、状态、特点的不同分门别类地对“它”加以利用,如人类“征服自然”的行径,马丁·布伯暗示此种关系必然会伴随“我——你”世界关系的削弱,艾略特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选择“出埃及记”和“舍己为人、同情和克制”警醒世人。
“我——你”世界即世界万物不再与“我”分离,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利用主体,我用自己的“本真”真正地将“你”视为“你”,不再掺杂任何预期和目的来建立联系,“‘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14]。布伯從宗教家的身份出发,认定我与“你”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指出以仁爱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这种“仁爱”和《雷霆的话》不谋而合。人类只有在真正认识到“我——它”世界的弊端才能真正理解“雷语”的真谛,“舍己为人、同情和克制”正是人类将世界视为“你”的方法,离开荒原,重拾信仰,再次与上帝立约,与上帝在“永恒之你”的瞬间相遇,构建“我——你”关系世界,才是《雷霆的话》的真正目的。
一战已成历史,但人类的智慧还在熠熠闪光。分析诗歌时不能带着冷漠虚伪的态度,干巴巴的典故罗列只会让本就晦涩难懂的文字索然无味。在耻笑“荒原人”的虚妄无知时,阅读者本身也会变成荒原中的一员,我们是否思考过“舍己为人、同情和克制”?是否反思“我——它”世界的弊端?是否有重建“我——你”世界的觉悟?一切都可以从雷霆的话中得到启示——舍己为人。同情。克制。
注 释
[1]艾略特:《荒原》,赵萝蕤,张子清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第55页.
[2]刘崇中:《解读〈荒原〉与文学鉴赏的困惑——兼与曾艳兵同志商榷》,《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77頁.
[3]蒋栋元:《生命·再生·罪与罚——〈圣经〉中的“水”意象》,《外国语文》,2010年第5期,第116页.
[4]艾略特:《前奏曲》,赵萝蕤等译,《艾略特诗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28页.
[5]李俊清:《艾略特与〈荒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90页.
[6]袁可嘉:《略伦英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第79页.
[7]李俊清:《艾略特与〈荒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22页.
[8]彭舜:《艾略特〈荒原〉的意象系统和解读困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103页.
[9]赵萝蕤:《〈荒原〉浅说》,《国外文学》,1986年第4期,第62页.
[10]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40页.
[1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40页.
[12]特雷·伊格尔顿:《持异议者: 关于费什,斯皮瓦克,齐泽克和其他人的批评文章》,王敖译,未在国内出版,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06688/
[13]张世英:《人生与世界的两重性——布伯〈我与你〉一书的启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28页.
[14]陈维刚:《马丁·布伯和〈我与你〉》,《读书》,1986年第10期,第42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