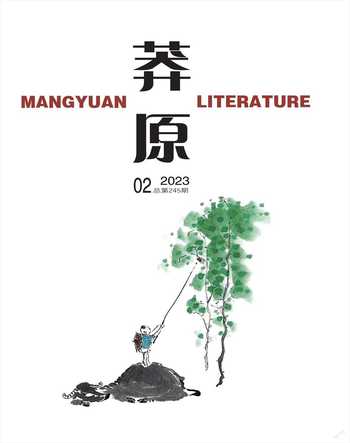一个影迷的秘密
唐棣
“看我的电影不需要说明书,我的作品有不少意义,我宁愿观众用自己主动的象征主义去解读。就好像心理分析那样,人总有自己的秘密。没有这秘密,就没有艺术。”
——杨·史云梅耶
一
对于一个生在北方乡村的人来说,我小时候的生活和电影无关。电影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一种场地艺术。1992年,我告别乡村,随家人搬到县城。现在看来,并不遥远的空间变化,对一个从未离开过村庄的九岁男孩影响还是很大的。他发现,小小的县城似乎比村庄外那片田野更大,然后就是大大小小的汽车和各种招牌的商店在眼前交错,感觉每天都有新店开张,旧摊撤走……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我第一次接触电影,就是这个时期。有一天,我走在放学的路上,发现路边一个很大很高的门面开业,敲锣打鼓,一道又宽又长的台阶通上去,门口还挂着各种“画”(海报),那就是小县城的第一家电影院。当时我站在路边看了半天,即使调动所有的想象力,恐怕也很难想象里面会是什么样子。之前,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去县礼堂集体活动,可能电影院和礼堂是一样的吧。后来有一天,学校照例集体活动,本来,我和同学正排着队按过去的路线走向礼堂,忽然老师通知说,临时改地方了,继续向前走。队伍经过礼堂时,我发现礼堂正在装修,关着大门。
我就是这样闯入了电影院。第一次坐在红丝绒椅子上,被黑暗包围,那是一种我到现在都没法概括出来的感觉。从那次开始,一到寒暑假,老师会给我们发电影兑换券,让我们假期看电影写日记。可能是知道我们整天只想着玩,日记没什么可写,这么说,电影有时候也曾充当过一种弥补生活的东西。这是老师的想法。其实放假后,我觉得什么生活都变得有意思起来,才不愿意去看一场电影。所以,我对那时看过什么电影没留下印象——为了完成作业,我肯定去看过一些。
等我再长大一点儿,想起电影里那些美丽女孩时,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县城电影院,忽然成了小商品展销会的场地。很突然,平时上学放学几乎天天路过,却从来没有留意。可能没落是慢慢发生的,只是我太疏忽了。
我当时不是个影迷,不爱电影。应该说我什么爱好也没有,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什么叫爱的。让我描述,就是县城电影院的没落,就像它当初忽然出现在我眼前似的,真是来得快去得快。
这里说的电影和电影院是相连的。当然在村庄里我也看过的露天电影,距现在不过二十几年。我一直觉得,电影院里的黑比乡村的夜晚更黑,露天电影的观众永远没有那么整齐,我印象中旅行箱大小的放映机,经常烧断胶片。每次电影一断,眼前的人群,就变成黑压压的人浪,这时我总会注意后方的放映员,他满头大汗,一边轰我们这些起哄的孩子,一边手上快速地粘胶片。电影重新投射到风中的幕布,现场马上安静下来。
只记得露天电影里的对白,永远配合着夜晚的风声,传得很远很远。我们这些喜欢爬墙头的孩子们长大后,估计也没人记得当初看过哪些片子。应该是一些战争片,我努力回忆出来的是,孩子们在人群里学着电影情节,互相追逐,打打杀杀的片段。那应该就是电影对我们的最大影响了。
其他的事,就是我到县城后,心里产生了对比,就觉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通过更大的银幕看的电影才叫电影。索性就把乡村夜晚看的那些不叫电影的电影全忘记吧。
也就那么几年,电影院没了,我的生活又和电影断了联系。中学、考试,偶尔在电视上看电影,大部分时间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有人会想到那时候的孤独,我就不知道这回事,县城的日子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句电影台词,那部电影是我偷偷看的。一个男声说:“岁月匆匆,而今我爱上了许多女人,当她们紧紧拥抱我的时候,都会问我是否会挂记着她们,我想当时的我的回答是,是的。但是,我唯一没有忘记的,却是从来没有问过我的那个人……”一闭上眼,就是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孩,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
这个电影是我从集市的一个旧货摊上买的。VCD封面上,除了女人的侧脸和半身轮廓之外,其余部分都是黑色的,一道侧光从胸部划过带来的诱惑,让我赶緊交钱,匆匆逃走了。
而后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困扰我很久,直到有一天,看《四百击》时,心理上获得了解脱。小男孩安托万和同学逃课看电影,离开电影院时,从橱窗里偷偷撕下了一张剧照——伯格曼电影《不良少女莫妮卡》的剧照:少女莫妮卡,微闭着眼,迎着阳光,整个上半身最显眼的,是裸露的肩膀,还有松松垮垮,随时脱落的上衣……当年我偷看电影《玛勒娜》(又名《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年纪,可能比小男孩安托万他们大一些,但看到《四百击》这段情节的那一刻,我立刻紧张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上面那段偷看电影时脸红心跳的回忆。
现在我从事电影这一行,偶尔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喜欢看电影。我偶尔半开玩笑似的说,爱上电影的理由很多,不过最重要的一个,是莫妮卡·贝鲁奇!
当初我以为,只有自己那个年纪才会面红耳赤,觉得亲吻、裸露这些很新鲜。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很多西方人觉得美国电影《七年之痒》(就是梦露站在井盖上裙子扬起那张照片的出处,其实电影里没有这个镜头)里的梦露,就让人心跳加速。这是一部关于欲望的、美丽的女性电影?
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法国电影报刊很多都在写美国电影(还有其他国家)里的女性。法国影评人不是喜欢玛丽莲·梦露,就是喜欢奥黛丽·赫本(《罗马假日》),要不就是简·拉塞尔(《绅士爱美人》)、玛琳·黛德丽,等等,据说“这些出自影迷之手的文字,口吻往往像是爱的告白。”(安托万·德巴克《迷影》)新浪潮导演特吕弗还创造了一个词,专门说这类电影带来的影响,叫“迷影情色症”。
话说回来,现在我可以算是一个影迷了。当我走进电影院,坐在红色丝绒的椅子上,整个空间暗下来,只剩下一束五光十色的光,从背后投向大幕,心里还是有些激动的。无论电影好坏,对于影迷来说,看一场电影的意义,牵扯着不少回忆,像阿姆斯特丹电影资料馆馆长埃里克·德·凯伯说得那样,“整个过程宛如经历了一次情感教育。”直到从电影提供的碎片里,悄悄整理出一个自己。过去的自己让现在的自己变得丰富,这可能就是我的变化。
二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了解一个影迷脑子里在想什么了。我有时候也想不明白。
随着时间流逝,电影和观众慢慢地都变了。虽然有点无法适应,但未来总是好的。这种改进,并不是同步的,有时候出现很多问题。这里主要说电影,现代电影艺术,甚至所有现代艺术都充满“敌意”,已经很少看电影时的温暖感受了。我也理解,那种对一成不变、多年形成、有年代感的标准答案的反抗——这也是每次提到“迷影精神”(电影之爱),就意味着跌进了一种怀旧、忧郁氛围的原因。
看电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复杂?之所以提到观众想什么,是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一切似乎都在使观众程序化地失去幻觉,观众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只能见证电影的这一过度膨胀,从而把有关电影的幻觉推向终结。”(波德里亚)
在我和电影有关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影迷的变化好像赶不上电影的进步了。这种进步,首先是科技进步,其次是与之配合的观念,关键在于看电影这个事有点特殊,不是内容、场地等等一变,就可以让人的感受也跟着彻底变过去的。
应该说,县城电影院给那时候的我的震撼,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高科技的电影院已经远远超过那时候的影院配置。我没有震撼坐在杜比影厅,看120帧4k3D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因为,我在电影里只看到现代技术侵入了传统电影叙事而已。观众、评论者感受上,哪怕导演自己都没有离开24帧审美的影响。这是由漫长的电影回忆组成的。
不能否认电影和其他艺术一直处在改进中。至少现阶段,更清晰、沉浸的现代美学没有及时跟上时,谁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件好事。回到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那句话里的“幻觉”,我觉得,它指的可能是过去式的、24帧速的古典好莱坞模式下的情感共鸣?作为一个影迷,我还没法完全适应“现代科技”电影。当然,它还已经程序化地失去了——程序化和科技发展有关,一方面人为事物的终结而伤痛;另一方面人也为事物流逝后,可能会显现出更恒久的东西感到了安慰。
想想看电影——这个行为本身也有矛盾性:既属于少数人,可以激发多种表达,又依赖集体发酵这种感受。看电影不是一件孤独的事,我们现在看电影的情况变得和读书差不多,这非常奇怪。
我从小就意识到真正的电影就是在电影院里看的电影,首先来自大银幕。现在我可以加上真正的电影来自观影的仪式感和不间断的令我们产生幻觉的光影。
影迷可以崇拜电影院,认为那是一个流动着感情的场所。看电影时,影迷会不知不觉把自己记忆装进他人的故事,以至于分不清幻觉和现实,有一种说法是延长了“生命”。也许,波德里亚所谓的“幻觉”表示一种类似的模糊事物,它不是从影迷的眼前消失了,刚刚去世的法国导演戈达尔说过,“电影不是梦境或幻觉,电影就是生活”。电影被现代生活重构之后,也让你的生活有机会进入电影,电影又连接着更多人的生活,生活这个词的内容变大了。
我知道,人再也没法回到小时候。电影不仅和我相连,它和每个现代人都有关了,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今天的电影既不知道暗指,也不理解幻觉……没有空白,没有间断,没有省略,没有沉默,如同电视一样……”这些都是一个影迷的抱怨。这些理解一旦跟不上它变化的速度,就意味着失去更多,所以我反而买起了影碟。
下面的话出自波德里亚的《艺术的共谋》:“它已经不再是真实时间里被生产出来的图像。我们越是接近绝对的清晰,接近现实主义的完美图像,幻觉的权力就越缺失。”应该说,一个影迷钟情的是超出内容(现实反映)的幻觉:“最深切的体会来自一次一次确认(拥有)幻觉的快感,像上述追忆一样。幻觉把我带入一个想象。”
大部分时候,记忆像“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处于四处流散,一片混乱的状态”(瓦尔特·本雅明)。而我看到了做记忆收藏家的可能性,“和收藏品的四处流散进行斗争”,在混乱的时间中,建立秩序,也就是去看,去听,去感受。假如我说清了这一点,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意识容器”的说法就好理解了:电影可以把过去带到当下的意识副本,其中裝入复杂的情绪和与现实世界不一样的“时间感”。
人们从电影里得到的,不是一种在现代生活里无法得到的庇护,更像是一种生活更具体直接的打开方式。灯光亮起,走出影院,每个人对电影的看法还是在起作用,它在不知不觉间组成了生活中的话题,进而让人刷满人的存在感。一切关于电影的谈论,借助的都是它这种包容性和复杂性。
影迷和社会的变化势不可挡,在这种变化之中,人感受电影的能力需要一个稳定的审美,而我们对这些的关注不多,有时我也劝自己忘记这些,让看电影回到小时候那种简单的欣赏上来。
现在,影迷好像成了“孤独的人”的代表——至少心理上没那么合群。我当初和很多人在电影院,看过一个电影叫《鲁迅》,里面有个场景印象很深。那是一个深夜,两个文坛后生送鲁迅回家,分开时,鲁迅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孤独的,但我孤独。后来,鲁迅一个人越走越远,他们忽然朝着鲁迅喊,先生,我们也想做孤独的人!
现场观众有不少人掉了眼泪。放现在的话,孤独的形式和感受可能不一样了,“您知道吗?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凝视着被您的天才所照耀的那块银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独……”一位女性观众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镜子》后给导演写了这些话,现在的影迷已经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我长大后曾读到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句:“请理解,一个人必须独自在人间创造/一个新的天堂和地狱,是多么艰难。”人间不就是一个黑白交替的空间吗?创造它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关系和关系组成的生活。这个时代除了借艺术谈一下孤独这件事,也没有别的好方式了。
接下来我写一点体会。这么多年过去了,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创造的“穆谢特”形象,还是会让人想到米沃什的诗、伟大的鲁迅,以及他笔下的那个旧时代。
小说《少女穆谢特》开头是“西面吹来的黑色狂风吹散了夜色中人们的声音。安德烈说这风来自大海……穆谢特刚才听见的那个声音久久徘徊在天地间,如同一片不断坠落的枯叶。”这种感受如同她在小说结尾,滚入河中而死带来的震撼。
穆谢特一生是短暂的,“穆谢特憎恨,蔑视周围的人,只有厌恶他们才能让她狂野的心灵真正得以休憩。自己這种叛逆的本性和对他人的排斥用理智是解释不清的,她便用自己的方式挑战孤独,就像有时累极了,她会故意躺到泥泞的道路上一样。”贝尔纳诺斯在小说最前面,写到“故事一开始,我就选定穆谢特这个熟悉的名字,自此已不可能再更改了。《少女穆谢特》中的穆谢特与《在撒旦的阳光下》中的穆谢特只有一个共同点:两个人都是在极大的孤独中度过了一生。”
1987年,导演莫里斯·皮亚拉把后者拍成电影。这次电影里的少女穆谢特遇上了好心的神父多尼桑,16岁的她杀了人,多尼桑希望帮助她获得上帝的原谅,后来穆谢特还是自杀了,随着她的死,多尼桑身体里的恶魔也被放了出来,开始折磨他。其实,他们在接触的过程中,都不曾走进彼此的心,虽然神父想帮穆谢特,但神父自己的问题也很多,最后两人都失败了。有意思的是电影成功了,导演皮亚拉在第40届戛纳电影节的颁奖现场,手拿金棕榈奖牌,面对台下的嘘声说:“法国人不喜欢赢,而我赢了。”
关于莫里斯·皮亚拉这个导演,我还有一些话。1968年,就是特吕弗《四百击》拉开法国电影新浪潮之后的九年后,皮亚拉才拍出了处女作《赤裸童年》,制片人就是导演特吕弗。因为题材相近,有人指责皮亚拉“模仿”特吕弗。众所周知,“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实现的,无非是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西奥多·阿多诺语)我相信皮亚拉。他在《赤裸童年》里,设置的小男孩弗朗索瓦是个孤儿,不断被人收养,慢慢变得听话,“家人”也都对他很好,他也开始理解别人,一切看似都在好转。转折发生在1小时19分28秒,负责照顾他的老奶奶问弗朗索瓦,你想在阳光下散步吗?54秒后,弗朗索瓦和几个小男孩躲在桥边抽烟,成熟地把烟倒着放入嘴里。镜头切中景,对准小男孩弗朗索瓦的笑脸上。阳光很好,几个孩子所在的地方不远处,是一条有点喧闹的公路。没有比“扔”这个动作更让人舒服的了。这隐喻着释放与抛弃,整个动势充满对胜利者的想象——
少女穆谢特在电影《穆谢特》14分49秒向同学扔出了石子;小男孩安托万在《四百击》第1小时4分17秒也拿着管子,向街上吹石块;《赤裸童年》在1小时11分4秒,小男孩弗朗索瓦,从桥上朝行驶的汽车扔出了铁路边捡来的螺母,飞出去的螺母砸中一辆车,车紧急刹车,撞在墙上,弗朗索瓦转身就跑,23秒后他被捉住了。新一轮的流浪又将开始,故事的结局陷入一种不可躲避的现实。
和《四百击》温柔的结尾相比,现实更像《赤裸童年》里的那样——弗朗索瓦做事一点儿意识都没有。结尾是在少管所的弗朗索瓦给对他很好的那对老人写来一封信,他天真地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我非常想念家里和你们。我保证在圣诞节之前,还有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会很好……”
三
人好像一直活在过去里,每一秒都是曾经的一秒。电影也是一样,它表现的是时间上的过去,空间上的曾经,感情上的灰烬。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写:“这一切都已过去……我的童年已不存在,可以说,虽然我还活着,但童年已经死了。”这句话直指上面三部电影里讲的那种影响至深的孤独。
人活着,就想离开,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孤寂,更多的痛苦,更多的离弃。同时,有一种期待,一种我自童年以后就不曾体验过的期待……”(约翰·伯格《抵抗的群体》)
再次谈到记忆时,我想说它有意思在越近的事越记不住,怀旧就是离现在很远很远那个时间点的记忆。它与时间的关系很特殊,是“虽然我还活着,但童年已经死了”的关系。我一直想写这些关于电影的回忆,和自己对时间的好奇有关。
波伏瓦回忆录《清算已毕》里说:“我的人生被分割成碎片,变成一连串凝固的瞬间,但实际上,每个瞬间都包含着过往、当下和未来,三者密不可分。”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人们孤独得就像五根脚趾头,互相依存,却谁也不理谁。”
作家徐星的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写的那个时代,我应该正处于少年时期,和我上面写到的三个少年形象年龄接近。“我们一天天地活着,而就在同一个瞬间,另一种时间也的的确确在缓慢地流动着。能不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用内心的角落惦记着这一点,必定会带来天壤之别。”(星野道夫《旅行之木》)人在社会上走一圈,就发现失去比得到的多。所以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孤独。既然如此,可能就理解孔子捋着胡须,站上河岸,一边吹风,一边感慨: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至今,这种情景也没有消散,只是变成了其他形式。1906年9月28日,塞尚去世前给儿子写信:“我必须保持孤独,人们是如此狡猾,以至于我永远也无法从中脱身。”由此可以想到,某个在都市里选择在周末走进电影院的影迷,与他们相对的另一个情景是,一个北方少年,某个下午放学后,匆匆跑进县城电影院——没人知道他们看的是什么内容的电影,但他们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仿佛那人的身上保持着某种圣洁、高傲的东西——我相信,他在电影中能获得别人所无法获得的体会。那种体会和电影内容无关。
再问一遍,我看电影的时候想到过孤独吗?
我这次想说,不知道。
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孤独像一种宿命。也许,我没法完全理解齐奥朗写的那些书,但他有一句话触动了我:“孤独不是教你去独行,而是教你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影迷的秘密就是在电影中埋藏自己的记忆——独行是自己,而独特是有参照物的,像众人在同一家电影院看同一部电影,就能形成一种“集体感受”,在这个集体中,你独一无二的感受很重要。
他人能影响你吗?你相信他人的感受?大家会觉得电影和生活一致?其实,电影和生活的关系一直都没有说清过。我们不希望“电影就是生活”,因为不想陷入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所说的“无处遁逃,这就是我”的窘境。当然,也不希望电影和生活完全无关。我们对未知的恐惧也没法免除。按W·H·奥登的分析,电影在生活与创作间建立了一种奇异的时间观念:电影是一种与现实时间同步的艺术形式,并且鼓励观众如此想象。
而任何一个影迷心理上都不愿想象恐惧,更愿意回忆甜美,哪怕甜美中始终带有伤感。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