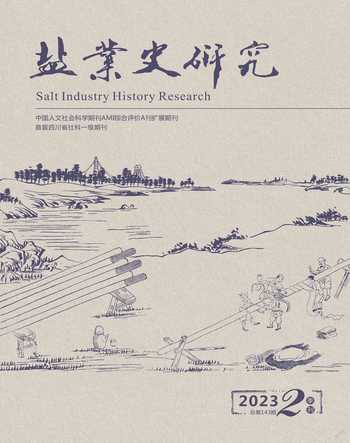民国时期自贡王三畏堂中落研究
莫秋月
摘 要:王三畏堂是晚清民国时期川南最有名的盐业家族之一,其发源于明代,兴起于晚清,衰微于民国时期。王三畏堂的兴亡过程是近代自贡地方史、盐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其兴起和发展与晚清农民起义、政治现实等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其衰落除了自身内部原因外,与民国时期的军阀、财团、新的政商关系的产生,以及传统民营方式与现代化的冲突都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近代;王三畏堂;家族;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2-0067-9
王三畏堂发源于明代。根据王氏宗族族谱记载,明朝初年,王氏先祖王公自湖廣黄州府麻城县迁往四川荣昌县。到成化年间,王氏心二和心七两兄弟来到富顺县仙骡井,以煎井为业。明末四川暴发张献忠起义,王氏族人四散逃亡至成都、邛州、泸州、贵州等地,致骨肉分离①。直到清朝初年,一部分族人才又回到自流井定居。后来,王氏祖先在自流井与当地王姓人私下联宗,结为兄弟,并分为金、木、水、火、土五支,王三畏堂属于其中的木支②。
一、王三畏堂的兴起
王三畏堂是在当家人王余照时期发迹的。可供世代蒸尝的族产如房屋、土地、井眼等基业为王三畏堂的崛起提供了原始资本。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川盐济楚”政策成为王三畏堂兴盛的关键性因素。众所周知,自清代以来,统治者对于盐销区的管控向来十分严格,致使川盐尽管质美价廉,具有与海盐竞争的实力,却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其市场也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切断了淮盐行销至湖南、湖北地区的道路,使楚地陷入淡食。清政府为了解决食盐问题,改变了原来的引岸制度,允许川盐销往两湖。清政府对川盐销区管控的放松促使川盐的市场一时间空前扩大,王三畏堂也是在这一时期应机而起,发家致富。
膨胀的市场,高额的利润刺激企业家们加大对盐业经营及技术的投资。王三畏堂在当家人王余照的经营下建立了集井、枧、灶、号为一体的家族式垄断集团。据统计,极盛时期的王三畏堂拥有黄、黑卤井数十眼,推水用牛1500余头,日产卤水1100担,盐锅700多口,管理人员200多人,雇工1200余人③。作为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工场手工业民营集团之一,王三畏堂开设了广生同盐号,其分号远至邓井关、泸州、重庆,以及湖北的宜昌、沙市,其拥有的土地跨富顺、荣县、威远、宜宾等数县。自流井地区还有“川省之富者,向以自流井之王姓为巨擘”① 的说法。
一个晚清时期赫赫有名的盐业大家族,却在短短几十年后就走向衰落。王三畏堂的中落研究是研究王三畏堂家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自贡地方史的一个微观视角。
二、民国时期王氏家族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恶化
(一)民国时期政商关系的变化
绅商阶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介于官与民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又涉足官场,游迹于功名职位间,成为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一支活跃且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②。王三畏堂是传统的民营企业,其当家人既有商人的基因,同时,在获取了巨大财富之后,他们也积极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王余照就曾捐候补道,后又加按察使衔。光绪五年(1879)正月二十一日,王余照因捐银5530两赈灾山西、直隶,李鸿章即奏请光绪帝赏其二品顶戴以示奖励③。据史料记载,同年三月初十,丁宝桢对王余照进行了严厉控诉,并请求光绪帝对“候选道员王余照革职提审”。三月十二日,光绪帝下令将王余照先行革职并交由丁宝祯审办。又根据同年四月初五丁宝桢上奏光绪帝的奏折中可知,王余照已经因“反官运事件”出逃在外④。两年后,王余照回到自流井。光绪十年(1884),王余照去世。因此,受赏二品顶戴实际上也是王余照仕途的重要转折点。
复杂的社会属性赋予了王三畏堂家族企业丰富多元的社会关系。在商界,王三畏堂通过联姻等手段与富荣盐场其他盐商家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家族与家族之间互相沟通,利益相关,形成了家族掌控富荣盐场的局面。在政界,王三畏堂利用所掌握的财富,通过捐官、科举、资助教育等方式构筑了庞大的政界关系网。晚清时期的富荣盐场,盐商家族控制着主要的盐业资源,同时也主导了地区的社会关系。
就王余照个人而言,此人聪敏,能力极强,且性格较为强势。巨大的财富让他有底气,他坚信财可通神。光绪五年(1879),丁宝桢控诉王余照:“咸丰年间,(王余照)在原籍富顺县犯事受刑,随朦捐候选道员,交结官绅……同治七年七月,以抗阻井捐,经前署督臣崇实奏参革职拿办,潜逃严缉未获,嗣乘崇实交卸督篆,朦准开复……前经李春霖、李吉庆、张永发等赴臣署具控该劣绅私抽井厘数万两,估夺民妻,并控有广行贿赂、交通京外等语。”① 财力、能力、胆识以及运气等因素共同促使王余照一次又一次躲过了官府的制裁。
魏斐德认为:“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是府州县官与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一个地方只要有绅士势力的存在,就保证了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播各种社会信仰,这些信仰长久且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在安定时期,绅士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动乱时期,更是决定性的。”② 富荣盐场位于川南一隅,本就远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受清王朝控制的力度相对来说较小。进入近代以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显得更加力不从心。同时,地方政府也常常会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依赖于当地的富商精英。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李蓝起义军攻陷自流井,给盐场造成很大破坏。以富顺知县胡汝开为代表的清军不足以抵御来自起义军的攻击。于是,当地的盐商士绅在知县倡议下,参与承担主持地方事务的责任,集资修建了军事堡寨三多寨、大安寨和久安寨,保护了大量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王氏族人甚至还亲自组织团练,配合官兵作战,抵御农民起义军。
地方政府与大盐商在财富、力量等方面都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巧妙平衡关系。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官府也会慎重考虑富商精英们的诉求。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政商关系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新的互动模式,商会即是其互动的产物。1911年,四川通商会联合会自贡商务分会成立,1915年改名为自贡商会。新式的商会是介于官与商之间的机构,相较于旧式的会馆、行帮等组织有了很大的进步。商会规模较大,其内部机构设置较为健全,规章制度也较为完善。此外,商会是跨行业的统一联合组织,其组织构成摆脱了原来的行业、血缘与地域的界限,将全城各个行业组织构成一个整体。商会通过年会、常会和特会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充满公正、民主的气息③。自贡商会是近代自贡评议盐业纠纷的重要机构,客观公正的运行机制促使商会只站在中立角度解决纠纷。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控制自贡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事务等各个方面。为了维持自身生命力,军阀不断盘剥当地盐产业,并借用武力对盐商极尽剥夺。因此,盐商与地方政府之间原本的牵制平衡关系也不复存在。
(二)乱世中保守求生
清末内外交困的现实使清廷对地方的管控与权威遭到严重挑战,而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的军阀割据则更是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地方上形成军阀控制军、民、政等局面,军事首领霸占地方大权,北洋政府形同虚设。更为重要的是,军队的经济支出大多通过自筹,因此,经济富庶的富荣盐场自然成为各路军阀竞相争夺的地方,其丰厚的盐税和盐政更是受到军阀的严厉控制。
辛亥革命爆发前,川军为拉拢滇军反抗清政府,协议将自流井盐税划归滇军作为滇军出兵的条件。然而,就在滇军援川的半道上,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力量已土崩瓦解。1911年11月,滇军以“援蜀”为名进入四川,12月底,滇军第一梯团长谢汝翼率军占据宜宾,之后进占自流井、荣县和贡井盐场。也就是说,滇军实际上在不費吹灰之力的情况下断断续续霸占了自流井近十年的盐税。1920年,滇军势力撤出四川,自贡改为川军驻守。然而,不管是滇军还是川军,为了增加军饷,发展军队,对于当地的盐政和盐税都是极尽霸占和剥夺。
四川自进入民国时期,有长达18年的军阀执政的混乱时期。频繁的战争、军阀割据混战首先破坏了盐场的正常生产。根据记载:“前清宣统末叶,争路事起,同志军数千人据此,滇军逐去同志军,此地又为客军之战区,民国二年,两被成渝之军,地方受大影响,士绅疲于供应,且疲于奔命,此为民国时代之自流井。”①
在这一动乱时期,王三畏堂家族企业内部的运营也极不稳定,短短20年间就经历了王素峰、王作甘、王如东三任总理的轮换,1929年以后又进入王德谦管理的时代②。
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促使王德谦的盐业经营不断趋向保守,其本人甚至选择隐居避世。自进入民国时期王德谦就开始终年幽居大安寨,潜心佛学,不问世事③。传言他在大安寨只与爱妾住在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门前设有重门作为关卡,门与门之间有窗,可窥见来客。即便是亲信进入,也必须一门启而复闭,再启二门,窗内换人辨认。宅后还设有一道隐蔽的小门,通往大安寨的城墙,以防意外④。据此可见,王德谦防备之心很强且十分缺乏安全感。
当时的报道称:“本市巨绅王德谦君痛恨军阀时代之污浊政治,改为本市一与世隔绝之怪杰。数十年来潜居大安寨上读书礼佛,亲族中除数人外,均皆知名而不得一见,营业范围内之人员亦皆作其事而不得见其人,至于当地军政首长、市民自更无缘见面……”⑤ 对于企业的管理,王德谦则是通过分驻在各井灶点的代表向他传达信息,从而进行盐业经营。在沟通方面,王德谦与自己员工常常能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却不愿面对军政界人士,实在要见,也手足无措,口似不能言⑥。
身处乱世的王三畏堂,在驻军的管控下,不得不仰人鼻息,以谋求寸步的生存空间。与王余照时期积极谋取政治地位、甚至敢于捣毁水厘局和反对官运的锋芒毕露相比,王德谦在历史上留下的更多是低调谨慎、信佛吃斋、忘情山林、乐善好施的美名。其在地方的教育、医疗、慈善以及公共建设等方面都积极地投入。1934年,王德谦与廖树卿、吴冰国向富顺县政府呈请,在自流井公园内设立佛学社,社内经费大部分由王德谦捐赠。此外,1938年,他还出资修建了一栋300平的楼房供社内人员活动⑦。全面抗战时期,王德谦光个人捐款就达1400万元⑧。为此,1945年10月,国民政府颁给王德谦四等景星勋章①。1944年11月,王德谦夫人捐款国币两万元补助妇女会工读②。时人评价王德谦:“王氏(王德谦)现已五十九岁,但精神甚佳,谈锋亦健,学识超人,为改造桑梓不可多得之人物。”③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谙世事的“王大善人”,在族人眼中也曾有过精于算计的一面。王德谦本是达生堂王达之养子。在养母肖氏弥留之际,王德谦以尽孝为名随侍在肖氏身边,等肖氏咽气,立即在肖氏身上找到其随身钥匙,获取其财产。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成为达生堂唯一继承人,并高价收买了王三畏堂以及王作甘兄弟、王文琴兄弟等的达生枧股份,以绝后患④。
王德谦并非天生的隐士,其性格也并不是生来就保守消极。究其长达几十年的隐居生活,除了常被讼事缠身、独特的个人生活习惯以及性格外,很大程度上源于王德谦畏惧且痛恨军阀时代的动乱与污浊。盐运使刘树梅曾说:“军政界想他的方子,他害怕。”⑤ 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富商,害怕遭到迫害与掠夺,但对于现实却又无力改变,因此只能潜心佛学,逃避现实,做一个“与世隔绝的怪人”。
(三)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
企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借债本是正常现象。然而,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之间的债务纠纷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十多年间,涉及的金额更是高达百万,诉讼地多处。期间,渝沙债团不断向王三畏堂施压,并往自流井派驻债权代表。到了后期,债团对王三畏堂家族企业的渗透不断加深,以至于达到干预其内部决策的程度。曾小萍认为,渝沙债团在瓦解19世纪庞大的盐业家族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甚至渗透到了军阀统治时期的整个川南地区⑥。
学界按地域分布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大财团分为华北、江浙、华南及华西四个集团⑦。渝沙债团是重庆和沙市等地的金融人士组织的一个金融股份企业,其主要业务是通过放债获利⑧。与渝沙债团地域相关的华西财团是以重庆杨氏家族开办的聚兴诚银行为核心的金融集团。聚兴诚银行的前身聚兴仁商号在19世纪末就兼做存放款汇兑等业务,并与当时重庆的山西帮、陕西帮、云南帮等票帮建立广泛往来⑨。从地域分布的角度看,渝沙债团大概率与华西财团相关。
王三畏堂在王星垣时代即向渝沙债团借款六七十万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双方的债务关系一直持续不断,直到1928年王三畏堂宣告破产。
根据档案记载,王惠堂时期因经营不善,欠渝地票帮、钱帮白银八九十万两。王达之时期将所有乡庄田产红契交给债团作质,并励精图治,最终将债务基本偿清。然而,王作甘时期又以广生同号的名义向渝沙各票帮、钱帮借贷银钱,且数年拖欠本息,引起渝沙债团的强烈不满⑩。1914年到1928年,债团曾对王三畏堂发起了一系列诉讼,诉讼的机构从富顺县衙、自贡地方戒严司令部、自贡审厅、成都高等审厅到重庆审厅,甚至北平大理院,但都未取得实质性的结果①。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的债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本金,据王氏后人回忆,从1896年到1923年,王三畏堂借款本金基本保持在70万两左右②。除了本金,王三畏堂每年还要支付渝沙债团一分五厘的年息。
然而,渝沙债团对王三畏堂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沉重的债务与连年的利息上。更重要的是,债团持续向自流井派驻债权代表刘润卿、唐子城等,对其经营业务管理进行监督。债团代表的监督实际上是对王三畏堂内部权力的控制与渗透,当债权代表在王三畏堂的权力足够大的时候,王氏部分族人与代表会产生一种依附甚至勾结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其内部的自主发展。1919年,王氏族人与渝沙债团代表内呼外应,将当家人王作甘赶下台。之后王如东继任总理,为讨好债团代表,王如东将总办事机构移至债团代表所在地的牛氏巷“巴山渝水”宅内办公,被人奚落为“受降城”。1921年,王文琴在债团代表的监督下任营业主任。1923年,王德谦借外力勾结渝沙债团代表取代王文琴③。王氏后人王余杞在《自流井》一书中写到:
第一次回家是离家五年之后,那時候,稍稍看到一两双紧皱的眉头,固然穿布面绸里镶边袍子和粉红或翠绿色腿裤的人仍然不少。重庆、宜昌、沙市的债团派来坐岸的代表们已建筑好高大的洋楼,雄踞在井区中心,板起了威严恶毒的面孔。官司打到省城里,结果是一切企业交由债团监督,所有的余利,尽先还债。必然的,时代逼着你崩溃,我并不惋惜,对着家,我只有冷笑。④
王余杞出生于1905年,是王余照的孙辈,作家。在他看来,渝沙债团是跟自己家族相对立的新兴资产阶级,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的债务纠葛,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⑤。然而,不管性质是什么,财团的势力已经影响到王三畏堂家族企业的核心。此时的王三畏堂虽然仍是王家人担任要职,但实际权力已被渝沙债团严重渗透。王氏当家人的任命以及下台,都能看到债团代表参与的影子。
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之间债务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通过破产抵佃的方式来完成的。1928年,王三畏堂宣布破产抵佃,将营业的井、灶、枧等生产资料限年进行偿债。经核算,王三畏堂欠渝沙债团银近931,874两,经王守为以盐号经营困难为由请求减轻债务,再加上调停人的中间说和,实收王三畏堂银533,000两,又王三畏堂欠已经加入渝沙债团的同寿荣债款26,000两,综上,王三畏堂共偿还渝沙债团银559,000两⑥。
王三畏堂破产抵佃后的井、枧、灶等资产,在年限到期后,可要求债权人无条件归还,这是一种“井债井偿”的现象。采取这种方式摆脱渝沙债团的逼索对王三畏堂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也算是无奈之举了。
(四)传统民营方式与现代化的冲突
近代中国社会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独资经济组织、一般合伙经济组织和股份合伙经济组织。其中,股份合伙经济组织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合伙制中内容最丰富,形式也最完备。股份合伙制将合伙的资本等分为股份,且以股份制为其实现形式。它是合伙经济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合伙经济组织,一般合伙经济组织的投资者在出资时,其全部资本不会等分成相应数量的等份①。
富荣盐场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属于股份合伙经济组织。清代中晚期的富荣盐场盛行一种股份合伙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彭久松根据其特点,将其命名为中国契约股份制②。这种制度的合伙人成分属性比较复杂,既包含当地人与外地人,又包含亲属与非亲属。它的存在完美地解决了主方资金不足、客方缺乏土地的弊端。早期王三畏堂也是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发的家。王余照依靠陕西商人的财富,开发了扇子坝的废旧盐井,奠定了其井盐事业的基础。
家族堂是富荣地区集结商业资产,进行多种经营,反对收税人、债主和家庭成员攘夺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将早期的有限责任与纵向一体化完美结合,是晚清时期中国最先进的商业组织之一,存在时间至少半个世纪③。祠产作为一种家族财富,可利用血缘和亲属的纽带,通过世代蒸尝的手段使其族人世代享有祖上留下的基业。在王氏家族井盐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族产给予了王余照发家致富的原始资本,族人群体又给予王三畏堂人力的支持。借助家族的力量,王三畏堂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性盐业集团。
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现代化的条件下,公司制逐渐普及。这是一种能有效组织生产、集中资本、扩大企业规模的高级企业组织形式。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它的出现从法律上对“公司”进行了界定,且对公司内部运作以及股权的转让、股票的买卖等内容都作出了规定。《公司律》的颁布有利于维护营商环境与营商秩序,从而促进一大批华商踊跃投资,大办公司④。
清朝末年,王余照通过契约股份制和家族堂的企业组织形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井盐事业,获取了巨大的财富。然而,随着生产发展的现代化,传统的家族企业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也是王三畏堂后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章开沅在对近代官绅商的研究中认为,明清以来,长江中游的乡村社会形成了宗族式的乡绅“自治”社会。但是,进入近代后,宗族社会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迁,从而陷入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衰败之中,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严重崩溃的现象⑤。在传统宗族制度下,家族内部一方面积极鼓励生育、增加人丁,同时又提倡族产平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族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从而导致资本分散在各房,无法集中,企业也无法继续扩大经营生产。抗战时期,当“新盐业家族”都在凭借“第二次川盐济楚”的政策优势改良生产资料,改进生产方式,扩大盐业生产时,老一批的盐业大家族却因为种种原因贻误了这次历史契机。
公司制的产生、机械化生产的出现,给市场带来新的动力与生机的同时也给传统的家族民营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王三畏堂在当家人王德谦时期就趋向保守经营,其本人也终年隐居大安寨,不理世事。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跟随时代发展更新陈旧设备,引进新式的生产经营理念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三、王三畏堂家族内部危机四伏
王氏家族的中落,除了外部因素,与其族人的奢侈浪费以及家族内部的分裂、争端等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余照在世时以勤俭和睦为立身之本,但自其堂侄王惠堂起,就开始了崇尚奢侈浪费的风气。王惠堂作为王余照的接班人,任职期间,挪用公款,大兴土木,王惠堂在清疆井旁修建厂房,又在长灶房附近修建新枧,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由此负债。此外,王惠堂还在玉川公祠左侧修建承德堂,作为附属建筑的承德堂不管是在用材还是规格等方面都超过了玉川公祠,违背了我国的传统宗族礼制,以致遭到王氏族人反对①。
自贡盐商经营盐业获利颇高,往往出手阔绰,生活奢靡。在饮食方面不亚于宫廷,在排场方面不逊于官府,在娱乐消遣方面,自贡地区茶房、赌场、烟馆、妓院、戏院等场所生意兴隆②。王氏族人大多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总理王达之就是个老烟枪,常常早饭后大吸鸦片,他死后在孝堂守夜的人都以抽鸦片来消磨时间③。当时的《鸦片歌》唱到:
鸦片鸦片,大祸弥天。
费尽产业,金钱荡然。
伤害身体,败坏心田。
销毁精骨,断绝炊烟。
废时失业,洗瘾缠绵。
鸦片宣战,回忆从前。
清廷力弱,英兵炮坚。
既割香港,又赔金钱。
奇耻大辱,猛作警鞭。
凡我同志,戒之为先。④
王余照一直坚信财可通神,也希望其子孙后代能守住基业。光绪三年(1877),王余照与王余炇、王余升商量,仿照范文正义田法,将价值丝银46,890两的20眼井、600亩土地作为家族产业,供族人世代享有⑤。同时,王余照还向清廷申请立案,以望子孙永世遵守。然而,在他死后,王三畏堂逐渐走起了下坡路。三房派系斗争不断,王达之继任总理后,长房和幺房结成一派拥护王达之,二房则仗着人多势众另结一派,双方互相倾轧,一直持续到王三畏堂破产。
“丘二”,是重庆和四川的方言,原本指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太多技能的打工者,后来泛指所有受雇佣的人。自贡地区一般称受雇佣的员工为“丘二”。王三畏堂“丘二”数量众多,其中有不少“丘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的管账“丘二”甚至拿东家的钱财去放高利贷,谋取私利。同时,在职员中也出现了根据长房、幺房和二房两派而形成派别的现象,并相互斗争。
正是由于王三畏堂内部从上而下的挥霍以及分裂争斗,给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带来了恶劣影响,这是导致王三畏堂破产的内部原因。
四、结 语
王三畏堂作为晚清至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盐商家族,其存在和发展一个多世纪,期间盛衰枯荣都与社会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王三畏堂的衰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个必然,除了家族内部的矛盾以及分裂外,更与社会环境、财团、政商关系的演变以及现代化对传统家族民营企业的冲击息息相关。面对巧取豪夺的军阀,王三畏堂的当家人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这自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与壮大;面对渝沙债团的巨额债务,有人选择勤俭刻苦努力还债,也有人选择数年拖欠本金利息,甚至一部分族人還与债权代表勾结一气,出卖家族利益,导致王三畏堂不得不宣布破产抵佃;面对近代政商关系的剧变以及民营企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王三畏堂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最终错过了历史发展的契机,从而逐渐衰落。
(责任编辑:李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