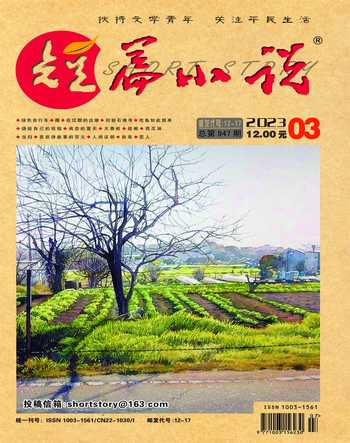喜欢讲故事的百义
李同书
百义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把一个故事从头讲到尾的人。他表情夸张,语气跌宕,像专业的说书人。每当夜幕降临,小小的屋子挤满了人。我拉上王妮,沿着何二家的土墙,从四方形的豆角地穿过去,来到百义家。如果来晚了,找不到好地方,我就抱着王妮的腰,一用力,她就坐到了窗台上。灯光照着百义的脸,满嘴的唾沫像蛤蟆肚子,百义讲得正酣。王妮很高兴,窗台成了她的专座。有一次,百义讲鬼吹灯的故事,鬼被百义讲得很恐怖,王妮吓得直哆嗦,要不是被一个大娘抱住,非从窗台上摔下来不可。村里有了电视机,百义的故事便失去了吸引力,有人卸磨杀驴,诟病百义那些编出来的故事害人。我和王妮是两个忠实听众,我们不喜欢到何二家看电視。天一黑,我们就出现在百义家。百义很感动,想起那次王妮差点从窗台上摔下来,很过意不去,要用锤子砸窗台,我和王妮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胳膊,央求道:“你别这样,百义叔,没有窗户,房子就没有房子的样子了。”有一个秘密我们没说,听完故事回家,灯光会从窗台上爬出来,送我们走很远。百义也不一定真砸,丢下锤子,答应给我们讲一个新故事。我和王妮很高兴,期待着百义讲新故事。
何二把我们堵在了百义家,原来他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气鼓鼓得像一只被蹂躏的青蛙,我和王妮踩了他的豆角地,“种豆角容易吗,”他一脸委屈和愤怒,“翻地,浇水,还要锄草。”他越说越气愤,一定要我们赔他豆角。百义一个劲跟他说好话,替我们讲情:“俩孩子,不懂事,以后不走豆角地了。”何二像一头斗牛,额头的青筋暴出来。“看在你以前听我故事的分上,饶他们一次。”百义脸上堆着层层笑纹。何二眼睛瞪得溜圆,“呸”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提到故事的事,好像是一种羞辱,更加不依不饶,非拉我们去现场。到了现场,吃亏的肯定是我们,想到众人围观的结局,浑身瑟瑟发抖。最后,百义陪了何二一只老母鸡,事情才算完。
故事没听完,我和王妮就回家了。我们没听百义的话,走南壕那条路回家。原路比南壕近多了。豆角地铺满了月光,一股寒气袭来。我拔掉了一根篱笆,快意地朝豆角地迈出一只脚。王妮拉住了我,指着何二家的外门,说:“你看,他看着我们呢。”我扭过头,视线刚好跟何二的眼睛撞在一起,他晃着一只鸡腿,夸张地咀嚼着。周围的地上,散落着沾满鲜血的鸡毛。“真香!”他继续晃动手里的鸡腿。“走!”我拉起王妮。“有人生没人养的野孩子。”身后传来何二气急败坏的谩骂。
百义并没有居功自傲地还原我以前的日子,他的缄默,跟讲故事形成反差。也许,他怕我伤心,终归是为我好。后来我知道,他真的一无所有,靠耍嘴皮子换取微薄的收入,也就一瓢红薯面或者几个鸡蛋而已。鸡蛋不舍得吃,煮熟了,揣在怀里,给我送过来。趴在小小的窗子前,看见一个黑点儿变成一个人,我赶紧跑过去迎接,百义一把抱起我,从怀里掏出热乎乎的鸡蛋,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看着我吃完鸡蛋,摸了一下我瘦弱的肩膀,站起身走了。也许,正是他无声的陪伴,使我过早地产生了依赖,那些数不清的夜晚,我完全可以避开黑暗的恐怖,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遨游。百义仿佛一块磁铁,每到傍晚,吸引着我。虽然那些故事经不起推敲,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使我懵懂的是百义何以讲出那些让人兴趣盎然的故事,他心里藏着一个宝葫芦,只要一张嘴,故事仿佛长了翅膀,一下子就飞出来了。他注意到我在看他,表情并没有变化,缓缓叙述着。忽然,扔过来一条破旧的毛毯,我展开,盖在自己和王妮身上。听故事的人都走了,王妮打了个哈欠,百义说:“天不早了。”但是王妮意犹未尽,不想走,百义没揭穿,刚刚她睡着了。看着那束摇曳的灯光,我陷进扑朔迷离的故事里。“那个妖怪是不是被老僧收进了瓶子里?”王妮想找一个结局,难道她睡着了还在听故事?百义匪夷所思,这俩孩子,轻轻摇了摇头。
也许,这是王妮和我形影不离的原因,她同样是一个故事迷。她的父亲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孩子,只要不惹是生非,干什么都行。不过,他并不喜欢我,一双漠然的眼睛充满迷惑,“你说你这个小孩,怎么就长大了。”他倚着门框,因为力量过大,有点儿腐朽的木门发出吱吱的呻吟。“你这孩子。”他继续发泄痛苦和不解,“喝风吃土也能养人?这事怪了,那年,王妮饿得眼睛发绿,我给她吃麸子,她憋得屙不下来,我用手抠,她才脱离危险,那以后,就没让王妮吃过不中用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指着门口,撵我走。厨房热气腾腾,他们要吃中午饭。王妮皱着眉,喊了一声“爹”。我知道她的意思,想留我吃饭,但是,我想保住仅存的自尊,识趣地走出了门。
有一次,何二在豆角地浇水,看见我从土墙那边走过来,喊住了我,他打着赤脚,裤腿挽到膝盖以上,看我走近了,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吗,百义不识字,是个睁眼瞎。”我不信,特别是何二的话。我跳着躲过流过来的水,碰倒了一截篱笆,何二竟然没恼,继续说:“那些故事,都是胡扯,也就你和王妮愿意听。”我打断何二,说:“你不是也听吗?”他凑过来,说:“我有电视,才不稀罕他白话。”我跳开了,他身上有一股怪味。听说,他最近开始收费,每人一角,没钱,给两个鸡蛋也可以。他关上大门,怕有人偷听,电视声音放得很低,门缝也用纸糊住了,不漏一点儿缝隙。有人憋得慌,让他开一扇门,透透气,何二不同意,口气很呛,“不看拉倒。”大伙眼睛睁得卵大,正在看电视,出现了小小的骚动,“别吵吵,行不行?”有人实在憋不住了,“咣当”拉开门,“哗哗哗”把尿撒在咸菜缸里。何二吃出了别的味道,不好对外宣传,只好告诉我百义不识字的事,发泄内心的怨气。“也只有你和王妮听他瞎白话。”何二继续嘲弄。“王妮,咱们走!”我拉着王妮从豆角地中间穿了过去。何二气急败坏地在后面嚷:“我的豆角!”
村里有一个人,年龄很大,是何爹。在我有限的记忆里,何爹死了一回,没有死成。一个没有日头的中午,大伙儿要吃午饭了。何爹看了一阵子书,突然想到太行堤上看一看。好久没出门,他有点憋得慌。何爹没拄拐杖,走得很快。后面像有人推着走。后来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就告诉何二,我想死了。他终于原谅了儿子,柔软的口气让所有人吃惊。何爹出了村,何二刚好也过来给爹送书。书是何爹给何二看的,何二用一年时间把那本书看完,看完之后,好像明白了很多道理,第一时间来还书,还带来了一篮子鸡蛋。何爹上了太行堤,俯瞰着脚下的村庄,发现急匆匆走过来一个人,压根没想过是何二,何二好长时间没喊过爹了。那个人跌跌撞撞,一声接一声喊着爹,终于看清是自己的儿子,老爷子甚为感动,一下子摔在地上,不省人事。
“你说何爹咋想的?不知道,我告诉你,他在赌气呢。何二越盼他死,他越鼓励自己,不死,就是不死。”百义忽然发现何二走了过来,把话收了回来,继续讲鬼故事。“那个人喜欢走夜路,天一黑,就迈开双腿,不停地走。白天,他的背是弯的,夜里,像竹子一样直起来了。头发飘飘,衣袂飘飘,活像个神仙。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路,路明晃晃的,像河水发出哗哗的声音。他与一个婆婆在岔路口相遇,婆婆是一个穷婆婆,也许饿了,坐在岔路口哭,有气无力的。那个人好心,说婆婆你哭啥?婆婆说我想吃东西。那个人说,你跟我走吧,我给你找吃的。两人一前一后往前走。其实,那个人根本不知道哪里有吃的,他也饿,只是出于好心,不忍心婆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婆婆走不动了,说你背我走吧。他犹豫了一下,蹲下来。婆婆说,你走啊,我已经在你身上了。婆婆一点儿重量也没有,像一把灰。天黑黢黢的,越来越黑,不是一般的黑,墨一般。看不见路,也没法辨别。婆婆指挥着他,往这边走,往那边走。他深一脚浅一脚,按照婆婆的指令往前走。婆婆越来越重,像一座山,他再也背不动了。一回头,发现背的是一个口袋。月亮出来了,口袋金黄金黄,是一坨黄金。”
“知道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吗?”
“百义叔呗。”我和王妮异口同声。在我们心里,百义是故事大王,没谁比他更会讲故事。
“不对。”百义手往下一劈,很不满意我们的回答。
“是何爹。”百义像完成一项任务,轻松地吐了口气。
我压根不知道何二他爹叫何秀才,那个披头散发的老头,总是在我绕过豆角地的时候,叽叽咕咕念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捧着一本发黄的书,目光呆滞,空气中有一股沉沉的木头味。我怕他真的喊住我,赶紧溜了。
我还是把何二的话偷偷透露给了百义。百义看着我,王妮不在,我真有点儿担心他去找何二,那样,我不就充当了告密的角色吗?百义替我摘掉头发上一片树叶,看着我说:“我就是不识字啊,何二说得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跟何二可好了,好成了一个人。我家弟兄多,日子过得不好,甚至吃不上饭。何二家家底厚,经常接济我们。他爹识文断字,读过很多书,会讲故事。偏偏何二不听话,偷偷把老爹的书拿出去换零食吃。老爹教他识字,他学会这个,忘了那个,压根不是那块料。我经常到何爹家去,想着法让他高兴,抓泥鳅,逮蛐蛐,学各种各样的鸟叫,逗他开心。夜里,我不回家,守着他,怕他磕着碰着,把尿壶放在床头,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在瓶子里,给他照明。他教我认字,给我讲故事。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善良、真诚、坦荡和向上。”
我看着王妮,王妮看着我,难道,百义叔的故事是何爹讲的?
我们努力了好多次,始终没勇气走进何爹的家。自从知道了故事的原发地,我和王妮亢奋而郁闷。站在篱笆墙边,看着豆角地里虎视眈眈的稻草人,仿佛看见了何二手里的鞭子。他在村里放出狠话,只要我们再踏进豆角地,就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我们想去何爹家,又怕何二知道,撵过来,这个念头一出现,屁股隐隐约约有点儿疼,好像鞭子真抽了过来。百义还透露给我,何爹的那本书何二看了一半,不想看了,越看越头疼。何二担心,看完那本书,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把百义的话说给了王妮,本来想让她跟我一块去何二的豆角地,夏天来了,豆角又粗又长,像魔女的头发,摘一把,可以当鞭子耍。王妮风一般走了,我以为她爹站在门口,抬头看去,只有王妮一个人。
何爹家离何二有一袋烟的距离,平时爷儿俩不往来。我家离何爹家比王妮家近,有时候,出于好奇,我想看看那个古怪的老头。他家的木门很厚,总反锁着,高大的院墙像一座城堡。古老的皂角树矗立在院子当中,树冠像一片云,罩着四四方方的院落。如果刮东风,木头的气息像波浪般涌过来,鼻孔沉沉的。有一天夜里,我被嘈杂的脚步声和哭声惊醒,何爹家灯火通明,皂角树乌黑的叶子簌簌发抖,像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想去喊王妮,没有王妮做伴,我感到害怕。天亮了,嘈杂声和哭声消失了。我像半截木桩站在篱笆墙下。大人们说,何爹死了,又活了。何二经过大喜大悲的情绪转变,整个人要疯了。
何爹的房子是清朝的老建筑,堂屋明三暗五,厢房东西相对,五脊六兽,雕梁画栋,整个建筑没用一颗钉子,全部用的是木楔卯合。建筑保存至今,纯属奇迹。有人出大价钱买这套建筑。何爹不死,何二就卖不了房子。
后来我长了记性,不再走豆角地了。百义告诉我,何二要疯了,看见踩豆角地,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我不怕何二,但听百义的话。这一点令我激动而无奈。王妮看我从太行堤过来,眼睛瞪得溜圆,你可以走南壕啊!我说南壕有鸭屎,弄不巧,踩一脚屎,多埋汰。王妮好像不耐烦,两只脚在地面搓来搓去。我觉得她有点儿小题大做,心想,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走,我就一个人去百义那儿。一、二,我无法消除身上那种亢奋带来的快感,鼻孔哼了一声,快意的感觉令我血脉偾张。王妮感觉出了我的异样,三还没喊出来,她反身关上门,准备跟我走。
出了家门,发现月亮悬在头顶,很大,路面像水一样平静。我能感觉王妮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我甚至不屑一顾地往何二家的豆角地看了一眼,即使让我走,我也不走你那里。不就是一块豆角地吗,百义不识字,不照样能讲故事?
我不想告诉王妮,我是从太行堤过来的。她可能有一种预感,知道我故意走太行堤。我想告诉王妮,为什么舍近求远走太行堤,如果她能理解,不枉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日子。何二总不能连晚饭都不吃,像鬼一样跟着我,我不喜欢看电视,王妮也不喜欢。我们喜欢听故事。
王妮终于发表她的意见,她说:“你这是何苦,你可以走南壕,那条路比太行堤近多了。”接着,王妮又说:“太行堤多危险,不知道有长虫、蚂蟥和野狗啊。”夜幕下,看不清王妮眼里的内容,她渐渐落在后面,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个东西,看不见,但肯定有。那天晚上,百義讲的故事我一点儿都没有印象。
我坐在太行堤上,村庄掩映在蓊郁的树丛里,王妮家的土房子像一个鸟窝,看不到我的房子,只能辨认一个大概位置。何爹家的皂角树像一个擎天柱,傍晚的时候,树冠周围氤氲着团团乳白色的雾岚。很多鸟雀在上面做窝,它们都有自己的领地,互不侵犯,叽叽喳喳唱着歌谣,相安无事。整个白天,村庄像一个窒息的容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也许,声音被那个看不见的容器吸纳,没有了节奏和音律。只有到了傍晚,生命的信息才如此凸显。
村庄是鸟的天堂。
大伙似乎忘记了百义,那些曾经伴随着难眠之夜的故事也同人一样被忘记了。他们忽然觉得,晚上是多么无聊,那些故事,一点儿也不好玩。他们找到了新的乐趣。生活是一个大宝库,曾经忘记了挖掘,原来有那么多可以享受的东西。电视、收录机、游戏机、台球或歌舞,如果有足够的精力,村庄没有睡眠。
百义也来到了太行堤,我本来去他那儿听故事的,他却锁上门,走了出来,我们碰了个对面。前方是砖窑厂,高高的烟囱像一个摩天柱,视角的关系,烟囱向我们这边倾斜。百义竟然有一种伤感。他指着砖窑厂,说:“这里埋着金子。”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默不作声。他说:“听说王妮去上学了。”
王妮有一天没有在我急想见她的时候见到我,在对方眼里,我们像影子一样缥缈。那是从太行堤回来后的第二天。百义的话在我耳边萦绕,如果王妮真的去上学,我怎么不知道。何二说,她有意躲起来了,我不相信。
从太行堤回来的那天晚上,百义有点失落,他一直没有讲出我期待的新故事,也许,真如何二说的那样,他已经黔驴技穷,再也讲不出新的故事了。我不懂黔驴技穷这个成语的意思,一直在焦灼中等着百义的新故事。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急,也许,他同样在等待,等待王妮和村里人。我中午去见了王妮。我鼓足勇气才在白天见王妮,她父亲不喜欢我。她母亲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孩子也没保住。那时候王妮刚学会走路,她跟我一样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她家的门在里面锁着,我知道王妮并不像她父亲说的那样不在家,我绕到后窗,扣了好几下,王妮才打开窗户,她的脸很白,几天不见,就变了样。“我去上学了。”她说。
我去见百义,告诉他王妮这几天没来的原因,其实,不用我说,百义也知道。百义沉吟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元钱,递给我,说:“你也去报名上学吧。你不应该玩了。”他拍了拍我的头顶。
我想去何爹家,百义给我描述过何爹家的景况,没事的时候,我闭着眼睛想象皂角树下的场景,何爹躺在棕床上,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看书。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的味道。几只翠鸟在树枝间打闹,婉转的鸣啼像一首歌谣。很长时间,除了百义,没有第二个人叩响厚重的木门。百义什么时候来,何爹有感觉,像对自己的器官那么敏感。百义每次来,都不空手,不是带着吃的,就是带着酝酿好的故事。没什么好吃的带,无非是熬好的红薯粥,或者两个菜窝窝,每人一半。夜长,两人不着急,细嚼慢咽,吃得很香。何爹发现百义两手空空,知道带了故事来。赶紧沏茶,没有好茶,柳叶也能喝出兴致。有时候,两人为一个细节争来争去,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最后不欢而散,没几日,又聚在了一起。
我想象不出在何爹面前自己该有怎样的想法,也许,更应该表现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当然,百义要站在我后面,有他,我就有了主心骨。他会跟何爹介绍,就是这个孩子啊!多聪明的一个孩子啊!没爹没娘!
何爹一拍脑门,说:“这不是狗叼回来的那个孩子吗,一个血糊糊的肉团,长这么大了。你这孩子,是狗给了你一条命,你不知道那条狗吧,把你叼回来,狗就死了。你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命硬着呢,生生要了一条狗的命。”
我真的应该跟百义去见何爹,他一定知道我的身世,说不定,见了我,会编出一个励志故事。
百义没等我去找他,买了一只新书包送给了我。“何爹让我告诉你,好好识字,以后要学会讲故事。”
百义承包了村里的砖瓦厂,他跟何二两个人竞标,何二头天晚上喝醉了,扬言要把砖窑厂卖掉,第二天,很多人在会场上议论纷纷,说何二是败家子,不能把砖窑厂给他,要是他承包了砖窑厂,我们就会喝西北风。
我想见百义,要到太行堤后滩的砖窑厂。砖窑厂换了几个老板,已经负债累累,百义临危受命,责任重大,每天吃住都在厂子里。整整一个学期,我都没有见到他。
我和王妮在一个学校读书,她在一班,我在二班。我们经常见面。我们是贫困生,学杂费、住宿费全免,靠勤工俭学交给学校一点儿伙食费。
有一天放学,我走了另一条路,我想看看何爹。趴着门缝,我看见何二给何爹整理头发。何爹脸色红润,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百岁老人。长长的头发白得像雪,披在肩頭,因为刚洗过,散发着潮湿的水汽。何二脸上有一种祥和的表情,简直与平时判若两人。时间能改变一个人。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百义,他忙着找人卸煤,丢下一句话,就走了。何二惦记老房子。我琢磨着百义这句话,觉得何二是有目的的,如果真如百义说的那样,他可真可恶。
何爹死了,就在何二离开的那天晚上。何二拿出何爹的遗嘱让大家看,老房子的产权归何二。我喜欢给生活找一个注脚,也许,这些年,我真的变了。不管发生怎样的离奇故事,冥冥中,好像有一个幕后推手左右着我们。比如,我和我的老婆王妮,尽管我们走过了很多曲折离奇的路程,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都留下了彷徨孤独的身影。王妮的父亲始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一直不看好我们。那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提起我,他就嘴角上扬,鼻孔朝天。有时候,我在梦里,时常被惊醒,看见王妮还睡着身边,突然泪流满面。
何二拿到卖房子的钱,在县城胡混了一阵子,举报了百义。砖窑厂被封了。百义欠了很多债,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欠着工人的一部分工资。年三十,一帮人把百义堵在家里,砌了锅灶,不给工资,他们吃住在这里,不走了。
王妮赶集回来,把听到的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她眼角爬满了皱纹,看着她,我有些心疼。她脸上的表情分明在问我:咱能不能帮他一下?我们的积蓄虽然不多,但起码能帮助百义渡过这个难关。我觉得王妮一直希望我有所作为。我说:“你去做饭吧,让百义叔过来吃。”我走出了门,王妮撵出来,说:“你跟百义叔说,他还欠我们一个故事呢。”我回头看看王妮,说:“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