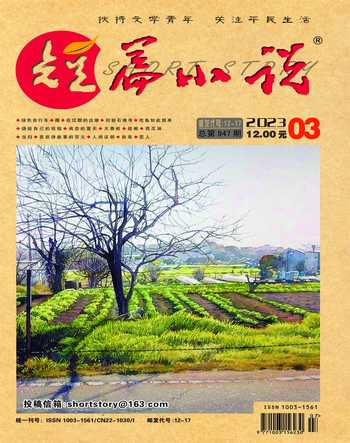西瓜妹
徐玉向
32年前的夏天,一个连知了都懒得叫唤的闷热傍晚,在一大片碧绿的西瓜地中,西瓜妹抽出一根光溜溜的荆条向我们冲来。
金牙扭身沿着西瓜地间的界沟,似只被吓惊的野兔一跳一跃向南跑。钢头个子不高,身段极其溜滑,怪叫一声,纵身跃过几步宽的水渠,转身向西瓜妹来的方向窜去。西瓜妹见有人往这边跑,愣了一下,可是水渠太宽,跳不过去,任由那个家伙扬长而去。我只好向后跑。转身跨过桥,沿着马路往碾盘桥方向跑去。跑了几步,见她果然只朝我这边追来。我边跑边扭头观察追兵。无奈平日里看似温顺的乡下丫头,一旦发起火来,气势绝对不输任何一个小子。我边跑边回头瞅。临近碾盘桥时,冷不防脚下一滑,跐溜跌到鲍家沟里了。
八月的乡下,正是雨水丰沛的季节,鲍家沟的水齐着碾盘桥面呼呼往前涌。刚浮出水面的我,只觉得又有一股漩涡不住地把我往水下扯。纵然双臂不停地拍打着水面,湍急的水流义无反顾地拥着我直往桥下钻。
耳边仿佛听到西瓜妹在死命地叫唤:“救人啊!快来人啊!”呛了两口水,我几乎连咳的机会都没有,水开始猛往嘴里灌。河水漫过鼻子,额头仿佛撞到了什么东西,接着眼前一片昏暗,我渐渐没了意识。
待我醒来,耳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悲伤地号哭,夹杂着“不是有意的”。另一个声音连说:“好了,好了,顺过来了。”
尽管眼皮似有斤重,我仍挣扎着睁开了。钢头硕大的脑壳、金牙尖尖的耳朵以及无数个人影一下冒了出来。那隐隐的哭声,也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西瓜妹,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姑娘,被她妈硬薅着辫子,似牵着一条小狗一般,扯到病床前。
刚才的一觉,我不知睡了多久,浑身比跟着家人浇两天地还累。当我真的睁开眼时,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小命没有被无情的河神收走,而是躺在村卫生所里。西瓜地、碾盘桥、汹涌的河水及西瓜妹的含恨追逐,皆成了过去。
感觉头仍有些晕,来不及说上半句话,连额头的疼痛似乎也没心情搭理,又沉沉睡去。
再度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村子里的大公鸡连叫了几阵才把我唤醒。我的床头堆满了营养品,家里人说大部分是西瓜妹家人送来的。村里的规矩,就是人家道了歉,再大的事都算过去了。
躺在床上的我,只好睁着眼,盯着悬在房梁上的盐水瓶不紧不慢地往下滴着液,一边努力回想着昨天傍晚发生的事。
其实,昨天真的没啥大不了的事,也不能全怪西瓜妹。我在瓜庵赶暑假作业,金牙和钢头舍了自家瓜庵来找我下六周棋。下棋要有彩头,输了的人就要表演一个搞笑的节目。混战结束后,各输一局。
轮到我表演,猛然瞅了相隔几块地的西瓜妹正在臭美。她在瓜庵前揪了几朵凤阳花,用力捏出汁正往指甲上涂。指甲立刻变得似天上的火烧云一般艳丽。
于是,我站在瓜庵前,号起了一首幼儿园时代学过的儿歌:“小丫头,背巴斗,背到河沿拾豌豆。豌豆开花,丫头来家,家里放炮,丫头上吊。”
西瓜妹停了手,朝这边瞅了两眼,扭过脸再继续涂,没吱一声。
钢头接着瓮声瓮气地又来了一首:“小花鸡,上磨盘,一挠挠个大皮钱。先买酒,后买烟,娶个西瓜妹子好过年。”
西瓜妹这下有点儿毛了,竖起刚涂好的指甲点着钢头说:“你个小死孩,再瞎扯,看我不告诉你妈。”
轮到金牙,他边跳着边对着西瓜妹比画地号道:“张大料,李大刀,我的白马随你挑。挑大的,有大的,挑小的,有小的,单挑二愣子会跑的。”
这下西瓜妹彻底火了,气哼哼地用力一扔被捏成一团的凤阳花,从瓜庵上抽出一根荆条就冲了过来。唉,平时看起来好端端的一个丫头,又是同班同学,说两句笑话,真成了会跑的二愣子了。
说起这西瓜妹,原是同村异姓的邻居,比我们大三岁。若攀了亲戚,她还是八竿子打不到的表姐。在我们村,丫头上学都迟,再加上她二年级时生病休学,我上三年级时她才来插班。也不知道她二年级时得了什么病,盡管个头挺高,脑袋有时不是很灵光,脸盘倒是极出彩。按村里老人的话来说,四方大脸不为俊,腰子长脸爱坏人。她不仅长着一个腰子脸,两腮还种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去年过年,村里二流子大强拿了瓶酒和一串鞭炮,在西瓜妹家院子门口,先放了炮,吸引一大群人,再灌了半瓶酒,把她爸拉出来,说,这是他的老丈人,西瓜妹是他家里的。众人大笑,西瓜妹掂着一柄切菜的石刀冲了出来。大强只好丢下“老丈人”,落荒而逃。从那以后,谁要在她面前说嫁人的事情,必定讨不到好脸色。大强没有放弃对她的追求,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她家门口,还有一次跟到了学校。
大强每出现一次,西瓜妹家院子里就鸡飞狗跳一次。她妈拿着鞋底,一边追着打她,一边吼,说,这么大的丫头怎么一点儿不知道丑,尽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扯在一处。在乡下,丫头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观念自从娘胎一落地就开始培养起来了。她当然极力为自己辩解,边躲边叫唤。
村里每年都种西瓜,西瓜妹家的地又离我们生产队的责任田不远。有好几次,我看到几个过路的叫花子在路边的树下靠了靠,她就捧着小半个西瓜过去。有放牛的老汉路过地头,她也会捡个小香瓜递过去。更不要说过路的熟人,隔着水沟脚踏车一闸,都不用招手,半个红瓤子大西瓜就来了。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请你吃西瓜吧。时间长了,村里人去她家串门都夸她懂事,她妈嘎嘎地笑一阵,说,我家丫头确实有点儿缺心眼。村里人连她小名都不叫了,直接喊她西瓜妹。
离开卫生所后,我仍回瓜地打发时间。一天中午,瓜庵前摆着一地新鲜的西瓜皮。早已失去午睡和吹牛的兴趣,又无他事可供消遣,我和两位发小瞪眼瞄向几米外的土路。
“狗!”一条草狗伸着舌头转过碾盘桥,一颠一颠快速向我们移动。当它毫无防备地踏入与我们仅一沟之隔的路时,不知是谁抛出了一片西瓜皮。尽管没有砸中,狗的叫声却似给我们打了一针兴奋剂,三个浑小子,六七片西瓜皮,照着脑门飞了过去。可怜的家伙,号叫着窜向远处。
村子方向响起一阵清脆的声音,那是脚踏车的铃铛向土路中的大坑发出的抗议。为了争取第一个抛瓜皮,我们猜石头剪刀布定顺序。好不容易议定,路上早不见了人影。
就在我们相互责备时,西面又传来一阵脚踏车的声音。一袭白色连衣裙徐徐靠近。一顶米黄遮阳帽,齐肩长发收拾得十分顺溜,鸭蛋脸白白净净。或许是赶了不近的路程,细密的汗珠从她的额头延到红彤彤的脸庞。她的车子有些奇怪,前面没有大梁,车身也较二八式娇小许多。一只小包乖巧地躺在车篮里。
“一看就是市里的。”金牙嘀咕了一句。本在犹豫的我们,立刻像吃了枪药,专去捡个头大的瓜皮。常听大人们说市里吃公粮的人如何如何不待见乡下人,这次终于有机会让市里人长长记性。一块砸准前轮,一块落在右脚踝,其余瓜皮全部跌在路中心,溅起一阵灰。
那姑娘车头一歪,被惊得险些摔倒。她气冲冲地刹住车,丝袜和裙子下摆上尽是斑斑点点的红色汁液。面对她屈辱中杂着愤怒的眼神和大声质问,我们觉得十分有趣,手里的瓜皮举在空中,不知是扔还是不扔。忽然,我们头顶的瓜庵上传来噼噼的响声。伸头一看,原来又是多事的西瓜妹。她一边用力拍着瓜庵,一边朝我们大声吼,说,你们又在作死了,信不信开学时我告诉乔老师。
其实,我们每次做了坏事,西瓜妹真会告诉我们的家长,换来无非打骂一顿。可是,她要是告诉我们的班主任的话,那就会被当着所有人的面罚站,这个脸可丢不起。我们扔了西瓜皮,把草帘子一拉,挤在床上装作睡觉。
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刚走远,西瓜妹的声音又传来了。我们把帘子掀开一个角,发现她正在跟那个骑车的市里姑娘说话。时常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西瓜妹,没想到站在市里人面前竟然一点儿也不掉价。尽管没有那位姑娘个子高,西瓜妹更显身材,尤其是翘翘的屁股。脸盘更不用说了,直接把那个鸭蛋脸比下去了。一根盘得密实的又黑又亮麻花辫子,比那个松松垮垮的披肩發强上太多。唉,就是天天看瓜,她的皮肤黑了些。乡下人,风里来雨里去,又有哪个皮肤是白的呢。
两人在一棵大树的阴凉下,一边说,一边还朝着我们这边瞅。唉,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话。见她们不断地往这边瞅,我们赶紧把帘子放下来,支起耳朵听。又过了能啃完半个西瓜的工夫,才听到脚踏车离开的声音。
秋天开学,我们没有被乔老师罚站,心里仍觉得不痛快。为什么西瓜妹要帮市里人,平白无故地还讲我们坏话。一直盘算着要让她长个教训才解气。
下午的预备铃似催命一般。“当当当”急迫的声响回旋在房梁上,最终钻入那些昏沉的脑壳中。很多同学半闭着眼睛把手伸进抽屉掏书本,第二遍铃再响,老师就要进教室了。一声刺耳的尖叫,直接盖住了第二遍铃声。西瓜妹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边跳边叫,边叫边号。边上的同学也吓得纷纷起身,不明所以地看着她。就连最前排的同学也扭着脖子往后望。大概,全班只有我们三个最淡定了吧,个个装成无事人一般,假装打着哈欠,慢腾腾往外掏课本和文具。
“抽屉里有个东西。摸着凉飕飕的,肉乎乎的,不知是什么。”
“那会是什么,有没有毛?”
“没有!”
“有没有爪子?”
“好像,没有。我就摸了一下,现在头皮还发麻。”
“是不是蝙蝠?那东西很恶心的。”
“有没有小疙瘩?”
“起立!”还没等西瓜妹回答,随着值日生的大喊,班主任乔老师站在讲台前,正朝着教室后面挤在一处的学生瞅。
“是不是都还没睡醒,要不要到太阳底下凉快凉快。”乔老师掂着小棍子往这边走来,严厉的目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沿着教室的第一排一直到最后一排。当她的目光扫过我时,我心虚地往桌子上一趴,把铅笔盒也顶到桌子下面去了。我急忙弯腰去捡,头又被桌子下沿碰了一下。
再起身时,猛然发现乔老师正站在我的面前,有意无意地瞅着。我感觉自己的头发都快立起来了。努力地挺着腰板,规规矩矩地坐着。“乔老师,你不要过去,我抽屉里有东西。”看见乔老师上前,西瓜妹赶紧挡在她前面。
乔老师两步跨到她课桌前,小棍子穿过书包带,往外一挑。书包跟着小棍子跳出了抽屉。她一手攥着书包,侧着身子朝抽屉里看了一眼,接着棍头噼里啪啦在桌沿一顿猛敲,倒竖起柳叶眉,原本白净的脸上竟然罩着一层寒霜,一个声音似从牙缝里挤出来,“说,谁干的!自己站出来。”
乔老师的声音不大,却似一个霹雳在教室炸开了。她刚才用棍头扒拉出一个物件,掉在了地上。围观的同学中,就连平时号称胆子最肥的家伙也轻轻抖擞了一下。
一截被剁了头的水蛇,剥了皮,蛇皮里注了水,再把前端扎紧,周身仍圆挺挺的,猛地一看,似一条活的水蛇。青褐色的尾巴,一翘一翘地颤动着,让这半截注了水的蛇皮,就像活着的一般。
本来,我打算趁西瓜妹睡熟时放在她脖子上的。当你睡得迷迷糊糊时,忽然一个凉飕飕肉乎乎的东西掉在你的脖子后面,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至少会吓出尿来吧。
金牙听了只顾搓着手,嘿嘿地笑。这截蛇还是他的杰作,我们可没有这般手段。其实我也是怕蛇的,尽管水蛇没有毒牙。当他把这截蛇皮搁到我掌心时,我的头皮也是一阵麻酥酥的。
钢头不同意,说,要是吓出个毛病来,我们几个怕是连学也没得上了,何况她本来脑子就不好。我只好改变主意,从饭后就睁着眼睛,挨到快打铃时,悄悄把蛇皮塞进了西瓜妹的抽屉里。
“说,谁干的。有知道的告诉我,奖励两个练习本。”乔老师提高了嗓音。她的话刚说完,马上有个女生跑到我座位前,用力指了指装作一脸茫然的我。本以为做得很隐秘,不想还是被上完厕所的一个女生看到了。这个女生住在西瓜妹家后面。不过,她只看到我猫着腰从西瓜妹的座位边回来,没看到我塞东西,当时也没在意。
在乔老师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她从三年级就带我们,班里每个人的德性早摸透了。小棍头朝我脑壳上一点,说,同伙呢。我只好左右各瞅一眼,金牙和钢头极不情愿地站了出来。三个人,像三根杵在黑板前的木桩,一直站到放学铃响起。就连下课也不让走,差点把尿憋到裤裆里。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被叫到办公室,没有聆听教导主任和校长更深切的轮番教育。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大人竟然不知道下午发生的事。
回家舒坦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学校。刚放下书包,屁股还没坐稳,教室里忽然闪进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直奔我的座位。我抬头一看,竟然是村里那个二流子大强,一个自称西瓜妹是他家里的家伙。不知何时,他竟剃光了头发,光秃秃的脑袋像颗骆驼蛋。瘦巴巴的脸上卡了副蛤蟆镜,花背心掩不住胳膊上的文身。脚上拖着双二夹子,在长过膝盖的绿色大裤衩下,踢踏踢踏地晃过来。
大强一把薅着我的衬衫领子,把我从座位上揪了起来。周围同学纷纷起身,值日生赶紧往教室外面跑。
大强另一只手攥着拳头,高高举着,作势要砸下来。见到金牙钢头一人摸了一个板凳腿掩在背后慢慢靠近,我放下刚开始的慌乱,抬头默默地与他对视起来。
大强一米七的个子,也仅仅比我高出一个头,只是身子骨比较单薄,在我们这一带的小混混中算是比较差劲的。打也不能打,沾酒就醉,只会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几乎每年都进去喝几天稀饭。
我顺势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只手搭在大强攥在我领口的手腕上,另一只手掂著铁皮文具盒。没有出现大强预想中的求饶场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连窗户口都挤满了脑袋。大强脸上有点儿挂不住,又有些后悔没有带同伴来,只好强势着场面。他扬了扬拳头,大声喝道:“你个小瘪三,怎么敢惹老子的女人。今天不给你厉害尝尝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大强说这话的时候,西瓜妹正抱着一个小西瓜迈着轻盈的步子进了教室。可惜,他的背后没有再多长一双眼睛,大强仍在喝问我。西瓜妹听到这话时,立刻停下了脚步,表情有些复杂地望了过来。
“谁是你的女人?有种再说一遍。你要不敢说就是孙子。”我故意激了大强一下。
“连西瓜妹是老子家里的都不知道,你还混个啥。”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货。一副狗腰,哪个大女孩能看上你。”面对我的回应,大强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看了很解气,又为西瓜妹被这种无赖沾上感到可惜。好端端的一个大丫头,天天被这种人纠缠,将来怎么说婆家。更何况昨天的事,她也没和我家大人讲。今天索性豁出去,我也替她讨个公道吧。
“你说是你家里的,她爸同意了吗?她同意了吗?你们摆了酒吗?”围观的同学也注意到停在门口的西瓜妹,都幸灾乐祸地往前靠了靠,在一片哄笑声中把我们牢牢围在中间,关系好的男生开始往前凑。
“老子把她都睡了,你说她是不是老子家里的。”大强连脖子一下子变得又粗又红,青筋突然冒了出来,一只拳头眼看就要落在我的脸上。还没轮到金牙钢头动手,他的脑袋上就被飞来的西瓜砸得狠狠一歪,蛤蟆镜也跌在地上。
西瓜如一枚炸弹,啪的一声掉在地上,鲜红的瓜汁喷得一地都是。外围的人下意识地往外挪动脚步,内圈的几个人,已准备动手。趁大强分神,我手往下一压,打开了他攥着我衣领的手,顺势朝他胸口踹了一脚。他往后一退,踩到了西瓜皮上,一屁股跌在西瓜瓤上。“谁是你家里的!你再胡说试试!”西瓜妹已蹿到大强身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扬着刚从金牙手里夺过的板凳腿。
“你是不是想再进去喝两天稀饭。”人群中,一位高大的身影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大强听了立马停止叫骂,摸起蛤蟆镜,一骨碌爬起来就往门外跑。他单薄的身子,裹着沾满鲜红西瓜汁的绿色大裤衩,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校长紧跟在大强后面也走出教室。西瓜妹将板凳腿丢到我桌上,说,我请你吃西瓜吧。
责任编辑/文媛